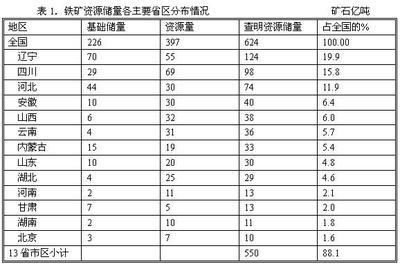内容提要伍国栋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接受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有深厚的传统音乐研究功底,在引入外来学术理念的同时将其消化吸收的同时用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探索的实践之中。经过多年对民族音乐学学术理念系统梳理并加以夯实,然后将既有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与民族音乐学两种学术理念整合,从而形成“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念,从初版《民族音乐学概论》到增订版凸显这种崭新的面貌。他的探索具有开拓与践行意义,引领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研究走向深入。
关 键 词 伍国栋中国民族音乐学 开拓 践行学术榜样
一个人既然选择了学术的道路,就要在不断求索的同时常回头看,进行阶段性总结。个人、同道、晚辈的学术评价都有“意义”。但凡做出成绩者,无不默默耕耘、长时间积累,如此方能够得到幸运之神垂青,成为学术界的榜样,伍国栋先生就是这一代学者中的佼佼者。
在传统音乐文化研究领域,当下主要有两种学科理念,一是以传统音乐理论命名,一是以民族音乐学命名,从各自视角来看,两者之间在研究论域和思路上存在相当差异,学界以为时下这两种学科理念还是有各自独立存在的空间[1]。
建立一个学科、或称形成一种有着相对广泛认同的学术理念非一朝一夕。传统音乐研究主要侧重于存活于当下传统音乐本体中心特征(律调谱器曲)多层面把握,强调音乐的艺术性存在,重技术性分析。上世纪下半叶由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著的《民族音乐概论》(北京音乐出版社1964),将中国传统音乐分为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五大类,这种分类虽有不足,却有着较强的实用意义。正是这本书让我们把握了中国传统音乐各类型的基本结构以及分布。这种撰写方式重在音乐本体,其音乐形态要么是学者异地采风所获,要么由当地学者挖掘,然后对音乐本体基本形态进行深入分析,使学界认知中国音乐传统当下存在的样态。我们的前辈学者不断探索研究思路,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就。
这种学术研究理念当然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仅在分类意义上就有多种探索[2],否则学界也不会认为有延续之必要。但我们也应看到,仅以这种学术理念进行研究存有一定局限,诸如更多针对一时一地一种类型,对整体意义有所忽略;侧重音乐形态而淡化文化整体存在;只以当下认知传统音乐样态,难以把握其与历史大传统的关联。正是基于以上的多种考量,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音乐学界开始了学术研究方法论的探求,学术刊物纷纷推出介绍新学科的栏目,许多新理念逐渐涌入,令人目不暇接的同时学界也开始反思既有研究理念和方法之不足,这是当时学术界的整体样态。
在这个学术潮流中,以文化人类学为本、或称将文化人类学的学术理念用于各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方法,“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的学术理念进入中土。一时间诸如局内、局外;主位、客位;几个W;注重实地考察等理念和范畴进入,这在既有方法论基础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的同时,也使得学界既感兴奋又有失落,毕竟这是与既往不同的学术理念。文化人类学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必定有其合理性,那就是将包括音乐在内社会上存在的多种现象都视为文化的整体构成。既为有机组成,则需在深入研究音乐形态本体的同时把握文化的整体意义。强调活态与既有的传统音乐研究理念相通,把握文化的整体意义则是对既有研究理念的扩展。学者们在解读这种理念之时有不同的切入点,即从音乐本体切入看文化整体;从文化整体把握并辨析音乐本体在其中的意义等等。无论从哪一种视角切入,两者都要考量,这与仅将音乐作为艺术、仅从本体形态进行辨析有着相当的不同。虽然这种学术理念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某些偏差,诸如学界所诟病的强调“文化”而没了“音乐”,机械地运用所谓方法论而更多模仿,以至于在某一时段相当数量的文章似曾相识,在把握这种学术理念之时有机械唯物论或称“跑偏”现象。不管怎么讲,这种学术理念的确带来了学术进步。
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理念的开拓践行
人们常常以学术史的理念追根寻源,本人在此无意探求引入这种学术理念孰为先后,更想把握群体意义。民族音乐学理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引入中土,南京艺术学院的确成为以这种理念命题展开研讨的先驱,接下来则是福建师范大学的王耀华先生于1987年运用这种理念在日本出版的《琉球、中国音乐比较论》[3],如此应为民族音乐学理念在中国的早期实践。我们还应看到有这样一片学术阵地。1978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批音乐研究生。这批研究生年龄相对偏大,在其时已经有相当学术造诣,他们熟谙既有研究方法,入学之后积极探索、引入、吸收,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民族音乐学理念最早实践群体。记得在八十年代中期,山东省举办传统音乐学术会议,吴犇、薛艺兵发表对河北固安屈家营音乐会调查研究的论文,他们宣称文章的前半部分是用传统研究方法,后半部分则是运用了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理念,笔者作为在场者的确感到耳目一新。吴、薛二位是艺研院的首批研究生毕业后所招的“黄埔二期”生,作为“黄埔一期”一员的伍国栋先生1981年毕业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服务20余载。《中国音乐学》创刊不久即刊载了伍国栋先生《田野作业的方法论思考》(1986年第3期)一文,接下来又有《民族音乐现象系统化结构的综合研究》(《音乐研究》1989年第1期)、《<白族音乐志>体例》等多篇运用民族音乐学理念的学术文章,可见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理念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已经进入到实际运用的状态。笔者多次听“黄埔一、二期学员”谈起他们带着这种学术理念走向全国各地,“黄埔三期学员”在主持研究生部工作的伍国栋先生带领下深入云南、四川做实地考察的状况。伍国栋将这种研究理念不断被应用于教学以及考察实践,不断思考,并反映在多篇学术文章之中。他运用民族志的理念对白族音乐文化整体考察与探讨,这在中国显然走在了前列。
1992年春天,我曾有机会与伍国栋先生等几位学者一道在云南的昆明、楚雄、大理、德宏等地进行了接近20天的考察[4],在昆明见到了与伍先生合作《白族音乐志》(1998出版)的李汉杰先生。白族相对集中地分布在大理的苍山洱海周边区域,作为学术实践考察层面会相对好把握,但这绝不等于难度小。两位先生走的是专家路线,在不断的实地考察以及学术实践的过程中,他们依照文化人类学的学术理念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单一民族的“音乐志”,这种研究在中国有第一个吃螃蟹的意义,为学界提供了学术榜样,毕竟这在中国是为首例,其学术意义自不待言。
笔者与伍先生一道相对长时间参加实地考察的机会是在1995年,台湾群视公司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合作考察纳西族音乐文化,在38天的时间里我们走进纳西族祖源地迪庆州中甸县(现称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的白水台,大东、塔城,来到丽江古城、玉龙雪山、哈巴雪山,进入摩梭人聚居的泸沽湖区域,近距离考察祭祀歌舞、葬礼仪式,伴着月色爬山,踩着篝火打跳,我看到了伍先生如何与民族群众交流,如何采集整理音乐形态,把握民族文化中的音乐现象,先生既尊重采访对象又不时闪现出学术火花的学者风范为后学提供了学术榜样,所以我们说,伍国栋先生是民族音乐学学术理念在中国的开拓与践行者。
我所见伍先生田野工作只不过是管中窥豹,但却深切体味到民族音乐学学术理念践行的意义。伍先生一有机会便不断深入乡间社会实地考察,并将这些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心得与他主持下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的学子们分享,也就是在这种不断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伍先生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民族音乐学概论》(1997),全面而系统地将这种不同于既往的学术理念、学界实践与其自身践行加以总结惠及学子,显示出很强的学术意义。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他们是这个群体中专事音乐理论的佼佼者。他们熟悉传统音乐,懂得从传统音乐理论视角做学术的基本方法,如此在汲取新学术理念之时便如虎添翼。2011年夏天,清华大学的一位学术朋友根据“中国知网”提供的数据对音乐学术界做了一点辨析,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H指数”(学术因子、征引率)达到20,为学界征引的相关学术成果多集中在改革开放后这一段时间,如此显现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群体在中国音乐学界相当时段内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这是群体的力量。伍国栋先生就是这个学术团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在下以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音乐学研究之所以能够为学界瞩目,在于早期集聚了一大批著名学者,诸如杨荫浏、李纯一、郭乃安、吉联抗、李元庆、黄翔鹏、李佺民、吴毓清、何芸、苗晶、吴钊、刘东升等等等等,依照当下话语,这些学者哪一个都是那个时代的学术精英,如此形成了音乐研究所的“学统”。本来就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重镇,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生教育当然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研究生们在这个学术环境中首先受到的是系统的既有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良好教育,借开放之东风,这个音乐学界最早的研究生群体接受来自西学的民族音乐学理念用于传统音乐文化研究,采两种研究理念之长,面对同一研究对象,这是非常重要的样态,当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生院之音乐学系的教学都承继了这种学术理念。作为“黄埔一期”的伍国栋先生应该是这种学术理念的引领者和践行者,他以此理念所进行的学术研究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无论是他所做的大课题,诸如《白族音乐志》和《江南丝竹——乐种文化与乐种形态的综合研究》[5]以及多种实地考察个案和学术方法论的相关思考,都显现出两种学术理念的有机结合,为学界树立了学术榜样。伍国栋先生的学术著作均为一篇篇非常严谨的学术论文或称学术个案基础上的累积,如此彰显学术著作的价值。我们在“中国知网”上键入伍国栋三字,截止2011年12月7日,被收录的论文有65篇,下载13982次,引用303次,这是传统音乐文化研究领域相当高的数据,加之数本沉甸甸的著作,显现伍先生在学界的学术分量和学术威望。
虽然学界有观点认为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与民族音乐学研究代表了不同的研究方向,时下有各自独立存在的空间,但不能不看到两相结合可能更具学术优势。虽然研究有侧重,但整合起来会取长补短,毕竟面对的是同一学术对象;以民族音乐学为学术理念进行研究,更是要倚重传统音乐理论所积淀的诸种学术成果,绝非另起炉灶、对既有研究成果视而不见,那种不尊重前辈学术积淀的研究难以修成正果。在以民族音乐学为方法论的学术实践中,把握学界既有研究成果,以乐为主线拓展学术领域,可以真正彰显学术优势。如有偏离则会落入空谈的陷阱,这显然不是以此理念为学术的初衷。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音乐学界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更多关注形态本体特征方面,更多将其作为艺术而对乐在文化整体中的作用和意义有所忽略,在研究陷入瓶颈之时寻求新的路径以开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文化人类学而来的民族音乐学学术理念引入恰逢其时。
伍国栋先生在“中国音乐学网”上更新博客,谈起增订《民族音乐学概论》的初衷,那就是听取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吸收了学界践行这一学术理念的新成果,使得该书在夯实既有基本学术理念的同时注重学理,更具实用性,这是作者不断总结归纳以期日臻完善并惠及学界和众多学子之新举。如果说1997年版的《民族音乐学概论》更多为消化吸收,那么,十数载之后的增订从内容和结构上则以崭新面貌示众,这种新就在于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具体实践的把握。
伍先生将《民族音乐学概论》定位于“一部基础性学科理论教程”,在原著基础上“有选择地充实学科学理当代信息”,增加“学科学理综合性特征构成的重要历时依据和现当代学科发展势态的实证材料”,“继续揭示学科基本理念及方法的实践性内涵,充实具体研究实践得失材料的经验总结,将此作为学科理念、理论实践性本质认知的进一步彰显”,“增强本土音乐文化研究及其个案研究实例举证,为读者和学习者提供更为切合现实音乐生活实际、更能为他们认知和理解的研究范例和成功经验”,并增写“若干操作性和应用性内容”[6]。
教科书的意义在于实用、系统、完整,学子们依此能相对容易地进入状态。伍先生增订本书,其内容充分显现了作为学者的严谨、开拓和持续探索,最令人感佩的是他的践行性以及将传统音乐研究与民族音乐学理论相通性把握。这与那些只是热衷于引进学术理念、停留在介绍层面、不关注中国传统音乐本体、却声称代表了学术前沿者不可同日而语;伍先生注重用这种学科理念的实用性意义,用以解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现象,从音乐本体到文化整体,既有个案又有宏观更有实证,这与那些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缺乏深层认知,将传统视为残存、残留,遗存的认知显然不在一个层面。我们说,学子们全面系统地把握了本书内容,应该会对学界当下名目繁多声称用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展示作出自己理性辨析与判断,找到可以依循的学术路径,在入行之时不至走偏。理论用于指导实践,但如果仅仅将理论停留在理论层面,特别是对于引进的理论,如果不是努力把握深层内涵消化吸收以为用,也就失去了理论的意义。既有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需要开拓视野,学术需要进步与发展,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引入正逢其时。应该明确:把握既有探寻前行与抛开既有另起炉灶,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差异。从前者前行则如同施足肥水的禾苗;不关注前者则如同一只没有笔芯的笔。理论用于实践,在实践过程中对理论不断检验、修正以致发展,对于外来理论更是需要这样的过程。伍国栋先生从理论汲取到实践,在践行过程中不断思考修正,在“化之”的基础上形成系统性认知后回馈学界,用于解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深层内涵,这样的理论有用、实用,真正体现学术意义。
我注意到鲍元恺先生在伍先生博客评论中的话语:“我很奇怪某些自称‘掌握了西方的最新方法与理论’,却对研究对象——丰富多彩音乐现象毫无兴趣的人,他们自命‘先进’,鄙视从事中国传统音乐(过去称‘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的老一辈学者。”鲍先生引用伍先生的一段话与此相对应:“事实上这种方法论经验,早在20世纪80年代‘民族音乐学’学科还未在中国兴起之前,就已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实践中有了突出表现。……甚至可以说在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阅读这些当时称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相关调查研究成果,其所含‘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学术份量,并不逊于当代某些由空泛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拼凑起来的所谓‘成果’。这也是笔者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纳入‘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一部分无可辩驳的实证材料依据。”[7]
作为作曲家的鲍元恺先生在理论上也很有建树,他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伍国栋先生恰恰是将传统音乐研究(或称“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纳入到民族音乐学的理论视野之中,具有接通的意义,而非将两种研究人为区隔、形如泾渭,这才是最为要者。也许一些专事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的学者尚不能完全认同此说,但我们看到,民族音乐学之于传统音乐理论研究提供新视角、新认知所具有的时效性毋庸置疑。
回到学科原点的思考
诚如大家所知,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原点应该是文化人类学与音乐学的结合,即将文化人类学的诸种理念和研究方法用于侧重各地传统音乐的研究实践之中,这里强调的是针对音乐文化现象的学术意义。20世纪60年代梅里亚姆经典的学术著作即是以《音乐人类学》命名,可见这是以文化人类学理念用于音乐学研究。文化人类学学科自身具有开放的传统,广泛吸收诸如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针对研究对象的不同在核心理念的基础上不断引入新视角,以利更好地辨析与解读。正是这种学科方法论的包容性和有效性,成为多学科借鉴和使用的对象。我们看到,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是大的学科概念,既然文化人类学能够成功汲取,音乐学当然要借鉴,在某种意义上借鉴文化人类学的同时也部分汲取了上述学科研究方法。需要辨析的一点在于,舞蹈、美术、戏曲、曲艺均有与之对应的所谓××人类学的学术理念,与之相比较,音乐学是否应与这些学科称谓相一致呢?其实音乐学界也明白这就是文化人类学的理念与本学科的结合,但既然国际音乐学界已经形成这样的认知,将这种学术理念引入中土之时也有对“Ethnomusicology”称谓的讨论,但已然约定俗成只要明白事理但叫无妨,我们在这里提此话题不过是以为学界应该有相对统一的认知和称谓,不然这里开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研讨会,那里又以音乐人类学名义进行学术研讨,明明就是一个东西,却让初入道者摸不着头脑。
回到原点、回到大学科理念,我们的研究者关注自身学科发展的同时还应该关注“原点”学科的发展,毕竟这是我们的学科与文化人类学结合的产物。因此,我们既应关注音乐学界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亦应关注文化人类学自身的发展趋势,从原点把握可能会更有助于适时调整理念跟上学术发展的步伐。近期笔者有幸在几次学术研讨会上与国际、国内多位引领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潮流的学者交流,如此感知和感受到当下同为大学科的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有怎样的交集,所谓“历史人类学”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以及两种学科结合的学术方法论究竟有怎样的意义,这些我已经在《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8]一文中有所阐述。我们也回溯了音乐学界借鉴文化人类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理念,如此说来,无论是大学术界还是音乐学界都认同这种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所谓“学术方法论”意义,这值得我们音乐学界深思。在下以为,这种学术趋势并非在既有学科理念上仅仅又添一种视角,而是深化既有学科理念的认知。
说起来笔者对于文化人类学也算是音乐学界较早接触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厦门大学读研期间到人类学系选修了多门相关课程,这为我以后田野实地考察奠定了基础。我与人类学系的研究生住在同一层楼上,因此也就有了时常向诸位学友请教的便利。有一点困惑搅扰我多年,那就是当时所研读的人类学学科理论著述更多注重当下、活态,对历史存在的意义有所忽略,一些相关音乐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诸如西格的《苏雅人因为什么歌唱:对一个亚马逊族群的音乐人类学研究》等,感觉学者们更愿意选择那些文字记述不多的部落区域来实施异文化的田野作业。我所困惑的就是这种方法似乎对于那些尚未形成本民族文字、缺少文献记录的区域更为可行有效,而对于那些有着深厚传统底蕴的文化存在能否深层把握就有疑问。对于音乐这种具有时空特性的文化形态,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如何对待传统与当下结合不得要领。近十多年来我在与大学术界学者的交往中逐渐把握“历史人类学”理念的同时也欣喜地看到,国际音乐学界也已经注意到大学术界的发展趋势,已然形成了“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理念,这更使我坚定了两种学科可以接通的学术信心,如此我在《山西乐户研究》学术实践的基础上撰写了《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论域的交叉》[9]一文,对两种学科理念的交结做出辨析和探讨。
反思文化人类学既有学科理念以及历史人类学的意义,回到音乐学自身,为要者是应注重对传统音乐文化自身脉络的把握。既然是为传统,一定是历史上生成经不断发展演化积淀在当下,如是,我们则不能够仅仅将其以当下的“民间态”仅仅从一时一地加以考量,而应调整知识结构和学术理念将传统与现代接通,如此这一对学术范畴、所谓共时与历时方具有实际意义,这是立体研究的意义。从当下、活态切入,绝不等于将研究对象平面化,从当下活态中感知历史、感知传统的存在,我们的民族音乐学理论才更具实效性,展现1+1大于2的意义。即便关注活态,也要注意个案与整体的关联,更何况从整体中显现出的同一性应该从历史传统的角度对其合理解释。
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认知与把握,如果离开了历史的视角还真是难以说清楚。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学者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一点值得考量。在下以为,有历史代表有传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征,我们不应一方面将中华文明挂在嘴边,需要时拿出一用,一方面又将其视为“沉重的包袱”者。需要思考的是,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意义究竟何在?要不要将当下与历史大传统接通?仅以当下论不接通历史如何能够认知或称把握中国音乐文化内涵?中国音乐文化本身具有历史感,如果将其作为包袱,那还是中国音乐文化吗?伍国栋先生重视海外华人的学术评价,主要从评论相对客观,而不会像大陆学者多为“歌德”式。但我们也要看到,作为专修音乐学的研究生也还难以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真正意义上的认知与评价。不知伍先生“这对于过去仅片段翻译西方学说,或仅站在中国学术立场,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学者而言,无疑的更显出这本书的独特性”[10]的评价以为然否?是否从另外角度理解成为先生要修订本书的理由?
关注原点,关注学科发展趋势,用以解决本学科学术研究中存在的诸种问题,学术的意义就在于此。伍国栋先生近年来对江南丝竹的乐种学研究就具有这种历史的民族音乐学意义,该书的前三章“丝竹乐溯源”、“江南丝竹的渊源与形成”、“江南丝竹的相关乐社”渗透着这种学科意识,整体来看,本书可谓融合了传统音乐的研究方法,又将丝竹乐置于历史文化大传统中加以观照,并从活态切入,真正体现了学术个案对应文化整体、活态接衍传统、音乐本体分析细致入微、既有共时又有历时的学术意义,虽然在王朝典章制度以及历史上乐人承载群体层面的把握尚有缺憾,但我们要说,这是体现新理念研究江南丝竹的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具有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意义,是新学术理念的践行。应该明确的是,仅将西方学术理念以为标尺来卡中国传统音乐的位,与将这种学术理念消化、吸收,把握其长短,然后加以夯实的情状下再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结合,两种学术理念整合后用于研究实践,具有整体宏观把握,这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差异。站在中国学术立场吸收多种学科方法论方为正途,将传统视为包袱,却又不去把握包袱中的内涵,又如何能够深层次认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几年前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中非音乐对话”学术研讨会上,一位来自埃及的学者论文题目是《作为非洲乐器的钢琴》,这是很有意思的表述。钢琴源自欧洲,当其漂洋过海来到非洲,当地音乐家在把握其性能的同时“站在非洲人的立场”围绕其进行创作,这种创作的音乐思维和理念显然融入了非洲人的审美风格,其表现非洲人思维和风格的音乐作品通过钢琴得以充分展示,我想这也就是钢琴作为非洲乐器的意义。同理,中国当下的“民族乐队”组合中,诸如管子、唢呐等等,若细究起来都不是华夏民族的创造,但它们却完全融入了中土,在一般意义上谁也不会认为其不是中国民族乐器,但我们还是应该明了这些乐器的“前世今生”,这就是学术的意义。如此说来,无论作为“工具”的乐器,还是作为“工具”的学术理念,都是可以借鉴为用者,关键是怎样用,如何用。就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讲来,关键在于怎样能够比较合理地应用于解决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学术实践过程之中。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客观存在,但我们要真正认知和把握还需不懈努力,这当然要让自己有能够认知的知识结构,否则如同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即便将一块璞放在面前也不知其真正的价值岂非憾事!
一种理论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方显长久意义,理论需要发展创新。文化人类学带给音乐学界的清新就在于注重“活态”的同时考量乐在文化中存在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传统的活态存在把握整体内涵,认知何以存在、怎样存在,何以能够将传统传承到当下,如此就要立体化的研究使之与传统、历史接通。中国文明延续数千载,中国音乐文化有着悠久传统是不争的事实,传统积淀于当下,当代人承载的音乐文化形态中渗透着传统的基因,我们显然不能够仅仅将其以当下、民间态认知,应考量其历史上的生成、存在方式,传承与传播方式。中国文化的特质就在于有传统的存在,这也就是不能仅以当下、民间态认知音乐传统的道理。忽略了这个基本事实,难以把握传统音乐文化的演化关系,方法论意义上最为要者还在于更有效地认知和解读传统的实质内涵并以为创新发展之用。
伍国栋先生是我非常尊重和敬佩的学术前辈。我也曾是为他的部下(受乔建中所长委托负责研究生部音乐学系学生管理工作数年之久),因此多有向先生直接讨教的机会。伍先生敏锐的洞察力,高度的学术敏感性,尤其是他将引入的学术理念身体力行不断用于实践,勤于思考,与大传统接通,与传统音乐理论研究方法接通为用的把握,非常强的践行意识,如此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伍国栋先生是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理念的重要开拓与践行者,他在西学理念引入之后不断将其夯实,辨其合理实用性,并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理念接通,使其融为一体向前发展,如此更加有效地应用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这是有理论有实践具有体系化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理念。当然,一种新学术理念的形成绝非一蹴而就,亦非在展现之时就呈完善的形态,尚需不断吸收调整补充。实际上,当下中国音乐学界将两种理念整合在一起来研究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已经形成了群体、团队的力量,伍国栋先生作为最早有意识将其整合发展并不断践行的一线学者,在自己不断探索的同时也引领和关注学界,增订版增加众多的例证就是很好的证明。我们期冀伍先生若干年后再次增订之时会以更新的面貌示众,甚至干脆就打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旗号也未尝不可。这是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念显现中国特色的学术实践与理论意义。在这种意义上,研讨会对于伍先生的学术生涯应为阶段性总结,伍先生不会停顿学术探索的脚步,他会与学界共同培育这种学术理念使之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衷心祝愿伍先生学术之树常青!
初稿完成于2011年12月初,修改于2012年元旦。
本文为2011年12月13-14日南京艺术学院“《民族音乐学概论》修订版出版暨伍国栋教授南艺从教十周年研讨会”而作。
刊《中国音乐》2012年第1期。
[1]参见江山:《2011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及其学科建设研讨会》,刊“中国音乐学网”2011年12月2日。
[2]代表性的观点反映在王耀华、杜亚雄、袁静芳等多位学者以“中国传统音乐概论”名之的学术著作中。
[3]王耀华:《琉球、中国音乐比较论》,日本那枷出版社1987年版;吴茵:《民族音乐学的新成果及其方法论——<琉球、中国音乐比较论>读后》,刊《人民音乐》1987年第12期。
[4]当时我参加的是韩宝强先生主持“中国少数民族乐器音色库”的采集考察工作,在昆明与伍先生相遇后一路共行。
[5]伍国栋著: 《江南丝竹——乐种文化与乐种形态的综合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
[6]参见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发行感言》,刊“中国音乐学网”2011年12月2号。
[7] 同上
[8] 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刊《音乐艺术》2011年第1期。
[9] 项阳:《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论域的交叉》,刊《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3创刊号。
[10]参见“中国音乐学网”2011年12月24日伍国栋先生的博客《为什么重视海外学人对本书的评价》,其中有转发台大研究生张慧文的相关评论文章:《<民族音乐学概论>书评》。
图1:伍门弟子之一
图2:邹建平院长、樊祖荫教授与部分伍门弟子
图3:王耀华教授贺寿
图4:居其宏教授与夫人贺寿
图5:管建华教授与樊祖荫教授
图6::《人民音乐》于庆新先生贺寿
图7:秦序教授与伍先生弟子邓钧贺寿
图8:弟子田耀农奉上贺礼
图9:贺寿宴会上的蛋糕
图10:儿子伍洲彤为父亲祝福
图11:徐元勇、杨和平教授等表演“四只小天鹅”
图12:范晓峰教授领衔表演现代舞
图13:项阳演唱《我的太阳》
图14:伍国栋先生深情告白
图15:研讨会现场——居其宏教授主持
图16::伍国栋先生向南京艺术学院赠墨宝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