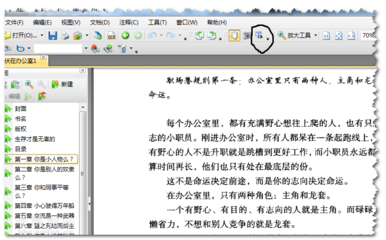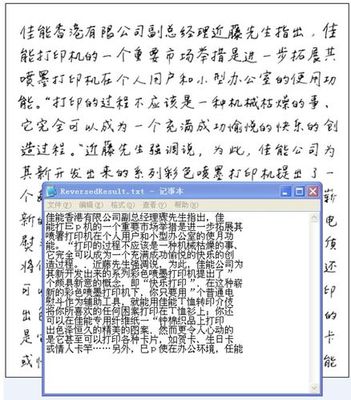文/凌霜降
十五岁时,我在一个很平静的小镇初中里读初三。我叫叶蔷薇,蔷薇是那种在南方的野地里长势疯狂却开着粉色的带刺的花朵的蔷薇。不需要温室,我想在原野里夺目。但我却不是蔷薇,我只是一株只长叶子的灌木。老师给我的期末评语中,永远是这一词语:文静乖巧。只有我自己知道,所谓的文静乖巧,意思就是老师拿着显微镜才能勉强在一堆同学里找得到你的意思。与我相依为命的爸爸是这个小镇里为数极少的单身父亲,大多不工作的时候,他都在沉默地想念天国的母亲。

我也很沉默。我觉得自己一支沉默的鱼雷,在冰冷的水里沉默,在等待着某一个让我爆炸的沸点。在但爆炸之前,我周围全都是冰冷的沉默的平静的水。这让我感觉自己的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左冲右突的想要冲破我而出逃。我就这样沉默地,像一粒落在教室里的微尘,如同经过长长的一个冰河世纪一样漫长的时光的漠视,我高一了。那句话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我既没有爆发,也没有死亡。我只是,长大了。我的身体,像一朵要开放的花一样,仿佛只是一夜之间,它柔软地,饱满地,满怀希望地准备要开放。我忽然发现,原来我那些要爆发的,不是一枚在冰冷的水里的鱼雷,而是在春寒料峭中想要开放的花,一朵快要掩饰不住它张狂的美色的蔷薇花。我有些担忧,却又有些兴奋地看着自己柳枝一样细软开来的腰身,以及春笋破土一样的胸部,这让我感觉自己像一朵快要绽放的蔷薇。
我开始察觉到男生躲闪着的却追随着我的背影的目光。那一些目光,小米说你应该骄傲,全校没有一个女生的身材比你更好了。但我却是惶恐的,那些目光非但没有让我骄傲,反而让我无所适从,我总感觉他们那些目光仿佛在剥开我的衣服,有时候这种感觉让我不断的低下头来检查自己是不是扣子没有扣好,尽管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穿着很规矩的T恤,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没扣扣子这种情况,我想或者是我的感觉神经太过于敏锐,还有我的想象太过于下流。但我真的我没有办法从没有人注视到没有人不注视这一种转变中适应过来。我巴不得找来一条长得过份的厚重白布把自己身体的曲线缠成一条直线。不,我原来并不喜欢这样被注视的生活,我开始怀念那些“斯文乖巧”的日子。
而杨磊的目光正是我浑身不自在的主因。我开始不再理会他向我借东西的每一句话。无论他说什么,叶蔷薇借我像皮,叶蔷薇我的书呢,叶蔷薇老师来了,叶蔷薇借我作业本,我都只用“哦”一个字来回答他。我含着胸走在校道上,杨磊常常从后面跑过来,或者不跑,而是骑着他的自行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会听到他的口哨,或者一些别班的问题男生的口哨,此刻的我会惊恐地听到杨磊说:叶蔷薇抬头站直!我居然还会“哦”一声然后条件反射地站得笔直。然后我会听到杨磊爽朗而大声地笑,那种笑声在校道上的枝叶间缠缠绕绕,让我的心忽然生出了一些无名的忧伤。甚至会感觉天就要暗淡下来了。那些日子,发现青春真的很长很长,讨厌自己为什么还没有长大到能够接受变化,长大到可以骄傲小米所说的“骄傲”。
杨磊与我同班。就坐在我的后面。他总喜欢向我借一些橡皮铅笔什么的。我的同桌是小米,她的话就像小米一样又多又碎。我看杨磊一定是对你有意思。小米啃着零食,非常肯定地在我耳朵边宣布。我对于零食的兴趣像对小米的话一样没有兴趣,我宁愿趴在桌子上看窗外的飞鸟,我整天都在做一个这样的梦,梦见自己是一只自由的白鸟,我可以飞。很自由的飞。但我知道自己不是白鸟。只是一相貌很普通的女孩子。
我其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自己的外貌特别特别的介意。开始厌恶生活太过平静,没有快乐,不感觉到幸福,甚至没有痛苦。没有痛苦也是一种痛苦。这样的青春让人窒息。但我从来不会与小米说这些话。小米不会懂的。所以我从来不说。我仍然是含着胸,低着头走路,原来,对于一个原本就内向的人来说,美丽或者张扬都是一种无形的伤害。这一个认识让我更加沮丧。
而这时,我收到了人生的第一封情书。那是一个隔壁班的男生,名声像他的文笔一样差,他提到了喜欢我的理由时说到:因为你的胸很大。
我看着这七个字,感觉自己全部的血液全都涌上了脑袋,我不知道我的脸是不是红得特别的可怕,我只知道有一种无以言喻的羞辱令我浑身颤抖,甚至没有办法思考。我能想到的就是冲到隔壁班去,当着那个男生的面撕碎这封信,然后狠狠的甩他一个耳光,然后再语无伦次地骂他不要脸什么的。
我忘记了自己是不是还因为这种羞辱的感觉而哭着,我按照自己的冲动跑出了教室,在走廊里撞倒了谁我不知道,我几乎是手脚并用,混乱而准确地把那封信丢到那个男生的脸上,然后甩给他一个耳光,或者因为我的力道太大的关系,那已经不能算单纯的耳光,而是一个拳头。
那个男生好象被我打得流了血,我的泪水让我的视线模糊得可怕,几乎是跌撞着跑离了那里。
那个寂静的放学后的我感觉耻辱的黄昏,我蹲在教学楼下的球场阶梯上哭泣。
空旷的球场上,我听到自己回荡着的抽咽声,还能听到我大颗大颗的泪水滴落在水泥地上的响声。这让我感觉自己孤独而又悲凉。甚至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更让我伤心。
这有什么好哭的。你是很丰满呀,我也很喜欢。
我猛地从泪水中抬头,居然看到了杨磊。我瞪着他,用一种耻辱的,可怕的,或者还充满了憎恨的眼光看他,他没有再说话,脸是红的,也在瞪着我,我读不懂他的眼里是什么样的情绪,但我想我眼里的目光一定是充满了一种厌恶的愤怒的火光,它们烤干了我眼睛里原本充盈的泪水,让我的眼睛变得异常干涸地疼痛。这种疼痛扯动了我那些积压着的忧伤,他们让我感觉自己正在变得空洞。
我直直地瞪着杨磊,忽然发现此刻的他跟那个写信给我的男生没有什么两样。这样的认知让我的眼神渐渐地也空洞起来。
我慢慢地站起来,不再瞪着他,我感觉自己很冷,很空。像一具丢失了灵魂的躯体,我轻飘飘地经过杨磊的身边,踩着荒凉的夕阳,是的,我是这样的空洞的伤心。
我真的去找来了一根长长的白色棉布,缠紧了我那像我的伤心一样疯狂生长的胸部,这让我的十七疼痛中到来了。因为打人事件,我在学校里很是出名,而这样的出名,是一种难以名状的难堪。我对此的直接表现,除开那根让我无限疼痛的白色棉布,就是一种沉默。我甚至不和小米聊天了。对于她的话,我甚至开始用“哦”来回应。而对于杨磊,对于他的任何言语,我连“哦”也不用。我想我会在沉默中死去。有那么多的东西没有人懂,我也不懂,无疑就只有沉默。沉默。沉默。在这种孤独的,沉默的,疼痛的,有很多说不出的忧伤时光里,那一根同样沉默同样疼痛悲伤的白色棉布牵着我同样疼痛的青春陪着我走到了高三。一切如白驹过隙,我却感觉无阻漫长。我仍然叫蔷薇,只不过,是沉默的蔷薇。
其实站在河边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到了死。于是就在听到身后有人喊叶蔷薇你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失足,真的是失足掉进了冰冷的河水里。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觉得自己离死亡已经很近,我甚至不去挣扎。河水开始变得很蓝,透明清澈纯净的蓝,让我想永远这样冰冷地睡过去。
但我醒了过来,看到杨磊在滴水的头发,还有他潮湿的目光,他说,你这样,不痛吗?
我散开的扣子,还有那一根的松开了的白色棉布,都像我此刻的心情一样,潮湿而冰冷。
同样冰冷的,还有我眼角的泪水。
因为那样压抑的冰冷的哭泣,以至使我几乎不记得后来是怎么回到家的。
因为这一种不为人知的尴尬,让我在面对杨磊时更加的沉默。我甚至不再看他。
杨磊曾经偷偷塞到我文具盒里的那一张纸条上的地址,我去过的,是一间在角落里卖一种叫做文胸的内衣的小店。那里进出着一些年龄比我大的骄傲的也害羞的女孩子,去了好几次,我都没有勇气踏进去成不她们其中的一个。
半年后的大学校园里,我丢弃了那一根已经不再洁白的棉布,我离那个安静的小镇已经很远很远,这个城市里的女孩子,全都妖娆美丽得像怒放的玫瑰。这个城市里,也有很多更漂亮内衣小店,已经有很多与我同龄的女孩常常很快乐地从里面走出来,我开始成为其中的一个。
再次碰见杨磊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站在我的对面,用那种当年在那个伤心的黄昏的眼神看着我说:你很美丽。真的。
我忽然泪流满面,为这一句话,也为那一些蔷薇花开却沉默不语的少年时光PS:最近非常喜欢这个女子的文字。也看了一些她的专访,经历真是坎坷丰富,希望她的身体快快好起来,这样敏感的女人,应该被很多人爱着的才对。我才发现之前在很有杂志里看到比较喜欢的文章,好几篇都是她的。把这篇帖子转过来,是因为曾经也有那样的心情。青春期时的自卑,成为心底好久的秘密。直到很大以后,跟好友聊起来时,才知道,不仅是我,那时的很多女生都曾经有那样的心情。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