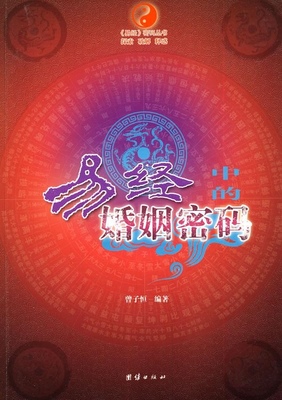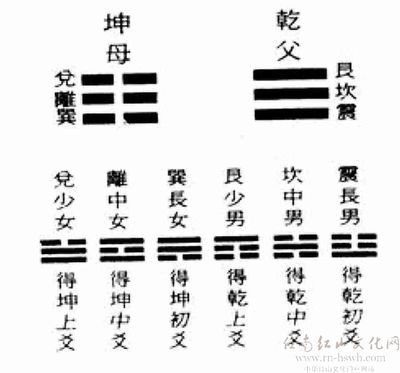明清易代中的泰安士人
——《泰安施氏族谱》中相关人物史料考索
周 郢
提要:明清易代之变中,泰安士人命运也随之起伏不定。新发现的《泰安施氏族谱》上对此即有生动反映。其中所记萧启濬谋叛罪案、施天裔曲折身世及赵国麟应试经历,分别显示了明朝勋臣的末路、从龙新贵的崛起与治世名臣的产生。三家不同的人生遭际,折射了明清之际社会巨变之一斑。
伴随着“天崩地坼”般的明清易代,饱受冲击的汉族士人,也呈现出悲喜荣辱之不同命运。新发现的《泰安施氏族谱》之上,便对此际泰安人物境遇有生动反映。《泰安施氏族谱》(亦题作《泰安施氏家谱》,以下简称《施氏谱》)创修于清康熙八年(1669),后续修于乾隆十四年(1749)、道光五年(1825)、咸丰十年(1860)、宣统三年(1911),今所见为民国时期钞本。谱前收有乾隆十四年(1749)施元度等撰《先王父暨先府君事》及诗、序、尺牍等,涉及了萧启濬罪案、施天裔家世及赵国麟交游等情况,对明清之际泰安史事的考索,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
一
泰安名臣萧大亨历掌兵刑,显声于明末政坛,其子和中、协中也在朝堂文坛留有声名。如自萧大亨入仕算起,家族前后荣贵七八十年。但入清之后,这一高门却神秘消失,乾隆程志隆修《泰安县志》说大亨曾孙萧启濬“死于流寇”(大顺军),清康熙时金简《泰山图说》中写到萧大亨府第时言道:“神仙府内,萧司马之宦迹何存?”则可知入清之后,萧大亨嫡裔死于非命,萧府也已人去堂空。萧氏家族在明清易代中遭到何种变故,成为一桩历史谜案。
民国泰山学者王次通先生《岱臆》首次提出此案,推测“顺治四年(1647)萧氏竟有灭门之祸,盖惩其(萧启濬)延贼登城之罪”。萧启濬(号松庵)系萧大亨长孙萧友贤之子,《明神宗实录》卷四○七载:万历三十三年(1605)三月庚子,“兵部尚书萧大亨嫡长孙萧友贤于原荫百户上加一级,并授(锦衣卫)衣左所副千户,俱世袭。”故得袭锦衣卫世职。崇祯时历官至锦衣卫堂上佥书管卫事(此衔见岱麓关帝庙东墙外所嵌崇祯十七年三月泰安州洛庄香众题名碑)。崇祯十年(1637)左右犹供职于朝,《明季北略》卷十三(崇祯十年)“圣驾巡城”中提到其人:“崇祯丁丑(1637)八月,上欲巡城,……如萧大亨之武荫萧松庵,锦衣佥书也,内止派其领值酱色绉纱深衣一袭。”[1]甲申(1644)时家居,时逢大顺军攻泰安,启濬为妻孥计,启北门纵“贼”入城,旋被大顺军押解北行,乘乱逃归。[2]后事不明。王次通先生揭明萧案由启濬触发,至于具体细节,则云“其详不可知矣”。
随着台北中研究史语所藏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公布,使我们得以获见此案的第一手材料。档案目录有《钦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儒秀为违禁旗印有据谋叛形迹已萌谨据实题参仰祈圣断事》揭帖,适学友李俊领先生赴台访学,请其便中将该档抄回。今迻录其全文于下:
先据按察司按察使王任重呈,据济南府报称,蒙抚院案验,准刑部咨,该本部覆奉圣旨:“萧启濬着即就彼处斩,家产妻孥入官,王无欲、李瑞徵姑各责拾板,馀俱依议,钦此。”钦遵抄出到部,移咨到院,案行到司行府。该知府张善略会同本府推官李振春,于四年八月十二日将萧启濬提出押赴市曹正法讫。其犯人王无裕(即前文之王无欲——引者注,下同)、范洪宪等,本司恪遵圣旨,分别责惩发落、完法等因缮疏。间录妻孥未有解京字样,覆咨该部示明行司,续于顺治五年正月初六日据署司事佥事刘宗舜呈,解到萧启濬妻孥辛氏等十六名口,并马牛驴俱解刑部发落,其家产、器皿另变外,今将正法过缘由理合呈报等因到职,理合具题。伏乞敕下该部查照施行。为此除具题外,理合具揭,须至揭帖者。顺治五年正月。
根据这件山东巡抚张儒秀题本,萧大亨家族在顺治四年遭灭门之祸,不仅首犯萧启濬被诛,其妻孥亦被解京为奴,家产并遭籍没(萧府第当在此时入官成为公产)。而其犯事之由,并非是甲申“延贼登城”的旧案,而是图谋反清的新罪。——官府在萧府中搜出“违禁旗、印”,认定“谋叛形迹已萌”,因而痛下杀手。顺治三四年正是山东各支抗清武装高潮迭起之际,先后有周魁轩、李桂芳、蔡妳憨等部活动于泰安周边。萧启濬作为原任明锦衣卫千户,又是兵部尚书之后,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很有可能被抗清义军奉为谋主。而因萧启濬秘密制作军旗、印信,等待时机打出反清之帜,极有可能。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萧大亨在主持军务期间,诘责努尔哈赤,与女真结怨甚深,清廷入关后寻隙报复,用谋叛之名而将萧府诛灭。不管事件真相如何,沸沸扬扬的萧司马家族却由此消逝于历史舞台。
卷入萧启濬谋叛案的三个人物王无欲、李瑞徵与范洪宪,三氏在史籍上均留记其名。王无欲为清初进士王度(历官山西大同知县、大理寺卿、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等职)之子,《泰山王氏家族》(清代钞本)载:“第六世:无欲:度长子,字佐可,顺治戊子(1648)科举人,戊戌(1658)科会副,庚戌(1670)科拣选知县。敕赠文林郎。”范洪宪当为范弘宪,《泰安范氏族谱》(民国刊本)载:“弘宪,行三,字凌谷,父早逝,惜无岵屺。壮岁就武弁,为将材守备,值土寇猖獗,胆勇招抚。抚台嘉之,委补平阴县,贼盗屏迹,阖邑安堵。”行实均未述卷入萧案事。李瑞徵,据康熙《泰安州志》卷三《科第》,其人系顺治乙酉(1645)武举。从《题本》中对三人量刑轻微看,王无欲等可能涉案不深,如是谋叛核心人物,当难逃诛杀之祸。
在《施氏谱》卷首乾隆朝施元度等撰《先王父(施文明)暨先府君(施镰)事》文中,出现了关涉萧启濬狱案的记述文字,极大补充了档案之阙略。谱云:
先王父龙田公,讳文明,姓施氏。原籍乌程,为司训任庵公(施弘道)少子。家故贫,弱冠即勇于为人,喜结纳,好施与。……前明万历间,王父北上,道过泰安,与锦衣萧公、绣衣赵公、副使李公相友善。是时盗贼蜂起,土旷人稀,王父独身赴京无諕色。及我朝定鼎,寄留长安(按此指北京),亲娅自南来,有贫乏者多助之金。虽再三,弗厌也。从叔泰,以犹子来省,叩其欲,出赀除商河县尹。时萧公罹害,妻孥北迁入辛者库,给功臣家为奴。仲冬,萧夫人犹衣罗衣。先王父闻之,出二百金赎焉,更为治装,送归里门。赵绣衣诸先达辈咸义之,奋笔立石,以志不忘,迄今虽字剥落,而文犹仿佛可诵。府治西郊,即其立石处也。
这段记载,提供了诸多萧案细节。先是明万历间,浙人施文明北上入京,道过泰安时,结交了三位士绅,“锦衣萧公”即萧启濬(锦衣卫佥书),“绣衣赵公”即赵弘文(官御史,故称绣衣),“副使李公”即李雨霑(官甘肃兵备副使)。三人中除启濬袭锦衣卫官不知在明末何年,赵、李之官绣衣、副使均在入清之后,故各衔应是追呼后来所任之职。而二三十年后,发生明亡清兴的巨变。当日显赫无比的萧府已遭弥天大难,不独府主蒙难,眷属的遭遇更为可悲,档案中称“萧启濬妻孥辛氏等十六名口并马牛驴俱解刑部发落”,而据《施氏谱》,其处理结果是悉被发入“辛者库”,给功臣家为奴。——辛者库是满文“sinjeku”的音译,乃管领下食口粮人之意,所指系八旗之下一个包衣(奴仆)组织。其初为收编管束降民的机构,尔后逐渐演变为收管罪犯家属的刑外执法机构。据清史专家考论:“‘入辛者库’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纪纲’,统治其臣民的一种惩罚措施。它所惩罚的对象,是‘本犯佥妻及未分家之子’。但是, 本犯大多根据所犯罪行或斩, 或监禁, 或发遣,实际上被贬为辛者库的大多是他们的家属。一人犯罪,全家少则几口, 多则几十口, 都要被贬为辛者库。”[3]入辛者库者之境遇,《施氏谱》中提供了一个细节,即萧启濬夫人辛氏,仲冬之时“犹衣罗衣”。大柢萧氏案发约在顺治四年夏,至仲秋已将萧启濬“正法”。而在当年严冬,辛氏羁押中还身着被捕时之夏装。清初刑狱之残酷暴虐,数百年后犹使人为之寒慄。
当遭逢这种谋叛大案时,不仅亲友恐引火烧身,避之不及,即心怀同情的权势之家,也慑于法令,弗敢过问。而与萧启濬只有萍水之交的一介布衣施文明,却能不负死友,无惧株连,奔走刑狱,醵金赎出故人妻室,且为“治装送归里门”。《施氏谱》的这段记载,不仅让后世得以了解萧启濬案的最后结局,更从施文明身上,看到闪烁着的人性之光。难怪当时赵弘文等人为之感动莫名,立碑铭德,永志不忘(此碑赵氏《光碧堂稿》不载,已佚)。
萧族籍没后,其府第没入官府,因是罪人故宅,无人敢入居其中,故闲置百年之久(至乾隆四年[1739]方于其处设立泰安县署,即今之“泰安老县衙”址)。华屋画栋,渐化陋室空堂。以至时人有“萧司马之宦迹何存”的悲叹!述史至此,使人顿感似在演说一部《红楼梦》。——此倒真应了红学家二知道人(蔡家琬)之论:“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4]古来王侯结局率皆如此,萧大亨家族又曷能例外!
二
当王朝易代之际,泰安一地既有殉葬前朝的旧勋,也自有随新朝“龙兴”而发迹的新贵。其中声名最著者当推施天裔,《先王父暨先府君事》中对此人也颇多涉及:
(施文明)与宗人天裔者情好尤笃。天裔,泰山人,业儒。甫冠,游盛京,获从龙京师,依旗人周。周与先王父友,王父过周遇之,叩其先世居吴兴,因联谱,而天裔得所矣。久之,因话及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两先生讲学处流风如昨,胡翼之投书涧遗迹犹存,欲就不果行。适州主簿乏人,得捧檄来游(指施文明出任泰安州主簿)。……先是定鼎之初,南北犹然两朝,先王虑终无南归期,再聘于汶上王公讳为鼐女,即度祖母也。生府君(施镰)一人。迨南还,祖母北人,不耐湿热,僦舟偕府君北归,临行王父嘱之曰:“天裔,吾宗也,可依托。”抵岱时,天裔已贵显,任本省藩司,而其弟天爵家居,一见如亲子侄。爵妻梁氏尤笃爱之。及府君秉铎螺峰,梁捬府君背曰:“汝虽非吾亲子,所欠者无食吾乳耳。”遂数行下,府君亦唏嘘不自胜。……(去官后)归居城西隅旧宅中,先王母命府君事梁如母,终梁之世,府君始归济河。
按《谱》中之“宗人天裔”,即施天裔(1614~1690,字泰瞻,泰安人)。其人身世极为曲折。据天裔墓中所出《皇清诰授通奉大夫原任巡抚广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盐法部都察院副都御史显考施公泰瞻府君暨元配诰封夫人周太君合葬墓志铭》[5]载:“会前丁丑(1637),我大清兵入境(按丁丑清兵未入关,此应为戊寅[1638]之误),薄(泰安)州之郊,公趋视贾公(天裔外祖贾治安),未及舍,为逻兵所获,偕出关。”则天裔在清兵攻掠山东时被掳,驱往辽东。天裔从一介明朝书生,成为清军俘囚。《施氏谱》称之为“甫冠游盛京”,盖隐讳之辞。
施天裔作为俘奴驱赶入辽,流离道途,身染重病,将化异乡游魂之际,幸而遇到命中福星。此人名周日宣,字明吾,辽东人。隶汉军镶红旗。仕于清廷。其见天裔器宇不凡,收留家中。《墓志》云:“道病,遇原江右道周君讳日宣者,奇公器宁,馆之家。适衡文者至,以周姓应童予试,辄冠军。时好学者无远近皆从游焉。”施天裔借助周日宣之力,得以摆脱俘奴身份。此后参加清廷在盛京举行的科考,获得贡生学衔。顺治元年(1644),清廷入主中原,周日宣随军入关,历任直隶唐县知县、东昌兵备、山西按察副使易州道、江西粮道等(《奉天通志》卷一九九、《临清县志·秩官志》)。施天裔也随后出仕,历官至山东布政使、广西巡抚,宦业远胜养父,成为“从龙入关”的开国勋旧。从俘囚到疆吏,人生命运之诡谲变幻,从施天裔身上得到生动体现。
在《施氏谱》中,提供了一个关于施天裔的细节。即清廷入北京后,天裔随义父周日宣至京,而施文明与周日宣为好友,文明过周府时偶遇天裔,访其先世居吴兴(以墓志所载,天裔祖籍章邱,吴兴或为远祖乡贯),遂与联宗。——天裔被周日宣收养后,一直从周姓,称“周天裔”。与施文明联宗后,重入施氏宗族,故云“而天裔得所矣”。至康熙六年(1667),施天裔上书康熙皇帝,请求恢复原姓,获批准。其源实导自与施文明之联宗。施天裔复姓后,清廷追赠天裔祖、父施所学、施可兴为通奉大夫、山东布政司布政使,并于其故里(施家结庄)树立“龙章褒赠”坊与敕命碑,坊碑至今犹存。
——与施天裔经历相仿的,还有昌邑李士桢一族。李氏也是从明之士民,经历了被掳、易姓(原姓姜)、入关、显达这一系列人生悲喜剧。新近于山东昌邑发现的清李煦(李士桢之子)《虚白斋尺牍》,其中一件为《与南通州施牧》[6],“施牧”即南通州知州施其礼,为施天裔之子,李煦称其礼为“老世台”,系世交本辈之敬称,则天裔、士桢为故交无疑。若集中考察施天裔、李士桢这类“旧俘新贵”的家族命运,颇有助于解析清初社会阶层的裂变与《红楼梦》产生的历史背景(李煦为曹雪芹之外祖)。
《施氏谱》中提到的施天爵,贡生,系施天裔同父异母弟。后以子其智赠奉直大夫、姚州知州。施文明于顺治二年(1645)赴任泰安州主簿,管理香税事务(泰安夏张镇南故县村弥勒寺康熙十一年(1672)重修观音殿碑后题名有“原任泰安州管理香税总巡厅施文明”,可知施氏正式官名系“管理香税总巡厅”),不久去官南归,命其子施镰(时年六岁)来泰投奔施天裔,时因天裔在外任职,受到里居的施天爵全家的护持,天爵妻梁氏更把施镰视同己出。施镰成年后出任招远训导,因挂念梁氏年老,上任未几便坚辞教职,归里侍亲。招远知县夏灿在《送施修仪先生归里序》中述云:“以恩抚婶氏(施镰称梁氏为婶)为念,早欲辞官归省。……兹春三月,因思省念切,抑郁成疾,特为余言曰:‘今断不能勉留矣。’遂唏嘘泣下。……不得已,勉从其请。”施镰归泰安后,未返济河故宅,而且留居城中,奉养梁氏,直至其寿终天年。泰安二施的这番宗谊,在大动荡社会中演出了极为温馨的一幕。
另,岱庙环咏亭中旧有施镰跋《登泰山唱和诗》真书石刻,《泰山石刻记》云:“施镰跋、施其信四言古一首、施德裕五言古一首、施复五言律一首,康熙丙子(1696)二月,並刻记(金古良《登岱记》)后。”(按施镰等石刻久佚,民国王次通《岱臆》云:“环咏亭岱人题识如施镰、施复、施其信之作均失,诚一大损失。”又云:“(环咏亭存)石刻皆外人游诗,其岱人诸施氏之作无一存者。真文献之奇厄。后五年,在历下得施氏拓片,诗文俱在,惜已残矣。”今宁波天一阁尚存拓本,系杨氏清防阁旧藏)施其信系施天裔子,施德裕系施天裔族人(《八旗通志》卷四八记其为康熙三十六年岁贡)此刻也可佐证施镰与施天裔家族的因缘。
三
伴随着社会由乱转治,登场人物也由从龙勋贵而渐易为治臣名臣。此时泰安人赵国麟(1673~1751)即以科举入仕,登上康乾盛世的政治舞台。国麟字仁圃,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初讲学青岩义社,后历任福建、安徽巡抚,屡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所著有《云月砚轩藏稿》、《调皖记行草》、《塞外吟》、《近游草》、《拙庵近稿》等。后人将其列为“泰山五贤”之一。《施氏谱》中详细记叙了赵国麟与施镰一族的交迹:
府君(施镰)始归济河,锐意文教,绝迹不入城市矣。礼延仁圃赵公(国麟)为诸生祭酒,公入讲堂,大究六经百子之旨,往复上下,其议论侃侃凿凿,根极始末,府君每昼坐檐下倾耳听,听毕辄抵掌叹惜。公(国麟)问之,曰:“君解经如生公说法(生公,高僧),倘得三年馆于此,诸生学之不已,何患不大成耶?”公诺之。先府君拜公,公亦拜。是科(指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科)公成进士,不廷对而还。三年中人才蔚起,彪彪炳炳,多得志飏去。度时尚幼,未获受业。后公居揆席,尝语人曰:“某一生廉介自守,皆以施修仪先生(施镰字修仪)为法程也。”
按这段记录涉及赵国麟早年一段重要经历。郢旧撰《赵国麟生平系年》[7]时,注意到民国范明枢所撰《五贤祠碑》中一条记述:“赵仁圃先生,……少时家赤贫,唯负薪携米、汲井灌蔬以娱亲。及遭大故,几案盘盂,典质殆尽,终不以贫故干人。二十六岁举于乡。三十四岁馆于济河,计偕入都,试竣即策蹇归里。捷音至,不赴廷试,以与济上主人有三年之约,不以相负故也。”当时读之,既不知“济河”与“济上主人”之所指,亦不明范明枢此条史料所从出,心中蓄疑久之。今据《施氏谱》,乃知“济上主人”即施镰(居济河,清初为泰安州济河保,即今肥城市边院镇济河村)。赵国麟时任教于其家,其在丙戌会试取中后放弃廷试,返回济河任教,不但反映国麟重诺之诚与淡泊之怀,亦可见其对施镰知遇的感念,洵属一件诺重千金的士林佳话。
不过笔者以为,赵国麟之所迟迟不赴廷试,除去其重诺守信一点外(其实参加廷试后不一定立就实职,亦有中进士后归乡之例),实与其面对出仕之犹疑态度有关。赵国麟之祖父赵瑗,为系孤志抱节之胜国遗民,尝授以明忠节名臣金正希(声)、黄陶庵(淳耀)遗书,曰:“此节义文章也。”[8]明示与清廷的不合作姿态。但随着清廷统治的日益巩固与重儒政策的推行,部分士人的政治态度有所松动,心态逐渐地融入“新朝”中,一时出现“遗民不世袭”的局面。赵国麟也一直在“仕”与“隐”中徘徊,虽屡次参加科举,但取中会试后不即赴当年廷试,三年后中廷试也不服官,而是以候补内阁中书衔家居,其内心隐秘,在与会试同年赵东暄的通信中有所披露。据赵东暄函称:“老年兄(赵国麟)上承年祖(赵瑗)家学,任重致远,守先待后,固非弟辈所敢望其肩背也。然既不我鄙弃,示以隐衷,犹欲一广其说。窃谓出处多途,本难一致,亦顾所遇何如耳。今年长兄既受知遇之恩,倘时至事起,安得过于诿避?即年祖当此,亦难固守前辙。此所谓禹、稷、颜子,易地皆然者。况年长兄再传学后,犹抱此耿耿之怀,似亦可以不必矣。传曰‘善继善述’,夫所谓善者,非执守之谓,而变通随时之谓也。若执守之,则不能尽善矣。”[9]赵东暄之劝辞实不失为一种通达的见识,现实的态度。直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赵国麟出任长垣知县,方摆脱这一心理困境。而此时距其会试中试,已过十年之久。从赵国麟不即赴廷试一事上,生动展示了易代之际汉族士人抉择于节义与时势中之间的那番心理苦痛。
在赵国麟此后的人生历程中,始终与济河施氏保持着密切关系。这在《施氏谱》中载录的赵国麟文书中多有体现。
康熙四十五年(1706),施镰以廪贡被任命为招远训导(按道光《招远县续志》卷二《职官·训导》:“施镰,泰安人,贡生,(康熙)四十五年任”),教诲诸生,循循善诱。《泰安县志》本传称其“恺悌醇谨,士民信之”。赵国麟在《贺卓人游太学序》中对其招远教泽予以热情称颂:“先生为德于乡者久。乡人德之。畴昔奉诏乡饮礼,先生为大宾。岁在乙亥(1695),先生以岁荐,廷试第一,授螺峰(此指招远县)外史,辞不就,邦伯再四劝驾,迫于公令,不得已而行。甫二载,解组归。予告之日,螺峰绅士编民以及商贾行伍卧辙攀辕,唏嘘请留者,何啻万计,先生辞不可,群裹粮载酒,相送数百里,骊歌之赋,遍满交衢。迄今二十年,螺人问安好、请起居者,岁不绝使。夫以寒毡冷署,何与民社国家?而螺人爱之深,戴之至,勒之贞珉,载之国乘,以永志不朽,以视世之持禄位,患得失者何如哉?”但施镰淡于宦情,思亲怀乡,归心似箭。在任二载便绝意辞官。赵国麟复赋《寄呈招远施广文先生》古风一首,“为我府君(施镰)解组作也”。其诗云:“螺峰学舍如宛邱,螺峰先生似子由。身长屋矮低头坐,凉风吹面雨打头。广文官冷自古昔,先生把卷笑不休。金门待诏资割肉,方朔一饱复何求?东邻溟海蓬莱阁,长风万里来磅礴,海中蜃气幻楼台,波底鱼龙恣腾跃。夜半红日浴鲸涛,仿佛扶桑枝姌嫋。先生此时正狂喜,手换北斗酌海水。天吴出游相揖让,龙女掷珠舞花蕊。灵鼍负鼓声鼕鼕,老蛟跳波陈簠簋。骊龙啣杯竞上寿,琥珀光浓味甘美。珊瑚支枕水晶床,酣然一梦忘故里。呜呼故里不可忘,兹游虽乐可已矣。今年岱阳风雨和,满篝满车黍稷多。浮蛆甕熟酌瘿螺。灯前听雨颜微酡,手披目览口吟哦。兴来我和先生歌,人世仕途多坎坷。不即寻乐更则那?归去来兮归去来,先生其奈广文何?”[10]诗极写施镰居官之淡泊与归里之畅适,可谓深知施公心曲。
施镰之子施元英(卓人)“性英敏,精神爽露,善读史,工楷书,娴尺牍,广交游,干选事务,悉中机宜,为族党乡里所推重”(《施氏谱》)。雍正二年(1724)入太学。赵国麟为作《贺卓人游太学序》:“皇上(雍正帝)即位之元年,首尊至圣先师,加封启圣王以上五世徽号,饗以王礼。越二年,释奠先师于太学,躬行养老,再拜乞言,文治之盛,旷千古而仅见者也。而尤加意人材,两岁之间,两举制科,再行选拔,一时蔼吉之士,充满朝端。其在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汇。我皇上为保泰之圣主,用能以贵下贱,共成泰交之治。猗欤盛哉!犹恐奇士拘于绳墨,致叹野有留良也,诏凡山隅海澨一村一艺者,咸得自入于太学,临雍而陶甄,培养储用焉。其即辟门吁俊之意,与一时思皇之士,翘首皇路,共翔步辟雍之庭。……今卓人以弱冠遨游成均,觇其器宇,允称象贤。读秘阁之奇书,友天下之善士,对扬大廷,作宾王家,以竟先生未竟之业,拭目俟之矣。乡国亲友,争具牛酒,为贤乔梓(父子)寿。不远千馀里,乞言于余,以余知先生者深,故不惮跋涉如此也。谨即先生之素履而论次之。”对施元英能绳其祖武、不堕家风,充满欣慰之情。
施镰之侄施远龄(镜泉)“性严重,敦朴,素勤稼穑,乐宾朋,诱掖后学,善读古文,为乡里所敬畏”,不幸于雍正二年(1724)英年早逝,使施镰有折翼之悲。赵国麟时在永平(今河北卢龙)知府任上,特致函劝慰,感情真挚:“春间承台驾光临,未得多伸依恋之私,遂匆匆说别,殊深慢忽之愆。四月杪,忽闻镜泉大兄辞世之信,不胜骇异,忽忽如有所失者累日。戚友凋丧,老成典型衰谢,非仅一家一乡之不幸也。老叔台修身齐家,皆圣贤真实学问,故叔侄父子兄弟之间,雍雍蔼蔼,迥异寻常。麟亲炙数年,感发兴起,受益实深。故麟于岱中亲友无不爱而敬之,而于贤叔侄更心悦而诚服者,此盖衷曲之谈,非悠悠泛常之论也。今一旦凶变,老叔台素笃友爱,悲痛之情,自不能已。但修短之数,与穷通之运,似无二理,达人既不因穷通异节,岂以修短二心。麟愿老叔台节情以顺理,达观以自爱也。商隐(施远龄之子施伟)兄弟幼失怙恃,闻老叔台委曲劝导,用心甚苦,其从否皆有天焉。而在老叔台之道,则已尽矣。东望云树,不尽所怀,临风依结,伏惟丙鉴。”施镰有复函,自述家世始末,文繁不录。
施镰去世于雍正八年(1730),至乾隆时始葬,由赵国麟为之填讳。《施氏谱》载赵氏题衔云:“赐进士第、通奉大夫、原任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兼行管理国子监事务、己未科会试大总裁、文武两次殿试读卷官、充《明史纲目》总裁、咸安宫行走、回籍,赐复礼部尚书原衔、眷晚生赵国麟顿首拜填讳。”按国麟复衔在乾隆十五年(1750),施镰之葬当在此年之后。谱中又录“文渊阁大学士赵仁圃病后谢修仪诗”:“原是江乡旧合簪(赵原籍浙江上虞,与施氏同系浙籍),相逢迁国(迁徙之地,此指泰安)愈知音。三年讲习千秋业,四世相交一片心。我病忽如风雨至,君情更比水云深。深恩欲报无言说,稽首床前泪不禁。”确如诗中所言,国麟与施镰生不仅四世相交,情深水云,且生敬其人,死题其主,莫逆石交,可谓生死以之。
除去以上萧、施、赵三位历史人物史料,《施氏谱》中还存录了其他一些颇有价值的史料,如施文明谏阻原任泰安州同、升任保定巡抚之于清廉剿杀直隶避兵难兵一事,以及文明出任泰安主簿、司掌香税一事。前者因不属泰安地方史,此不置论,而后者则是香税制度变迁的重要史料,将详论于拙稿《泰山香税制度新考》中,此不赘及。
2014年6月1日草此
《泰安施氏族谱》抄本由施永林老师借观,谨此志谢!
《泰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1](清)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0-221页。
[2](清)王度:《伪官据城记》,康熙《泰安州志》卷四。
[3]王道瑞:《清代辛者库》,《历史档案》1983年第12期。
[4](清)蔡家琬:《红楼梦说梦》,曾祖荫选注:《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版,第224页。
[5]翟所淦:《施天裔夫妇合葬墓志铭得失记——兼述施天裔其人》,《泰山研究论丛》第二集,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186页。
[6]张书才等:《虚白斋尺牍笺注(一)》,《曹雪芹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2012版,第44页。
[7]周郢:《赵国麟生平系年》,《泰山文史丛考》,泰山区档案馆1992版,第191页。
[8](清)赵国麟《居岱渊源》,清代钞本。
[9](清)赵东暄函,《泰安赵仁圃相国苔岑录》,山东博物馆藏原稿本。
[10] (清)赵国麟《云月砚轩古体诗稿》,《泰山丛书》丙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