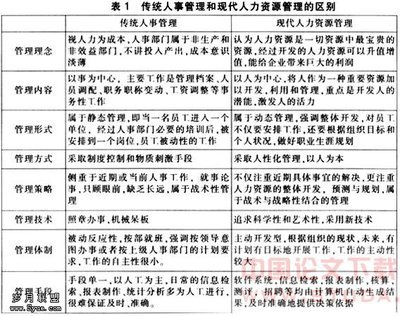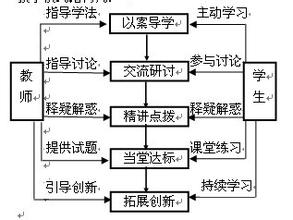伟大并不惜毁灭
——沈浩波诗歌模式初探
概述:《命令让我沉默》是他第一本正式流通,并集大全的诗集。我称之为“凝聚的写作”和“淬火的诗歌”。这是因为他已经从向外的沸扬转向向内的凝聚,挤出所有的水分,让烧红的铁淬火,让诗歌变得冷静坚硬并更加尖锐,在漫不经心中突然让你一剑封喉。而诗歌的刃尖一直朝向心灵朝向真相朝向忙着生忙着死的草根大众生存的核心,他随时挑开生活的帷幕,他是时代的揭盖者;他随时让心尖的淤血滴出,他是灵魂的守护者;他抻长了诗歌的边界,他是诗歌写作的拓荒者;他就是沈浩波,一个一直把诗意种进聋聩之中的大智慧的傻子!
以上是去年沈浩波诗集出版时,我写的一个简短感言。因为我从中看到了他的变化,也看到了经过火花四溅、四处出击后的沈浩波已经找到了方向,也找到了最得心应手的那把剑。如果用金庸老先生笔下的剑客独孤求败代表不同时期武功的剑来比喻,刚出道的沈浩波用的是独孤求败的第一把剑,剑名我忘了,反正是凌厉刚猛,无坚不摧”,且青光闪闪,锋芒毕露;诗坛对他的争议和非议基本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他的心狠手辣他的口语尤其是“下半身”,使他成了诗歌传统者的眼中钉。这本诗集依然削铁如泥,但刺眼的浮光不见了。诗歌越来越往核心凝聚,结实而饱满,像烧红的铁经过冷水的淬火,更加坚硬锋利,且出奇的冷挺。这是独孤求败武功的第三层境界(共四层),就是第三把剑,曰玄铁剑,重达七八十斤,剑锋已钝,曰“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是四十岁前所用。这非常适宜沈浩波此时的写作,就是尽弃花招,不求锋刃,而是朴实无华中的稳准狠,沉实有力,只一下就割下毒瘤。他的诗歌越是草根越喜欢,越是大众越觉得过瘾。他的贡献是把诗歌五彩的气球捅破,让我们看到人生干瘪的真相;他的超出诗歌教义书上的写作方式,让诗歌的疆域扩大了;他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没被驯化的孩子那样,用诗歌告诉大家灿烂并不存在,真相很残酷,而且美丽的人性中有我们看不见的黑暗。让那些伪善者说谎者沮丧,也让淤在心里的血和情畅通起来。
其实沈浩波只是一个对诗歌写作的痴迷者,“走火入魔”之后,像神父把道一直布进听不见看不见的人心中,他把诗歌也操练到聋聩的地步。他是单纯的诗人,也是一个不喑世事的傻子。即便如此,他的诗歌与原始教义也不矛盾,譬如诗言志,譬如兴比赋,在他的诗歌里都有。争议的焦点是他不像传统诗歌那样看见了花朵就喊美,而且夸张到满世界都是花海,满世界人的内心都是美。他也看见了花,但同时也看见了花的下面有个虫子,不仅是虫子还很可能是条蛇。于是他和他的诗歌让人感觉不舒服,甚至别扭和反感。所以他的诗歌为诗歌正统者不容的还不是怎么写,而是写了什么,前者是方法,后者是思想。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冷硬冷静冷酷成了沈浩波诗歌的标签,虽然近期的写作融入了温暖,但诗歌土匪和强盗之名号已经传遍江湖。下面笔者就从时遇、哲学基础、个人心理模式三个方面探究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样式的诗歌,为什么是沈浩波而不是别人选择这种模式写作。
引爆: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如果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沈浩波肯定不会这么写诗,也想不起来这样写。那时候的诗人大部分还是端坐在写字台前,对词语反复的磨练和淘洗,冥思苦想咬牙切齿非要把诗歌弄得神乎其神,诗人也变得神经兮兮了。那时诗歌是绝对上半身,是圣言是圣女,拒绝红尘不食人间烟火。而且大家都这么仰视着,朝着一个方向。这是那个时代的诗歌政治。齐刷刷一个脸孔写作的背后,是中国几千年历代尊崇的“权出于一孔”的宗法制度即宗族文化的顺延,这不仅造成了政治上的专制,也造成了文化和审美上的集权,就是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族长或领袖一个人决定一个时代的走向和模式。这样的文化中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消失了。但是到了本世纪初,几代人的革命已经有了成效,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化,自由意志代替了宗权意志,大一统碎成无数的碎片,宗族权力转变成自己的事自己做主。这是很多志士拼死也没挣来的自主权,千年后已经有了可能。所以沈浩波适时而生:我不听你的教导了,我个人怎么舒服怎么来。诗歌彻底地走下神坛,崇高走向平凡,诗人不再视宗权为神,而且有权质疑。虚假伪善都给我滚开,我要真实和真相。所以在沈浩波的诗里,首先是拒绝乌托邦,把伪装扒下来,甚至把皮肤也给扒下来,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于是他的诗歌成了飞镖和炸弹,他专盯人性的黑点和盲点,还有冠冕堂皇包裹着的獠牙和罪恶。心灵与表达零距离了,也宜心宜情了,却不合“诗”宜了。如这首《自我出生以来》:自我出生以来/没有见过一个诚实的人/每个人都在对着空气/校对口型/自我出生以来/没有见过一个有尊严的人/我们熟知所有事物的价格/脸皮和灵魂/不过是枕头和枕头芯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永远抱着一觉到天明/自我出生以来/没有见过一个干净的人/在污泥中奔跑/也有骏马的心/自我出生以来/没有见过一个好人/我们互相指责/如同骗子抓住小偷/自我出生以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一个都没有/站着撒尿的姿态/令人看着/都为之心酸”。
这确实有点极端。但是真相就是这么残酷。从中我们看到了诗人的真诚和真率,还有血性和铁锤与斧头。审美类型上显然与明媒正派的诗歌不一样。那些追求美和秩序的诗歌最终总是主观地营造一个意境,一个虚拟的高于生活,但寄托着理想和愿望的境界,这个境界是高尚的美好的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为了这个无法实现的境界,人们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九死一生百折不挠。这美好的境界就是诗人们精神上的乌托邦。沈浩波的诗歌显然是对这种传统诗学的背叛,他不但拒绝乌托邦,并质疑它揭穿它。他上下求索的是——真。所以沈浩波诗歌的视角是向下的,一直向下,像探测仪,一定要找到生活和人类生存的根和真相。所以他诗歌的终极不是美好的虚拟的意境,而是真理。真理必无美,也与愉悦无关甚至不是善,但是只要真,只要是生活本来的样子,他就要把灵魂扒出来给人看。一个诗人担起了哲学家的职责,对世界和生活的种种现象发出诘问,包括权威经书语录,甚至上帝。他的质疑很普遍很深,从乡下到都市,从往事到现在,从感性到理性,从皮肉到灵魂。即使是亲情他也不盲从,也是在质疑和理清是与非之后再选择,这让他的爱很理性,也更深刻更科学更牢固。
所以读沈浩波诗歌特别过瘾:“一个秃驴/眼放贼光/身穿僧衣/坐头等舱(《时代的咒语》)”。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短诗,犹如高明的剑客,漫不经心之间,手起刀落,干净利索,却让人目瞪口呆。这也说明哲学家靠理性来推论出真,诗人则是用直觉闪电一样洞穿本质,揪出灵魂。所以沈浩波的诗歌直接简洁,而且准确迅捷。这就让他的写作方法上也拒绝象征,拒绝修辞。他把语言当剑,啪啪几下挑开外衣,让真相显露。他用的是扒光法,轻灵随意,口语化。没有了修辞上枝枝蔓蔓的阻碍,拔剑出手就更干脆利索,从这个角度来说,沈浩波更像一个游侠,游走在人间,遇到非人性的事与物,便扬眉剑出鞘,或随时赐之以飞镖和子弹。
但是真相有时是复杂的,犹如人性深处的幽暗,看不清却感觉有钝器在撞击,让人心疼而难过。譬如《她叫左慧》、《下岗女工》还有给那些腐败人群按摩的少女等等。轻松下笔,冷静观照,但是疼痛像摁不住的岩浆,直接刺伤了我们的良知。最著名的当然是那首网络上流传的《玛丽的爱情》(限于篇幅例句略),一个美丽优雅有教养的女孩,不但勤奋地给老板挣钱,还陪老板睡觉,这一切只是因为相信老板这个骗子爱情的谎言。这首诗因残酷的真相而让我们心疼且发堵,欲说无语。此诗含量很大,文体的边界也模糊了,广度和厚度上像一篇小说,像一个融无数爆炸力而浓缩的镭,轰炸面也非常之大。它把你心被拎起来,一直飞到空中,再啪地摔在地上,让你看到命运的真相。
此时沈浩波的诗歌不繁华不炫目,但朴实平淡中却力若千钧。诗歌有了深度宽度和高度,同时也说明没了羁绊的口语最有力量。所以对沈浩波诗歌的争论不是因为口语,甚至不是下半身,而是他诗中的快刃和锋芒,他的爱谁谁,他的火力之猛和一个都不放过并诛之的态度。这也是这个时代造就的他的诗歌之剑。说到底,他的这些诗歌就是药品,他是用他的作品来给迷茫的世界和病态的人生医病,所以他的诗歌具有启蒙的功效,他是通过揭穿谎言和表现人性的丑陋来医治有了病菌的人类,通过人类之殇,让人类从彻骨的痛中涅磐。

支撑:哲学基座上的感性蹦迪
蹦迪是人体的自动起落,但基础和支撑点是蹦床。那么弹起沈浩波诗歌的蹦床是什么呢?让我们顺着他的诗学思想找找他写作的哲学基础,也就是理论支撑点。
柏拉图、康德、弗洛伊德、海格德尔,对生存着的“此在”都是悲观的态度,虚幻、断片、焦虑、烦等等。叔本华更是把人生比喻成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同时他认为摆脱这种状态的药方是到艺术的千变万化中去寻求解脱。这无疑把艺术就看成一种意淫。但有一个人却与他们相反,提倡越是痛苦萎靡颓废越要来劲,越要高扬生命的旗帜。这个人就是尼采。沈浩波对权威的否定与对生命力的强悍态度恰好与这位哲学上的强盗契合。尼采喊出了上帝死了,他认为此在颓废的原因,是因为个体生命力的疲软和枯竭,还有理性、形而上学、道德、基督教这些人为的精神鸦片。他说:“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颓废的形式”,“语言到处都病了”。他认为五光十色的外表掩盖了人内在生命力的匮乏,造成社会一方面极度空虚无力,一方面又在故作奢华与自命不凡。于是尼采从生命本体论出发,以强力意志去唤醒人的积极乐观,让人像酒神那样沉醉于生命,用生命力的强劲来对抗颓废和虚无的此在,从而实现人生的审美化和艺术化。
我把这视为沈浩波诗歌的理论根源和原动力。不管是他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的巧合,都说明沈浩波的写作不是胡来,而是有强大的哲学靠山做引擎。首先沈浩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相信自己是自己的救世主,幸福来源于自己的流汗流血,而不是所谓的上帝,他认为上帝从不现身,“我不会去信”,哪怕因此而被认为是邪恶的虫豸了,等待的是“布鲁诺的绞刑架/和脚底升腾的大火”,那么在今天仍然要为自由意志而准备牺牲。这是一种坚挺的人生态度,更是酒神精神。所以他不要那些虚幻的东西,为此隐忍地“用一把刮刀/捅进自己的内心/让那些如气球般膨胀的部分干瘪下去”。再好的肥皂泡对人都是无用的,活着必须像蚯蚓一样坚韧,像打夯一样脚踏实地。所以尽管他的生活像换频道,节奏快得如被人追杀,他依然没有一点倦怠和颓废。譬如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先是对不长记性的员工咆哮,接着对签约的女作家温情款款,五六个电话后才想起:“此去机场/飞赴海南/是要参加一个诗会/赶紧把内心的频道/使劲一掰/硬生生地/从生意/掰到诗歌/嘎嘣一声/心惊肉跳”。
这劲健豪迈的人生态度让他像一匹狼,在都市里不屈不挠,凶猛无畏,这其实就是尼采强力意志的外化。这样的态度反应到诗歌里,诗歌的脊椎强健如钢柱。而且是一种俯瞰的姿态,像鹰击长空,宽阔自由。用司空图的诗品来形容就是:“荒荒油云,寥寥长风”,翻译过来就是雄健的诗风像苍茫滚动的飞云,像浩荡翻腾的长风。譬如沈浩波有首《都市宠物》,写一个假正经假正义的假人,在电视各种栏目中流窜,时而尖叫,时而大笑,时而打扮成摇滚青年,时而变成名流;一会义愤填膺,一会热泪盈眶:“……这个胖宝贝,在谈到某个/令人悲伤的,社会话题时,伸出硅胶制成的假手/抹抹已经通红的眼睛,我不禁为他叫好,大声喊:/再用力憋一下,再用力憋一下,再用点力//眼泪就出来了。只见假人的脸上,眼泪/哗地就出来了,我笑得都快喘不过气来。/我的肥胖宝贝,塑料心脏里,装了几百个/暗格抽屉,他喜欢,和自由知识分子谈论民主;/和左派知识分子,讨论底层;和诗人,讨论精神;/和艺术青年,讨论电影;和女人,讨论金钱;/和商人,讨论政治和中式家具。我曾经见过他/不停翻弄心脏里的那些小抽屉,哗啦哗啦,/打开,关闭,打开,关闭,一分钟,能换七八个/所有与他交谈的人,如遇知音,敞开心扉///这个假东西,他迷上了做一个人类。与时俱进。/二十年前,他爱睡出生在六十年代的女人;十年前,/他爱睡,出生在七十年代的女人,五年前,他爱睡/出生在八十年代的女人……每当我想起,那些条真阴道,/被一个假鸡巴,一顿乱捣,就笑得,直不起腰。”
这个都市宠物我们一点不生,生活中衣冠楚楚下的禽兽太多了。这里再解释等于累赘。这首诗证明了沈浩波写诗犹如铸剑,一针见血一触见底。这其中的揭了皮又剜出肉的批判精神和咣咣金属之声,让诗歌真如淬了火的刀剑硬朗而有生命力。有人会认为有些语言有点黄,但我觉得很过瘾,非这样的脏话无以有这样的力度和杀伤力。其实我们的诗歌比小说落后多了。莫言里这样写能得诺贝尔奖,诗歌里蜻蜓点水一下就是反动就是淫秽就是大逆不道。而且这脏话是自然表达时自动迸溅出来的,是恰到好处,像《菜根谭》说的“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这让我想起朱光潜的关于诗歌的起源说,他说诗歌起源于谜、谑和文字游戏。其中的谑就是说笑话,反讽和自嘲。沈浩波诗歌主要表达形式就是反讽,这正好应和了朱先生的观点。这也是沈浩波诗歌文本上的理论支撑。
需要指出的是,浩波的诗歌如坦克的链条,很难把它弄断,像上面这首《都市宠物》就是。这是因为他的诗歌中有一股气,这气在外是气势,在内是元气。而这些诗歌他是一气呵成的。这也是一种强力意志和酒神精神以及丰盈的生命力的体现。随着呼吸的轻重缓急,他的诗歌也随之跌宕起伏,或奔腾呼啸或飞流直下。这气就是激情,激情让诗歌流速很快,并像滔天巨浪,一浪逼着一浪,直到海天人都奔涌成一线苍茫。典型如《离岛情诗之伤离别》。这说明沈浩波的元气底气中气很足,一直成连绵之气。我们找一首比较短的为例:《外婆去世》:“外婆去世了/故乡的亲人/在一场瓢泼大雨中/为她送葬/送葬的路说长不长/用去了我三十年的时光/我花了整整三十年工夫/才把童年时认识的那些老人/一一送进坟地//一个都不剩了/战火/逃亡/饥饿/批斗/贫穷/他们的一生从未幸福/连死亡/也被烧成骨灰//再花三十年工夫/为现在的老人/我的父母们送葬//他们从出生开始/就被剥夺了灵魂/在谎言中长大在空洞中衰老”。这是呼出的一口冷气。但是冷中有暖,暖中有大爱,是诗人在用完整的心去触摸这个残缺的世界。这也是尼采精神的外显,这冷而清醒且挺拔的诗歌品质,让艺术在强大的生命动力推动下成为了“苦难的救星”,诚如尼采说的:“生命通过艺术成为自救”。沈浩波自救的方式就是呼大师蓬勃之气,为诗歌补钙注钢。
原型:向记忆即生活的元点寻根
写到这有个问题,就是产生这样的诗歌虽然有时代和哲学做土壤,但是为什么是沈浩波这样写,而不是别人?
文艺心理学认为任何一个作家都有一个创作胚胎,就是原型,一切由此发韧,一切从此开始。那么沈浩波的创作原型是什么,又是怎么形成的?让我们顺着他的诗歌作品往回漫溯,回到他记忆中,打捞一下他的少年时期的生活,这是他人格形成的前史,从中可以发现形成他心理模式的因缘。在浩波诗歌中写家族和少年时期生活的作品比比皆是,尤其是长诗《蝴蝶》,本身就是一个散页似的自传、家族史和心灵史。
让我们首先看看他眼中的父亲和母亲的形象:“上帝为女人发明了一万种荡妇的姿态/没有一种属于我的母亲/上帝为男人发明了一万种小丑的姿态/每一种都属于我的父亲”。显然是在扬母抑父。这与感情没关,也可能是写作的策略。但用心理学的角度解析,就是父亲在他的记忆起点是黑色的,或者说曾经伤害过他,以至于他的潜意识保留并巩固了这个印象。再看《父亲》中的一段“……你有/一双横断的手掌呼啸的耳光落在妻子和儿子脸上你有/天生的大嗓门母亲躲在角落里垂泪而你旁若无人你有/一双劣质皮鞋的双脚愤怒地踢向我的胫骨/父亲你揍我因为我在课桌上写字/但是你不能折断刚刚给我买回的圆珠笔那是我的第一支圆珠笔/是你给我买的/父亲你揍我因为我写作业字迹潦草/但是你不能让我下跪在门口的水泥地上让所有人看到/我血管里的血都快喷出来了但是我不能说/父亲你揍我因为你喝酒的时候吹牛而我小声咕哝了一句/但你不能永远在酒桌上当着那么多人吹牛所有人/都知道那不是真的都知道我的父亲在吹牛……”
父亲修理儿子很普遍。但是像他这样记住每一个细节,并能完好地情景还原,显然这记忆一直在刺激着他。同时父亲的暴戾带给浩波的震动和伤害,也永久地包裹在记忆里,这形成了他的记忆胚胎,在创作上叫原始意象,也就是性格原型。父亲的暴力和专制让他心里有了阴影,看世界就多了一份冷和暗,这冷暗凝固在他的记忆原型里,并衍生出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冷暗是一种态度,自我保护就是不屈和抗争。这种情绪像油漆一遍遍一层层在心里刷着,就形成了一个人的潜意识,而潜意识就像看不见得锁链,牵引着你的思维想象幻觉和情感的走向。这是一种力量,有外国学者称之为原始力能学,相当于灵气、体力、魔力、繁殖力、甚至上帝等等。从写作上来说这就是创造力。也是一个人最初的体验,即开始的起点的体验。写作就是把记忆复现,就是把体验形象化。从这个角度来说,体验就是诗。浩波在父亲那里获得是愤怒和不服不屈,这像炸药储藏在他的记忆里,等待未来写作时爆发。
再看《蝴蝶》中的另一段:“初恋的小情侣/转回城里上学/直到我读高中/来到她所在的小城/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等着与她重逢//终于等到她的消息/送信的是她的好友/站在教室门口/等着我出来/城里的女生/扬着漂亮的脖子/白色的裙裾/像童话里的公主/在她面前/我招供似的/嗫嚅着说了几句/转身落荒而逃//来自乡村的学生/衣服太长/裹在比这公主矮半头的/瘦小身躯上/显得那么可笑/回到座位上/脸依然通红/从此再无勇气/去和当年的女生见面//每天晚上恶狠狠地手淫/女主角换成/站在教室门口等我的/明媚得像初春阳光的公主”。
这是又一个打击,是自尊心的打击。这让他写作的胚胎里多了一份对自尊的敏感和捍卫,继而形成要申诉和改变的冲动。直接的结果就是:“曾经有过最黑暗的时光/没有任何人肯给我一丝光明/当我踉跄着将自个儿拔出/就发誓再也不做一个好孩子”。
父亲的暴力与自尊的损害,让他过早地有了悲伤体验、英雄体验、孤独体验和想象体验。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解释就是,当一个人的情感受阻,便会产生一种缺失性的体验(心理失衡),为了获得满足性体验(新的平衡),人就要找到新的力量来支撑倾斜的情感。这些体验被压缩成芯片。储藏在少年沈浩波的记忆里,当他后来找到了写诗这种摆脱压抑和孤独,获得灵魂的解放和自由的方式时,这些记忆就集体爆发了。所以沈浩波的诗歌大部分都是以凛然和决然的方式进入写作,而且精神非常集中,情感像蓄满了炸药的汽油桶,诗歌节奏也越来越快,直到把情感推向极致,然后让情感从高峰上砸下来,重重地砸在读者的心上。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记忆爆发时意义与技术的自动生成。
而另一方面,自尊损害带来的孤独意识让他经常沉湎于幻想,这开发了他的想象力,也决定了他的想象与众不同。这就让他诗歌中总是有出人意料的比喻,像他把云南上空的云比喻成新疆的羊肉一样肥腻,于是“我想捏一把/云的肥脊”。还有《秋风十八章》中:“高速路桥下的爬山虎/死死抱着夏天消逝的马腿/这个臭不要脸的小蹄子/不管秋风如何抽打/就是不肯变红”。这两个比喻在中国当代诗坛类似情景中绝无仅有,可以说沈浩波拉长了想象的边界。这是不是得益于少年时代情感的创伤呢?因为生活的门关上了,心灵就更加活跃,想象的世界也更加辽阔。
所以应了那句名言:精神创伤成就艺术创作。鲁迅和狄更斯都是这个定律上的典型事例。沈浩波也不例外,我们可以把沈浩波这些诗歌看成是他情感缺失和孤独意识催生的诗篇,是诗人在为倾斜的记忆寻找另一种形式的支撑点。虽然对他而言只是出于本能,但是原始的体验是看不见的基因,像导航仪导引着诗人写作的航向,并让他带着这种印记去体验万物,让他写着写着就不知不觉回到了生活的起点。所以沈浩波诗歌中总是揉进了那种挥之不去的少年体验,所以《蝴蝶》更像一个挽歌,再现着也祭奠着亲人的情感,和自己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这方面《蝴蝶》是一个非常广阔又厚重的诗篇,尤其是对爱的梳理和解剖,非常不留情面不留余地,即使是父亲母亲和一路淌来的血缘,也要把灵魂刨开给大家看。这种看见了残缺还坚定不移地爱着,让爱更彻骨并真实而丰满,如:“一生中的一顿饭/蹲在椅子上/光着膀子/吃煮得很烂的面条/使劲地喝面汤/一口气吃了三大碗/全身是汗/如被水洗/那叫一个美啊/从此之后//天下再无美食/那面是母亲做的”。
在母亲面前,铁石心肠也会变得像面条一样温软。何况沈浩波的冷硬只是他诗歌的皮囊,他最终要端给世界的还是爱和温暖。这就是沈浩波走不出的血缘情结,也是他诗歌永远要走去的方向。
结语:沈浩波不是一个笑容和蔼举止优雅,面面俱到的诗人,他有冲劲也有破绽,他一直在拒绝着僵化拒绝着世故,因为他知道成熟的玉米虽然圆润饱满但没了汁浆。这让我想起金庸的独孤求败的第四把剑:一柄已经朽烂的木剑,上书“四十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修,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无剑胜有剑!这肯定也是诗歌的最高境界,为此相信浩波会为此肝脑涂地,因为他心里铭记着尼采的话:我爱这样的人——他创造了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并因此而毁灭。
2014年5月1日据平日散记改于北京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