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看少女愁何在?
——浅析“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豳风·七月》是《诗经》农事诗的杰作, 对于其中颇具情韵的“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历来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从汉代到当代已有种种不同的解释。近现代学者在前人基础上又有了更多的申发,并加进了时代特点, 以致歧义纷呈。
最早对这句话作出解释的, 是汉代的毛亨和郑玄。《毛传》曰: “伤悲, 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 感其物化也。殆, 始。及,与也。豳公子躬率其民, 同时出同时归也。”[①]毛氏把“女悲”和“同归”看作不相关的两回事,这样的解释似不大确切。《郑笺》申明《毛传》并加以发挥道:“春, 女感阳气而思男;秋, 士感阴气而思女, 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 欲嫁焉。”[②]郑玄的解释可称为“感春而思嫁”说。清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分析了以上两种解释后说:“公子嫁不愆期, 故冀幸庶几与公子同时得嫁也。传言豳公之子躬率其民同出同归, 男女不谋, 情事未合, 不若笺义为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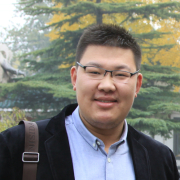
宋代兴起疑经废序思潮, 对于《诗经》的理解多从探求本义出发, 因而新意迭出。朱熹《诗集传》说: “公子,豳公子也。盖是时公子犹娶于国中, 而贵家大族联姻公室者, 亦无不力于蚕桑之事。故其许嫁之女, 预以将及公子同归,而远其父母为悲也。其风俗之原, 而上下之情交相忠爱如此。”[③]王贵民《中国礼俗》说:“古代嫁女之家思相离, 宋代有的地方始与哭嫁。”可见朱熹是以时俗解诗。
而清代的姚际恒在《诗经通论》认为:“公子, 豳公之子, 乃女公子也。此采桑之女在豳公之宫,将随女公子嫁为媵, 故治蚕以备衣装之用。而于采桑时忽然伤悲, 以其将与公子同于归也, 如此则诗之情境宛合。从来不得其解,且写小儿女无端哀怨, 最为神肖。或以为春女思男, 何其媟慢! 或以为悲远离父母, 又何其板腐哉! ”[④]姚际恒否定了郑玄和朱熹的说法,认为他们太淫秽或太陈腐, 引用孔颖达《毛诗正义》的“是诸侯之女称公子也”, 从而提出了“媵嫁说”。方玉润《诗经原始》与姚际恒针锋相对,他说: “‘采蘩祁祁’, 女子众多, 焉知其谁为许嫁, 而谁非许嫁人耶? ……岂举国采桑诸女尽为媵妾哉? 曰‘公子’者,诗人不过代拟一女心中之公子其人也。曰‘殆及’者, 或然而未必然之词也……此少女人人心中所有事,并不为亵, 亦非为僭。王政不外人情,非如后儒之拘滞而不通也……又何必沾沾辨其为男为女公子耶! ”[⑤]方玉润一一驳倒了姚际恒的观点,可谓通达、平实更本之人情。
新中国建立后,盛行阶级分析法,很多学者受此影响而认为当时为阶级对立非常鲜明的奴隶社会,女子伤悲是因为受到奴隶主的压迫和欺凌。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认为《七月》“反映了当时奴隶充满血泪的生活……使人想象到当时的劳动妇女,不仅以自己紧张的劳动为奴隶主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而且连身体也为奴隶主所占有, 任凭他们践踏和糟蹋”;[⑥]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解释为“采桑女心里伤悲,害怕自己被公子们掳去”[⑦];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⑧]解释为:“农村少女恐怕随时被贵族公子掳去,所以不免伤悲”;陈子展《诗经直解》[⑨]说得更为具体:“女子自知得为公子所占有, 恐为公子强暴侵凌而伤悲耳。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为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生产工作者,此生产工作者即奴隶主所当作牲畜买卖屠杀的奴隶。”……这种“以今解古”的历史研究方法我不是很赞同。
由“阶级对立”说衍生出“抢婚说”。”邹德文在《〈诗经·七月〉中“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平议》[⑩]一文结合周代习俗和文字的含义理解为“抢婚”。
还有的学者从更深层的文化学角度进行挖掘,指出这句诗与桑林社祭或高禖祭祀有关。赵雨《〈诗经〉与夏商周村社文化》[11]以为“少女对即将到来的桑林社祭的不安,且伤悲的词义还不完全和今天相同……此句所喻与周历四月仲春祭报之礼有关。桑林社祭日是集献祭歌舞和性活动于一体的宗教节日。这种性活动原是一种企图刺激土地繁殖的生殖巫术,交会后女子就被纳入贵族宫中”。而程保生《也说“女心伤悲, 殆及公子同归”》[12]认同赵雨的观点,认为“女心伤悲”有两层意思: 一是远离父母亲人之悲,二是对新家的惆怅、不安。夏德靠《〈豳风·七月〉“采蘩”考辨》通过考证得出“采蘩”与高禖之祭有关, 意为“祭高禖后,后妃悲伤地同豳公一同回去”。
我认为所谓“远离父母为悲”乃至于“哭嫁”说显得有些迂曲,是后人根据时俗推测出来的;而抢婚说无论如何不能成立它与美好的自然环境和全诗的主旨是如此的大相径庭,纯属后人臆测。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强调“ 阶级对立”,《七月》一诗是以“赋”的手法, 直接再现农民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其基调是豳人对其劳动生活和劳动本身的赞美。虽然有“无衣无褐”、“为公子裘”等诗句,但也不能断章取义地把整个诗篇理解为表现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和压迫。《七月》是周初豳地之诗,作为举行礼仪乐章的《七月》当然不会是暴露讽刺之作。按全诗内容来看,其主旨是表现了随季节之变化而进行劳动生产的公社农民的团结与和谐的活。《七月》不是诉苦诗, 也不是悲愤诗,它更多地表现了当时公社农民的生产劳动和日用饮食, 虽平淡却热闹,、简单也繁华,在粗放的劳作中有细腻情感的流露。整首诗的基调是清澈明朗、清新明快的, 而非凄苦哀怨的, 故阶级对立说同样说不通。
综上所言,还是离《诗经》时代最近的汉代学者的解释最为素朴、贴切。钱钟书先生说:“苟从毛、郑之解, 则吾国咏‘伤春’之词章者,莫古于斯。”[13]由此见之,对于就年代而言,毛亨、郑玄二人之言论,去古未远,而且作为汉代学者他们的注释严谨求实,对字词的解释基本可信。少女“感春而思嫁”更为接近诗意,所以我赞同毛亨、郑玄的观点。
[①]【汉】毛亨传、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
[②]【汉】郑玄笺、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
[③]【宋】朱熹:《诗集传》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排印本
[④]【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排印本
[⑤]【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上海:泰东图书局,1924年影印本
[⑥]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⑦]朱东润:《中国历史文学作品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⑧]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⑨]陈子展:《诗经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⑩]《佳木斯师专学报》,1994年4期
[11]《商丘师专学报》,1999年5期
[12]《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3期
[13]钱钟书:《管锥编·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