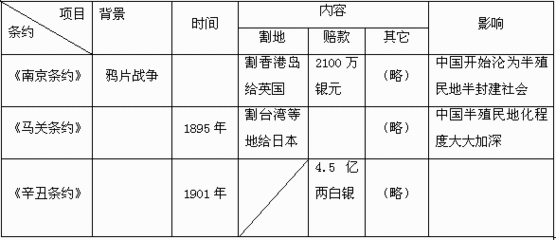1958年国防教育法与美国高校的非西方区域研究
吴原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美国高校非西方区域研究发展的黄金时代。美国高校的非西方区域研究能够飞速发展,与1958年国防教育法的实施是密不可分的。基于此,本文拟对国防教育法颁布的时代背景、出台的历史过程及其对区域研究的影响作一简单概述。
一、国防教育法颁布的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军事实力及国际政治影响力的膨胀,美国自诩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和守护者。为此,美国积极采取政治、军事、经济等措施遏制共产主义扩散,促使共产主义国家垮台。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并没有如美国政府所设想的那样趋于消亡。举例言之,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些政界人士预言:中国共产党上台执政只是短暂的现象,中共政权在美国的遏制之下将因经济困难、农民反抗,或国民党的反攻而被推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为:“孤立它,减少它对外部的影响,防备它,遏制它,威胁它,向它的领国提供援助,并不停地向它施加外部压力,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成为瞬息即逝的现象”;美国国务院情报司于1949年秋对新中国进行评估,其结论是:在未来五年之内中国新政权没有被推翻的希望。但是,内部困难和外部压力将使中共政权大大削弱,从而为其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1]对中国共产党有深刻了解的鲍大可(A.DoakBarnett)也对新中国政权的前途满腹狐疑,“共产党只是赢得权力斗争的胜利,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取得成功,真正的难题仍然横亘在共产党面前,而且他们面临的困难可能还在继续增加”[2]。然而,新中国的茁壮发展,使这些预言不攻自破。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新中国。1956年,美国《国家情报估计》(nationalintelligence estimate)认为:
中国共产党已经牢固的控制了中国大陆,正沿着苏联模式大规模重建经济、社会机构以及军事力量建设。在苏联的帮助下,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加强,并已有相当程度的现代化,经济产量已经超过以前的最高历史记录。它所取得的成就和不断增长的力量的后果是:共产主义中国在亚洲的声望和影响已经有极大上升[3]
1958年的美国国家情报评估更是明确指出:
在1958年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中共政权已经取得令人信服的成就,五年计划的目标实现或超过:GNP每年提升7%至8%;农村合作社、工业国有化以及贸易的目标都以较快速度实现。尽管在1956年和1957年,经济和政治遇到困难,但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政权的稳定性并不存在严重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已经牢牢的控制了中国,其政权在莫斯科集团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已得到承认,它在亚洲的地位大大加强。[4]
新中国没有如美国所预料的那样走向垮台,相反它在新兴国家中的影响却与日剧增。1957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代表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写道,“共产主义中国在非共产主义世界,尤其是在亚洲中的影响显著上升。中国共产主义已经在非共产主义的亚洲世界制造了这样一种印象:共产主义中国是一种永久的活力。”[5]
与此同时,民族解放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1951年,伊朗建立以穆罕默德·摩萨台为首的民族主义政府;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取得政权,次年废除君主制建立埃及共和国;1954年,法国在越南奠边府一战大败,被迫停止印支战争,签署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越南、老挝、柬埔寨获得独立。这一时期,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要求民主改革的国家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断涌现。截止到1955年,新独立的亚非国家达13个,该地区的独立国家总数增至30个[6]。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在欧洲局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之下,苏联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第三世界,积极利用各种机会扩大其在第三世界尤其是新独立国家中的影响。1954年1月,苏联同阿富汗签订“经援”协定,向阿富汗提供3500万美元贷款,这是苏联第一次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援”;1955年2月,苏联同印度签订第一个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1955年9月,苏联通过捷克向埃及出售一批价值2.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1955年11-12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表示将给三国以大量的经济“援助”;1956年7月,苏联同也门签订第一个“经援”协定,10月又开始向也门出售军火。[7]到1956年为止,苏联同亚洲和中东国家签订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协定已达14个之多。[8]在美国看来,苏联极力扩大其在新兴国家的影响,将使美国面临失去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和重要自然资源产地的危险,阻碍美国的全球称霸战略。罗斯托在评估20世纪50年代末的世界局势时曾忧心忡忡的指出:
在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欠发达地区,莫斯科力图通过以下方式扩张势力:即运用游击战、颠覆、贸易、援助等各种各样的手段;挑动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突出共产主义的形象,把它标榜为欠发达地区现代化的最有效的方法,标榜为正在迅速地从四面八方围住那懒洋洋地跑在前面的美国人的一种制度。……自由的事业看起来处于守势。[9]
面对急剧发展变化的国际环境,美国越来越感到不安与恐惧。这种不安与恐惧随着苏联成功地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进一步强化,并使之传递到普通民众。1957年10月4日,苏联将一颗水球大小的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号”一号送上了太空。相隔不久,苏联又于11月3日成功发射了比第一颗卫星几乎重7倍、轨道距离远一倍并载着一只小狗的“斯普特尼克”二号。为挽回颜面,美国于12月6日在卡纳维拉尔角也发射了一颗卫星,但却并未成功,美国朝野为之震惊。美国著名作家威廉·曼彻斯特描述道,“这件事引起的震惊之强烈,竟不亚于当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10]。绝大多数美国人“尝到了低人一等,甚至蒙受耻辱的滋味”[11]。《时代周刊》分析指出,“美国一向为自己科学技术上的能力和进步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走在别人前头,第一个取得成就感到自豪。可是,现在不管做出多少合理的解释,由于一颗红色的月亮使美国人黯然失色,终于突然间在全国出现了强烈的沮丧情绪”[12]。不仅如此,美国民众在沮丧和失落之同时,更多的是惶恐不安。波特兰《俄勒冈人报》评论说,“让苏联卫星在空中盯着我们,这实在太可怕了”。[13]
二、国防教育法出台的历史过程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之前,美国教育界关注的重点是职业教育以及如何引导学生适应现实生活,普遍不重视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及外语的教学。著名教育学家阿瑟·贝斯特(ArthurBestor)教授指出,“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基础知识是教育的根本。在学生日益增多的今天,学校关注的是职业培训和学生如何调整生活以适应社会。这种教育的部分后果在于引导学生更多的关注情感和个人问题。偏离基础学科的教育预示着这样一种日渐危险的事实:很大一部分的传统学科课程已不再开设。……从课程表中流失的课程要比其他领域更为令人印象深刻。外语看起来似乎是流失最为严重的。”[14]著名学者亨利·里斯顿(HenryWriston)同样认为,“令人奇怪的是,(在美国高校)有限的数学教学,甚至英语教学居然被认为是‘困难’的科目。他们被称之为‘使人困惑的死结’,如果坚持原有标准……将使学生离开学校,这是人们所不希望看到的。对于外语的学习更是被严重的蔑视。”[15]由于美国教育界不重视外语教学,以致在1950年代美国外交部门所组织的一次外语能力测试中,几千名应试者中仅有一小部分人通过这场难度系数一般的语言测试。[16]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国际环境的极剧变化,尤其是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美国感到其全球霸主地位面临严峻挑战,他们开始关注教育。《生活》杂志刊载评论指出,“人造卫星把这个长期被忽略的全国性问题变成了人们意识到的危机。”[17]一位知名的学院院长注意到,“我们社会过去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看重教育的作用”。[18]在关注的同时,社会各界对美国教育体系所存在的缺陷进行反思。参议员富布赖特批评道,“我们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已涉及到我国社会根本。它涉及到我们的教育制度,这是我们的知识和文化价值来源。在这方面政府的学术复兴计划目光短浅、令人不安”[19];著名学者欧内斯特·沃尔夫(ErnestM.Wolf)认为,如果美国不重视传统学科和外语的教学,“我们在结交朋友以及与外国结盟之时,将会遇到诸多困境”;更为重要的是,这将使美国在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时处于劣势,因为“苏联并不仅仅只是保证其工程技术人员比我们多。它所培养的语言学家同样比我们多”[20]。
为此,社会各界建议应对美国教育进行改革,重点是加大对基础学科及外语的教学和资助。参议员利斯特·希尔(ListerHill)认为,“40年前还只是一个农业国家的苏联,今天却开始挑战声称在将科学转化为技术这一领域处于超级地位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必须给予基础科学研究、教育、物理学、外语培训等领域更为雄厚而持续的资助”[21];教育专家阿瑟·贝斯特建议,“我们(美国)应该这样去教育年轻一代: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重视数学;加强历史课程教学以使增强学生们的历史意识,而不是肤浅且缺乏远见的讨论当前问题;引导年青人学习那些作为不朽精神遗产的经典文学及思想著作;强化中小学的外语教育”[22];著名数学家马歇尔·斯通(MarshallH.Stone)认为,当前的学校教育应加强有关传统学科以及诸如俄语、阿拉伯语、印度语、马来语、汉语等重要外语的教学[23]。
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美国参议院劳工与公共福利委员会于1958年1月举行“国防与自然科学及教育”的听证会,邀请来自公私机构的专家、学者、官员出席作证。这些出席作证的知名人物,就如何解决“来自敌对世界的全新而复杂的挑战”阐述各自的看法。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面对这一挑战美国必须加强现代外语教学和地区研究。1958年2月6日,主管卫生、教育和公共福利的马里恩·福尔瑟姆(MarionFolsom)作证时就认为,“在这个剧烈变动的世界,现代外语提供了一种改善交流的方式和手段。对于国家而言,外语能力是增进国际理解和友谊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对于外交官而言,这种能力意味着在国外能够通过非正式的私人间外交以及各种政府活动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福尔瑟姆进而指出,在美国的外交官中仅有四分之一的人精通一门外语;不仅如此,世界四分之三人口所说的语言几乎没有出现在美国教学中,“就非西方语言能力而言,美国是世界上最为落后的大国。”为此,他建议设立众多小型的特别训练中心,以加强对“那些极少被讲授但却具有重要政治和经济意义的语言”的教育[24]。教育委员会委员劳伦斯·德西克(LawrenceG.Derthick)在作证时特别指出,超过一半的公立中学没有开设任何一门外语课程。在他看来,外语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重视外语教学。他论述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由于在语言能力方面的毫无准备而不得不花费巨大代价去培训各种语言人才,我们需要采取措施以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今天,美国政府对美国公民外语能力的关注反映了语言对于国家利益而言处于最为优先的地位,尤其是在处理与非西方文化国家的关系之时。[25]

美国国会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也于1958年4月1日专门就“外语教学及其在外交关系中的作用问题”举行听证会。在出席听证会的专家学者中,大多数人同样呼吁加强外语和地区研究。美国现代语言联合会主席肯尼思·米尔登伯格(KennethMildenberger)第一个出席作证。他指出,“绝大多数美国大专院校仍没有将全球百分之七十二人口他们所说的语言列入其外语教学课程中。东南亚地区新兴国家的语言更是不为人所知。”然而,“美国如果真正要承担起作为一个世界领导者的责任,就必须拥有大量不仅精通外语而且愿意虚心学习外语的公民”[26]。罗伯特·罗尔斯(RobertRolles)将军回顾了二战期间由于美国对全球历史及现实的忽视而使其军事和政治领导受到的不利影响。同时,他还联系到当前的情况指出,“苏联人正在有预谋的学习外语,他们通过学习语言以深入理解他们准备与之交往国家的心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正在赢得冷战的胜利。”[27]
听证会之后,国会参众两院于1958年8月就国防教育法案展开激烈辩论。部分议员认为,联邦政府援助美国高校将产生诸如对自由主义教育的破坏、教育失衡、巨额财政负担等问题。举例言之,众议员威尔·尼尔(WillNeal)就认为,“这一法案将使国家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破产国家”[28];众议员约翰·比默(John Beamer)亦认为:
我们尝试采用苏联的教育体系来与苏联竞争,这使我非常担忧。对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而言,他们的体系是非常有效的。我确信,如果我们准备突出强调自然科学而削弱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那么我们将使我们的民主处于非常危险之中。[29]
然而,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苏联的挑战,更多的议员赞成通过这样一部法案。众议员施托伊弗桑特·温赖特(StuyvesantWainwright)指出,170名在阿拉伯国家工作的美国外交官中仅有5位精通阿拉伯语,苏联却有300名精通阿拉伯语的外交官,“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30]。众议员詹姆斯·罗斯福(JamesRoosevelt)详细阐述缺乏外语能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当我们必须使用翻译才能与外国民众打交道时,我们经常遭遇到严重的误解,有时甚至完全是阴谋诡计。由于不懂得他们的语言,我们经常被认为是殖民主义而被人所憎恨……。因此,我们不得不迫使他们用我们的语言进行交流。苏联人懂得他们的语言,因此他们不需要这样。”[31]众议员爱德华·博兰(EdwardBoland)认为,“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公司机构都急需大量培训小语种的院校机构和能够说俄语、阿拉伯语、汉语、日语、越南语和其他语言的人。”[32]参议员利斯特·希尔(ListerHill)则郑重指出,“在海外的部分外交官缺乏语言能力,一直以来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主要障碍。由于这种缺乏,我们的外交官不能谋求私人间的友谊。实际上,这种私人间的交往在诸如外交事务、为我们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友谊等许多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建立语言和地区研究中心,“尤其是有关非洲、中东、亚洲和苏联的语言和地区研究中心”[33]。参议员戈登·阿洛特(GordonAllott)同样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用他们的语言进行交流,便可以使他们理解我们的动机和目的;同时,我们可以对中东、远东和非洲等地区的思想和观念产生更大影响。”[34]
出于美国全球称霸战略的现实需要,1958年8月26日美国国会在经过激烈辩论之后最终以212票赞成、85票反对、131票弃权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当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案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热烈欢迎。他认为,“在今天,外语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美国肩负着领导自由世界的重任。然而,大多数美国人缺乏外语知识,尤其是亚洲、非洲和中东那些新成立国家的语言。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而言,我们必须克服这一缺陷。”[35]因此,一个星期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法令,国防教育法案正式生效。
三、非西方区域研究的兴盛发展
如上所述,为在冷战中压倒竞争对手苏联,夺取巩固世界霸主地位,外语教学和地区研究成为美国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众议员罗伯特·伯德(RobertByrd)对此给予了具体而生动的说明:
今天,苏联的导弹和火箭正对着我们……美国正面对着精明而又毫无道德的敌人――苏联,这是一个在无神论者领导下的,具有侵占整个世界野心的、残忍的、极富侵略性的、不达目标誓不罢体的国家。现在我们应该意识到,共产主义者正在竭力向我们发动战争;我们已经身陷于一场巨大而又重要的战斗之中,如果我们想继续生存下去……美国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对于知识的态度,尤其是对外语及区域研究的蔑视。[36]
很显然,加强对外语教学和非西方地区研究的资助成为国防教育法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国防教育法的第六章,专门详述了联邦政府在加强外语教学和非西方区域研究方面所应采取的措施。国防教育法第六章第601款规定,“1958年7月1日至1962年6月30日期间,授权联邦政府通过合同协商方式资助高等教育机构建立现代外语教学研究中心。联邦政府资助建立的现代外语教学研究中心,必须是联邦政府、公司企业或美国社会所急需的语言。任何一所现代外语教学研究中心,除提供语言教学之外,必须提供有关这门语言所使用地区或国家的历史、政治学、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教学,以使学员能全面理解使用这门语言的地区或国家。现代外语研究教学中心还应为到国外地区从事研究工作的成员或到研究中心从事教学研究的外国学者提供资助。”国防教育法第六章第603款规定:为语言和地区研究中心开展上述工作所提供的财政资助每年度不超过8000000美元。国防教育法第六章第611款就加强中小学外语教学作出规定:到1959年6月30日为止,这一财政年度应拨款7250000美元,且应连续拨款三个财政年度,以保证高等教育机构能够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指导性教材,对那些正在从事或准备从事中小学现代外语教学或管理人提供高级培训。每一位参加培训的人员,在培训期间将有资格获得每星期75美元的补助金;其家属也将获得每人每星期15美元的补助。[37]
随着国防教育法的实施,联邦政府每年向美国大专院校注入数额不菲的资金以资助其开展外语教学和非西方区域研究。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行的报告书,联邦政府在1959年至1964年期间共拨款8555660美元用于美国各大学语言和区域研究中心的设立及其教学。[38]在国防教育法的引导之下,美国社会各界走出麦卡锡主义的阴影,积极资助美国高校的非西方语言教学及区域研究。例如,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曾遭受政治责难和打击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古根海姆基金会等私人基金会,受国防教育法案的影响开始踊跃资助非西方语言及区域研究。卡内基基金在1959至1970年期间,总计提供了170多万美元用于资助中国社会研究、建立香港大学服务中心、在中学开设汉语教学、以及培训在东亚工作的记者等。[39]福特基金会在国防教育法案通过后不久,便于1959年2月制定了一项长期支持非西方研究的计划,即在全国为著名大学非西方地区研究能力的发展提供长期的机制建设资助,拟在今后两三年时间里为大约19所大学提供至少2000万美元的十年资助款。1959年6月,福特基金会董事会批准了这项旨在使非西方研究在获得资助的美国大学中从此永远成为它们整体教育中一个卓有成效的组成部分的计划。基于此项计划,1960-1962年,福特基金会为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西北大学等15所大学提供了十年期和5年期的用于非西方研究的资助款2650万美元[40]。据统计,在1959年至1966年期间,福特基金会用于资助美国大学开展地区研究的资金总额超过了2亿7千万美元[41]。长期以来将开展远东研究视为是“奢侈的事情”的美国高校[42],自国防教育法颁布实施后亦特别重视非西方语言教学及区域研究。在1958年至1970年期间,美国各大学自身对中国研究的拨款额达到1500万美元左右。[43]
由于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及美国高校大批资金的投入,众多知名大学如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先后建立了非西方语言和区域研究中心。据统计,截止到1964年,由联邦政府资助成立的专门从事非西方语言教学及区域研究的中心达57个。[44]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又有59所大学设立了非西方区域研究中心,从而使得非西方区域研究中心达到106个之多。[45]
在资助非西方区域研究中心建立之同时,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美国高校等还积极为攻读非西方语言及区域研究博士学位的学生提供资助。在1959年至1970年期间,联邦政府通过国防教育法共为攻读非西方语言和区域研究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提供了1796份奖学金,其中有600份提供给了攻读中国研究博士学位的研究生。[46]得益于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的资助,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培养了一大批非西方语言和区域研究方面的人才。在这一时期,获得拉丁美洲研究博士学位的人数为1299名、获得苏联和东欧研究博士学位的人数为610名,获得南亚和东南亚研究博士学位的人数为435名。[47]
与此同时,学习非西方语言的学生人数也日渐增多。在1958年,只有14名学生学习南亚语言。十年后,学习南亚语言的学生人数增加到350名;同一时期学习东亚语言的学生人数则从1500人增长到了10000名。[48]除此之外,有关非西方语言及区域研究方面的著作、图书资料建设、中小学的外语教学、师资培训、教材编撰等在这一时期也有了巨大发展。以中国研究的著作为例,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据统计,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在1955年至1965年期间出版了中国研究著作37部;[49]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在1960年至1970年资助出版了200部研究现当代中国的著作。[50]
总之,自1958年之后,美国的非西方语言及区域研究进入“起飞阶段”。美国非西方语言及区域研究的发展,很显然得益于国防教育法的实施。担任亚洲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O.Hucker)曾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亚洲研究的发展……最为重要的还是得益于国防教育法的推动”[51];有关的评论也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尤其应“归功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对中国研究领域的资金投入以及国防教育法的实施”。[52]不言而喻,国防教育法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非西方语言和区域研究发展的最大外在推动力。
参考文献:
[1]资中筠著:《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P223
[2]A Doak Barnett,Communist china:the earlyyears,1949-1955, Pall Mall Press,1964.P25
[3]National intelligenceestimate,Washington,March19,1957,communist chinathrough196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states,1955-1957,VolumIII,P231
[4]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washingtonFebruary10,1959,Present trends in communist china.FRUS1958-1960Volume XIX,china,P520
[5]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fo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state Washington January14,1957,FRUS1955-1957,VolumIII,china,P498
[6]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P277
[7]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讲义》,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印行1982年,P110
[8]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六卷上》,人民出版社 2002,P191
[9](美)雷迅马著,牛可译:《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P44
[10][11][12][13][19](美)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译:《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1979年,P1105、1108、1109
[14][22]Arthur Bestor,“Education really needed for a changingworld,”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27,No.1,1957,P5、8
[15][16]Henry M.Wriston,“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interest,”Foreign affairs35,No.4,1957,P572、577
[17]Robert A.Divine,The Sputnik Challenge,New 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3,P159
[18] Barbara Barksdale Clowse,Brainpower for the cold war:theSputnik crisis an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1958,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81,P8
[20]Ernest M.Wolf,“Foreign Languages in American education,”The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27,No.9,1956,P488
[21][24][25][35]U.S.Senate Committee on labor and publicwelfare,Science and Education for nation defense:hearings beforethe committee on labor and public welfare,85thcong.,2nd sess,21 January1958,P2、193、341、342、197
[23]Marshall H.Stone,“What universities can contribute to theconduct of foreign affairs.”The Journal of highereducation28,No.5,1957,P369
[26][27]Wernher Von Brau,Director,Development operationsdivision,Army Ballistic Missile Agency,in House Subcommittee of the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Labor,Scholarship and loanprogram:hearings on H.R.10381,H.R.10278(and similar bills)relatingto educational programs,85th cong,2ndsess,1958,P1816、1837
[28][29][30][31][32][33][34][36]U.S.Congress.Congressionalrecord,85th cong,2nd sess.,1958,104,pt.13:16574、16688、16582、16692、16693、16702、17234、17246、16744
[37]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Publiclaw85-864,September2,1958
[38]US State Department:Language and area study programs inamerican universities,Washington D.C:1964 And US.StateDepartment:Language and area centers,First 5Years.Washington,D.C:1964
[39][43][46][47]Lindbeck,John.M.H.. Understanding china:an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resources,P79、10、48、62
[40]韩铁著:《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P139-142
[41]Theodore Vestal,International education:its history andpromise for today.Westport,CT:Praeger,1994,P137
[42]Meribeth E. Cameron.FarEaster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arEastern Quarterly, Vol. 7, No. 2, Feb., 1948,P117
[44][52]A.T.Steele.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McGraw hill book company,1966, p191、183
[45]Richard W.Wilson.Chinese studies in crisis. worldpolitics,January1971,P315
[48]Ainslie T.Embree, The tradition of mission—asian studiesin the united states ,1783 and 198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1 February 1983
[49](美)费正清著,陆惠勤、陈祖怀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P437
[50]George E Taylor,Special report:the joint committee oncontemporary china,1959-1969. Asian studies professionalreview,vol1,no1,Fall1971,P59
[51]Charles O.Huke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aninterpretative history.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press,1973,P43-44
原载《海外中国学评论》第2辑,2007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