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与朱元思书》
孙绍振
原文不长,节略如下: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欲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吴均(469~520),和郦道元(约470—527)差不多生活在同时代,在文学史上,都属于“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的时期,但是,文章的风格和郦道元却相反。郦道元的句法和章法完全是散体,而这篇《与朱元思书》则是骈体,这是因为郦道元生活在北朝,其文质朴;而吴均则在南朝,为骈体散文代表。吴均又是官方文人,其主要作品,不论是诗还是散文,均为骈体风格。骈的原意是两马并驾,故有并列、对偶之意。这种文体,相对于“散体”而言,除了特别讲究对偶之外,还讲究声律、典故和词藻。如他的《橘赋》,为了阅读方便起见,我们将对仗的句子,分行分组排列:
增枝之木,既称英於绿地;
金衣之果,亦委体於玉盘。
见云梦之千树,
笑江陵之十兰。
叶叶之云,共琉璃而并碧;
枝枝之日,与金轮而共丹。
若乃秋夜初露,
长郊欲素,
风齐寒而北来,
雁衔霜而南渡。
方散藻於年深,
遂凝贞於冬暮。
这里对仗的密度是相当高的(只有“若乃”二字没有对仗)应该说,作者驾驭文字的工夫是很到家的。汉魏以来,中国文人逐渐发现了方块汉字和汉语句式的对称美,在此基础上,创造了特殊的诗体和文体,很快被广泛地接受,到了齐梁时期,蔚为风气。流风所及,这种手段,就难免被滥用起来,好事就变成了坏事,创造就变成了规格,乃至成为思想感情的桎梏,在艺术上也变得单调。前面所引这篇骈体散文,对仗手法为集中使用优美的词语提供了方便,使原来空间和时间上距离遥远的、甚至毫不相关的语汇在对称的结构中系统地统一起来,造成一种有机的感觉。像:
称英於绿地
委体於玉盘
使颜色和质地上本是不相干的“绿地”和“玉盘”,由于对称的结构而形成一体。又如“云梦”和“江陵”,本来空间距离甚大,但由于对仗,就很自然地形成统一的结构。以下如“共琉璃而并碧”、“与金轮而共丹”,本来八杆子打不着的意象(琉璃、金轮),在这里有了统一感。“风齐寒而北来,雁衔霜而南渡”,两句季节上的相关性倒是很强的,都讲的是秋天的景象,但是,在空间方位(南北)二者上的距离是很遥远的,由于对仗的效果,距离感消失代之以整体感。对汉字的驾驭达到如此精致,这不但是吴均的水准,也是当时文学水准。这种工夫和技巧,是世界性的独创。正是因为这样,它在中国文学文体和诗体的发展中,表现出生命力。例如,在律诗中当中两联对仗的规定,在后代散文,甚至当代某些散文家的文章中,仍然作为一种手法,有增加文采之效,如徐迟的《黄山记》中就有:
高峰下临深谷,幽谷傍依天柱。
当然,这只是偶尔一见的笔法,当代作家显然是回避集中地使用。因为集中,就可能显得堆砌,显得单调,而且可能为对仗而对仗,把一句可以说完的话,分成对仗的两句。吴均的这篇文章中,就有这样的毛病,例如:
方散藻於年深,遂凝贞於冬暮。
说的本来就是一回事,年深就是冬暮,在时间上没有对仗所特有的概括功能,反面显得不精炼,很罗嗦。过多的地使用对仗,还有一个毛病,那就是耽于对仗技巧,而忽略了情志的独特和活跃。在这一篇中,我们能够感觉到的,就是橘树的叶子、果实的颜色、质地,在南方北方,春天秋天冬天,都是美好、贵重的。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作者的感情在对它的赞美中,被束缚得紧紧的,作者的想象,不能自由的张扬。正是因为这样,同样是吴均的创作,这一篇就没有什么名声。《梁书·吴均传》说他“文体清拔有古气”,在当时颇有影响,时称“吴均体”。所谓“有古气”,就是有古文的韵味。先秦诸子的散体文章,是不讲对仗、典故和声律,也不讲究字句整齐的。
吴均最有名的,也就是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章,不是这样的文章,而是《与施从事书》《与顾章书》和《与朱元思书》。为什么呢?先来看看《与施从事书》:
故鄣县东三十五里有青山,绝壁干天,孤峰入汉。绿嶂百重,青川万转。归飞之鸟,千翼竞来;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为霜,春梦被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信足荡累颐物,悟衷散赏。
这里也充满了对仗,其中“绝壁干天,孤峰入汉(银河),绿嶂百重,青川万转。”还是名句,这样的对仗,充分利用了对称的结构功能,把视野抬高,天高地濶,仰望银河,俯视百川,提供了一幅宏大的景观,同时也反衬出了作者心胸的博大,因而并没有过分淹没了作者的精神境界,特别是加上了《诗经·郑风》里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句子,在色彩、声音上、光线上又有了对比,就更加显示出了作者情绪的复杂:“信足荡累颐物,悟衷散赏。”信足,的确,确实。荡累,消除烦恼。颐物,留连物态以怡情养性。悟衷,启发性情。散赏,随意欣赏。这就给人一种从世俗事务中解脱出来的感受。所以,这一篇就列入他的代表作。但是并不是最高的代表,因为这里多多少少还是有拘于对仗,情志受到束缚的痕迹。如“归飞之鸟,千翼竞来;企水之猿,百臂相接”,未免给以玩弄文字技巧过甚之感,不像前面的“绝壁干天,孤峰入汉。绿嶂百重,青川万转”显得有气魄。至于“秋露为霜,春罗被径”有什么特点呢?秋天有露,有霜,春天有藤罗,对读者的想象没有多少提示性,因而显得空泛,纯粹是为了对仗而硬生生用技巧来凑句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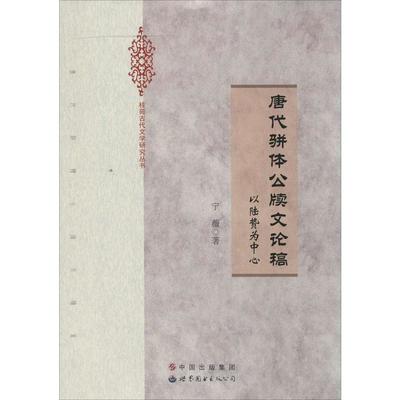
另外一篇《与顾章书》,就比这一篇略强一点了:
仆去月谢病,还觅薜萝。梅溪之西,有石门山者。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幽岫含云,深溪蓄翠。蝉吟鹤唳,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华,偏饶竹实。山谷所资,於斯已办,仁智所乐,岂徒语哉!
全文共二十个小型句子,只有“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幽岫含云,深溪蓄翠。蝉吟鹤唳,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和“幸富菊华,偏饶竹实”,一共十个句组单位,是对仗的,也就是说,其中有一半是不对仗的散句。明显可以看出,作者的情致,比前面一篇要自由、活跃一些。这是因为,对仗在齐梁时代被过多地用来作自然景观描绘,而散句,则往往用来叙事和抒情感慨。而在这里,有一半的句子,是表现作者的情绪的,因而就比较活泼了。这也就是“文体清拔有古气”的表现。清拔,就是不太沉郁。而沉郁,则是说长期郁积的情绪。但是,形容性的意象,密度很大,不但限于视觉,而且是静态的、平面性地展开,这正是对仗的弱点。超越了这个弱点,在用了一连串对仗的描绘以后,转而进入抒发情感,
山谷所资,於斯已办,仁智所乐,岂徒语哉!
虽然语言相当朴素,没有什么夸张的形容,但是作者的性灵的特点,还是能够得到表现。如果严格地要求,似乎写到性情的时候,缺少了一点什么。主要是“山谷所资,於斯已办,仁智所乐,岂徒语哉”这样的议论,有一点平淡,苛刻一点说,有点贫乏。和华彩的对仗丰富,似乎不太相称,情感有一点被压抑住了的感觉。
而到了《与朱元思书》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句法是骈杂交织的,而其中的骈句、对仗并不严格:“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飘荡”和“东西”在词义上并不完全对称,“飘荡”是同类的,而“东西”是相反的)。特别是,这样的对仗句,不像一般的骈体对仗句那样(如前述之“称英於绿地”,“委体於玉盘”)词藻华丽,而是以平常词语出之。风烟、天山、净、色,都极普通的词汇。“风烟”中的“烟”,在散文、诗歌等艺术作品中,和日常语言中的所指是不一样的。这个烟,如果是日常生活中的烟火,就没有艺术感觉意了。“风烟”不是风中之烟,也不是风吹着烟。这里的烟,是雾(如唐王勃:“江上风烟积,山幽云雾多”),而且是薄雾(黄庭坚“明月风烟如梦寐,平生亲旧隔湖湘。”)在中国古典诗文中,烟雨、烟云、烟霞、烟柳中的“烟”,常常是薄而淡的雾。风烟,就是风中淡而轻的雾。淡而轻的雾,轻淡得好像风在其中流动没有痕迹,加上“俱净”的“净”,就是干净、洁净、明净,有透明的意思。虽然风烟就是淡雾,但我们不能把风烟改成“风雾”。因为“风烟”的微妙联想比较丰富,有轻,有淡,有明,有净,有在江南平原上一望无垠的感觉。这种感觉,和“天山共色”联系在一起,就更加突出了。雾淡到、轻到、明到、净到什么程度呢?天和山没有分别。天是蔚蓝的,山应该是更深的,但是在空气中的雾气的笼罩之下,变得没有区别了。这就是一种透明的效果,但又不是绝对透明,绝对透明,山的颜色还是要深过天空的。这样就构成一种天宇之间,无不明净的感觉。
文章的好处还在于,这种明净之感,不仅在天宇之间,而且和大地的景观特点有着内在联系,达到高度统一的境界:
水皆漂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
首先是颜色,和天与山的颜色是统一的。其次是水的特点,是透明的,透明到千丈见底的程度,和空气的明净,互相映衬。而这个映衬景色,并不像一般骈体文句那样,全用对仗句法,而是散体句法。这就不但构成了一种上下天光,明净无垠的和谐背景,而且显示了骈散交织的自然意趣。这个背景,呈现着一种宁静的氛围。如果下面的描绘仍然一味宁静下去,也可能构成一种极静的意境,但是作者没有作这样的选择,而是选择了相反的特点:“急湍甚箭,猛浪若奔。”这就使得水的美感丰富起来了,不但有静态的千丈见底的透明的美,而且有奔腾的美。虽然奔腾的水并不透明,但有另一种动人心魄之处。
接着写到树木和山石。二者本来是静止的,作者却不写其静态之美,而是从静态中看出了动态。他笔下的寒树:
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
这里的关键词是“负势”、“争高”,都是拟人的暗喻,所表现的就不是一般的动态,而是在压力下、在竞争中崛起的动态。
中国古典山水游记,写山水之动态者不胜枚举,但是大都集中在山水本身(如郦道元的《三峡》)。赋于静态的树木和山石以动态,使之有拟人的灵性者,可能是比较后出的。吴均的这篇文章,应该是比较早的。在这以前,我们只能从左思的《蜀都赋》中看到:
山阜相属,含溪怀谷;岗峦纠纷,触石吐云。
“属”、“怀”、“纠纷”、“触”、“吐”虽然是拟人的动词,然而的所形容的基本上仍然是静态的山、石、云、溪的关联,基本上还是静态的。“吐”字,有一点氤氲之态,仍然是靜中之动。但是到了吴均笔下,山石就活跃了起来,而且有了一种意气相争的意味,这在自然景观人文化的程度上,性质上,进展是很明显的。这一点似乎很能得到后世文人的欣赏和发挥,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写到山石,是这样的:
其石之突兀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熊之登于山。
这种对于大自然的观照方式,不一定是受到吴均的直接影响,但是,“负土而出”的“负”字,和“争为奇状”的“争”字,应该和吴均的“‘负’势竞上”,“‘争’高直指”属于同一传统。
吴均的这以动显静的自然美,与上文的静态是相对的。而接下来的描写,并没有继续把动与静作重复的对比,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把视觉的动态转化为听觉的喧响:
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
汉语中同样一个“静”字,可以向两个方面分化:视觉的静止,是与动态相对的;听觉的宁静,是与喧响相对的。这样的山水景观,就不仅仅有了画图的美,而且有了音乐的美。在这样视听交响之中,作者的思绪达到了高潮:
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
这是从心理效果上强调眼前景观的“天下独绝”。鸢,是一种黑色的猛禽,鸢飞戾天,典出《诗经·大雅》:“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比喻为功名利禄而高攀,这是从心理效果。景色的美好,居然使得追求世俗名利(包括“经纶世务者”)的人,心灵沉静下来,沉醉到大自然之中,忘却世俗的牵挂。这应该是主题所在了。文章到此,可谓卒章显志。但是作者还没有满足,又来了一个句组:
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这不这多余的吗?但这是表现作者在激发了自己情致的高峰体验以后,并没有向理性升华,因而也没有转移对于自然景观的迷恋,仍然一如既往地沉醉在美好多变的景色的之中。对于文章来说,这是结束感,但是对于欣赏(包括作者和读者)者来说,这是欣赏的持续。于结束处,不是嘎然而止,而是使结束感和持续构成一种张力,是这最后几句的妙处。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