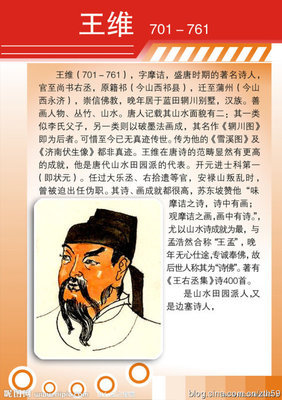《姜片》延续了王芫对于微妙与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探索。当描写社会转变过程中,都市女性遇到的两难处境时,王芫的笔锋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姜片》的主人公是一个南下淘金的北京女人。《姜片》的戏剧则是围绕着几个人之间的心理操控战而展开的。这个微观世界里,不乏机会主义者的计算、资本的交换、阶级的冲突与权力的斗争。而凡此种种,都是更广义的中国社会大舞台上永不停演的戏码。
故事的叙事者“我”(琳达)是个女公关——一个在中国非常有弹性的职位。她从北京来到海南——南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验场。那时的海南,由于远离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比较灵活,因而头脑灵活的人能抓住机会迅速致富。生活层面上,海南则以性交易著名。作为一个女公关,琳达的老板不仅期望她向客人敬酒,还希望她向客人提供更为“私密”的陪伴服务,虽然他从来也没有明确表示过这一点。琳达对自己的位置,则一直有着自欺欺人的幻想,直到一个多事的傍晚,一位姓陈的“石油大王”走进故事,她才见识到了商业世界的严酷现实,权力、性与金钱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当琳达的老板图穷匕首现的时候,琳达感到屈辱,尽管她完全不应该感到意外。
在《姜片》的世界中,商场的竞争,更像是男性比拼骄傲的竞争。在这场斗争中,男性的操控力与手段,女性的美丽与青春,都成为了硬通货与稀有商品。于是,一些女性就会免不了这样思考问题:作为商品的女性,又该如何在一个男性中心的、商业化的社会里生存,如何运用她们的“资本”来获得利益并维护自身的尊严呢?显然,这样的思考本身就已经将思考者关进了囚笼。而在《姜片》中的三分之二篇幅中,主人公琳达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试图为自己解围的。她认为,这个又矮又瘦的陈先生,除了钱什么也没有,只配得上夜总会的小姐露西。
于是,这个故事就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故事中的女性,为了实现她们自己的目的,也并不反对利用其它女性。琳达使用三陪小姐露西来使自己解套,琳达的自我辩解成为小说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幕。“想到这里,我又对露西生出了歉疚。这种歉疚一时压得我抬不起头来。但我又是个不肯认错的人,哪怕是对着自己的内心。我转念一想:我又没强迫她,她作什么,完全是自愿。况且她既以此为业,我给她介绍客户,难道不是帮她?”
但事实上,露西自有保护自己的方式,比如不停地嚼姜片,以阻止男人强吻。最终,琳达意识到,其实露西比自己拥有更多的智慧,更知道如何在这个丑陋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小说因此抓住了当代中国年青女性面临的那种微妙的两难处境、变幻莫测的人际关系,以及前进路上神出鬼没的障碍。小说对琳达醉酒状态的描写,似乎是对当下社会中人人身不由已的一种形象概括。在整个社会的堕落和不稳定状态下,似乎没有一个人能站稳自己的道德立场,谁都免不了要从一个道德高度上掉下来。“直到今天早晨,当我坐在办公室里的时候,我还能清楚地描述出那种感觉。那是一种周围的一切都在和你作对的感觉:当你想向前迈步的时候,你觉得有一种力量阻碍着你,当你想原地不动时,却又有一种力量推动着你,让你无法站立。”
有一些女性作家,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源于两性之间与生俱来的冲突,王芫则不同,她认为两性矛盾只是复杂人性冲突的一部分,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她小说中的规定情境则从来不是黑白分明的,不可以简单归因于性别模型。尽管《姜片》描述了一个机会主义的,金钱至上的,男性中心的世界。但在这样的世界里,王芫仍然看到了男性人物身上的复杂人性。琳达的老板关经理,尽管满心希望能把琳达献给陈先生,但内心深处仍然会偶尔感到内疚,最后一半是出于骄傲,一半是出于残存的道德意识,他决定放弃这笔交易。
当代中国小说不乏控诉与揭露,但控诉与揭露同时也容易流于道德主义的说教。像《姜片》这样,以反讽的文字再现复杂的人间百态,于中国当代小说中,是一种不多见的品质。在一个叙事层面上,通过琳达的观察,我们看到自负的暴发户陈先生拒绝承认(或者假装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征服女性上的失败;在另一个叙事层面上,怀疑的聚光灯照在琳达身上:她的道德优越感是脆弱的,她对其它出场人物的误读是简单化的。最后,老关对“北京女人”的酸溜溜的评价,以及露西出人意料的内心披露,都动摇了琳达心中既有的观念。大卫·洛奇(DavidLodge)认为,这种“存在于现实处境与人物对现实处境的理解之间的落差”,正是小说中典型的“戏剧性讽刺(dramaticirony)”。在王芫小说中,这种“戏剧性讽刺”源于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层以及各阶层之间的隔膜。人们必须挣扎着理解自己的新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改变后的人际关系,而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指引他们的只有奄奄一息且错漏百出的本能。
这种“戏剧性讽刺”在本书的最后一篇故事《北京女人》(原题《北京人》)中具有更强烈的针砭时弊的功能。在此,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将小说原题《北京人》改为《北京女人》。这样做的原因,是这本集子里的故事重点在于讲女性的生存。然而改成《北京女人》后,却又可能失去原题目所能够带来的丰富联想。故我在这里特别分析一下原题目《北京人》的隐含意义。
首先,“北京人”这个说法不可避免地令人联想到考古学上的“北京人”,这显示了小说在人类学意义上解剖人性的企图。其次,它令人联想到中国著名当代作家曹禺(1910-1996)的话剧《北京人》。该剧是二十世纪早期的一部杰作,描写了一个亦学亦官的家庭在当代中国即将破晓之时的挣扎与衰落。而在王芫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一种新型的人际冲突;第三,该题目又将我们指向一部名为《北京人》的口述历史著作。作家张辛欣和社会历史学家桑晔由1980年代初开始对一百多位普通人进行了采访,后将采访结果于1986年结集出版,名为《北京人》。自然,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也是王芫关注的焦点。
然而,我相信绝大多数普通读者看到这个题目后,最直接的联想则与地域有关:“北京人”就是拥有北京户口的人。他们住在首都——中央政府所在地,拥有得天独厚的特权与机会。他们享有最好的教育资源,又有一种智识上的优越感,于是在气质上便有些居高临下。当然,这种概括有些模式化。但我相信所有曾在中国居住过的人,多少都会遭遇过这种基于地域的模式化认知的洗礼。比如说,上海人通常会让人联想起有教养、时髦等都会气质,温州人则普遍被认为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冒险精神。同时,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会被相应地妖魔化:比如,北京人会被认为喜欢说大话、吹牛不着边际;上海人势利、崇洋媚外;举凡国际市场上的假货,一律产自温州。
《北京人》的主人公是一个叫林百惠的北京女人。作为一个教师出身的餐馆老板,林百惠和王芫笔下其它的女性形象一样,在经营企业和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过程中,游移在过分自信与困惑之间。在一个风云变幻的社会里,她一面暴露着自己的“傲慢与偏见”,一面被迫寻求新的身份与心理平衡。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的经验和道德信念变得无关紧要。她面临的问题都是全新的:不仅要跟各色官僚打交道(从无利不起早的小企业局,到街道居委会,到公安局),还要从头开始训练、管理一群来自乡村的十几岁女孩子。他们朝气蓬勃,但对城市生活缺乏认识,对她们的训练要从如何说、做、站等细枝末节开始。
林百惠和其它大多数北京人一样,对于文明标准的判断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她时常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试图纠正外来妹们的口音。她声明这并非是出于歧视。她教的只是“普通话”,而不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文明化”的象征。而她的雇员则毫不费力就看穿了她,并且经常质疑她在企业管理上的才能。她的经理,一个聪明的四川小伙子,暗示说她的优势其实就是一个北京人,这种身份使她能免于外地人通常会面临的系统性的歧视。这位聪明的小伙子,自己曾经开过几家餐馆,但都失败了。他从未质疑过自己的经营才能,而是把一切归咎于自己的外省人身份。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林百惠的镜像。
社会结构的严格,既影响到人们的物质存在,又影响到语言、文化术语,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人们的心态。众所周知,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十分严格的,绝大多数人在出生时,就承袭了父母的户口身份,此后一生中都很少有机会改变。1949年以来,中国的户口制度隔绝了城市和乡村,成为一种虽然极不公正,但却行之有效的管制手段。除了物理上的限制之外,它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心理和人际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从事城市人不愿做的工作。但政府并不准备给外来人口以永久居住的权利,因为这将给城市的社会服务增加负担。为应对管理难题,政府采取了发放暂住证的办法。而实际操作中,为餐厅员工办理暂住证的责任通常都会落到老板身上。而老板又经常以暂住证为筹码,加重对员工的剥削。

对《北京女人》中林百惠这个人物的理解,特别是她身上的优越感和自以为是的腔调,必须放在这个背景中去了解。她可以以执行政府规定的名义去实现个人的目的,而政策的朝令夕改可以成为她不遵守诺言的借口。这些外来的劳动力成为林百惠降低经营成本至关重要的因素,但她并不把他们当作有血有肉的个体。她不惜牺牲一个年青女陔的精神健康,去与当地政府官员交换自己的利益。而对于外来妹兴丽、二丽和他们的父亲来说,他们手中并无筹码,为了留在北京,只能任由老板剥削。毕竟留在北京还能挣钱养家,一旦回到农村,他们就会陷入失业的困境。
虽然户口政策的不公平,不是林百惠的力量所能改变的,但在故事结尾,林百惠从兴丽的眼神读到的变化,仍然引发了她内心的愧疚反应:“兴丽的眼神把林百惠吓了一跳,这是什么样的目光啊?林百惠早就不思考了,变了个头脑简单的人,她的语言能力也就随之退化。她无法描述兴丽的目光给她带来的震憾,她只觉得很不舒服。那目光把一层长久以来罩在她眼前的迷雾刺穿了,直达她内心深处。”这个一直在梦游似地表演动作的“北京女人”,到了小说结尾,终究还是被唤醒了。
王芫耐心地用她的四篇故事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了人类的困境:这是一群在道德上不完美的人,也是一群挣扎着不欲进一步堕落的人;这是一群脆弱的人,也是一群有韧性的人;这是一群能随机应变的人,也是偶尔会露出残酷本性的人。这些人犯下了错误,他们的错误与社会制度的不公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多少有关,但同时也与人类的普遍弱点,如贪婪、虚荣等密切相关。以一种可以与伟大作家比肩的态度,王芫用有技巧的叙事、反讽的语言、冷静和精确的观察,从事着文学创作。读她的小说,我们仿佛在一组全新的复杂的灯光装置下,看到一群普通中国人,在出演一幕接一幕的道德戏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