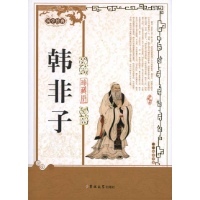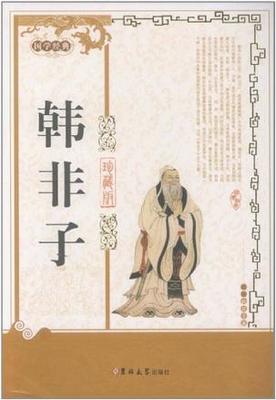49·11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解说】
1、上一节是从公私的对立关系,讲到不能把人们引导到“修行义而习文学”的道路上去,主旨意思是:喜欢、重用“修行义”的游侠剑客和“习文学”的儒生,那是治理不好国家的。由于一般都认为前者是“贤者”,后者是智者,所以本节就进而指出:况且当今所谓的智者,只是会说一些深奥难懂的理论,那不能用来治国,也不是民众的追求;所谓贤者,其特点不过是诚实无欺,但那不是君主所需要的。——开头三句是用来承上启下的。前两句似乎主谓不搭配:“贤者”、“智者”是人,怎么分别成了“行”和“言”?我的体认是:这里,“贞信之行”等于“行为贞信之人”,“微妙之言”等于“言说微妙之人”。接着是评论这两种人,为了紧承“上智”句,就先评“智者”了。
2、从“今为众人法”起,到“非民务也”为止,全是申明不可用智者(实为儒生)的“微妙之言”来治国,理由讲得不够明确,但无疑可归结为:因为他们的理论不能为民众了解,而且只能用来指导处理长远的问题,不能靠它解决当前的困难。——要注意的是:①开头的“则”字句,前半句(前件)是说,如果制定要求民众遵守的法规,却采用具有极高智慧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话语来表达的话:“法”字用作动词了,“立法”的意思;“上智之所难知”只是个定语,中心语省略了;后半句中的“识”字是记住义。②接下用“故”、“夫”领起的几句,我以为前一“故”字同“夫”字错位,因为“糟糠”句明显不是上文的推论,而“夫”字领出的意思又明显是从上句意思得到的启发。“粱肉”必是泛指精美的饭菜,“短褐”是粗布短衣。③“夫妇”在这里不是夫妻义,而是“村夫俗妇”的压缩,用以泛指下层民众。
3、从“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起,直到结尾,是对“贤者”的评论:首先指出他们(即游侠剑客)的基本特征是“不欺”,继而交代他们形成这个品性的原因,最后据以论证说,这品性对于君主来说并无意义,因为君主本人无人敢欺,明君治下是“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以致官员无从行其奸诈。——这部分要注意:①“若夫”相当于“至于”;“贤良贞信之行者”是指人,亦即“贤者”。②“必将”的“必”字是借作“毕”(同于《诡使》篇第5节中的“必”字),“将”是表示推测,可译作“大概”。③“亦无不欺之术”的“亦”字相当于“皆”(《左传·成公二年》:“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④“富厚”是联合结构(故可同“威势”对言),即“厚”也是“财富”义(《韩非子·有度》:“毁国之厚,以利其家。)⑤“相与交”的“相”是“相互”的意思,但“相利”、“相惧”的“相”是表示“一方对另一方有所作为”。⑥“有一国之厚”的“一”是全、满的意思(“一身的汗”这说法中的“一”)。⑦“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句是说:能够运用他掌握的政权去处置“法律之光”照到的一切问题。这里,“柄”指权柄,亦即政权;“修”是整治、办理义;“术”指法律(《商君书·算地》:“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其中“术”字就是指法律、法令。)这样解读此句,后句才能有所承接:君主如此,故再能干的奸臣也不敢欺他了。⑧“田常”、“子罕”分别是齐国、宋国的两个敢于弑君夺位,并且成功了的“能臣”,前面的“有”字是词头,没有意义。⑨“故明主之道”以后的几句是整个这一节的结语:“智”和“信”都语带双关:既指“智者”和“贤者”其人,也指智和信这两种品性;“一”和“固”,都用作及物动词了:“一”是统一义(从空间上说),“固”是稳定义(从时间上说);“法”、“术”是同义词;“败”是“败坏”的“败”。
【辨析】
1、对本节头句的“主谓不搭配”问题,注家们的处理同我不一样:都把主语理解为“贤”与“知”,而非“贤者”、“智者”其人,于是将那两句翻译为:“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指的是忠贞诚信的行为;所谓的智,指的是那些深奥微妙的言辞。”(刘译)我觉得按这理解,就不好解释“者”字的用法了,加之后文论说的明明是“贤者”、“智者”,所以没有采用。——对接下评论“智者”的话,注家们的理解还有以下“共同的误处”:①把两个作连词的“今”字,错解为时间状语,译作“现在”。②未看出“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句的作用与含义,又不知“识”字是记住义,以致将“则”字句翻译为:“现在把智慧极高的人都难以懂得的(深奥)微妙之言,作为民众的行为规范,民众当然无法了解它。”(《校注》的注释和陈著的译文)③未能体认到“民间之事”乃是前面说的“政(事)”的“明确语”,加之误把“今”字理解为“现在”了,对该句的误解就更大,译文也难得通顺了,例如刘译:“现在用来治国的政治措施,那些民间习以为常的事理,或是普通男女都明白易知的道理都一概不用,却去好慕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这种做法跟正确的治国之道是违反的。”
2、后一部分,注家们对几个“难句”的理解,错得更为严重,但“说来话长”,我就不征引了,只指出几个“不该发生的误处”:几乎一律将“亦无不欺之术”的“亦”字理解为“也”;将“相利”、“相惧”的“相”也译作“相互”;将“一国之厚”译作“一个国家的财富”;将“一法”理解为“专一地用法”;将“固术”理解为“坚定地用术”——还有:“虽有田常、子罕之臣”句中的“有”字是词头,竟照搬到了译文中。说明一句:这既使我惊讶,也让我感到“似乎有理、可取”,因此,究竟是我错了还是他们错了,请读者细审之。
【译文】
况且当今所谓的贤者,是指其行为忠贞诚信的人;所谓的智者,是指其言说深奥玄妙的人,而深奥玄妙的言说,是具有极高智慧的人都难以理解的。制定要求民众遵守的法规,要是使用具有极高智慧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话语来表达,民众就没法记住它的内容了。一般说来,酒糟稻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急着谋求米饭和鱼肉的,粗布短衣都还穿不上的人,是不会迫切期望穿绣花衣服的;与此同理,进行社会治理,要是紧迫的事情尚未解决好,就不该急着去处理可以缓办的事情。所治理的如果是民间之事,连村夫俗妇都能明白的道理不予采用,却希求用“上智”都难懂得的深奥玄妙的理论作指导,那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就是背道而驰了。所以,深奥玄妙的言论不是民众所追求的。至于行为贤明善良忠贞诚信的人,他们一定都只看重诚实无欺之人,因为诚实无欺之人都没有不被欺骗的办法:平民百姓的互相交往,谁都没有财富来让对方获得物质利益,也没有威力权势使对方担惊害怕,所以他们一定要寻求诚实无欺之人与之交往。君主既然处于可以控制别人的有权有势的地位,又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既可给别人以很重的赏赐,也可给予严厉的惩罚,还能运用他掌握的政权去处置“法律之光”照到的一切问题,即使像田常、子罕那样奸诈的臣子,也不敢欺骗他,他哪里还要倚仗诚实无欺之人呢?要是忠贞诚信之人不超过十个,国内需要的官员却数以百计,还一定要任用忠贞诚信之人为官的话,合格官员的人选就供不应求了。合格官员供不应求,能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员就少,会把政事办糟糕的就多了。因此,明君圣主的办法是:统一用法律处理问题,不求助于所谓的智慧;稳定法律规范的内容,不寄希望于办事人的诚信。所以在明君圣主那里,法治不会遭到破坏,官吏们也无从施其奸。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