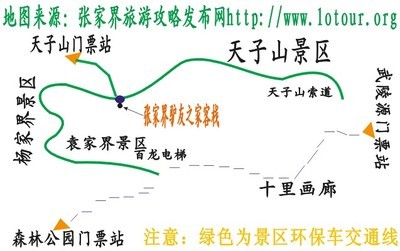TS-Radio《静夜听书香》第十五期:邱妙津的精神世界(20110618015):一个公认的天才,一个隐秘的同性恋者,26岁在巴黎用水果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死后,人们才发现她的身份,把她给前女友写的信收集起来,辑成《蒙马特遗书》。是怎样的爱让一个天才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主播音乐水果与我们一起了解台湾女同性恋作家邱妙津的精神世界。
邱妙津(1969年-1995年),台湾彰化县人。著名的女同性恋作家。她的著作影响台湾的同性恋文学相当深远。邱妙津的名字早已成为传奇,只要看过她的文字的人,莫不震撼与那强烈的情感与极度敏感的心灵。邱妙津是北一女中,国立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毕业。曾在张老师心理辅导中心担任辅导员,接着在新闻杂志社担任记者;同时她也尝接受半年电影导演课程训练,拍摄了三十分钟,十六厘米的电影《鬼的狂欢》。曾获得第一届中央日报短篇小说首奖,联合文学中篇小说推荐奖。着有小说集,《鬼的狂欢》、《寂寞的群众》、《鳄鱼手记》、《蒙马特遗书》。1994年出国就读于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第二阶段心理学系临床组。之后曾转入女性主义研究所。
《蒙马特遗书》
在“泰坦尼克”撞得大半个星球天昏地暗之前,台湾先已为一卷遗书引发了一场“地震”:一部名为《蒙马特遗书》的书信集,轰得整个岛屿发抖。——26岁女生邱妙津自杀前写于法国的数封信件,缘何会在台岛青年中激起如此深切的共鸣?这部以发现地蒙马特命名的《蒙马特遗书》,缘何能在出版后连登《中国时报·开卷》“一周好书榜”、《联合报·读书人》“每周新书金榜”,获得“96年金鼎奖优良图书推荐”,并最终摘取“《联合报·读书人》96年文学类最佳书奖”?轰动性图书常让人感叹“花期”短暂,这卷遗书又如何时至今日仍“余震”频频?……
日前来京的台湾著名作家兼学者、东海大学美术系教授蒋勋,就此接受了本报专访。当年,蒋勋正作为《联合报》评委亲自参与了“96年文学类最佳书奖”的评审全过程。谈起《蒙马特遗书》的初读感受,蒋勋第一句话就是:“这部书让我吓了一大跳”。
吓人一大跳的作者
这部书的作者先就要吓人一跳:邱妙津,女,研究生,一个公认的天才,拥有一张从台北第一女中到台大心理系的“阳光履历”;但她同时是一个同性恋者,这一重隐秘身份人们只有在她死后才从其日记里得知——这个双面女孩好像一茬不规则的刀锋:既不为正常社会所兼容,亦不能游刃于正常社会。
关于邱妙津的自杀,说法有很多。一个也许不是最关键但却起了点火作用的因素是感情困扰:邱妙津赴法继续心理学研修时,陷入了一场狂乱的三角恋爱。最后她选择了一种激烈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水果刀刺入胸口,“只有26岁,大二就能用法文读原典……这样一个女生,却说死就死”。邱妙津在巴黎自杀后,从附近的蒙马特地区,人们发现了她死前写给女友的信;逐一收集起来,辑成《蒙马特遗书》。
无法在白天启齿的话,邱妙津在遗书里披露无遗。“女性的情欲和肉体往往是男性描写的对象;我从没见过一个女性自己写自己的情欲与肉体写到这么细”,凭籍多年的阅读体验,蒋勋认为就“年轻人的情欲”这一面,《蒙马特遗书》实现了某种原创性书写。
但这种书写又与暴露性、展览式写作判然有别。蒋勋指出,《蒙马特遗书》不是对人类窥视癖的迎合或满足;而是向每一个阅读者开启“一个你完全不懂的领域”:对于这个领域,在看这本书之前人们的态度多半还是不屑、嘲笑或责难(惯性思维和传统标准早已成就无数的共识);但《蒙马特遗书》却会使读者从“真正进入的一刻”起突然被感动甚至于——“悲悯”。
绝对的“遗书式”写作
两类写作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不同?蒋勋认为根源在于不同的写作预设:如果说展览式写作更多是一种投合阅读、讨好市场的商业行为;《蒙马特遗书》则是一种设定死亡后的绝对写作,换句话说,“这是一部真正的‘遗书’”。
“只有当设定了自己的死亡之后,才会这样写”,在蒋勋看来,“死亡是解构的最大力量——惟有死亡能解脱‘生’的相对性”。从而这里所谓“遗书式”书写,并非指写作内容,而是强调作者在写作之始预设的死亡坐标:整部作品由此获得了一种终极意义并显示出一种绝对重量——读者也正是为这种“空前的重量”而悲悯。
为了说明这种写作的特质,蒋勋举出另一位和邱妙津相类的作者——同样要“吓人一跳”的法国作家惹内。当惹内还是一个孩子时,他因为讨厌制服而“逃”进黑社会;人生的定型期完全浸泡在反体制的环境里,长大后的惹内成了一名惯偷和男妓。他一次次的坐牢,一次次遭重判,判决又一次次累积,以至最后成为一名无期刑犯——惊人的是惹内竟以“无期刑犯”的身份开始了个人写作:写自己的故事,写监狱里男性间的情欲关系……这些作品大多散失狱中或被看守们毁掉;但有一部分却意外地传到了萨特手里。萨特读后惊为天人,作《圣者惹内》指出:惹内是在替所有主流文化“赎罪”;同时说明:这才是一种绝对的写作——而那些意图发表、预设别人评论的写作,其纯粹度往往要打折扣——在这个意义上,《蒙马特遗书》与“圣者自白”表现出相当的同质性。
台湾青年为什么因《蒙马特遗书》而发抖
从感性的个人生命体验反观《蒙马特遗书》,蒋勋的独特发现是该书中惊心动魄的死亡美学:邱妙津以她自己26岁的绝望,聚焦并凸显了普遍的青春期的向死意识。几乎每个人都或深或浅地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这样的感觉:在最灿烂的年华、在人生的巅峰状态下突然生发对“死”的空前强烈的体感、认同乃至——渴望!也许这就是很多台湾青年都要为《蒙马特遗书》而发抖的原因。
这无疑是一种“春寒”;但其冲击范围又远远漫过了青年。“我也经历过青春的死亡”,51岁的蒋勋感到,“一个年轻的蒋勋早已经死去——很多年前,和很多他那个年龄的朋友一起”。所以这原是整个人类的宿命。
从青春的向死意识中,蒋勋进一步提升出一种“青春期的死亡美学”——毕业于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数十年沉潜于书画创作和美术史研究的阅历,使蒋勋在作家的感觉之上,又始终贯通一种美学的趣味与眼光。蒋勋以为这种美学只要留心,便可以在古往今来的许多艺术作品中发现。比如西洋美术史上有一个贯穿性的形象组合:一个异常俊美的身体与一支致命的箭;几乎是一种对应,在汉字中有一个意为“花凋”的“谢”字——而它的另一个涵义是“感激”。从这个角度还可以解释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台湾青年中的流行:通过他的作品中总可以共鸣出一种向死的青春的美轮美奂;同样从这个角度回眸中国历史,蒋勋认为最美的一景是辛亥革命:年轻的秋瑾、邹容、陆皓东、林觉民们一一奉上“死”的热烈与“爱”的柔婉——蒋勋在诗集《来日方长》中有一首《致秋瑾与徐锡麟》,其中写道,“他们在人间/匆匆一次来去/就指点完了/江山”。也就是说,青春的死亡之所以美,在于她保持了一种绝对的完整,“正是借那个年轻时死去的蒋勋,我才达到了今天的完整”——因为任何一个状态的极至都是死亡,而死亡也就是开始,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这就是蒋勋眼中的《蒙马特遗书》。在最近于北大进行的小型交流会上,蒋勋对在座的文史哲系研究生讲,“如果要我向你们推荐一部书,那就是这一部”。
最后蒋勋还要提醒读者:看这部书时要有一种严肃的心情。不是休闲而是沉重。这是蒋勋当年的亲身经历,“我不能像通常一样躺着看下去,我必须坐起来”。
——转自《中华读书报》1998年5月6日
爱的证据
生命是不是一定要承受某种苦痛,才会往心底更深的地方挖掘,进而创作出值得探索生命的文学呢?而为什麼所有经典的伟大文学,总是潜藏某种程度的悲伤?若生命本质不够沉重,是不是就不会写出好的文学呢?
读完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之后,心底不断浮出这些疑问?
《蒙马特遗书》是邱妙津的最后一本书,与其说他是书,不如说是写给情人的二十封遗书来得比较贴切。她在创作完这本书没多久后就在巴黎自杀。当时她年仅26岁,却选择了很刚烈的方式结束生命。
许多创作者会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好像死亡也是他们是因为作品本身的价值,还是因为创作者自杀而更增添他作品本身的某种神秘色彩呢?
刚刚说过这是一本写给情人的二十封遗书,本书的内容大要是描述一名在法国求学的臺湾女留学生Zoe"的爱情,Zoe"是一名同性恋者,在她与爱人「絮」在法国共同生活了八个月之后,絮离开了Zoe"回臺湾,基於对这份情爱的重视与絮的离开带来的无尽痛苦折磨,Zoe"写下二十封遗书。
书中充满对生命、感情的质疑与吶喊,藉由书写的过程,重新审视自己内心的感受。情人的背离產生时而悲伤、时而愤怒之情,充分显露女同性恋的爱情裡的爱慾与矛盾。
起初在阅读这本书时很困难,胸口有如大石压住。太过深沉、孤独,每个字相互交织生命的围篱,把她紧紧的困住在囚牢之中。
第一次接触到女同性恋文学,起初难以理解女同性恋裡的情慾,如何面对爱情裡带来的甜蜜与苦痛。直到闔上这本书后静静沉淀,才理解到不管是同性恋或异性恋,都会遇到爱情相同的烦恼、相同的痛苦。
撇开这故事裡的真实与否,以一位女子写给深爱的人的最后一书来看,文字裡面除了书发内心对爱情的期望、失落、憎恨、怀念,一字字都像在拆解自己的肢体那般,血淋淋的令人深刻。看到她对爱那样彻底的付出,然后在爱情离去后,又逐渐走向毁灭。确实深刻的感受到爱情本是她的支柱,在情人离去之后,剩下来的,只剩空洞的灵,恍惚的生命顿时失去方向,失去意义。
对於旁人,看似无意义的喃喃自述,都是生命当下最真实的感受。我想每个谈过恋爱的人都知晓,与情人分离后的那种痛苦,当下彷彿每个细胞敏感程度都被过度放大,一首情歌、一个曾与情人走过的地方,都是伤痛的回忆。有人勇敢走过,也有人无法跨越。
爱情是美丽的,但越是美丽的东西,往往就越伤人。这是许多人都学不会的一门课,多半都在一次又一次的经验裡,学习著受伤,然后成长。都在付出当中获得代价,这代价也需要时间的证明,才能让心更为茁壮。当下以为跨越不了的伤痛,到后来也能云淡风清。有人说是时间冲淡一切,我却觉得是在反省当中获得答案也获得解脱,当能放下所有的不甘心时,也没有什麼能让自己沉溺在难过之中。
对於邱妙津这样文字能如此细腻的一个作者,我感到惋惜。其实我反而更希望《蒙马特遗书》只是她爱情见証的一种形式,多年之后她又是如何看待当时这段感情?或许也会觉得年少轻狂,知道爱情并非生命所有的一切,也不会踏上死亡一途。
我觉得用信件传达心意是一件很美的事情,透过文字,有时能更贴切的传达内心的感受。但往往速食时代的速度毁灭了很多美的东西,就像爱情也是如此,速度之下,爱情只剩感官刺激,而失去对爱本质的思索。我从邱妙津的文字裡感受到那股强烈而又不可得的爱情是壮烈的,但壮烈之中是否也强烈到失去爱情的分寸呢?能真的作到拿捏得当实在不易,若能真的用理智在谈恋爱,那样的爱情也将失去热情。所以说,为什麼爱情永远是写不完的话题,在每个时代都有过属於那个时代的代表形式,但不变的,是爱情的本质。
最后,我不想用“美”来形容遗书,在《蒙马特遗书》我寧可看见的是一个人曾经爱过的证据,那样织热的情感下,那麼真实的自己。无论爱情的结局如何,至少代表自己当时是认真的对待彼此,唯有真正爱过、痛过、活过来了,那才是真正的美吧。
夜读邱妙津
外面在下雨,雨点落在地面的声音如有什么在蚕食着时间,算是秋雨吧,天气会慢慢转凉,原来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把最难熬的夏天给熬过去了——在某一天的深夜中。
你看,我还没有睡,双眼鳏鳏,床头堆满了新旧书,一本本翻看,一本本放下,然后联线上网,找一个女子的文字来读。鼠标滑轮不停移动,一目十行,再一次读她最后的遗书,忽然就想去喝一杯烈酒睡了算了——可是,是睡不着。
你知道这个女子吗?叫做邱妙津的,台湾女同性恋者,26岁时自杀于巴黎,那已经是6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网络不如今日发达,所以,她的死并没被我们所知,然后,又很快被所知者遗忘掉了——我们必须遗忘掉死者,有意或无意,因为我们必须活下去。
她是用水果刀刺入自己胸口的,如此激烈,如此无望。她死后,那封长长的遗书获得“《联合报·读书人》96年文学类最佳书奖”,然后是种种评述,种种感叹……喂,我甚至有点嘲弄的笑:这算是哀怜或是致敬?对于死者,我们很难学会沉默,用沉默以致敬。
然后,今日,我想借她说一点话,我乞求原谅,我知道会得到她的原谅:死者是不会在乎什么的,生者?生者的责难不代表她,我知道自己有点无耻,深夜睡不着的人多少都有一点无耻,因为他们没有很好遵守生存规则: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特别是,去想一些白天不会想而夜晚不该去想的事情。
请容我摘录其遗书开端,漫长的开端,copy:
小咏,我日日夜夜止不住地悲伤,不是为了世间的错误,不是为了身体的残败病痛,而是为了心灵的脆弱性及它所承受的伤害,我悲伤它承受了那么多的伤害,我疼惜自己能给予别人,给予世界那么多,却没法使自己活的好过一点。世界总是没有错的,错的是心灵的脆弱性,我们不能免除于世界的伤害,于是我们就要长期生着灵魂的病。
小咏,我和你一样也有一个爱情理想不能实现,我已献身给一个人,但世界并不接受这件事,这件事之于世界根本微不足道,甚至是被嘲笑的,心灵的脆弱怎能不受伤害?小咏,世界不要再互相伤害了,好不好?还是我们可以停下一切伤害的游戏?
小咏,我的愿望已不再是在生活里建造起一个理想的爱情,而是要让自己生活得好一些。不要再受伤害,也不要再制造伤害了,我不喜欢世上有这么多伤害。当世界上还是要继续有那么多伤害,我也不要活在其中。理想爱情的愿望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过一份没有人可以再伤害我的生活。
小咏,你是我现在相信、相亲的一个人。但我一个人在这里悲伤会终止吗?纵使我与世上我所伤害和伤害我的人和解,我的悲伤会终止吗?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伤害,我的心灵已承受了那么多,它可以再支撑下去吗?它要怎么样去消化那些伤害呢?它能消化掉那些伤害而再重新去展开一份新生活吗?
小咏,过去那个世界或许还是一样的,从前你期待它不要破碎的地方它就是破碎了;但世界并没有错,它还是继续是那个世界,而且继续破碎;世界并没有错,只是我受伤害了,我能真的消化我所受的伤害吗?如果我消化不了,那伤害就会一直伤害我的生命。我的悲伤和我所受的伤害可以发泄出来,可以被安慰吗?在我的核心里真的可以谅解生命而变得更坚强起来吗?
…………
你有没有耐心一字字一句句的读完它?你是读亦舒的吧?你嘴角现在有没有嘲弄的笑容?亦舒现实到极点的刻薄我们多多少少都感染到一点了吧:不原谅别人,不纵容自己,爱己胜人,等等等等。这些从现实角度来讲完全是正面教材,所以现在年过半百的她很健康愉快的生活在一个比较舒适的国度,偶尔写写娱乐性满强的文字让人骇笑。而邱妙津,26岁灰飞烟灭,痛苦中离去——她不是无知妇孺,大二就能用法文读原典是留学法国的心理学研究生,——那又怎么样?解不了自己的心病谁又能救她?她好不好算社会和生命的浪费?
亦舒反复的说过什么来着?对,生命是一场幻觉。但是她很坚强的将幻觉延续下去,同时看破世情,告诉我们:社会只爱健康的聪明的,肯拚命的人,谁耐心跟谁婆婆妈妈,生活中一切都变成公事,互相利用,至於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统统是正常的。
啊,对不起,我忽然发现自己将两人在做一点对比,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有人偏向死者有人支持活人,没有一个好的准星。但是,我不是作为裁判者,我只是代表自己的观点,对错自负——深呼一口气,现在我可以去谈邱妙津了。
首先,她是一个女同性恋者,这一身份直至她死后人们才从她日记和文字中得知。但是这绝对不是致死的原因(倒是炒作的好题材),6年前的社会也不至于去逼迫一个女同性恋者到走投无路,相反,她将自己隐藏在人群中隐藏的很好。不是社会的错,如果你读完她的遗书和所有著作,你会发现,这个女子死于自身,自身的脆弱和……梦想。
请你再回过头去读一读前面的遗书,仔细读一读,这象是一个26岁女子所说的话吗?16岁还差不多。她不停的提到“伤害伤害伤害”,世界给她的伤害,现实给她的伤害。其实,没有人压榨过她,她没有饥寒交迫过,她所谓的伤害只是心灵和感情上的——被欺骗被嘲笑,这些,谁不曾有过呢?有许多人甚至比她更深。要是这就是死亡的理由,很多人活到24岁都算很了不起了,可是,我们都活过来了,愈合了,而且决定无论如何要好好活下去,34、44、54、64、74……我们是很坚强和理智地,世界是我们支撑和维持地,不是逃兵地。
同时,我们也不是自己梦想的殉卫者,而邱妙津,她是。
或者说,她太过脆弱和梦想化了,所以她最终为其付出了生命——我犹豫了很久,不敢去说她是弱者,是错误。
真的不敢,不是怕对死者不敬。因为,我敬畏梦想。
她活得炽热、真实,沉浸在自己的欲望和情感中,如此纵容自己,一次次跌倒,但没有吸取教训,变得现实坚强,而依然相信他人,相信爱,相信这个世界能容许一点纯粹的东西存在。她以为不去伤害他人就足够了,始终没有学会去保护自己,抗拒伤害,甚至没有学会:放弃。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少年时梦想的那样,他人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善意和包容。唉,这个还用说吗?任何一个过了24岁的人都该明白的吧:除非你很幸运的还是暖房中的花朵。如果你已明白但是还是为此痛苦的话,那就活该痛苦下去好了,等34岁的时候你就不会再为此痛苦了,人到中年,有更重的生活担子需要你全力去承担了。
可是她不明白,或者说是明白了,但是无法释怀。
世界总是没有错的,错的是心灵的脆弱性,我们不能免除于世界的伤害,于是我们就要长期生着灵魂的病。——我们无力去指责世界,我们只能承认现实,然后让现实一点点磨除自己的脆弱,好让自己能好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我们都渴望快乐幸福,而这必须以生命为前提,死亡只能带走一切:我们憎恶和舍不得的一切。
那她为什么要去死呢?她可以再去找一个好的爱人,然后熟练运用她的法文,在巴黎享受生命与爱。她已经熬到26岁了,完全可以再熬下去,等下去,改变自己,好好活下去。可是,她选择了死亡,不可逆转的死亡。
她已经绝望,不屑,痛苦,不相信,放弃。
忽然想起黄碧云笔下那个流落巴黎的中国女子,叶细细,用刀片割开自己喉管的那个,她死后,生者哀叹:细细,何至于此。
可是,世界上真的有一种水晶,破碎成千万片,就无法在弥补,那不是水晶的错,亦不是世界的错,根本没有错误,真的,只要生与死为自由意志选择,就没有错误。
既然活着,就要好好活下去,亦舒给了我们那么多良方,一定能得到一点收获和幸福;如果活不下去了,熬到底线崩裂,剩下的一切他人也毫无办法,死亡只属于自己——求求你,不要对我说生命不只属于自己,不要太自私,因为谁也不能代替谁痛苦的活着。
唉,我眼睛发涩,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外面的雨还没有停,但是天也会亮,周末已经过去,一切都将恢复正常。我想结束了,我花了2个小时去呓语,说一个女子的死亡,说其实我自己根本无法确定的事,妄言生死,奢谈梦想。
最后,那封长长的遗书最后说,对所有生者谦卑而细小的说:
我祝福您幸福健康 但我不再能完成您的旅程我是个过客。全部我所接触的真正使我痛苦而我身不由己。 总是有个什么人可以说: 这是我的。我,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有一天我是不是可以骄傲地这么说。 如今我知道没有就是 没有。我们同样没有名字。必须去借一个,有时候。您供给我一个地方可以眺望。将我遗忘在海边吧。 我祝福您幸福健康。
你看,我也只能如此祝福,结束。然后去睡觉,日出而起,日落难息。——我一直没有告诉你,读她的时候,我居然哭了,这真是件很难启齿的事情,可是只有说出来才能安心说晚安,微笑。
——转自《文学视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