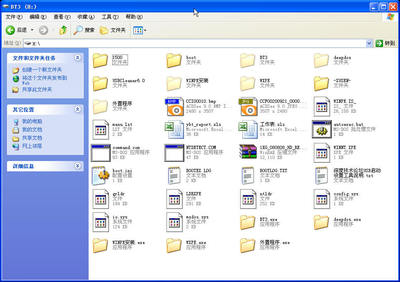孟子变成“门修斯”——学术界的耻辱
倪乐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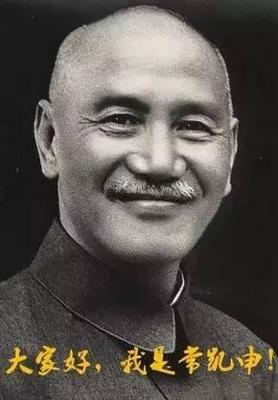
2001年3月21日
十年前的文章,重读由新。发来大家玩味一下
近日购得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名著《民族-国家与暴力》,此书由胡宗泽和赵立涛翻译,王铭铭校对,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5月出版。因作者是“当代欧洲社会思想界中少有的大师级学者”,所论又涉及与自己研究有关的战争和暴力问题,故不敢怠慢,认真拜读。读后,我对吉登斯的理论失去大半兴趣。问题不完全在吉登斯本身,主要是译、校的学术功底让人怀疑:吉登斯的思想是否在翻译过程中“变形”?
作者在“译后记”中称,对于人名,“尽量沿用了国内的固有译法”,但是书中屡有置过去习惯译法于不顾的地方。例如:19世纪著名军事学家、《战争艺术》的作者、瑞士人约米尼(Jomini)译成“乔米尼”(第27页);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译成“黑罗多特思”(第58页);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译成“阿肖卡”(第91页);公元742-814年在位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译成“夏勒马涅”(第136页)。这种现像不仅仅是个习惯译法问题,而是明显地反映出译、校者西方历史常识方面的欠缺。更让人吃惊的还是下面这段文字:
门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第99页)
乍一看“门修斯”,又以为是国人很陌生的一位外国大师级学者。译、校者显然不知Mencius即中国先秦思想家孟子。所谓“格言”,即“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且出自孔子之口,并非孟子所说。
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章句上》)
曾子问曰:丧有二孤,庙有二主,礼与?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郊社,尊无二上,未知其为礼也(《礼记•曾子问》)。
《孟子》和《礼记》都只是转引了孔子的话,不应当作孟子的格言。查阅第104页上的第35条注释,吉登斯这条材料引自《ThePoliticalHistoryofChina,1840-1928》一书,作者是LiChien-nung(李剑农)。到底是李剑农一开始就用错了?还是吉登斯引错了?抑或译者译错了?不管怎样,译、校者如能认出老祖宗,问题不会这么复杂,他们在“门修斯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国学底子的浅薄程度实在令人震惊,堪称数典忘祖之绝唱!
孤立地看,这属小事一桩,但和“北京大学”、“博士”、“北大教授”、“三联书店”、“学术前沿”这一连串头衔相对照,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什么叫浮躁?什么叫浅薄?什么叫文化断层?“门修斯”的诞生作了最好的注解。笔者虽不愿小题大作。但却不得不涉及导致这一现像的更为深层的问题。
坦率地说,“门修斯事件”是社会剧变冲击下,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出版界共同酿成的一次“学术浅薄综合并发症”。在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宰的新形势下,基础性知识(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领域知识)在高等教育中遭到严重冲击。发展应用性学科、知识为社会现实服务原则本身没错,传统学科和课程作必要的调整也无可非议,问题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人并不知道“度”在哪里。许多大学将必要的文、史、哲课程或压到最低程度,或取消,或干脆将历史、中文专业变成旅游、秘书专业,从而造成目前高校人材知识结构的严重失衡,即应用性、操作性知识和基础性知识的严重失衡。目前高校现状正如一位年长的博士生导师所言,“大学有向技校靠拢的趋势”。虽言词有些过激,但不失为警言。
高校在高级职称评定中必须要有专著的规定是高校青年教师,青年学者普遍浮躁的根源之一。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的规律是从写学术论文做起,在十年、二十年撰写学术论文的基础上,积累学术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有质量的学术专著正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判断中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准应以他们学术论文的质和量为准。现在的情况是:有些中青年学者发表了一、二篇像样的论文后,便匆忙地拼凑学术专著,急于当各类急就章式书籍的主编、副主编,造成社会上大量学术赝品的堆积,而“大胆培养青年人才”之类表面上挑不出毛病的口号,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事件中,往往更多地产生负面作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年青人出专著风气的始作俑者是80年代上海文艺评论界的个别年青人,当年《文汇报》还专门作了报导,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青年人著述立说表现了可贵的学术勇气”(大意如此)。年青人“著书立说”遂成中国学术界的“一道风景”。十几年过去了,这种勇气在今天看来对中国学术界的负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年青人“著书立说”从根本上就违反了学术研究规律。学术勇气只有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积累之上才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没有学术积累和功底的学术勇气只能造成类似“门修斯事件”的学术灾难,只能给后代造成不堪重负的辨别真伪和清理文字垃圾的负担。
市场经济虽然给目前出版界带来诸多难题,但出版社没有健全的学术审查制度却和市场经济毫无关系。谁都知道健全的学术审查制度是出版学术著作的根本保证,但许多出版社就是不愿这样做!相当一部分编辑们虽然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编辑而不是专业研究。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于专业的学术进展知之甚少,有的甚至空白。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必苛求,专业研究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专业。然而,我们面对的事实却是:仅由编辑来判断一本专业书的学术价值。这实在是对学术的不恭和轻率。
西方理论固然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也不必盲从,尤其在涉及中国问题时,因语言的障碍,外国学者受到很大限制。由于他们往往追求“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就不得不面对他们难以把握的东方文明。这时,他们往往会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比如这位吉登斯大师居然在书中写到:中国曾对印度尼西亚享有过名义上的行政权力(第100页),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乾隆皇帝名义上的行政权力也可以说是越过了英吉利海峡。除非翻译错误,不然可就有点信口雌黄了。
如果说吉登斯对中国历史了解甚少尚可原谅,那么他认为“民无二王”的格言“可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就令人对他的欧洲历史知识也深感遗憾,至少这一结论不能解释罗马帝国戴克里先时期的“四帝共治制”。如果不是翻译中的问题,联系上述错引材料和信口开河的事实,笔者感觉吉登斯至少是一个治学粗糙的大师。联系上下文,如果翻译没出错的话,吉登斯已把帝王的文明中心意识和帝王的王权独尊意识混淆在一起了,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说些什么。
西方学者在学术表述过程中,常常不知不觉地将从欧洲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规律误以为也适合世界其他地区。例如,西方战争史学者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步兵集团的诞生与民主政治有着必然关系。富勒(Fuller)等权威学者甚至斩钉截铁地认为步枪造就了步兵,步兵造就了近代民主政治,希腊步兵方阵造就了古希腊的民主政体。然而,这仅仅是欧洲的历史,他们不知道中国先秦以前的步兵传统造就的却是一种专制集权政治。
中国的历史还需中国人用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和自信来解释,而这些又都离不开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了解。恕我直言,没有以上素质且无丝毫国学功底,是没有资格奢谈中西文化对话的。此次“门修斯事件”实为中国学术界之一大耻辱。文化断层已经在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和出版社出现。高等教育、学术界、出版界急功近利造成的恶果,目前只是刚刚开始。如不予以警示,笔者深信,更大的惩罚正等待着我们,那时,我们将目瞪口呆地看着“孔修斯”(Confucius)也大摇大摆走进象牙之塔。诚如是,“我孔、孟之所痛哭于九原”矣!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