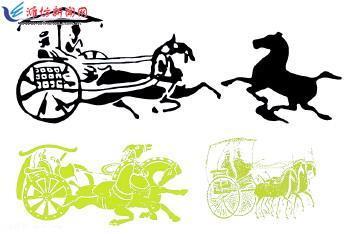“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将之与历史联系起来?
不妨先设想一下“流年”。我们去择日馆找一个大师算命,告诉他生辰八字,他就可以为我们列出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个年头、每个季节、每个月如何度过的清单来,这就叫“流年”。“流年”也有来年的每月运程,从正月某时,列到年终,既列出各时间段个人的运气特征,又暗示在各时间段个人该采取什么行动。写“流年”叫做“算”,它有一套算命方程式,结合了一些其他的综合知识,但还是用数学来称呼它。“流年”之获得信誉,部分原因是我们算它之前发生的那段历史与大师给出的“流年”之间的巧合。
“流年”根据人的生命时间,来推算人与世界万物之间关系在不同的时间段里的表现、性质与影响。为了适应凡俗的需要,“流年”的语言,包含许多有关福禄财富、事业及工作趋向、情感婚姻家庭、身体与吉凶趋向、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词汇,以人生时间与万物时间之间的关系,来阐述人之身心福利。
“流年”也是在说历史,但是它的基本旨趣是关于未来的,与想象中的“客观历史”至少有以下几点区别:
流年是一种个体的、主观的东西,而历史是一个集体的、客观的东西。二、流年即使算对了,也被认为是猜测,而历史被认为是一种科学,背后有论证。三、流年作为一种算命术,更像是预言家的言论,可以被prophecy这个词涵盖。prophet指的是预言家,prophecy指预言家的创造。流年通过对你过去的判断所得出的结论,无非是对未来的臆想和预测。而历史,则是对过去的一种真实的记忆,比较关注过去的日子。四、在真实性的来源这方面,流年与历史有所不同。流年要将事件和记忆做一个非常完美的对称,使它含有一种信仰的成分。而历史根据一些似乎是很客观的资料,包括文字的、口述的、考古实物的“事实”,来恢复过去。
流年与历史的区分,已被人们当作常识。不过,学者的使命不是接受常识,而是挑战常识。所谓“挑战”的一种方法,就是在思考时先做点“模糊化”的工作。按照这个方法,不妨先设想历史和流年之间的通性,而非一般常识中的差别。
为了触及历史,我顺便举出黑格尔《历史哲学》这本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一九九九年版)为例。书中,黑格尔区分了以下三种历史:
第一种历史,是原始的历史,这跟我们说的原始社会不一样,它指的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人写的历史。黑格尔认为,希罗多德等人是历史的目睹者,记录的是他们看到的、当时他们生活当中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他们记录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如同我们记录今天的情况。原始的历史在今天一般被我们当作“历史素材”来看,而黑格尔对它珍重有加,并给予它历史的身份,实在是伟大。
第二种历史,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历史,叫做“反省的历史”;意思是,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站在今人的角度去回顾它,可以写出历史来。“反省的历史”又有几个类型:普遍的历史、实验的历史、批判的历史、生活和思想等各专门部分的历史(比如说第三种历史,是黑格尔自己追求的“哲学的历史”,能提出这点也很伟大。所谓“哲学的历史”,就是把历史看成是一种历史理性或者历史精神的时间性呈现。黑格尔认为,在这种历史中,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国家的意志完美结合,而国家是个人意志的最高体现(他笔下的国家,跟我们今天所用的“国家”概念显然有所不同)。他花了很多篇幅来说明“哲学的历史”是什么,无非想说,他所追求的历史是指历史自身的某一种精神,及这一精神在不同阶段被事件表现出来的心灵实现过程:
我们不妨同意人类学史专家的说法,承认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就是人类学的最初类型。人类学的民族志描述的就是一种“原始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区别就在于,人类学做的是“原始的历史”,即“当下的历史”,历史学做的是“反思的历史”,即“过去的历史”。而,“哲学的历史”这一说,则更有趣味。
我以为,从深层看,黑格尔所追求的“哲学的历史”,与中国人的“命”这个概念实际没有太大区别。“哲学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世界的未来,特别是西方的未来。在《历史哲学》这本书中,黑格尔涉猎全世界,从东方到西方,寻找个人自由意志的最高表现。他比较了三种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他认为,在这三种文化中,只有中国存在个人意志的国家化的雏形;印度呢,一盘散沙,根本谈不上有一个什么国家的精神;而阿拉伯世界,其酋邦太强大,统一的国家无法实现,因此在那个地方也不存在“哲学的历史”可用的资源。黑格尔又从东方跳到欧洲,去历史上寻找种种可能性,并基于西方,提出一个对未来的历史预测。
《历史哲学》写于十九世纪初。在那个时代,把国家当成个人自由意志的最高表达,并非偶然。黑格尔期待欧洲应该建立起强大的、能满足任何公民需要的政体,此一政体,我们今日称之为“民族国家”。这么一位伟大的西方哲学家,在书写历史时,公然将自己区别于一般历史学家,而想成为所谓“prophet”,其历史之猜测成分自然也特别多。比如他猜测中国不是一盘散沙,猜测印度因为种姓制度的存在而无法有国家精神,等等。然而,同一个时期或者晚一点,不少学者却也在“论证”我们中国比印度还要“一盘散沙”。到底事实为何?没有答案,只有猜测。黑格尔在遥远地想象,试图探索一个问题:东方有哪些值得“我们西方”未来参考的东西?
如此说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流年的主要区别恐怕只是,前者是集体命运的猜测,后者是个人命运的猜测。
这样分析黑格尔,不等于在说所有历史。然而,世间存在多少完全没有算命术内涵的历史呢?我们能找到的,实在少。大多数历史,都在书写过去、反映当下、预测将来。所以“命”这个概念对我们理解现存的历史有颇多启发,在这点上,历史与命相通。
“命”的概念是很中国式的,但恰是这种“当地性”的东西,经常蕴涵着解释普遍问题的潜力。有社会学家认为,以命的观念为基础的社会和以风险的观念为基础的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两大类型,可以以此来划分人类史。在现代社会产生之前,所有的传统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都是围绕着“命”的概念而建立。社会学家认为,在这些社会当中,要建构社会秩序,必须首先要建构命的观念。我们如果生活在一个传统社会当中,我们会把自己的所有一切悬在“命”这个概念上,将个体交付于支配个体的宗教及专制政权来“领导”,由此产生“认命”的意识形态。到了现代社会,观念变了。科学使我们不再相信神创论和命运论,可现代社会并没有解决人生存的危机。怎么面对危机?“风险”这个远离宗教、接近“科学”的词汇,进入我们的思维世界。社会学家认为,现代社会在解决风险、克服危机中,将希望放在了专家身上。现代社会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专家体系:专家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构造克服个体风险的专业技术,成为新时代的命运掌门人。
古时候,人若生病,他大抵会想:“我是不是遭天谴了?”然后他就作罢,或者拜拜神,说说“饶了我一把吧,老天爷啊”就成了。复杂点的顶多就相信“犯太岁”、“冲”了,接着找个巫师、法师来解决。可如今不同了。医院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信仰和仪式体系,使我们相信我们身体上任何局部的问题,都得通过它来解决。作为克服个体风险的专家体系,医院之类的机构是替代传统社会命运体系的另一个权威体系。以前人们说,把握命运的人,也把握人生,如今不同了,把握知识的人,把握人生。这是人们的信仰。
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1990)即预测了一个走势,说人类从命运社会走向一个专家主宰的“风险社会”,在此过程中,那种融聚一团的“命”观念衰落了。我们可以延伸这本书的看法来考察历史这种东西,并据此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社会已如此变化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历史这种叙事也发生了从“命史”到“专家史”的变化呢?
社会学家的历史研究,大都是线性的,都在说传统到现代的变化。这个变化观自身有一些问题,这后面再谈。这里,我们不妨先看看“命史”的意义。
为了解惑,我不得不在历史上来寻找有启发的观念,特别是古代中国人的“史”概念。
说到“史”字,大家必定想到司马迁。据说,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的“史”,尽管在他前面还有《左传》等书,但他承前启后,承继上古史官文化,并对之有大的创树。司马迁不是人类学家,不过,他在当时可以绕的地方绕了一圈,从东部走,到蜀国去,再往回走,成为一个伟大的旅行家。他想以第一手资料来印证他的文献,如同今日的一些历史人类学家。而他写的《史记》,不仅是历史,也记述了不少异族及其文化。
提到司马迁,目的是要说,他对于我们理解命与历史的相互辉映关系有莫大助益。
今天在西方,“历史”不一定是一个好名词,有时被认定包含有污点。如今历史与故事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历史和男人的密切关系也被揭示了。“历史”怎么分解法?请容我戏谈之。
第一个分解法就是hi-story,hi是一个“高”的简写,就是说历史是一种“高调故事”,一种声音大、内容虚的故事。第二个分解法就是hisstory,就是“他的故事”、“男人的故事”,女权主义对这个揭示得很多。关于后面这层性别的意思,我看不一定很全面。中国被认为是个夫权主义社会,可我们的历史里有吕后、武则天,而且记述得很详细,不同于欧洲的王公贵族,他们对后宫的事一般不揭示。在我看,hi-story这一层意思更重要。的确,历史跟叙述不能简单区分,历史也是在“说事儿”,在说故事。性别的层次只有在与这个情况结合时才值得考虑,它无非表明,所有历史都包含着一种支配,而性别的支配是最基本的。
可见,无论怎么分说,历史都是带有偏见和力量的叙述。
对于历史的这一所谓“主观性”,当下史学家要承认时都还特别羞涩,而古代中国则不同,古代中国的“史”,有本事和勇气视其创造为主观之物。《说文》里面说,“史”字的解释是:“史,记事者也”。就是说,“史”是记事的人这个职业的称号。接着又说,“从右持中。中,正也”。中间是正。什么意思?后世的聪明人开始阐述,多数认为这个“中”,可解释为“历史的文本”,就是装着历史文件的包或者盒子,在人的掌握之中。许慎自己对“史”的解释中,“正”字特别重要。怎么理解?古代中国的历史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就是这个“史”字,指记事的人,另一方面,又对记事者的职业态度给予一种形象上的要求——史家必须用中立态度来记事。
“史”这样一种职业,在甲骨文时代,指的是管理记事和军事的那些人。这些人是最早的历史学家,但他们兼占卜,是一批应对国家所有大事的知识分子。当时,国之大事,全部由“史”来管,所以就叫“史官”。“史官”一说,很有意味,表明在古人眼里,进行中立——而非“客观”——叙事的人,也掌握了“正”,成为为国家管理祭祀、军事、占卜等事情的人。周代“史官”文化得到了系统化界定,其社会地位更加明确起来,职能就是:一、占卜的“卜”;二、占梦的“占”;三、记事;四、判断祥异;五、进行天文星历方面的研究(包括星占学)。周代对于“史”的定义,使我更为确信,历史与命,的确息息相关。史要占卜,要占梦,要记事,要判断灾异,要进行天文历法研究,其功业后来成了算命先生们的知识体系。
到了战国秦汉时期,中国的“史”观念产生了一些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历史学家研究得不少,作为外行,我所能做的可能仅是从中觉察到一些不一定恰当的认识。在这些复杂的变化中,我认为重要的是从天命观念转向天道观念。“史”的最早形态与“算命人”不能区分,他们承载的是天命;老天有命,看谁该当皇上,当了皇上该怎么办,每天的起居怎么安排,都由“史”来管着。承受着天命的“史”,可以监视政权把持者的活动,其职权具体而全面。当天命变成天道之后,“史”的角色产生了重要变化。天道与天命的不同是,它是人为的,是主动、积极的,人的活动有没有符合天的运行规律,除了受天的决定,还出现了主动迎合的趋向。特别是到了汉代,万物的生长规律,星辰的分布,山川的分布,成了皇帝通天的渠道,礼仪秩序成为表达其通天本事的象征。历史从上古的巫术、军事一类的东西,转入了另一个趋向——通过阐述过去来约制政权的行为。
《天官书》说: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这一“三五往复”的时间观,承继了上古天命说,与天道观念结合,对于古代循环史观产生深远影响。
从天命到天道这个变化,早已发生于春秋战国期间,到汉代得以体系化论述。这个变化很重要,但没有取消“命”这一说在古代中国历史叙事中的作用。理解司马迁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的“史”之重要,恰是因为他既承载了天命意义上的“史”,又参与开创了天道意义上的“史”。这一点,史学理论界还未给予充分的关注。而我从中意识到一点:上古时期,中国人对“史”的认识,隐含着对历史的“命”这一半的承认,古人认为,“史”应该承担一种有高度宗教和政治意义的使命。
回到与黑格尔相关的论题,我以为,古代中国的“史”观念,兼有了“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三种,没有对历史加以区分,而是认定其内涵混融一体,过去、现在、未来如一棵不能折断的大树。
再回到社会学对于传统与现代、命运与风险的论述,古代这种“史”观念,是否因历史变了,就不能解释今日之“史学实践”?
今天所谓“科学的历史学”,以割断历史为己任,将自身疏离于算命术之外,成为一种接近于专家体系的东西,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难道今日之“科学的历史学”就完全丧失了“知命”的成分了吗?并非如此。如果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高度体现了近代史学的特征的话,那么这种史学的特征恰在于都企图对民族精神做出定义,对民族未来做出“占卜”。可以说,今日史学为的是替社会摆脱可能的风险提供历史的“客观参照”,起“资治通鉴”的作用。因而,风险之观念并没有完全失去命运观念的因素,而无非是将之“集体化”,使之脱离“个体主义巫术”的身份,成为国家叙事。
要更好地理解古代观念对于解析现代意识形态的意义,还是要回到古代观念本身。于是,我们又有了一个新问题:在古代观念中,“史”的书写,在时间结构上是如何把握“命”的?
说到时间,不能不说到“易”这个概念与古代中国历史观念的密切关系。“易”即《易经》。“易”为什么与历史相关?因为它提供了一套运算命运的方法,同时,“易”本身就是“变”的意思,而历史学家宣称史学研究就是变化研究。以命运观念、宇宙秩序观念为基础的“易”,以宇宙生命力和它的秩序为其自身概念生命力的“易”,来自人与自然的关系,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地貌”,形成对世界的看法和实践模式。“史”“通古今之变”,乃是士大夫追求的理想。现代科学家也有这种追求,但没有像古人表达得如此明确,如此野心勃勃。“通古今之变”,可能被理解为一种历史感,但最重要的是,这里的“通”和“变”字,直接牵涉到日月星辰山川之变,及其与我们人之间关系之变。对于这种关系,古人并不是“客观地”看,而是用两个与己相关的概念来形容,一个是“德”,一个是“刑”,二者构成所谓“刑德之说”。“刑”指的是因天人关系相逆而产生不利于人的后果,如同“刑罚”;“德”就是二者配得很好,人的身体活动之变,与宇宙之运行轨迹产生和谐关系,或者说,宇宙氛围提供身心活动的最佳场合,使人“顺”。顾颉刚曾提出,在汉代,出现了一种“五德始终说”。五德跟五行有密切关系。所谓“五德”,就是指不同的朝代,有物质上的属性,比如这个朝代属于水,那个朝代属于土。这种物质属性有命运的“代价”,倘若属于该属性的朝代之天子采纳相反属性的符号与行动,那么结果不堪设想。“五德始终说”中的每一个“德”,都会有终了。
自古中国就有“革命”思想,改朝换代就是与前朝的“德”之终了有关。比如,一个朝代本来的“德”只有一百年,可皇老儿想继续当皇上,其结果是违反了天道,跟物质世界的循环不配,此时,“德”便要转移了;“德”的转移,在古书上叫做“革命”。
作为“德”的转移的“革命”,和“五德始终说”那套东西,直到二十世纪,一直对中国历史起关键作用。
“革命”被认为是近代西方的传统,但这个词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易经》说的“汤、武革命”就是一个早期明证。这个词古代已传到日本,在日本明治维新时代被用来形容尊王改革。近代传回中国,被用来翻译“revolution”(英语)、“revolvere”(拉丁语)。一个形容改朝换代的合理性的词汇,传播到东洋,到近代,与其君主立宪制的追求结合;接着,又回到中土来,变成近代中国的“激烈斗争”,其经历的历史进程复杂得很,意味也浓厚得很。其中一个引起我特别关注的历史讽刺是,近代中国的“革命”,在许诺彻底摧毁历史的同时,承载了古代中国思想对于“革命”的理解——改朝换代。我们所没有承认的是,即使是我们的“革命”,也没有脱离古代天论中所说的“天地革而四时成??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易经》)。
史学为了回归于历史,包容了人类学的“史前史”论点,这肯定是有裨益的。怎样认识历史?“史前史”有不少参考价值。史前没有文字的记录,而历史则指对于过去的书写,这差异衬托出历史的面目,表明我们一般理解的历史与文字有着密切关系。这一差异,如同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差异,可以说,人类学是根据没有文字的历史来认识有文字的历史,我以为这是人类学对于历史的批评与贡献。
然而,光知道这点还不够,我们还应对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类学——或者“历史人类学”——的贡献有深入了解。
不少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历史人类学将历史当文化来研究,至于怎么当,学者则语焉不详。于我看,历史人类学是对围绕时间的文化、围绕历史的文化的研究,是对不同文化如何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研究。以往历史人类学家告诉我们,要采用无文字社会的时间感来看有文字社会的时间感,现在更迫切要提供的是一种大胆的实验:用宗教的观念来看历史,而拒绝将历史等同于真理。
即使是在诠释“革命”时,以“命”的观念为中心的历史观,都是宿命主义的。这种“宿命”,使古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与近代以来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有着根本差异。然而,可能是因为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了宿命主义的内涵,我们才更清晰地认识到近代的、西式的“历史目的论”这种未来取向的历史观,与“命”这个概念背后的一套宿命主义思想,共同点比差异要大得多。
(《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王铭铭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