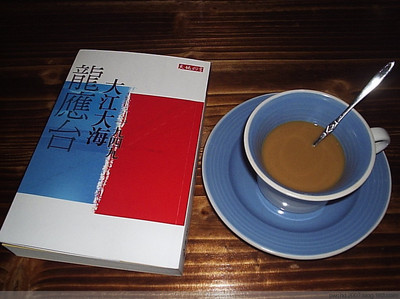感受整个荒原,有时只需一株小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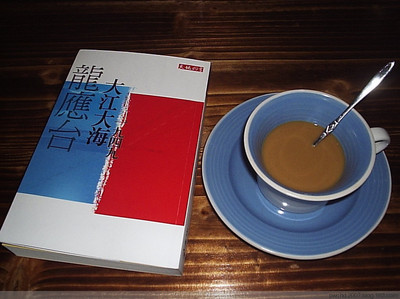
——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徐飞
在我看来,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具有同样品格,都像黑色深海中的鲸鱼以震动微波的方式向世界发出密码。
历史,既可以像历史学家讲述通史那样宏观铺开,也可以像索尔仁尼琴、龙应台这样着眼于局部,从一片混沌的现实中,截取半截山水而不是全幅写真,以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沉浮,还原一个时代的洪流。而事实上,这两种讲述都是不完整的,现实永远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只要思想一启动,现实就会被打碎,因此,这两种方式的历史讲述,都是对现实的切片观察,并不能还原出历史的全部真相。龙应台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有时候,感受整个荒原,只需要一株山顶上的小树,看它孤独的影子映在黄昏萧瑟的天空里。
这种对历史的谦卑姿态,为她的讲述赢得了巨大的腾挪空间。她可以不去理会党派意见,可以不去迎合国家意志,甚至还有意冒犯“胜利者”的尊严,她唯一关注和思考的对象是——“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因此,她对“一九四九”的认识不再停留于片面的历史记述——历史总是由“胜利者”记述的——而是把自己扎沉下去,与一个个历史的“在场者”亲切交谈,以第一手资料讲述当事人的命运,尽可能客观地还原出那段被掩埋的历史。“有时候,感受整个荒原,只需要一株山顶上的小树,看它孤独的影子映在黄昏萧瑟的天空里。”谁能说清,对整个荒原的全息影像,与一株小树的特写镜头,哪一个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这种个人体验式的历史表达有着很大的风险,它会因为写作者的思想局限和价值观误导而作出自以为是的判断和引导,但这种风险在本书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化解,因为有写作者知识分子的良心、超拔通透的思想、不偏不倚的立场、悲悯谦卑的心灵和坚忍投入的辛劳作为担保。为写这本书,龙应台采访了众多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从身边的好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蚌会战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春的围城幸运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俘亲身经历者,这些人都向龙应台提供了珍贵的回忆和珍藏的资料、照片。龙应台用“加持”来形容这段过程。佛教里的“加持”一词,来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寻常的力量附加在软弱者的身上,使软弱者得到勇气和毅力。除了勇气、毅力外,那些“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所“加持”给龙应台的应该还有对历史和人生的重新发现。不是理念先行式的历史讲述,而是随着历史的开掘,人性和人生的碎片重新整合,生命有了更为坚固的基座。
龙应台从事的是一项艰苦的“打捞”,从时间的长河与政治的黑洞里,“打捞”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也让历史露出了嶙峋荒凉的侧面。长春围城时有30万人被活活饿死,苏联红军对中国妇女的奸淫残杀,盐城争夺战中尸体填满了护城河,淮海战役中一波又一波的民工倒在了国军的炮火中,三万多名国军从十万大山中突围却又陷入了越南集中营……龙应台在搜集的各种资料中爬罗剔抉,让幽暗深埋的历史重新浮出水面。历史如果被忘却,罪恶有可能重新再来,因此“胜利者”也必须有勇气揭开遮羞布,直面苦难的历史与尴尬的人性。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人类事务中的永恒的和符合规律的因素就是人性,这是历史学作为研究普遍规律的科学进行研究的基础。以人性为座标研究历史,可以从纷繁的历史现象中厘清脉络、切中肯綮。龙应台说,可能要150万字才能比较完整地呈现那个时代,但最终只写了15万字,她所删减、选择的标准与“人”有关。
本书所选择描述的人物当时大都为十七、八岁,这由幸存者的年龄所决定,也与本书潜在的对话者“飞力普”的年龄接近。在龙应台看来,个人的命运与年龄有着密切的关系,她说:“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像希腊神话里的人身羊蹄一样,他带着孩子的情感想大步走进成人的世界。十七岁的少年,也许就在跟父亲一起弯腰锄地的时候,也许就在帮母亲劈柴生火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小孩了。”十七岁,当然是一段模糊的年龄,这个年纪的少年对着未来有着无限的向往,充满激情而又力量薄弱。在时代的洪流里,这是最易被卷走、漂浮在水浪上而最易受到伤害的玻璃器皿。陈宝善18岁读高中时,正值日本侵华战争,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从军,却在国共内战中受伤,辗转逃到香港,在调景岭做着苦工。他曾经抱着多么大的热情,把自己奉献给他的信念——国家!在时代的洪流里,多少少年的命运在一念之间被改变!
卡夫卡被问到,写作时他需要什么。他说,只要一个山洞,一盏蜡烛。龙应台在“闭关”写作的四百多天里,幽居在山间一室,但她的山洞并不黑暗,她的烛光也不昏晦。她从时代和人性的黑暗处,挖一个小孔,对温暖的人性怀着不尽的期待。在生存恶劣的越南集中营里,官兵们竟然创设了“中州豫剧团”,为患难同胞送去慰藉;屋子失火,一团惊慌中,张子静校长从草屋里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席慕蓉避乱香港,老师教背《琵琶行》,席慕蓉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六十年以后,她还可以用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流浪到香港,看到满街都是露宿的流浪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这些温暖的碎片,在那个黑暗混乱的时代弥足珍贵。
稍作估摸,书中记述的人物有上百位,但本书庞而不杂,乱中有序,这与作者的巧妙编织有关。但更让我叹佩的是作者在语言表达方面的掌控艺术,她没有一任自己的感情倾泻如流,而是用理性来控制:“我得忍住自己的情感,淘洗自己的情感,把空间腾出来,让文字去酝酿自己的张力。我冷下来,文字才有热的机会。”克制的表述,反而有了更动人的魔力。德国士兵埃德沃在列宁格勒战役中牺牲,妻子玛丽亚收到他从前方写来的信,几十年过去了,她一直保存着这些信,作者这样写道:“这一把信,纸的颜色那样苍老,可是用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层层包着,看起来很熟悉:玛丽亚常常系着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在她八十多岁满脸都是皱纹的时候,仍旧系着。”正如一株小树的孤独可以映现整个荒原的萧瑟,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也可承载一生中的最复杂、最沉重的情感。
人生的局限永远无法克服,对于每一个生命来说,他所能触碰到的只是极其有限的部分。宏大的历史对于个体而言永远立在地平线,如此接近而又无限遥远。而一个人文学者所展开的历史画卷,往往藏着我们的血泪和微笑,值得收藏,值得省思。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