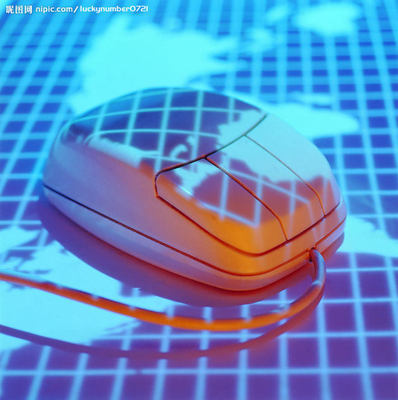谢谢我的朋友苏兄的鼓励与批评。
浅谈余同友的小说创作
——读余同友小说集《站在稻田里的旗》
苏诚林
恩格斯说:“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在于它有不同的诠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学的永恒魅力,在于永远不断的形式和内容的创新,而且离不开灵感的闪烁、血泪的铸就和人的本性的探究以及对时代变迁的关注。
纵观余同友的小说创作特别是近期出版的小说集《站在稻田里的旗》,与上文的表述是异曲同工、相互吻合的。在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余同友继承并借鉴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既小说的构建有一种“惟独期待”的故事的完整性,强调小说情节发展的因果关系,及其人物性格的基础与发展动因,以故事情节推动所描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从而启发读者的想象,在眼前闪现出一个个特写镜头,给人以高级的审美享受。
在题材和人物对象方面,余同友像著名作家路遥那样,擅长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擅长塑造新时期的农民形象。这部小说集中的7个短篇6部中篇,除了《暗劲》属于城市化小说故事以外,其余都是反映富有地域特色的农村生活的作品。余同友写他深情挚爱的瓦庄,因为瓦庄充满了乡土气息,是他生于斯长于斯最熟悉最有感情的地方,这里山美水美,风景如画,是皖南池州山村的缩影;可是,这里并不富裕,甚至还很贫穷。瓦庄里发生的许多故事,故事中的许多人物,既有鲜明的地域个性,又深深地打上了我们这个时代共性的烙印。他描写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市民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人情冷暖、悲欢离合和人性碰撞,以及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与身份、尊严等问题,为读者建构了一幅幅辛酸苦辣、悲伤哀婉的生活图景,让人们感受到了底层人物的心跳,感受到了他们的心灵落差和心理的挣扎与较量。无论《欢喜团》、《小秘密》,还是《青蛙搬家》与《我们村庄的好风景》,无论《夏娃是个什么娃》和《野鸭汤》,还是《点灯》与《蜗牛班》,这些作品所表现出的现实的无奈和缺失,人物命运的不幸与坎坷,别样生活导致的人性变化、情感潮汐,无不深深地打动并震撼我们的心灵,给人以深刻地反思。
从个人的偏爱来看,笔者比较喜欢余同友的短篇小说《乡村瓷器》和中篇小说《我们村庄好风景》、《夏娃是个什么娃》、《野鸭汤》及《蜗牛班》这几部作品。笔者以为,它们在艺术创作上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乡村瓷器》是较有影响的获奖作品,已有名家给予定评,这里不必赘言。
《我们村庄好风景》主人公王立正从外面打工归来,一心想坚守本土开发旅游事业,但孤掌难鸣,村里男女老少包括他的恋人美凤都不支持他,因为他们的观念都变了,他们需要钱,也只有外出打工才能挣到钱,甚至不管这钱来得干净不干净。王立正历经磨难和挫折,最后不得不向世俗低头,别人到罗城开洗头房去了,他也去了。观念的碰撞,无奈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王立正的梦想并扭曲了他的人性。
《夏娃是个什么娃》里,在部队当过侦察兵的杨利文和村姑苏眉外出打工挣了黑钱回来,平日无所事事打麻将消遣,看似平静,实际上心里都有事。后来刘公安来瓦庄查处所谓老光棍卖淫案,无意中惊吓了“心里有事”负案在身的杨利文和苏眉,杨利文夺路而逃,苏眉瘫倒在地;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美梦从此而彻底粉碎。小说的悲剧结局,给读者留下了无限思考的空间。
《野鸭汤》看似温馨而美好,但悲剧色彩尤为浓厚。小说描写了下放知青生活,题材很有特点,故事耐人寻味。小说里有一对命运坎坷相依为命的落难姐弟,麻烦的是,他们在苦难的人生中,竟然产生了不为人知的畸形恋,当下放知青马行突然闯入这对姐弟的生活,并发自内心地爱上费小倩时,不可避免的悲剧已悄然拉开了序幕。性情怪癖且心理阴暗的弟弟费高生终于不能容忍姐姐继续同马行相爱,于是采取了极端行为,他暗害了马行,并在姐姐不知真相的情况下,在野鸭汤里下了毒,与姐姐同赴黄泉。前途似锦的知青马行和命运多蹇的费小倩姐弟,都成了那个特殊年代可怜的牺牲品。
《蜗牛班》所讲述的故事,除了“毫不留情地直指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同时也直指偏僻农村的教育困境”(傅翔语)之外,还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难忘的农村教育工作者齐建成的形象。50多岁的齐建成是偏远山村头井小学身兼多职的老师、班主任、会计、总务和校长,“反正什么事都是他一个人,学生呢,总共只有14个,”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他一入唱独角戏。这个学校穷得可以,粉笔要省着用,粉笔擦子从来没买过……就是这样的穷小学,其教学成绩在学区排名前五位。后来一个偶然机会,这里来了一位姓张的省城记者和一个叫做李素的女孩,他们的到来使得这所小学焕发了生机。张记者在深入了解头井小学的境况后,在省报上发了一篇“脸盆那么大一块”文章,还配发了齐建成和学生的照片,于是产生了轰动效应,外界的单位和团体又是捐款捐物,又是来人参观。再后来,齐建成在下山去乡政府担回省城人捐赠的物资时,不幸遭遇突发的山洪而以身殉职。当人们第二天找到齐建成的尸体时,他怀里还抱着一捆旧书……。读到这里,即使铁石心肠也难免潸然泪下。
艺术的真实来自生活的真实。余同友以其独特的视角,以其含蓄的、极具暗示性的笔触,从城乡关系的层面艺术地再现多元的农村生活,其作品在表现城乡差别时,并非一味地描写农村的贫穷落后和农民的愚昧与守旧,而是重在表现都市道德的堕落和它对乡村淳朴厚实的道德风尚的无情玷污和吞噬,并于潜移默化中唤起人们的良知和觉醒。
余同友小说创作的另一特色,是他获得广泛好评的“诗化的意象语言”。我们都知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是一切事实和思想的外衣。余同友富有地域特点的小说语言贴近生活,充满乡土气息,它清新简约、生动明快并蕴涵诗意,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请看《乡村瓷器》里一段精彩的描述:
一朵云从七月的天空飘到池塘里,在池塘里游着,一会儿游出了塘面,小武和扁伢子知道,它们将慢慢地飘过田畈,然后就飘到了瓦庄,飘到他们家的屋顶上。
四喜就是跟着那一朵云来到小武家的。云朵在小武家的屋顶上留下了影子,四喜在小武家堂屋天井下留下了影子。不同的是,那块云朵马上就悠悠地飘走了,四喜则在那里孵着不走。
简洁、诗意的几个长短句,就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小武、扁伢子和四喜等人物也跟着出场了。
余同友在鲁院的同学傅翔认为:“余同友如此清新如此地道的小说语言,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是孙犁、汪曾祺他们留下来的。如此经典的语言在余同友小说中比比皆是,它就像是作家的血脉,流经身体的每一处。它不造作,不生硬,更不是遣词造句,而是作家的生命所在。”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中肯、客观而令人信服的。
当然,余同友的小说提供给我们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旨意远远不止这些,他含蓄、多义的描述风格以及人物塑造,为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和不尽相同的诠释。
诚然,余同友的小说也并非尽善尽美,某些作品还有瑕疵,某些细节显得稚嫩,某些情节还值得推敲。譬如:其小说人物存在几处重名现象,如王翠花和扁伢子先是《乡村瓷器》里的人物,后来又分别出现在《欢喜团》和《夏娃是个什么娃》的故事中;又如胡芋藤这个人物,竟分别出现在《我们村庄好风景》和《夏娃是个什么娃》里面。然而,其人物身份和性格并无内在的统一性,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无内在的联系。另外,《蜗牛班》这部小说,在写张铁林出场时间和地点这个细节上,存在明显失误。罗城的记者张铁林为了避免与妻子的情变冲突,决定逃离罗城去远方休年假。当他花了十多个小时乘坐上海至南宁的列车来到一个小县城时,他和在列车上偶遇的李素先后下了车,而这个小县城就是不仅为作者熟悉同时也为读者熟悉的瓦县。这样的设计本来并无矛盾,但是,由于在地理概念上,读者对于罗城和瓦县的方位和距离已经耳熟能详,因此,张记者花了那么多时间乘火车由罗城至瓦县,难免就露出了破绽。其实,这个细节要改起来并不难,只要作者下笔时认真推敲一下,问题就不会出现了。还有小说的思想深度和塑造典型人物方面,也有待于余同友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加以提高和精进。
总之,余同友近年来小说创作的成就有目共睹,令人振奋,令人鼓舞。他还年轻,美好的未来正在向他召唤,只要他在攀登文学高峰的路途中扬长避短,不懈努力,笔者有理由相信,他的小说创作必将上升到更高层次,他迈进优秀作家行列的这一天也肯定不会遥远!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