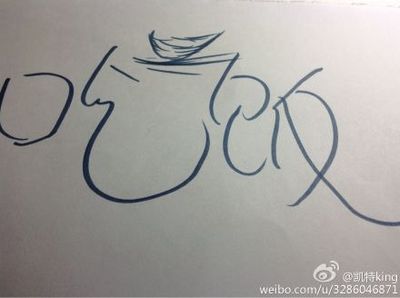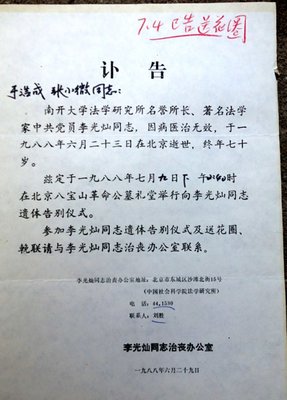于易简是谁?这个名字对许多人来说也许很陌生,但在235年前,他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山东省二把手,举省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贵为堂堂山东布政使,“掌宣化承流,帅府、州、县官,廉其录职能否,上下其考,报督抚上达吏部”,还管财税、粮食、民政、劳役、田产、人事、乡试、举荐贤能,“凡诸政务,会督抚议行”。总之,权力极大。
国泰贪腐案,史书上一般称为山东银库亏空案,是发生在清乾隆年间的腐败大案,案件的罪魁祸首是两个地方大员:山东巡抚国泰和布政使于易简。另外,两任济南知府吕尔昌(后升济东道、安徽按察使)、冯埏(调任福建漳州知府),历城知县郭德平等人也涉案其中,兴风作浪。
国泰,满清贵族,镶白旗人,姓富察氏,满清八大姓之一,是乾隆皇贵妃的伯父,富察作为乾隆宠爱的妃子,早年去世,被追赠为哲悯皇贵妃。因此,国泰可称得上皇亲国戚,国泰的父亲文绶为四川总督,弟弟国霖是乾隆御前一等侍卫。国泰在官场顺风顺水,先任刑部主事,乾隆36年(1771),由刑部郎中迁山东按察使,次年升山东布政使,乾隆42年(1777)升山东巡抚,到乾隆47年(1782)4月案发被革职拿问,在山东指鹿为马,呼风唤雨11年。
于易简(1725—1782),江苏省镇江府金坛县(今属常州)人,出生在官宦世家,祖父于汉翔任陕西学政(1698—1700),父亲于树范任浙江宣平知县,哥哥于敏中(1714—1779)是乾隆二年(1737)的状元,在1744到1747年和1753到1754年,两度出任山东学政,对山东的风土人情有切身的认识和好感,1765年他擢升户部尚书,连任军机大臣二十年,是乾隆身边的大红人,位高权重,非比寻常。
于易简比于敏中小很多,自小跟着哥哥在京城长大,监生出身。所谓监生,本意是在国子监(国学)里上学的读书人,一般先要取得“五贡”的功名,贡入国子监为学生,毕业后就有了任官的资格。这在乾隆之前掌握很严,有点现在考北大清华的意思,声誉很好,但难度极高,何况,国子监是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大学”呢。《清史稿·选举志七》说:“乾隆元年,罢一切捐例。廷议捐监为士子应试之阶,请於户部收捐,备各省赈济。从之。”这意味着从乾隆朝开始,监生都是通过捐粮(本色捐)或捐钱(折色捐)换来的,它为豪门子弟猎取功名提供了便利和捷径,也给社会风气带来了严重而恶劣的影响,可谓饥不择食,饮鸩止渴,于易简的监生资格就是这样来的。像甘肃冒赈案(国泰贪腐案前一年)中,地广人稀的甘肃一个省就有274450人报捐监生,这得办多少国子监才能容得下呀。因此,后来所有的“捐监”者都不实际入学读书,只买一个北大、清华的毕业证(监生名份),以跨过做官的最低门槛。因此,监生和真正的科举出身者进士、举人、贡生是不能比的,不算正途,矮人三分。
如此看来,这个于易简的才学有限,连个“五贡”都混不上,应该是凭借着哥哥于敏中(乾隆25年升军机大臣)的关系,在乾隆27年(1762),顺利地当上了直隶(今属河北)玉田县知县,后署磁州知州,乾隆36年(1771)升易州知州,乾隆38年(1773),于敏中升文华殿大学士,次年升首席军机大臣,牛气冲天,而乾隆40年(1775),于易简就得到了山东青州府知府的美差,官升一级,呵呵。乾隆41年(1776)11月出任济南知府,实现了重要突破。注意,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升任济南知府,首先意味着他来到了地方权力的中心,对于山东省来说,历城县为首县,济南府为首府,实际地位与别府不同,它承上启下,是通省知府们的班长和领头羊,起领率和桥梁作用。清朝惯例,进入首府的人一般先要经过省内其他地方知府的经历,不会直接委派,该“员缺紧要”,需“于通省知府内拣员调补”。像于易简的继任者吕尔昌,也是先在登州府任知府后才来的济南府。任首府知府还意味着再度升职都在情理之中,果然,乾隆42年2月,于易简升都转盐运使,乾隆43年(1778)再升山东按察使,成为三个省级干部之一,由于原布政使徐恕不明原因的死亡,他在半年时间里又升山东布政使,可谓火箭提拔。也不知道吏部官员是怎么考察的。这样计算下来,于易简和国泰直接打交道的时间至少有六年。
山东巡抚国泰是纨绔子弟,性情乖张,喜怒无常,飞扬跋扈,“嗜酒”、“好声伎”,对下属吹毛求疵,“小不当意,辄呵斥”,基本不拿人当人待,以致其妻妾、仆人都很难与其相处;于易简呢,虽然也是二品大员,堂堂山东布政使,却低眉顺眼,奴颜婢膝,曲意逢迎,投其所好,经常和国泰纵情声色,歌舞升平,花天酒地。国泰喜欢唱两嗓子(这应该是受了乾隆的影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另外一方面说,满清人极度喜爱汉文化,是清人文化自卑的一种反照。再如果引申点说,中国京剧艺术的生长、发展、繁荣、昌盛,是与清王朝奢靡、退化、衰败、灭亡相始终的。慈禧太后作为京剧的大力赏识、提携者,最终把京剧搞天上了,把王朝搞地下了。京剧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的象征),于易简也粉墨登场,与国泰一起玩票,在昆曲《长生殿》中,国泰饰演杨贵妃,于易简饰演唐明皇,真是活生生一对冤家。在戏曲里,他们扮成“君妃”,在现实中,他们扮演“君臣”,不过,顺序正好反着。
如果仅仅是这样,也不算出奇,最让人血喷的是于易简的“长跪白事”,在山东巡抚大堂,在国泰面前,他恬不知耻,自贬自抑,甘心隐忍,低三下四,反复上演不长骨头,双膝跪地,直着身子,说不完不起来的活剧,根本不像副省长给省长汇报工作的样子,这丑角演的登峰造极,无以复加,好歹他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也不知道他的“宣化承流(指官员奉君命教化百姓)”的职责是怎么履行的,真是令人切齿瞋目,恨不得踹他一脚。国泰不拿他当回事,他自己也不拿自己当人,丧失了一个官员最起码的人格。要知道,在清朝,一省的巡抚和布政使、按察使、学政之间是可以相互参奏的,巡抚有什么不当,布政使可以直接上书皇帝,“飞章上达”,巡抚无权过问,这也是皇帝驾驭臣下的一种手段。于易简呢,自我作践,在国泰面前如此卑躬屈膝,下作不堪,以至于他的下属官员,像进士出身的知府吕尔昌(1763年三甲第50名),拔贡出身的知府冯埏、举人出身的知县郭德平,都非常看不起他。这是居高位者的最大悲哀----被属下鄙视。署山东按察使梁肯堂“曾当面劝止,于易简不从”,梁“实不敢效尤”。这个堂堂不正正的山东布政使于易简太没品了,终清一朝,似无出其右者。
就是这样两个混人“官二代”,依仗着把持一省的显赫权势,沆瀣一气,“婪索属员”,遇到省内官员“题升调补”,辄设置障碍,从中渔利,通常的做法是不按照朝廷规定和惯例办理,而是由国泰交给于易简拖延,营私舞弊,吃拿卡要。当然,于易简本身就有考核下属官员的职责和便利。州县官要想得到一份美差,那更得好好上贡,只看行贿多寡,不看官声民望,只有达到国泰满意,才有可能保举上任。下属官员如果胡作非为,或不胜其任,只要给巡抚国泰打点好,也可保平安无事。国泰还打着为皇帝办贡品(这在当时是很郑重其事的“正事”)的旗号,通过于易简要求各州县属员先垫付银子代他购买各种珍奇古玩,买到以后,他则少付价款。然后,国泰又把低价到手的“物件”另定高价,让于易简、冯埏等人交各州县属员代他变卖,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这简直就是公开的敲诈,强盗买卖,这游戏谁玩得起呢?倒霉的山东官员们“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卖得掉的,算你运气好,卖不掉的,经手的官员绝不敢把“物件”退回,只好按国泰所定高价,自己先掏钱买下,再说。国泰讹人还有一手,更为直截了当:兄台,最近可好?我现在手头紧,给俩银子花花,咱说清楚了,这是“帮费”,可不是勒索。遇到这样的巡抚老爷,情何以堪?正所谓逼良为娼,变人为鬼,纵属作恶,官不聊生呀,那时山东的官员们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中足足煎熬了五六年。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乾隆听到后很不放心,1781年,在紫禁城专门召见于易简,当面追问:“国泰居官如何,其有无婪脏不法款迹,令其据实直陈”。于易简呢,极力为国泰辩白,拍着胸脯打保票,坚称国泰大人没有贪婪勒索、庇护劣员之事,只是对下属比较严厉,难免让人记恨。他回禀皇帝说:“国泰驭下未免过严,遇有办理案件未协,及询问不能登答者,每加训饬,是以属员畏惧”。自作聪明的乾隆皇帝“以为于易简为于敏中之弟,又系朕特用之人,其言自属确实。其所称国泰待下过于严厉,亦切中国泰之病。”他竟然听信了于易简的一番鬼话,使恶行在山东多持续了一年。
要论起来,这事情也不能完全说乾隆是个弱智,这里面有个心理学问题,人们总是容易轻信他所期待的事情。当时,甘肃冒赈案闹得不亦乐乎,省、府、州、县官员结成攻守同盟,共同做假账对抗朝廷,欺上瞒下。乾隆盛怒之下,下令绞刑一人,赐死一人,处斩48人,免死发配46人,另有若干畏罪自杀和病吓而死的,一个案件处理官员计113人。乾隆心有余悸,生怕再闹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案来,“朕实不忍似甘肃之复兴大狱”,面子上也受不了呀。另外,这话也印证了一个事实,于易简的快速升迁,乾隆主要是看大学士于敏中的情面,是超出一般的重用,和巡抚国泰的关系似乎不太大。
尽管如此,于易简还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帮助国泰敛财,除了帮他勒索官员银子八万两外,还在自己曾经任职的易州(今为河北保定市易县),以国泰弟弟国霖和两个侄子的名义,花巨款为国泰购买良田八千亩,外加五个大庄园,用于出租谋利。这事情干得很隐秘,几乎没有几人知晓,好像还有点智商。

布政使于易简最为“可贵”和“神奇”的一点是,虽然帮助国泰贪腐甚巨,造成的库银损失甚大,自己并没有贪污受贿,查无实据,“惟年节收受属员水礼绸缎等物”,就是过年过节收点年货绸布之类的,这在清朝不算受贿,没收过银子,甚至也没有像国泰那样购置房产,地产,田产,没有往老家转移过资金,怪吧。说怪也不怪,因为他的品行太差,“长跪白事”的丑行无人不知,“是以通省官员,共相鄙薄,不肯送给银两”,根本没人理他。他的死不是死在贪污受贿上,甚至也不是死在为虎作伥上,而是死在结党渎职,当面蒙蔽皇帝上,欺君之罪,罪莫大焉。
可是,于易简为什么要欺君呢?按照乾隆的想法:“设其时,于易简将国泰贪婪款迹据实陈奏,不但国泰营私不法之事可以早行败露,而于易简秉公持正,朕必特加褒奖。”说不定就升成山东巡抚了呢。“于易简身任藩司(指布政使职),受恩最为深重,明知国泰种种不法款迹,既不行据实参奏,复敢于朕前欺隐,其罪较重”。于易简之所以死保国泰,有些人不大理解,我觉得,可能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他才学不足,头脑有限,监生出身,一直在哥哥于敏中的羽翼下长大。虽然逐步飞黄腾达,官职高企,但其人德薄智微而又位尊任重,玩的是心跳,就像不会杂技的人走钢丝,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时(1781年),乾隆向他问话时,他的权倾朝野的哥哥已经去世两年,如果国泰这棵大树再倒了,对他来说是一种没有靠山的感觉,或者说在他的心目中,自己与国泰变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只有死保国泰这一条路了。由此,他也把自己送进了死胡同。
乾隆47年(1782)4月初,朝廷派大臣和珅、刘镛、钱沣到济南查案;5月初,将国泰、于易简、吕尔昌、冯埏、郭德平等革职拿问递解到京;6月,九卿候审,判决国泰、于易简斩监候,秋后处决;7月,继任山东巡抚明兴查实山东历城、章丘、东平、益都各州县亏空国库银200多万两,乾隆“实堪骇异”,即将“国泰、于易简,著加恩赐令自尽”。吕尔昌、冯埏、郭德平等人分别被发往伊犁和黑龙江,或充军或劳役,山东库银案告一段落。
很显然,乾隆对国泰案做了降调处理,将大事化小,不然掉脑袋的不只是两个人。但纵观乾隆60年执政,国泰贪腐案不是一起孤立的案件,它和乾隆朝的许多大案类似,性质极为恶劣,均属窝案、串案、高官主导下的集团作案,与粤海关三度腐败案(乾隆23年,33年,51年)、两淮盐政案(乾隆33年)、驻叶尔羌办事大臣案(乾隆43年)、云贵总督李侍尧案(乾隆45年)、江苏巡抚闵鹗元包庇贪吏案(乾隆55年)、浙江巡抚福崧两次贪腐案(乾隆51年,58年),还有文中提到的甘肃冒赈案等,共同标志了清朝衰落的真正肇始。据曹松林先生的研究,从乾隆元年到乾隆60年,贪腐案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仅大的贪腐案件就不少于46起,到乾隆中期后,达到公开而疯狂的地步,无从遏制,无法阻止。包括于易简的哥哥军机大臣于敏中在内,也是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甘肃冒赈案主犯)等许多贪官的靠山,乾隆后来彻查,发现其家财有200万之巨,于敏中的牌位被请出贤良祠,子孙被削夺世职。乾隆认为:“贤良祠为国家风励有位盛典,岂可以不慎廉隅之人滥行列入?”
但这些案件和和珅贪腐案比起来,都不在一个等量级上,大老虎和珅就像个核武器,一个人的破坏能量可以撼动整个国民经济。有人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嘉庆查抄和珅的财产清单进行了计算,和珅所聚敛的财富,约值八亿两至十一亿两白银,所拥有的黄金和白银加上其他古玩、珍宝等,超过了清政府十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在《清史稿》和珅传中,嘉庆皇帝列举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其中“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馀,多於大内(皇宫)数倍,大珠大於御用冠顶,大罪十五。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整塊大宝石不计其数,胜於大内,大罪十六。藏银、衣服数逾千万,大罪十七。夹墙藏金二万六千馀两,私库藏金六千馀两,地窖埋银三百馀万两,大罪十八。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赀本十馀万,与民争利,大罪十九。家奴刘全家产至二十馀万,并有大珍珠手串,大罪二十。”由此可见一斑。
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以他的自鸣得意为自己豢养了前仆后继、绵延不绝的腐败分子,自坏朝纲,自毁长城,他本身就是贪污腐败的总根子,对臣下的进贡永远津津有味,乐此不疲,不分过年过节过生日,来者不拒,大小通吃。乾隆22年,他还将康熙确立的四口通商改为广州一口通商。在乾隆看来,对外通商,主要就是接受外国的贡品,用不了那么口岸,关税也定的极低,他一人所接受的各类贡品占了整个清朝贡品的一半,而对御史钱沣废除进贡制度的劝谏则王顾左右,不以为然。他的宠儿和珅发明的“议罪银”制度,意味着花钱可以顶罪,这和“捐监”制度一样是颠倒黑白,以非为是,祸乱国家的混账逻辑。
我们有理由去除笼罩在乾隆身上的光环,还“康乾盛世”为“康雍盛世”的本源,看清乾隆帝的真面目。
打铁还需自身硬,乾隆吃贡上瘾,六下江南,好大喜功,玩物丧志,用自己一生的荒唐执政,将祖父辈治理国家的硕果侵蚀殆尽,令恶例合法并横行无阻,致嘉庆登基时,全国各地府库亏空已达2000多万两,为大清的最终灭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而于易简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斗筲帮凶。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