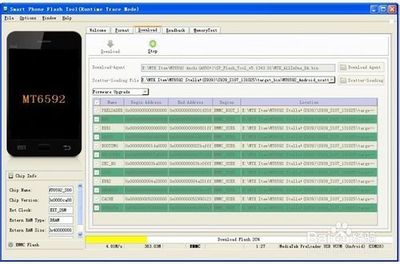生活在江南,往年每到四五月间,天上总断断续续飘着些雨丝,大的能够淋湿了人是衣衫,小的可以把人活活闷死,不过城市中小河的水会变得清亮许多,少一些隐隐泛出的恶劣味道,至于气温则是一年中最适宜的,跑着不出汗,走着不发抖。拂面之风是清新的,还带着江南独有的香气,香樟的清雅,白玉兰的浓郁,更有小城老太钟爱的白兰花,摘了两三朵,串在一起,别在衣襟的纽扣上,一路慢行满身的香韵。雨不紧不慢地下着,江南也就淡淡地蒙上一层朦胧,有一点梦幻中的诗意。
有时候面对稠雨也恨地牙痒痒,这长脚雨湿了衣衫不说,还把空气潮得可以拧出水来,这家中墙上的字画,书架上的旧书,可都是心肝宝贝的东西。从来没有想过江南的春天无雨,小城将会是如何的模样,似乎记忆中这是空白的。
谁料今年江南果然无雨,城市上空弥漫风沙不散,气温节节攀升,没到端午已经大汗淋漓,身上的衣衫一件件剥去,街上美色横流,女孩子再少一件就可以上演北京街头行为艺术,这要是到了六月,还不要扒了周身的皮。只是天有不测风云,刚还在担心惶恐的时候,雨姗姗而来,老天或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加倍补偿讨好,这下江南又惹了祸端,水淹了马路进了厨房。
无盐
生活在如此状态下,人很烦躁,偏是好事之徒还不时耍点神经。那天一早小胡给我发来条短信,就七个字:礼义廉孝悌忠信。看着发笑,这小子乘机考量我呢,我也给他回了七个字:柴米油菜酱醋茶。他立马就把电话打进来,手机那头笑得那个欢,苏哥,你还真知道市面上没盐买了。我苦笑,他母亲的,我家那盐罐子朝天了,跑楼下便利店去买盐,那苏北小女孩竟然给了我一个惊诧的眼光,好像我刚才神农架回来的一样。小胡咯咯的笑,像小狗掉粪坑的扑腾样:那你昨晚的菜就没搁那东西?我担心的说,问题是今晚怎么办,我总不能够跟我老娘以前养的花猫一样,整天吃那没盐的鱼腥吧。
打开电脑不用搜索,南方抢购食盐断货已经上来首页,原因竟然是浙江佬怕日本人核电站爆炸后的辐射,说是食盐可以防止,另外爆炸污染了大海,这以后出的盐是有核毒的。浙江佬一下就把本城的食盐搬回了家里,于是广东广西江苏等南方紧跟而上,呼啦啦席卷举国上下,都忙着把盐搬到自己家里。老实说这新闻看地我瞠目结舌的,日本人的海啸地震核爆炸没把日本人急得跳海玩,隔着蓝蓝的宽阔的浩瀚无边的大海,竟然把中国人炸神经了。这盐如果都能够防范了东洋人的核辐射,那它还能够越过大海长途跋涉来射杀你,如果太平洋的海水都给污染了,你不吃盐就可以保命了?
没法子我还得去买晚上烧菜的盐,骑着车赶去大型超市,进门后直奔买盐的货柜。结果还是可以预见的,货架空空荡荡,连盐星子也没瞧见,问超市的服务员,回答跟发疯似的,库存都买光了。既然没有,也就省心了,慢慢在超市里闲逛。
最近一段时间我挺享受信步闲走超市的感受,推了辆小车,随走随停,翻翻杂志,看看老太太争抢便宜的勇猛景象,老汉健步飞奔特价商品的速度。某专家人说,一个人某种习惯的养成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加上连续的重复,但是要戒除养成的嗜好也许得花上一辈子的时间,最典型的莫过于吸烟这件事情。我不知道闲逛超市的机械动作,会不会成为我接下来的一个难以戒除的习惯。
说也邪门,刚出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正巧是讲中国的盐。一笑,拿起细看,省却带回家要花的那几个银子,这可是能够买好几袋盐的,如果全吃进肚子里能够直接把人送回老家。真没想到平素看似普通的盐,在摄影师的演绎下会是那么震撼人的眼球,与人们陌生而神往的北极冰川什么的,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大自然的美丽果然不是人的想象能够包容的。世上的事情蛮奇怪的,地理杂志的编辑怎么就知道了东洋人会遭老天的灾害,然后晓得我们会忙着抢购天天都离不开的食盐!难道这些看着似巧合的故事,都是人们早就预谋的策划?
老太太们的智商是怎么也敌不过商人的,毕竟曾经的穷困是他们老一代心头的伤痕,年轻的孩子们是无法感知那些年代的辛酸的。一无所有的日子对于母亲来说,除了默默泪流,我不知道她还能够怎么样?我的母亲过世后,清理母亲的遗物时,竟然发现十几块已经如石块般坚硬的肥皂,母亲用报纸将它们包裹着藏在箱子的角落。小孩子们也许无法想象,当年肥皂也是凭票供应的,母亲用河边捣衣的旧法,一点一点省下这几块肥皂。
文化和公信或者其他东西的边缘,不是某些人造成的,恰恰是全民所为的结果。日本地震之后,很多人为几张东洋人排队拿救援物资的照片而感慨万分,一边称赞日本人的高素质,一边鄙薄自己国家百姓的没素质。然而实在不明白,在日本这样灾害频发的国家,饮用水怎么会如此紧张?其实我真正不明白的,一个远离日本一百三十公里的在太平洋地震,居然把一个号称有严密控制灾害措施,尤其是防御地震和海啸的日本,搞得如此狼狈,建筑在海边的核电站更是毁于一旦,那么关于这个岛国的许多美丽故事,不过是新汉奸们的神话传说罢了。
盐紧张了一天,第二天我再去超市,老太太们连看都懒得看它们一眼。
分别
天气依旧炎热无雨,新闻里说人们已经开始抢雨了,黑云压来一路的火箭弹加增雨弹的。老天也许会摇头,还要跟我斗啊,没吃够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其乐无穷之苦?
就在这缺水高温的时候,我时隔半载拨通了老夏的手机,电话那头乱哄哄的,听着他似乎很忙碌的样子。于是问他,是不是很忙啊,要不我待会再打给你。老夏忙着阻止,不忙!那些破事比不得你电话的重要。我笑骂,你妈妈的,调戏我。把我当成十八岁小女生了。老夏一本正经的回答,没有的,我不敢那样想的,那还不吐了隔夜的饭菜,你晓得现在的蔬菜精贵呢。我说,不跟你废什么唾沫。下周我请你吃个饭。老夏迟疑问,你换老婆了?我惊愕,你不怕她屌在你家的水晶灯上。老夏笑的非常可恶,那地方是我老婆专用的位置。
我找老夏还真的是请他吃饭,当然目的不是叙什么狗屁感情。我家侄子挑了个五月里的一天讨老婆,我得乘机敲他一笔。我说车子征用,红包厚点,要不你这个被称为“巧克力叔叔”的人忒没面子。老夏听完蹦出一句我没料到的话:你要当爷爷了。
我没理会他的话,跟他快一年没见了,这个弹丸小城怎么就变得这般的浩淼无边的。春节那当口跟星兄小聚,打电话给问他在哪里,他说千里外的河南,星兄当时没克制住,骂他嫁了女人忘了娘。老夏当时可能一下子懵了,支吾了几声我们没听懂的就挂了电话。我说星兄,你哪来的火气?后来我才知道,星兄他老娘又进了危重病房,这一年里已经是第三回了。我也不想跟老夏去说这故事,朋友间事情有时候该他自己去思量,谁知道一晃竟然半年匆匆。
老夏来的时候西装革履,比我这个当叔叔的人穿得还正式,我惊异望他:你不热?老夏笑的时候有点诡异。星兄赶来的时候已经快开场,他风尘仆仆的样子也让我奇怪:你这是打哪里来啊,不是说很空闲吗?星兄一笑,没回答。见老夏立马有声:夏总早来了,今天不醉不归啊。老夏说,我开车的,不喝,要坐牢的。星兄说,我管你呢,我顶多明早给你送床被子。老夏说,我还怕你,豁出去了。回头对我哥哥说,大哥给我们上白的。
正闹着我嫂子来跟我讲,原来做证婚人的孩子他领导被堵半道了,眼见婚礼要开始,这可怎么办。我眼睛朝星兄看,这家伙贼精,一边摇头一边指着身上的衣服:不成,我这打扮跟民工似的。夏总正装出席,就是给你们备着的证婚人。老夏推辞的话还没出口,我们都有恶狠狠的眼光看他。老夏不再说什么,整整衣襟,面带微笑,然而问星兄,你阿开心啊。
其实他们两个之间是有小插曲的,老夏节后回苏州,星兄特意请他单独吃饭,意思很明显为自己那天的失口赔罪,老夏一口答应。谁知道吃饭那天,这家伙居然去了上海,等星兄打电话给他时,老夏一拍脑袋说给忘了。老夏还真的不是故意耍小女孩的矫情,这阶段他为公司扩容的事情忙地焦头烂额,整夜的睡不着掉头发,按星兄的话这厮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那些事根本就是他瞎操心,贵妇一手都能够扯平。我问星兄后来怎么了,老夏插言,你没见他那神态,靠着老街的窗口,自斟自饮,不要太惬意哦。
酒过三巡,老夏的话多起来,还专讲眼前家里的事情,养着的藏獒送人啦,“孩子”申请墨尔本的大学啦,老娘天天烧了午饭给他送到公司啦,又说自己报了个英语班,正努力学习鸟语。孩子过来敬酒时,老夏把杯中酒加满一饮而尽,很是有点临上法场的味道。我很奇怪自己脑子里怎么会闪现这个不搭边的词汇。不过我和星兄虽感觉他有点异常,但始终没提一个字,倒不是怕勾起他的心事,而是怕坏了小孩子大喜的气氛。老夏最后还是忍不住,翻了半天的手机,把一条短讯放到我面前。
你要移民了?我说的时候声音有点发颤。
看画
老陈是我目前正耗着的公司的同事,平常不太讲究衣装,属于不修边幅的那类。不过他抽烟,还跟我抽相同牌子的,比起其他烟瘾实际比我厉害,却在老外前装清纯环保健康人士的斯文人实在。最初跟老陈也就是躲在门口旮旯抽烟的交情,直到有一天在古旧书店不期而遇,才开始有一点朋友的交谈,之后又一次不期而遇在博物馆的展厅里,方才成为家中座上客的朋友。那次辽宁博物馆将馆藏的清人徐扬的《盛世滋生图》长卷交流来苏州展览,因为徐扬是苏州籍的宫廷画师,长卷又描绘了盛世时期苏州的城市场景,所以在城内引发不小的轰动。老苏州内心的恋旧情节一下子激发,为了看幅画要排上几小时的队伍,恐怕也只有在这个城市才会发生了。
我是在画展的最后几天去的,原因是不想挤在哄闹的人群中,感受那份失常的艺术情节。在博物馆这样的地方,我个人以为闲庭信步的氛围比较好,一窝人扎在一起还是去酒吧比较妥当。遇见老陈时有点诧异,这跟他平时的表现相差有点距离,当然诧异的眼神我在老陈的眼睛中也看到了,或者他当时与我有同样的想法,他是随着大众一起来轧个闹猛吧。
徐扬的《盛世滋生图》长卷又称《姑苏繁华图》,是乾隆为纪念自己的爷爷和自己几度下江南,特意让徐扬画的,史料中说徐扬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才完成。后来画著收录在《石渠宝笈续编》中,溥仪逃去满洲当傀儡皇帝时,把此画带去了长春。长卷之所以为老苏州认同,是因为画卷上的很多图像,在今天的苏州城还能够找到,比如画卷起自城西的灵岩山,经木渎,过横山,渡石湖,进城后,再由葑门、盘门、胥门,直到阊门,然后转入山塘街,最后到虎丘山麓,这些景致在今天的苏州一样都不少,模样也基本不变。苏州这个城市恋旧情结相当严重,且不说清人笔下的图画基本未变,即便是宋人《平江图》上的巷闾格局也几乎未动。
老陈在看画时跟我攀谈,说有专家撰文怀疑这画是假的,不是当初徐扬的原画,证据有几个,画上序跋与《石渠宝笈续编》上的跋文有几处不同,阊门的描绘与同时代绘画和史料记载的不同,还有长卷不是整卷画纸,而是由十几张长短不一的宣纸拼接成的。我说这个人的文章我也看过,先前还觉得有点意思,可是读到他把金阊门臆想成今天苏州城的金门阊门,就完全没兴趣了,他连苏州金门城楼修建于民国时代都不知道,金阊门之说只是郡人对阊门繁华之喻,哪还有什么资格去评说画卷。造假摹仿古画历代都有,但仿皇宫旧藏的鲜见,一般仿造无非是图利,如果选徐扬的十二的米的写实长卷,这个人肯定是脑子坏掉了。
事后老陈约我几次去他家里坐坐,说是有好东西让我看看,我口中答应却一直没去,说老实话我怕去看,如今收藏古董的人太多,看了几本画册就想去觅一个宝贝,然后成为捡漏的幸运者,天下哪有那么多好事情等着你!直到老陈跟我讲家里有左宗棠的条幅,金底红边很有气势。我蛮喜欢左大人的,兴趣立刻被勾引,没废什么话跟着他就回家。老陈住在平江路上的岔巷里,石板的小路,一旁是小门大宅的庭院,一边靠河杨柳依依,环境不是一般的好。走到他住的大院前,看了一眼门上挂着的木牌子,不由摇摇头,说自己怎么不早来。原来老陈现在住的地方是居然是唐纳的故居,唐纳就是蓝萍(江青)的前夫,按这个缘故他和老毛的关系可不一般。
左大人的条幅挂在老陈的厢房里,第一眼觉得匠气浓了,少一点书卷气,左公虽非进士出身翰林老爷,但毕竟是一介孝廉老爷,寒窗苦读十载,他压根不是什么书法家,笔下是出不了书匠之气的。再看到条幅纸本中的双龙金描瓦当纹,左压角的“宗棠之印”“大学士章”钤印,做旧后仿基本是一定的。老陈见我蛮认真的模样,一旁说纸本和墨迹还有印泥都没啥问题。我说别跟我讲装裱,我又没学过裱糊匠的手艺,你讲的我根本不懂。
我知道老陈年少的时候跟老师傅学过几天裱画。“苏裱”是国内裱画行业中的翘楚,尤其在明代经文人的大量参与,其高超技艺之外更有一股文人的雅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曾有“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的赞誉,其实“苏裱”最出彩的还不是装裱,而是修复古画的功夫,所谓“书画郎中”的本事,支离破碎或褶皱残缺,经老法师之手,竟能够起死回生。当然老法师们手里有些东西是其他人没有的,比如前朝的纸墨印泥,独特的捣糨糊之法。老陈学装裱都何年马月的事情了,他早把那些窍门抛到九霄云外了,我曾经讨教过他捣糨糊的事情,老家伙居然扯半天捣了半天嘴皮子浆糊。
老陈见我没搭理他的条幅,知道再问也没啥好听的,所以就岔开了话题,挑了几件家里好玩的东西让我看,其实我真不懂那些门道,跟着胡扯浆糊,反正老陈这厮也外行的厉害,自说自话图个嘴上快乐。日落西山,我掐了烟蒂起身告辞,老陈望了一眼左大人的条幅。我笑出来,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真外行,看不懂。
那个收藏了许多宝贝的马未都马师傅曾经说,当你不懂的时候,就说东西是假的,十成中的九成九把握。
这世界真到末日了?
西苏于吴中沁庐东隅
二〇一一年六月九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