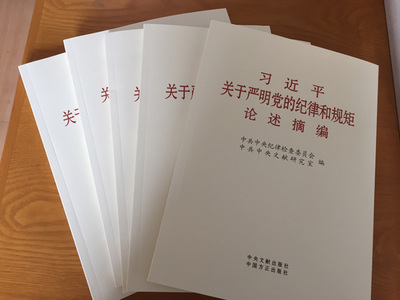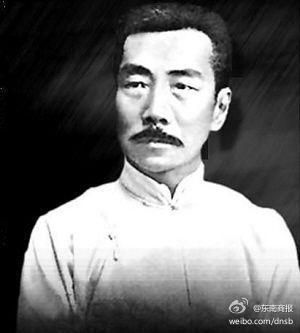蒲伯(Pope)在他的早年作品《论批评》(Essay on Criticism)一诗里,说过这样的话:
These rules of old,discovered,not devised,
Are nature still,but nature methodized.
Nature,like liberty,is but restrained,
By the same laws which first herself ordained.
这几句话的意思大概是:“古代的规律,乃是发见的而不是捏造的,还是‘自然’,不过是经过整理后的‘自然’。‘自然’就和自由一样,只要受她原来创造的法则所节制。”简单的说,蒲伯的意思是说,规律是不悖于自然的,并且自然本身也自有其自然之法则。
蒲伯是英国的新古典派的批评家,《论批评》这首诗可以说是集英国新古典派的意见之大成,上面这四行也是里面最警辟的几行。“新古典的”这一个名称在如今是一个令人唾弃的用语,所以蒲伯和那一派的批评学说在现今不能赢得人们的信仰。自从浪漫派的学说在近代得势以来,有两大思想横亘在一般人的心里:一个是“天才的独创”,一个是“想象的自由”。在西洋文学里,晚近的潮流差不多都是向着这两个方向走。所谓“天才”是对着“常识”(Goodsense)而言;所谓“独创”是对着“模仿”而言;所谓“想象”,是对着“理性”而言;所谓“自由”,是对着“规律”而言。总结起来说,全部的浪漫运动是一个抗议,对新古典派的主张的一个抗议。这一个抗议是感情的,不是理性的,是破坏的不是建设的。换言之,浪漫运动即是推翻新古典的标准的运动。
新古典派的标准,就是在文学里订下多少规律,创作家要遵着规律创作,批评家也遵着规律批评。首先把文学标准“规律化”的,不是亚里士多德,不是古希腊的批评家,却是罗马的批评家何瑞斯(Horace)。读过他的《诗的艺术》的,应该熟悉他的“适当律”(LawofDecorum)。何瑞斯所谓的“适当”,即是一大堆文学规律的总和。我且引哈克教授的一段的解释(见《哈佛大学古典文学的研究》卷二十七,R.K.Hack:Doctrineof Litorary Forms第二十二页):
……一切文学的作品,无论是描写人物或是建筑格局,各型类均各有其确定不移的形式完美的规律。守此规律的即为适当;否则失败。所以“适当律”便是理想形式与实验作品中间的一种作用;其效用西塞罗曾详为解释。例如:理想的悲剧分为五幕,若分为四幕或六幕,便不适当了。理想的老年人,必缺乏热心,诸事延迟,易触怒,喜怨言,对年青一辈人常作严酷的批评:如其把老年人描写成为一个热心的,敏捷的,慈善的,这便是违反了“适当律”。
这不过是只举出新古典派的始祖所订下的两条规律:一是悲剧必分五幕,一是人物必合型类。我们已然可以看出这样的批评学说是很无谓的。好的戏剧,一幕也可以,两幕也可以;有文学价值的人物,正不必一定丧失他的特有的人格。新古典派受人攻击者,以此。浪漫派所凭以号召者,亦以此。再举一个例,例如“戏剧的三一律”,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产物,喀斯台耳维特罗确定的,斯喀利哲儿宣扬的,到后来法国学院为了审查一篇不合格的“LeGid”掀起了文学批评里最大的一个辩论,一面说不合三一律便不适当,一面乃怀疑三一律是否适当,因此引出了文学里权威与自由的问题。这一场大辩论,是严酷守法的新古典派占胜,还是倡言反抗的占胜,这是不问可知的。
文学的规律是应该推翻的,浪漫派的批评家不是无的放矢。阿迪生是英国近代浪漫运动的一个先驱者,他在一七一四年九月十日的《旁观报》上说得好:
……有些人对于文学的规律是十分的熟悉,但在特别情形之下偏与规律相悖。古代悲剧作家中,此种例证,不胜枚举,彼等故意的违犯一个戏剧的规律,以成功一种更高的美,为恪守规律者所不能及。……这就是意大利人所谓艺术中之GustoGrande,亦即吾人所谓文艺中之高超性。……伟大的天才,不知艺术规律为何物,但其所作,往往比恪守规律之小天才为更美。……
但是浪漫主义者所推翻的不仅是新古典的规律,连标准,秩序,理性,节制的精神,一齐都打破了。浪漫运动的起因是不可免的,且是有价值的,但其结果是过度的,且是有害的。由过度的严酷的规律,一变而为过度的放纵的混乱。这叫做过犹不及,同是不合于伦理的态度。上面提起的“天才的独创”与“想象的自由”,便是浪漫的混乱之理论的根据。
上文是根据西洋文学史上的事实说明新古典派与浪漫派的势力消长的来由,其实这两种势力永远是存在的,有时在一国的文学里,在一时代的文学里,甚至在一个人的文学里,都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开扩的感情的主观的力量,一方面是集中的理性的客观的力量,互相激荡。纯正的古典观察点,是要在二者之间体会得一个中庸之道。规律是要打倒的,而文学里有超于规律的标准。我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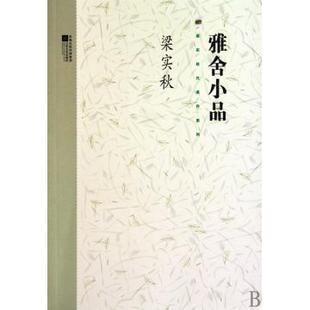
吾人不可希望文学批评的标准能采取条律的形式,因为“人性”既不能以条律相绳范,文学作品自不能以条律为衡量。不过我们确信文学批评有超于规律的标准。凡以“理知主义”趋诸极端者,和“绝智主义”一样,同是不合于“人性”。……(见《文学批评辩》)
总而言之:文学里可以不要规律,但是不能不要标准。从事于文学事业的人,对于这个标准要发生一种相当的关系,那便是文学的纪律的问题。
(二)
凡从事于文学事业者,无论是立在创作者或批评者的地位,甚而至于欣赏者的地位,其态度必须是严重的。晚近文学界,有许多与严重性相反的趋向。在艺术里,态度是最要紧的;所以讲起文学的纪律,首先要讨论文学的态度。
社会里永远有一个不能了解文学艺术的阶级。阿诺德所痛心疾首指责不遗余力的“非力斯侗,已然成了一个不朽的名词。其实足为文学艺术前途之是的,不是任何十足的不懂文学艺术的阶级,而是潜伏在文学艺术以内的而态度又不严重的人。
近代文明特出的一种产物,名叫T.B.M.,就是英文“倦了的商人”的缩写,他的特点是一天做了八小时的工作,筋疲力倦,余下来的时间所须要的是一点娱乐,是靠在沙发上口衔雪茄读一本新出的爱情小说,或是踱到戏园去看一出连唱带做的音乐喜剧。把文学艺术当做消遣品,便是一个不严重的态度。社会上这种不严重的态度一天比一天激进,从事文艺的人便有心无心的受了绝大的踏入歧途的引诱。近代的批评家说,文学要适应潮流,初不问这个潮流是属于什么样的质地。其实文学的创作,或宽泛些说,一切的文学作品,不是走在潮流前面,就是走在潮流后面,无所谓适应不适应。T.B.M.所须要的文学,是不含深刻意义的文字,同时就有人引了“游戏学说”(PlayTheory)来做理论上的根据。他们说,文学的创作本来就不过是人类游戏的本能的表现。游戏的结晶,拿来做饭后的消遣,谁云不宜?这样推论下去,文学作品能与人以最大之消遣,便为有最大之价值。换言之,文学的价值要纯视销数多少以为断。文学的标准定在群众的胃口。T.B.M.还不过是社会上对文学缺乏严重性的人的一种。然而他却可以代表一般群众对于文学的态度。求急功近利的创作家,也便随着走上不严重的路。这也便是经济学上所谓之供求相应的道理。伟大的文学者,必先不为群众的胃口所囿,超出时代的喧,然后才能产生冷静的审慎的严重的作品。歌德是个最厌恶群众最鄙视社会的人,他在一八二四年正月二日《与爱克曼谈话记》里说:
目前我们的天才是在群众的手里。无处无日不有批评,社会的群众也因此而纷纷议论,真正健全的作品在此种状态之下决不能够产生。如今若是不能与此种环境隔离,必致失其所措。
创作家所当顾虑的,不是群众的议论与嗜好,而别有超出环境的标准在。
另有一种人的态度,也是不严重的,但是比较的不容易辨视,所以其影响也就更为致命。这个态度便是好奇。我先引阿诺德的一段话:
关于智识的事物,有一种好奇是无聊的,并且是病态;但另有一种好奇,——是一种研求心灵上的事物的欲望,为的是因能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喜悦,——这种好奇心对于一个有智慧的人该是很自然的,并且应得称赞的。
阿诺德不承认第二种的好奇只是好奇,因为他给“文化”下定义曰:
文化正当之解释,其起源不是由于好奇心,其起源乃由于完美之爱好;文化即完美之研究。(俱见《文化与混乱》第一章)
好奇是研究文学创作文学的一个大玻英国十八世纪浪漫运动初期之一般的“Virtuosi”(搜求美术品者),法国印象主义所代表的那种Dilettanteism(游艺主义),这全是纯粹的好奇心的表现。文学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而此人性并不是存在什么高山深谷里面,所以我们正不必像探险者一般的东求西搜。这人生的精髓就在我们的心里,纯正的人性在理性的生活里就可以实现。人性是不希奇的,从事文学的人,若专从“奇”处着想,这条路便越走越远,所谓“道不远人自远之”。何瑞斯所谓“NilAdmirari”,英文的意思即是“To wonder atnothing”,亦即从事文学者不从“奇”处着想的意思。文学的研究,或创作或批评或欣赏,都不在满足我们的好奇的欲望,而在于表现出一个完美人性。好奇心的活动是任意的,不拘方向的,漫无别择的;文学的活动是有纪律的,有标准的,有节制的。
文学是男性的,强健的;不是女性的,轻柔的。把文学认为是女性的产物,这种观察的发生是很早的。弥拉(J.H.Mimlar)在他的《十八世纪中部之文学》第五页上有下面的一段有趣的记载:
柴斯特菲尔德是一个标类的代表,也是当时的一个政治家;何瑞斯渥尔波耳是一个十足的游艺者,也不曾与政治完全脱离关系。戏里的劳夫地先生说得好:“我们有事业的人,看不起现代的作家;讲到古代作家呢,我们也没有工夫读他们。诗是很好的东西,为我们的妻女,但不是为我们。”……
如今恐怕还有人这样相信,以为男性的力量只在机械工程或银行簿记的事上发展。殊不知文学是一种极严重的工作,——创作者要严重的创作,然后作品才有意义;批评者要严重的批评,然后批评才能中肯;欣赏者要严重的欣赏,然后欣赏才能切实。
(三)
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新古典派所订下的许多文学的规律,都是根据于节制的精神,但是那些规律乃是“外在的权威”(outerauthority)而不是“内在的制裁”(internalcheck)。把“外在的权威”打倒,然后文学才有自由;把“内在的制裁”推翻,文学就要陷于混乱了。新古典派所主张的是要执行“外在的权威”,以求型类之适当;古典派所提倡的是尊奉“内在的制裁”,以求表现之合度。这个分别是很清晰的。
所谓节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Reason)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
实在讲:理性与情感不是对峙的名词,就和“浪漫的”与“古典的”不是对峙的名词一样。我先引译阿伯克龙比教授(Abercrombie)一段很有见地的话(见《浪漫主义论》第三十一至三十四页):
以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对峙而言,甚为不当,因为古典主义不是列在浪漫主义同等的位置的。我曾说,浪漫主义是一种原质……古典主义呢,决不是一种原质,而是许多原质混合的一种状态。……古典主义就是艺术的健康:即各种原质的特点之相当的配和。如其你要寻出一个古典的成分,以与浪漫的成分相对立,必定劳而无功,因为二者不是对立的。无所谓古典的成分!不过有许多成分可以平稳的配合起来,这种配合,这种健康,就是古典主义了。我不知道这些成分有多少,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确数;浪漫主义却是其中之一……
确切的说,阿伯克龙比的解说是精当的。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畸形的现象,要做到这个地步,必须要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所以我屡次的说,古典主义者要注重理性,不是说把理性作为文学的惟一的材料,而是说把理性作为最高的节制的机关。作为浪漫的成分无论在什么人或是什么作品里恐怕都不能尽免,不过若把这浪漫的成分推崇过分,使成为一种主义,使情感成为文学的最领袖的原料,这便如同是一个生热病的状态。以理性与情感比较而言,就是以健康与病态比较而言。
感情主义(Emotionalism)是浪漫主义的精髓。没有人比卢梭更富于感情,更易于被感情所趋使。卢梭个人的行为,处处是感情用事,一切的虚伪,浮躁,暴虐,激烈,薄情,在在都是情感决溃的缘故,我们试读他的《忏悔》,就可以觉得书里的主人是自始至终的患着热病,患着自大狂,被迫狂,色情狂……一切的感情过度的病态。他是天才,是的,是一个变态的天才。卢梭的思想,也是弥满了感情主义的色彩,他自己说得好:“余之哲学非由原理演绎而得,乃由情感抽引而出。”文学里的感情主义当然是不自卢梭始,卢梭以前就有了“卢梭主义”。最明显的证据:卢梭的《新爱绿绮思》便是受了英国的李查孙的《克拉丽撤》的启示。台克斯特(Texte)所著《卢梭与文学里的大同主义》一书关于此点叙说得最详荆德国的“狂飙运动”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情感主义的混沌!近代的所谓“未来派的戏剧”以及战后新兴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新艺术,无一不是过度的情感的产物。
情感不是一定该被诅咒的,伟大的文学者所该致力的是怎样把情感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忱,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亚里士多德于悲剧定义中所谓之“Katharsis(涤净之意),可以施用在一切的文学作品。文学固可以发泄极丰烈极壮伟的情感,而其抒情之方法,却大有斟酌之处。文学本身是模仿,不是主观的,所以在抒泄情感之际也自有一个相当的分寸,须不悖于常态的人生,须不反乎理性的节制。这样健康的文学,才能产生伦理的效果。今且举雄辩的艺术以为例:希腊的雄辩术,是一个独立的艺术,第一流的雄辩家其遣词命意全要经过选择,用各种艺术的技能使听者为之动容,为之情感兴奋,然而在结尾的地方,必须极慎重的把紧张的空气松弛下来,使听者复归于心平气和之境。这是真正的古典的法度。现今所谓的演说,尤其是煽惑罢工的领袖的演说,一个人全部的为感情所支配,讲者叫嚣暴躁,听者为之摩拳擦掌,结果往往是一个暴动。这个分别是浅而易见的:一个是有理性统驭的,一个没有。文学也是如此。伟大的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
情感也有真假之分:真的情感是自然流露的,假的情感是故意造成的。有一种人,感情的生活养成了一种习惯,非在情感紧张的状态之下不能得到安慰,于是凡遇不关痛痒的刺激,也立刻发生情感的反应,是之谓伤感,是之谓无病呻吟。伤感主义近来已成了流行的症候。一个标类的伤感主义者,必是喜欢造做一种哀苦的围,以求自我催眠,必是要示人以无限制的同情,为一般被损害者做浮浅的抗声,必是把自己看得异常的重要,把自己的情感上的缺憾认为是人生最大恨事,必是故意的想象着自己的生活已临到险恶的绝崖,以图情感上受些尖锐的刺激,……。在英国文学里,麦克弗孙的欧迅诗,大概是可以算做很早的伤感的作品,勃恩斯的《给一只老鼠》也大有伤感的意味,拜伦更有极大的伤感的成分。伤感主义者的一个根本信仰,就是人性善。所以他认定人的感情是不会错的,可以做人生的指导。
(四)
一切的文学都是想象的,我们要问的是,这想象的质地是否纯正。新闻的文字之所以不能成为文学即因其是纯客观的描写,文字里面没有作者的人格。所谓“创造的想象”者,就是把文学的材料经过作者自己的灵魂的一番渗滤的功用。因为文学里有这想象的成分,所以文学才有主观性,高超性。但是这想象可以做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问题。所谓节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Reason)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
实在讲:理性与情感不是对峙的名词,就和“浪漫的”与“古典的”不是对峙的名词一样。我先引译阿伯克龙比教授(Abercrombie)一段很有见地的话(见《浪漫主义论》第三十一至三十四页):
以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对峙而言,甚为不当,因为古典主义不是列在浪漫主义同等的位置的。我曾说,浪漫主义是一种原质……古典主义呢,决不是一种原质,而是许多原质混合的一种状态。……古典主义就是艺术的健康:即各种原质的特点之相当的配和。如其你要寻出一个古典的成分,以与浪漫的成分相对立,必定劳而无功,因为二者不是对立的。无所谓古典的成分!不过有许多成分可以平稳的配合起来,这种配合,这种健康,就是古典主义了。我不知道这些成分有多少,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确数;浪漫主义却是其中之一……
确切的说,阿伯克龙比的解说是精当的。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畸形的现象,要做到这个地步,必须要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所以我屡次的说,古典主义者要注重理性,不是说把理性作为文学的惟一的材料,而是说把理性作为最高的节制的机关。作为浪漫的成分无论在什么人或是什么作品里恐怕都不能尽免,不过若把这浪漫的成分推崇过分,使成为一种主义,使情感成为文学的最领袖的原料,这便如同是一个生热病的状态。以理性与情感比较而言,就是以健康与病态比较而言。
感情主义(Emotionalism)是浪漫主义的精髓。没有人比卢梭更富于感情,更易于被感情所趋使。卢梭个人的行为,处处是感情用事,一切的虚伪,浮躁,暴虐,激烈,薄情,在在都是情感决溃的缘故,我们试读他的《忏悔》,就可以觉得书里的主人是自始至终的患着热病,患着自大狂,被迫狂,色情狂……一切的感情过度的病态。他是天才,是的,是一个变态的天才。卢梭的思想,也是弥满了感情主义的色彩,他自己说得好:“余之哲学非由原理演绎而得,乃由情感抽引而出。”文学里的感情主义当然是不自卢梭始,卢梭以前就有了“卢梭主义”。最明显的证据:卢梭的《新爱绿绮思》便是受了英国的李查孙的《克拉丽撤》的启示。台克斯特(Texte)所著《卢梭与文学里的大同主义》一书关于此点叙说得最详荆德国的“狂飙运动”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情感主义的混沌!近代的所谓“未来派的戏剧”以及战后新兴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新艺术,无一不是过度的情感的产物。
情感不是一定该被诅咒的,伟大的文学者所该致力的是怎样把情感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忱,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亚里士多德于悲剧定义中所谓之“Katharsis(涤净之意),可以施用在一切的文学作品。文学固可以发泄极丰烈极壮伟的情感,而其抒情之方法,却大有斟酌之处。文学本身是模仿,不是主观的,所以在抒泄情感之际也自有一个相当的分寸,须不悖于常态的人生,须不反乎理性的节制。这样健康的文学,才能产生伦理的效果。今且举雄辩的艺术以为例:希腊的雄辩术,是一个独立的艺术,第一流的雄辩家其遣词命意全要经过选择,用各种艺术的技能使听者为之动容,为之情感兴奋,然而在结尾的地方,必须极慎重的把紧张的空气松弛下来,使听者复归于心平气和之境。这是真正的古典的法度。现今所谓的演说,尤其是煽惑罢工的领袖的演说,一个人全部的为感情所支配,讲者叫嚣暴躁,听者为之摩拳擦掌,结果往往是一个暴动。这个分别是浅而易见的:一个是有理性统驭的,一个没有。文学也是如此。伟大的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
情感也有真假之分:真的情感是自然流露的,假的情感是故意造成的。有一种人,感情的生活养成了一种习惯,非在情感紧张的状态之下不能得到安慰,于是凡遇不关痛痒的刺激,也立刻发生情感的反应,是之谓伤感,是之谓无病呻吟。伤感主义近来已成了流行的症候。一个标类的伤感主义者,必是喜欢造做一种哀苦的围,以求自我催眠,必是要示人以无限制的同情,为一般被损害者做浮浅的抗声,必是把自己看得异常的重要,把自己的情感上的缺憾认为是人生最大恨事,必是故意的想象着自己的生活已临到险恶的绝崖,以图情感上受些尖锐的刺激,……。在英国文学里,麦克弗孙的欧迅诗,大概是可以算做很早的伤感的作品,勃恩斯的《给一只老鼠》也大有伤感的意味,拜伦更有极大的伤感的成分。伤感主义者的一个根本信仰,就是人性善。所以他认定人的感情是不会错的,可以做人生的指导。
(四)
一切的文学都是想象的,我们要问的是,这想象的质地是否纯正。新闻的文字之所以不能成为文学即因其是纯客观的描写,文字里面没有作者的人格。所谓“创造的想象”者,就是把文学的材料经过作者自己的灵魂的一番渗滤的功用。因为文学里有这想象的成分,所以文学才有主观性,高超性。但是这想象可以做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问题。所谓节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Reason)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
实在讲:理性与情感不是对峙的名词,就和“浪漫的”与“古典的”不是对峙的名词一样。我先引译阿伯克龙比教授(Abercrombie)一段很有见地的话(见《浪漫主义论》第三十一至三十四页):
以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对峙而言,甚为不当,因为古典主义不是列在浪漫主义同等的位置的。我曾说,浪漫主义是一种原质……古典主义呢,决不是一种原质,而是许多原质混合的一种状态。……古典主义就是艺术的健康:即各种原质的特点之相当的配和。如其你要寻出一个古典的成分,以与浪漫的成分相对立,必定劳而无功,因为二者不是对立的。无所谓古典的成分!不过有许多成分可以平稳的配合起来,这种配合,这种健康,就是古典主义了。我不知道这些成分有多少,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确数;浪漫主义却是其中之一……
确切的说,阿伯克龙比的解说是精当的。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畸形的现象,要做到这个地步,必须要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所以我屡次的说,古典主义者要注重理性,不是说把理性作为文学的惟一的材料,而是说把理性作为最高的节制的机关。作为浪漫的成分无论在什么人或是什么作品里恐怕都不能尽免,不过若把这浪漫的成分推崇过分,使成为一种主义,使情感成为文学的最领袖的原料,这便如同是一个生热病的状态。以理性与情感比较而言,就是以健康与病态比较而言。
感情主义(Emotionalism)是浪漫主义的精髓。没有人比卢梭更富于感情,更易于被感情所趋使。卢梭个人的行为,处处是感情用事,一切的虚伪,浮躁,暴虐,激烈,薄情,在在都是情感决溃的缘故,我们试读他的《忏悔》,就可以觉得书里的主人是自始至终的患着热病,患着自大狂,被迫狂,色情狂……一切的感情过度的病态。他是天才,是的,是一个变态的天才。卢梭的思想,也是弥满了感情主义的色彩,他自己说得好:“余之哲学非由原理演绎而得,乃由情感抽引而出。”文学里的感情主义当然是不自卢梭始,卢梭以前就有了“卢梭主义”。最明显的证据:卢梭的《新爱绿绮思》便是受了英国的李查孙的《克拉丽撤》的启示。台克斯特(Texte)所著《卢梭与文学里的大同主义》一书关于此点叙说得最详荆德国的“狂飙运动”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情感主义的混沌!近代的所谓“未来派的戏剧”以及战后新兴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新艺术,无一不是过度的情感的产物。
情感不是一定该被诅咒的,伟大的文学者所该致力的是怎样把情感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忱,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亚里士多德于悲剧定义中所谓之“Katharsis(涤净之意),可以施用在一切的文学作品。文学固可以发泄极丰烈极壮伟的情感,而其抒情之方法,却大有斟酌之处。文学本身是模仿,不是主观的,所以在抒泄情感之际也自有一个相当的分寸,须不悖于常态的人生,须不反乎理性的节制。这样健康的文学,才能产生伦理的效果。今且举雄辩的艺术以为例:希腊的雄辩术,是一个独立的艺术,第一流的雄辩家其遣词命意全要经过选择,用各种艺术的技能使听者为之动容,为之情感兴奋,然而在结尾的地方,必须极慎重的把紧张的空气松弛下来,使听者复归于心平气和之境。这是真正的古典的法度。现今所谓的演说,尤其是煽惑罢工的领袖的演说,一个人全部的为感情所支配,讲者叫嚣暴躁,听者为之摩拳擦掌,结果往往是一个暴动。这个分别是浅而易见的:一个是有理性统驭的,一个没有。文学也是如此。伟大的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
情感也有真假之分:真的情感是自然流露的,假的情感是故意造成的。有一种人,感情的生活养成了一种习惯,非在情感紧张的状态之下不能得到安慰,于是凡遇不关痛痒的刺激,也立刻发生情感的反应,是之谓伤感,是之谓无病呻吟。伤感主义近来已成了流行的症候。一个标类的伤感主义者,必是喜欢造做一种哀苦的围,以求自我催眠,必是要示人以无限制的同情,为一般被损害者做浮浅的抗声,必是把自己看得异常的重要,把自己的情感上的缺憾认为是人生最大恨事,必是故意的想象着自己的生活已临到险恶的绝崖,以图情感上受些尖锐的刺激,……。在英国文学里,麦克弗孙的欧迅诗,大概是可以算做很早的伤感的作品,勃恩斯的《给一只老鼠》也大有伤感的意味,拜伦更有极大的伤感的成分。伤感主义者的一个根本信仰,就是人性善。所以他认定人的感情是不会错的,可以做人生的指导。
(四)
一切的文学都是想象的,我们要问的是,这想象的质地是否纯正。新闻的文字之所以不能成为文学即因其是纯客观的描写,文字里面没有作者的人格。所谓“创造的想象”者,就是把文学的材料经过作者自己的灵魂的一番渗滤的功用。因为文学里有这想象的成分,所以文学才有主观性,高超性。但是这想象可以做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问题。所谓节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Reason)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
实在讲:理性与情感不是对峙的名词,就和“浪漫的”与“古典的”不是对峙的名词一样。我先引译阿伯克龙比教授(Abercrombie)一段很有见地的话(见《浪漫主义论》第三十一至三十四页):
以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对峙而言,甚为不当,因为古典主义不是列在浪漫主义同等的位置的。我曾说,浪漫主义是一种原质……古典主义呢,决不是一种原质,而是许多原质混合的一种状态。……古典主义就是艺术的健康:即各种原质的特点之相当的配和。如其你要寻出一个古典的成分,以与浪漫的成分相对立,必定劳而无功,因为二者不是对立的。无所谓古典的成分!不过有许多成分可以平稳的配合起来,这种配合,这种健康,就是古典主义了。我不知道这些成分有多少,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确数;浪漫主义却是其中之一……
确切的说,阿伯克龙比的解说是精当的。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畸形的现象,要做到这个地步,必须要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所以我屡次的说,古典主义者要注重理性,不是说把理性作为文学的惟一的材料,而是说把理性作为最高的节制的机关。作为浪漫的成分无论在什么人或是什么作品里恐怕都不能尽免,不过若把这浪漫的成分推崇过分,使成为一种主义,使情感成为文学的最领袖的原料,这便如同是一个生热病的状态。以理性与情感比较而言,就是以健康与病态比较而言。
感情主义(Emotionalism)是浪漫主义的精髓。没有人比卢梭更富于感情,更易于被感情所趋使。卢梭个人的行为,处处是感情用事,一切的虚伪,浮躁,暴虐,激烈,薄情,在在都是情感决溃的缘故,我们试读他的《忏悔》,就可以觉得书里的主人是自始至终的患着热病,患着自大狂,被迫狂,色情狂……一切的感情过度的病态。他是天才,是的,是一个变态的天才。卢梭的思想,也是弥满了感情主义的色彩,他自己说得好:“余之哲学非由原理演绎而得,乃由情感抽引而出。”文学里的感情主义当然是不自卢梭始,卢梭以前就有了“卢梭主义”。最明显的证据:卢梭的《新爱绿绮思》便是受了英国的李查孙的《克拉丽撤》的启示。台克斯特(Texte)所著《卢梭与文学里的大同主义》一书关于此点叙说得最详荆德国的“狂飙运动”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情感主义的混沌!近代的所谓“未来派的戏剧”以及战后新兴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新艺术,无一不是过度的情感的产物。
情感不是一定该被诅咒的,伟大的文学者所该致力的是怎样把情感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忱,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亚里士多德于悲剧定义中所谓之“Katharsis(涤净之意),可以施用在一切的文学作品。文学固可以发泄极丰烈极壮伟的情感,而其抒情之方法,却大有斟酌之处。文学本身是模仿,不是主观的,所以在抒泄情感之际也自有一个相当的分寸,须不悖于常态的人生,须不反乎理性的节制。这样健康的文学,才能产生伦理的效果。今且举雄辩的艺术以为例:希腊的雄辩术,是一个独立的艺术,第一流的雄辩家其遣词命意全要经过选择,用各种艺术的技能使听者为之动容,为之情感兴奋,然而在结尾的地方,必须极慎重的把紧张的空气松弛下来,使听者复归于心平气和之境。这是真正的古典的法度。现今所谓的演说,尤其是煽惑罢工的领袖的演说,一个人全部的为感情所支配,讲者叫嚣暴躁,听者为之摩拳擦掌,结果往往是一个暴动。这个分别是浅而易见的:一个是有理性统驭的,一个没有。文学也是如此。伟大的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
情感也有真假之分:真的情感是自然流露的,假的情感是故意造成的。有一种人,感情的生活养成了一种习惯,非在情感紧张的状态之下不能得到安慰,于是凡遇不关痛痒的刺激,也立刻发生情感的反应,是之谓伤感,是之谓无病呻吟。伤感主义近来已成了流行的症候。一个标类的伤感主义者,必是喜欢造做一种哀苦的围,以求自我催眠,必是要示人以无限制的同情,为一般被损害者做浮浅的抗声,必是把自己看得异常的重要,把自己的情感上的缺憾认为是人生最大恨事,必是故意的想象着自己的生活已临到险恶的绝崖,以图情感上受些尖锐的刺激,……。在英国文学里,麦克弗孙的欧迅诗,大概是可以算做很早的伤感的作品,勃恩斯的《给一只老鼠》也大有伤感的意味,拜伦更有极大的伤感的成分。伤感主义者的一个根本信仰,就是人性善。所以他认定人的感情是不会错的,可以做人生的指导。
(四)
一切的文学都是想象的,我们要问的是,这想象的质地是否纯正。新闻的文字之所以不能成为文学即因其是纯客观的描写,文字里面没有作者的人格。所谓“创造的想象”者,就是把文学的材料经过作者自己的灵魂的一番渗滤的功用。因为文学里有这想象的成分,所以文学才有主观性,高超性。但是这想象可以做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问题。
培根在他的《学问的进步》一书里说:诗是杜撰的历史。他的意思是说,诗是想象的记述,不像历史那样的忠实的记载事实,但是“杜撰”这个名词(培根的原文是“Feign”)是容易启人的误解。诗,一切文学,是真实的,并且比世界上发生的零零碎碎的事实还要真实的多。文学是较高的真实之实际的写照。文学不含有丝毫的虚伪的性质。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为更哲学的,更高超的一件东西:因为诗所欲表现的乃是普遍的,而历史则为特殊的。”(见《诗学》第九章)由亚里士多德看来,诗不是假历史,而是比历史更真实的记述,因为普遍的质素永远是比特殊的为经久不变。然而诗人怎样才能于森罗万象的宇宙人生中体会到这个普遍的精髓,这就有赖于想象。并且这想象还必须是纪律的,有标准的,有节制的,然后才能做为文学创造的正当工具。想象就像是一对翅膀,它能鼓动生风,扶抟直上,能把你带到你的目的地去,也能把你带到荒山大泽穷乡僻壤或是九霄云外的玉宇琼楼。文学不是无目的的荡游,是有目的的创造;所以这文学的工具——想象,也就不能不有一个剪裁,节制,纪律。节制想象者,厥为理性。
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很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所包括的是几样成分?)惟因其复杂,所以才是有条理可说,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准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所以在想象里,也隐隐然有一个纪律,其质地必须是伦理的常态的普遍的。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或能律”(TheoryofProbability)亦即是使想象(亚里士多德所谓“幻想”者即吾人所谓想象)就人性的范围的一个原则。想象是由平凡走到深奥的一条桥梁,不是由常态走到变态的一个栈道。
有人驳难我说:
……所谓“固定的普遍的常态的人性”这个标准,根本就办不到。即使宇宙到消灭的那一天,也决不会有什么“一个万古不变的普遍的常态的,可以通用古今中外一切的人类社会的人性”这回事。人性终究是多方面的,或许有变迁的,不普遍的。古今文学作品中表现这种人性的很不少,如莎士比亚戏剧中之Hamlet,Macbeth,Othello都是,关于这些,难道文艺批评家就可以置之不理吗?
我所谓文学须要表现常态的人性,并不是说文学里绝对的不可把变态的人物做题材。最变态的性格,我们可以用最常态的态度去处理。文学里很重要的是作者的态度。上面引的莎士比亚戏中的几个人物,假定都是变态性格的好例,其所以能发生文学价值者,不是因为里面引用了变态的性格,而正是因为作者施用了常态的处置,——使变态者永占在一个变态者的地位。其实还有比莎士比亚戏剧更好的例,例如希腊的悲剧,——里面有母子媾婚,父被子弑,种种骇人听闻的勾当。从表面观察,这似乎是与亚里士多德《诗学》所定的原则相反,其实不然。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批评家罗伯台利(Robertelli)在评释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时候首先提起了这一点似是而非的驳难。他说诗人有两种,一种诗人的创造是按照自然的,一种是超越自然的;在后者的状况之下,诗人以处置吾人已知的事物之法律处置吾人所不知的事物。(参看斯宾冈《文艺复兴期之文学批评》卷一论“模仿”一段。)所以由他看来,希腊悲剧中种种荒诞不经不合人性的题材,正好在“或能律”之下丝毫不妨碍作者伦理的态度。古典的批评家并不限制作品的题材,他要追问的是作者的态度,和作品的质地。诗人可以想象最可怕最反常的罪恶,并且引做题材,但是他能不自己卷入这罪恶的漩涡,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莎福克里斯是最古典的悲剧诗人,他却写下最诡怪的阿儿的婆斯,关于这一点,阿伯克龙比教授解释得好:
浪漫主义鼎盛的地方,乱伦的案件最容易发生:这是一个浪漫的题材,即因热烈的不合于惯例的礼法。不过这话反转来说就不见得准确:乱伦不一定浪漫。莎福克里斯便是好例,阿儿的婆斯皇帝是乱伦的最好的例。但在另一较高的意义之下,实是最古典的,即使乱伦是这篇莎福克里斯悲剧的主要点(当然不是的),莎福克里斯的艺术仍不失其为健全:他所想象的乱伦并不曾加以感情的渲染。……(《浪漫主义论》第一六九页)
(五)
文学的态度之严重,情感想象的理性的制裁,这全是文学最根本的纪律,而这种纪律又全是在精神一方面的。但是形式与内质是不能分开的。能有守纪律的精神,文学的形式方面也自然的有相当的顾虑。进一步说,有纪律的形式,正是守纪律的精神之最具体的表现。所谓文学革命者,往往着力在打破文学的形式,以为文学的形式是创作的桎梏,是天才的束缚,应该一齐的打破。其实文学的形式如有趋于单调呆滞的倾向,正不妨加以变换,不能因某一种形式之不合用遂遽谓文学可以不要形式。形式是一个限制,惟以其能限制,所以在限制之内才有自由可言。形式的意义,不在于一首诗要写做多少行,每行若干字,平仄韵律等等,这全是末节,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其真正之意义乃在于使文学的思想,挟着强烈的情感丰富的想象,使其注入一个严谨的模型,使其成为一有生机的整体。亚里士多德论悲剧,说悲剧必须有起有讫有中部,实在是说一切的文学都要有完整的形式。近代的文学常常以断片为时髦,(Vogueof the fragmentary)正和这形式完整的原则相反。
文学的形式是说文学的内质表示出来有没有一个范围的意思。至于字句的琢饰,语调的整肃,段落的均匀,倒都不是重要的问题。所以讲起形式来,我们注意的是在单一,是在免除枝节,是在完整,是在免除冗繁。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叙香菱学诗,黛玉的一段议论很有意思:
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也有对的极工的,也有不对的;又听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没事的,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我所谓形式,是指“意”的形式,不是指“词”的形式。所以我们正可在词的形式方面要求尽量的自由,而在意的方面却仍须严守纪律,使成为一有限制的整体。我们固然不该以词害意,然而就大体讲,词并不能害意。譬如说,一种严格的诗的体裁,无论其为律体,或十四行诗体,绝不会有束缚天才的能力。体裁繁复,在技术上也许是困难的,但惟天才乃能战胜困难。体裁固定,在表现上也许不能十分自然,但文学表现本是艺术的而不是自然的。文学的物质方面的形式像是一只新鞋,初穿上去难免有一点拘束,日久也就舒适。
(六)
临了我再重说:文学的纪律是内在的节制,并不是外来的权威。文学之所以重纪律,为的是要求文学的健康。我引柏拉图的一段对话做本文的煞尾:
苏格拉底:艺术家布置各物,使有秩序,使每一部分和其余各部谐和,以便建设一个有规则的有系统的整体:一切艺术家都是如此,前面提到的教师与医师,也是同样的给身体以秩序与规则:你不承认吗?
卡里克利斯:我承认。
苏格拉底:那么,有秩序与规则的家庭是好的,没有秩序是坏的?
卡:是的。
苏:船也是如此?
卡:是。
苏:人的身体也是一样?
卡:是。
苏:人的心灵呢?善的心灵是没有秩序的呢,还是有秩序与和谐的呢?
卡:已经讲过当然是有秩序的好。
苏:身体的秩序与谐和所发生的效果,叫做什么?
卡:你是否指康健与力量而言?
苏:是的;心灵的秩序与谐和所发生的效果,叫做什么呢?
卡:你为何不自己说呢,苏格拉底?
苏:我可以说,你若以为不对,你可以驳我。身体有合规则的秩序,叫做“健康的”,由此产生健康以及其他身体上的优点:是不是?
卡:不错。
苏:心灵的合规则的秩序与活动便叫做“纪律的”与“纪律”,便是使人们守纪律守秩序的主因:——因此我们才能有节制和正义:是不是?
卡:我承认的。(《Gorgias》,B.Jowett译本)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