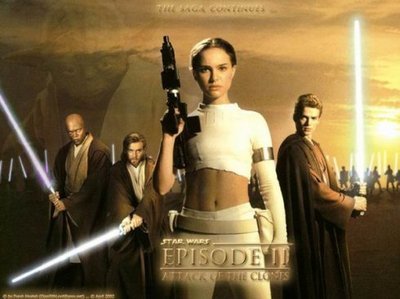我相信那一刻,我的嘴巴一定是张的大大的停在那里许久。
白宁羞红了脸:“青青,你不要这个样子。”
我抓住她:“天呐,宁宁,你知道你都说了些什么吗?你没搞错吧。”
白宁安静的回答:“我早就结婚了,跟许言。”
我心中不知道回荡的是一种什么感觉,麻麻的涩涩的,有点点苦,有点点空,还有一点点脑部的空白。
我定定的望着她:“你,能不能,说的清楚一点。”
白宁双胛那一抹红更浓了,她娓娓向我叙述着她和许言的一切。
许言和白宁是一个村子的,很小的时候,在白宁记事起,她就知道有一个大哥哥总会在河边冲她微笑,尽管村里的人都不和白宁讲话,但许言是例外的。
白宁的爸爸妈妈是在白宁出生的那一天双双死去的。
白宁说起这话时,水汪汪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雾,一眨眼,二行泪水便顺着长长黑黑的睫毛流下来。
“他们都说我是怪胎,一出生就把我爸妈给害死了。”白宁说这话的时候带着一腔无奈的冤屈。她仿佛像看透了我的心事一般继续解开我心中的问题。
其实爸爸是死于赶往医院的路上,失足跌下了水坝,而妈妈则死于……
白宁闭上双眼,陷入了无尽的恐惧与噩梦中,她摇着头:不要,不要,不要。
我问:宁宁?!
白宁猛然睁开眼:“我受不了,我不能回忆,很痛苦,下次,再告诉你,好吗?”
我点头。看得出她的神情非常痛苦,让人禁不住要去怜惜她。
白宁意味深长的说:“等有一天,你我都做好了思想准备,我再告诉你。”
白宁接着转到了她的阿婆,一个独行的老阿婆。
“是你的亲外婆吗。”我问。
“是的。”
白宁的阿婆是一个种蛊者,那是我们那里特有的职业。
“什么是……种蛊?” 我好奇地问着。

“种蛊就是下预言,预知人的生死祸福,就像你们这里以前的神婆,神汉。”
我有点忍俊不禁:“宁宁,你们那里还处在什么朝代啊,还有这种职业。”
白宁严肃的回答:“纳西族,一个神秘的民族。”
“那怎么种蛊,为什么种蛊呢?”
“以蛇为蛊,为情而蛊。”白宁不带一丝微笑,幽幽的回答。
我感觉一阵头皮发麻,仿佛全身的蛇鳞随着她冷冷的语调翻转而出。
白宁却不管不顾,照着自己的话语继续说着:“我住的村子正是纳西族原始东巴教的分支,我阿婆正是东巴教的东巴祭司么些达伯,传说中的情人死亡谷正是我们那个村。”
白宁宁静而安祥的突然双手合十,念起了一串我听不懂的语言,十分虔诚,像是在朗诵诗歌,却更像是轻吟浅唱,虽然听不懂,但是她那种认真而执着的神态还是打动了我,渐渐地感觉到一阵平和的力量在四周升腾。
白宁念完,突然伏于地,念道:“万物有灵,灵魂不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