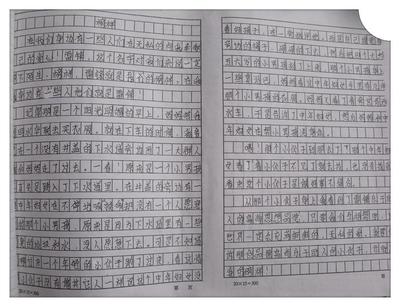我和英语的故事
话说成功的经验都类同,此乃英雄所见略同;而失败与挫折,却如同基因一般,全世界都找不到一个克隆。我的英语并不完美,我与英语的故事也充满曲折,现在拿出来晒晒,顺便测试一下前面的理论。
我与英语第一次
我是14岁那年才开始接触英文字母的。当时刚上初一。我小学毕业于一间不起眼的村校,小学期间没有学习任何英语。没错,我是从江苏农村走出来的。不象城镇的同龄人,一般都会有两、三年英语的经历,至少达到理解“这是一本书”的程度。
我当时爱钻牛角尖,除了纠结a,b,c,d的发音,究竟是先有英文还是先有拼音以外,还纠缠isn’t中的’究竟是否字母o的缩写。我成功地把我的同学和老师搞得很烦。我不断地刨根问底,结果被告知记住就好了,正如将Whatwould you like记成“what我就来”一样。

我的汉字虽然些得可以,但是英文字母写得很差,不是i少了衣领写成i,就是q少了燕尾成了q。那是因为,我试图将英文字母汉化为拼音。后来好不容易被英文老师纠正过来,结果一下子全盘西化,轮到语文老师批评我,将汉语拼音写成了假洋鬼子。
不过我的那股韧劲,还是得到了回报。第一次期中测试,我的英文程度从几近全班倒数,一下子窜到名列前茅。我考了96分,全班最高98分。我有自知之明,这不能代表我的程度有多高,纯粹是因为卷子太容易,很多有识之士高屋建瓴地粗心大意而已。不过有一个转折,自那以后,当我开始纠结can’t中的’是否no的缩写时,大家开始没那么不耐烦。
我很好奇最近流行一种讲法,说江浙人士学习英语有特殊优势,因为当地的方言的发音结构,容易发出英语的一些生僻音节,如v。没错。于是有人说江浙人士的英语,尤其是口语灵光,那是占了母语的光。但真理过头一点点,就成了谬误。
至少在我的中学期间,英文就像甲骨文,是用来研究和考证的,不是用来说的。这也是条件所限。就语言学而言,说好一门语言,特别要注意听力的摄入和口语的输出两部分,而且前者尤其重要。而当时,除了英文老师带有口音的朗读以外,就是朗文英语教材配套的磁带,在质量一般的教学录音机的喇叭中播放——那声音,有如鼻塞的人,戴了十张口罩在讲话。
不过我很幸运,在我的不断考证下,语法结构好像大蒜一样,被我层层剥开,其义自现。同时伴有泪水,那是师友们对我古怪的问题,哭笑不得的眼泪。一旦破解了英语语法的莫尔斯密码,我的英文考试成绩,就像绩优股票,一旦涨上去,就再也没有下跌过。
因为成绩的优异,我被选派参加首届全国英语竞赛,居然取得了全县的特等奖,凌驾于一等、二等、三等、优胜等统统所有奖以上。这让我飘飘然了好一会儿,直到有人告诉我全国至少有几百个县。膨胀的内心被戳破之余,我对伟大祖国的地理和人口,第一次有了直观的感受。而且当年没有考听力,这对我是万分的侥幸,因为次的比赛就要考听力了,听说挺难的。
大学时期栽跟头
后来就高考。结果失利,英文成绩也不如预期,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我被南京的一所大学录取之后,也得到了一张前赴香港学习交换的船票。当时香港本科还是三年制,所以第一年我仍然待在内地的大学,补习数学和英语。没办法,谁叫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比不上人家的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呢。
英语听力和口语,这两座殖民主义遗留给全世界的大山,最终要压在我头上。我无助的感觉象孙悟空,纵然有七十二般武功,但五指山一压下来,就死翘翘。彷徨的我,遇到了李阳的疯狂英语。要学老外,四肢肌肉要锻炼,口腔肌肉更要锻炼。这是多么有哲理的思想啊。
于是我作出了人生中第一笔的知识投资:购置了一套李阳的《疯狂英语》黄宝书和步步高的复读机。当磁带放入复读机,我人生第一次听到了清晰的美式英语发音。接下来就是疲劳轰炸,从此我们宿舍除了遍地垃圾的环境污染,又多了一项声音污染。
将近一年的连续轰炸的结果,就是将我江苏的直舌头,硬是拧成了北方的麻花卷,满嘴美式英语,咿呀都带儿字。在踏上赴港征途之前,我内心充满东方红,因为嘴上终于挂上了洋泾浜。良好的感觉维持了一阵子,直到踏入香港的教室,恍然发现,人家是英殖民地,讲的是英式英语。
不过不打紧,英美本一家。我很庆幸美国的开国元勋当时没有因为憎恨英国而指定法语为官方语言。短暂的调节,就像头发离子烫,舌头恢复了自然直。可是问题也来了当我翻开教学大纲,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陌生的单词,syllabus,course,academic,seminar,tutorial,等等。我额头的汗,象被泼了冷水一样,不断往下滴。
词汇,从来没有问题的词汇,出了问题。以前的学习的词汇,就像温室的花草,都是预先画地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