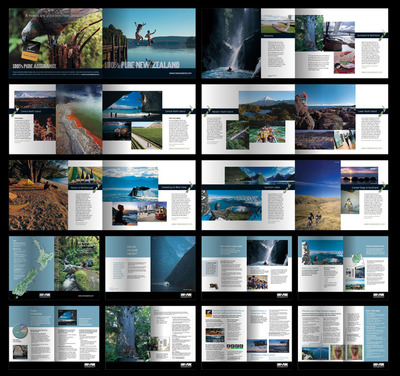梦里时常萦绕的还是家乡的山山水水,还有那些永远也抹不去的熟悉的面孔。叔母病重,于是丢开手头永远也理不完的公务,去探望久病的叔母。
忐忑不安的心情加上颠簸起伏的山路,叫人一阵阵昏晕不已。从县城通往老家的公路原本是一条省级公路,记得小时候公社还分配过养护任务,我随二姐往公路上运过沙。由于运输量大,这条路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搓板路”,据小道消息说,这条路国家早已下达了铺油改造计划,由于前些年县上发不出工资就挤占了,也就是说在国家的底册里,这条路已经是柏油马路了。可惜年复一年,面貌依然。不足四十公里的路程,即使车放足马力,也要行驶一个多小时。
上次见到叔母是今年春节刚过,因为叔母多年患有肺心病,听庄子上人说恐怕过不了正月。已近一年,叔母还是毅然坚持了下来,卧床一段时间后还能坚持到外面见见天日、晒晒太阳。“大雪”节气过后,北方的气温骤然下降,叔母再也坚持不住,终于再次卧床。大夫也说,这种病在这个时节最危险。见到叔母,心情异常沉重,她蜷缩在被窝里,苍白的头发散乱地飘落在被子外,听见有人进来,叔母慢慢地抬起身子,吃力地往起爬,我急忙拦挡,她还是坚持坐了起来。叔母极度肿胀、铁青的脸面上掠过一丝微微的笑容,即逝后在因肿胀已变形的眼睛中闪出丝丝泪花,接着便用沙哑的声音吃力地问家中父母可好,她猜测一定是父母让我们来看她。母亲也一直告诉我,在以前的农业社里,叔母是她最能靠得住的人,很多母亲一个人不能完成的活都是找叔母帮忙的。
自孩童时就记得叔母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不但能够认得钱,而且还会算帐,并且打得一手好算盘,什么“三一三剩一”、“二一添作五”她都记得很熟。队里分粮食时,叔母经常给会计帮着算帐,既快又准,庄里人都很佩服。家中的大事叔母也一手承担,拉猪娃、卖羊毛的事她都亲自出面。由于经常与堂兄一起玩耍、上学的缘故,叔母做的各样饭菜我几乎吃遍,总觉得比自家的香,特别是她烙的油馍馍,吃一丁点,也能让你香上好几天。堂嫂虽然口荐不好,但对叔母特别关心,叔母病重时,她便将叔母放在摩托车后,用一条长围巾与自己系在一起,开着摩托车从家中到医院、从医院到家中来来去去不知多少回。叔母患病多少年能坚持到现在可以说与堂嫂的关心呵护分不开。
每到老家,必要到祖坟上给先人烧香叩头,这不但是我的心愿,更是父母的心愿,因为那里埋葬着祖父祖母和大叔父大叔母,其实那就是我们永远固守的精神家园。坡还是那个坡,沟还是那条沟,只是再也找不着那口清汪汪、一年四季不干渴的泉水,沟坡上歪斜着的柳树依然还是二、三十年前那么粗,它正是在诉说和见证着家乡自然条件之酷劣!
离开叔母,无言以对,惟有眼泪汪汪。不知再能否见到叔母?痛哉,痛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