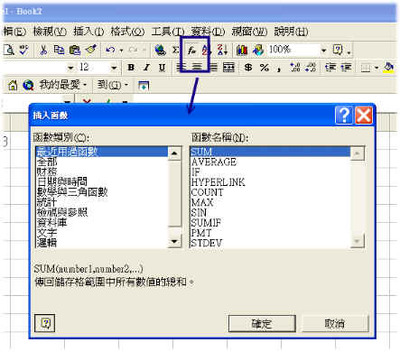“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1936年东渡日本的萧红在写给她的爱人、作家萧军的信中写道。于10月1日上映,由许鞍华导演、李樯编剧的影片《黄金时代》由此得名。
民国作家萧红短暂的一生跌宕起伏:20岁从呼兰逃婚到北平、24岁在上海发表小说《生死场》一举成名、31岁客死香港。尤其是她在战乱年代的漂泊命运,与四个男性的爱情纠葛,使她成为两次登上大银幕的女作家。就在2013年,霍建起第一次将萧红的故事搬上大银幕。“十年前就打算拍萧红和丁玲,但因为丁玲是政治上有争议的人物,可能通不过审查,现在就只有萧红”,导演许鞍华在接受采访时说。
电影《黄金时代》以萧红为主线,涵盖她的生平,重点描述了在东兴顺旅馆与萧军的相遇、在鲁迅家吃饭聚会、在延安与萧军分道扬镳等节点式片段;同时电影也涉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团体中的弄潮儿:鲁迅、丁玲、胡风、梅志、聂绀弩,他们以面对镜头叙述的方式亮相。这个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宣称,将重现“一个民气十足、海阔天空的时代,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自由地追求梦想与爱情”。在影片宣传上,《黄金时代》也主打“自由”二字。片方日前发布的八张“态度版”海报,创造了一种句式:“想……,就……,这是……的时代,一切都是自由的”。比如,萧军的海报台词是,“想爱谁,就爱谁!这是快意恩仇的时代,一切都是自由的”;鲁迅的则是,“想骂谁,就骂谁!这是畅所欲言的时代,一切都是自由的”。这种定位引发调侃,作家马伯庸在微博上评论道,“如何只用两行字来杀死一部电影?照这么做就行了。”
《黄金时代》萧军的海报台词是,“想爱谁,就爱谁!这是快意恩仇的时代,一切都是自由的”。
Courtesy of The Golden Era
《黄金时代》电影制作费用高达6000万元,耗时三年打造剧本,辗转大半个中国完成拍摄,有汤唯、王志文、郝蕾等十几位明星演出。然而拍一部作家传记片,在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上似乎有些冒险。“找投资时,都愿意出三分之一,但2000万拍不了,所以等了那么长时间”,许鞍华说。直到编剧李樯的剧本进入星美影业董事长覃宏的视野,才得以开机。
在阅读人物传记、作家作品和大量民国资料的基础上,李樯完成了剧本创作。李樯在接受采访时说:“2005年我们在合作《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那时候许导就想拍萧红,当时没有观影热潮,这样的题材更是不太好融资。但导演还想拍,我就开始写作,有没资金先不管,从2008年开始弄这个剧本。”许鞍华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写好第一稿就给我看了,我提一些意见,可是对他的创意其实我都很少改动的。我都同意,觉得非常好。”他们尝试用新的手法拍摄作家传记,于是就有了每个人物面对镜头诵读文艺作品的叙述结构。
故事的主角萧红并不为大众熟知。她的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描写东北人民困顿生活,曾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影响力日渐衰微。作家摩罗曾发起过一场关于萧红的讲座,他发现,读过萧红的年轻人寥寥无几。或许正是这个原因,2013年霍建起版本的《萧红》为吸引普通观众入场,不惜将重心放在萧红的几段情史上,结果引来铺天盖地的批评,投资也血本无归。因此,谈起票房时许鞍华颇为谨慎,“投资这样的电影是一次赌博,预计很难达到收支平衡”。但她也怀抱希望,“这几年的文艺片,尤其是都市浪漫喜剧卖得非常好。我们刚刚开拍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现象,可能观众也会喜欢创新。”
电影刻意避免了萧红一生所经历的左翼作家联盟创立、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描述,考虑到左翼作家团体的政治色彩,影片也选择通过主演的个人经历来回应历史。导演许鞍华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使电影在通过审查时比较顺利。然而折中的结果使一些批评人士不满,9月上海作家毛尖在给观察者网的评论《论爱情的反革命性》中写道:“我们如果由此轻易地认为萧红可以两次怀着别人的孩子跟另一个男人走,即是“自由”、“空阔”或“民国”,那真是太轻侮一代人的痛苦了。”
香港导言许鞍华尝试过武侠片、惊悚片、伦理片、文艺片、纪录片等类型,目前拍摄了35部电影。观众更喜爱她的文艺片。她镜头下的香港充满人间烟火气,于平凡之中隐藏着人性的深刻。其中,以讲述香港百姓生活况味的小成本影片《天水围的日与夜》和刻画主仆情谊的《桃姐》为代表。
编剧李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成为职业编剧前在北京漂泊了八年。用他的话说,“写了一堆拍摄不了的电视剧,或者写了之后不署名,编剧迈向成功之前遇到的各种困境我全都经历过。”2005年,电影《孔雀》拿下第55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编剧李樯也一举成名。之后,他陆续与顾长卫、许鞍华、赵薇合作,担当《立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影片的编剧,创作了梦想当伞兵的姐姐,渴望扎根北京的大龄音乐女教师王彩玲、人到暮年依旧疯狂的姨妈等女性角色。李樯偏爱与青春、尊严、梦想有关的故事。萧红是他创作的第一个历史人物,他眼中的萧红,对爱与自由有着超于常人的需求。他说,“无论他处在什么环境中、是什么样的政治光谱、有什么样的历史价值观,我永远只对人有兴趣”。
《黄金时代》是继《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之后,导演许鞍华与编剧李樯的第二次合作。
2014年9月,《黄金时代》的编剧/监制李樯在北京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以下为对谈实录,经过编辑和删减,未经李樯审阅。
问:片名《黄金时代》指的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人文环境还是自由思潮?
答:我觉得是分三个层次吧,第一个层次你知道萧红在日本给萧军写的一封信,有一段话很有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牢笼里度过的”那段话。那个是她个人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一个感慨。她觉得一边写作,还有面包吃,人是自由的,经济还算过得去,这就是她的黄金时代了。我的理解就是所谓的黄金时代并不存在。
第二个现在的人都特别愿意把民国时期称之为黄金时代,政治样态的多样化,各种思潮跌宕起伏呈现出了中国历史上意识形态非常丰富的一个时间段。当时在思想、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我们现在说的大师群落,所以说是黄金时代。
第三层意思是《黄金时代》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有桃花源式的气质,乌托邦式的气质,它有一种虚无性的浪漫性的气质。人类到底有没有黄金时代?人总会想象自己或者说人类的历史当中有一段黄金时代。好像觉得过去总存在一种美好的东西。
问:故事对准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团体和其中弄潮儿,你都做了哪些阅读和调研?最终你发现他们身上最明显的群体特征是什么?
答:那个时间的文坛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有左翼的、有右派的、有自由主义的,有很多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我得理清每个人的精神脉络。一个是延安派的,往延安那边走的;一派是尊重自己精神状态的个人主义者;还有鲁迅这种比较复杂的,你很难说他是左翼。我首先要理清这些人的政治光谱。萧红、萧军、端木等影片中人物,我都要去读他们的专著,发现他们与众不同。所以我阅读了大量民国的比较私人化的资料,从个人视角看待他们。我还看了很多民国时的纪录片,风土人情、人的精神面貌以及状态。
总的来说,那是一个人的面目比现在强,比现在的人更具有人性,更处在人性的状态。我觉得是今天的人面目不清楚,要不被金钱裹挟,要不就是被动的意识形态化,人的味道没那么强烈。另外,那时候的人们爱的能力,追求自由的能力,困惑的能力都比现在强,人的力量比现在发达。这就是我的心得,是当代人和那代人的一种比较,尤其是在当代还要拍那样的一种题材,你毕竟有当代性。其实并不是一种复古,你如何使那个时候的人和现在的人有一种寻找一个交集点,使现在的人对那个时候有一个兴趣。这是我阅读和思考的一个过程。
问:对于萧红你有哪些新发现?
答:我觉得萧红是被意识形态化的,都说她是左翼作家,其实她不是。她跟左翼不一样,她更自由主义,更个人主义。但比起真正个人主义的作家她又偏向左翼,她有轻微的个人性。所以她两边都不靠,被两边都误解,自由主义的认为她是左翼,左翼的人认为她偏自由主义。初中学英文有一个寓言叫《蝙蝠的故事》,蝙蝠说我有牙齿是兽类是胎生的,所以是哺乳类,可是哺乳类的觉得你有翅膀、能飞行,是鸟类。鸟类又觉得你不是卵生的,不归我们这一类的。我觉得萧红有点象《蝙蝠的故事》。
问:鲁迅、丁玲、萧红,这些人物曾出现在党史里。在电影处理中,你是按照党史的叙事形态塑造的,还是希望找回他们的故事还原一个新形象?
答:所谓新的形象,我觉得这个新只能是发现,而并不是真的新。我不排斥萧红在中共党史意识形态中的形象,那毕竟是她的一部分。我没有排斥约定俗成的形象,只是希望在约定俗成中去发现一些被忽略的、被遮蔽的东西。
问:你找到了哪些被遮蔽的东西?
答:历史是不能复原的,历史的真相象海市蜃楼一样。不论是历史上的公共人物,还是一个普通人,你越去接近它就越觉得它象一个影子,很难被确切化。我觉得历史很多是被粉饰、被篡改、被矫正、被遮蔽、被公共化的,每个角度都是历史的一个封锁点。人也是如此。萧红象一座移动的远山,你越走近她越远。我发现人类历史的虚无性是一个核心,唐朝、民国、无论哪个朝代烟消云散后,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盖个章,每个人都可说一段它的评断,或许永远没有真实面目。包括对萧红,永远无法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成了我写作定义的一个要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虚无性在写作中一直伴随着我。一个人的生活和她的传记紧密绑在一起。以往的人物传记片都是力图表现一个确定的形象,我却背道而驰,所以虚无性、模糊性成了这部电影的特色,这也是我想真正讲述的一个重要内容。
问:你怎么看待鲁迅、丁玲、萧红在1949年之后的文学命运?
答:我觉得这是在中国特殊情况下生存的作家难以逃脱的命运。我常常想那些离开大陆去了别处的作家,如果他们留在大陆,要不就是哑然失声,要不就是被裹挟在这个洪流之中,似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就像沈从文,建国后只能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做一些文物研究。
问:在如今这个拜金的时代,文化与文艺退居边缘,你觉得观众可以真正理解民国时代的文学团体吗?
答:我觉得萧红面临诸多的人生选择,贫困、爱情、信仰、坚持自我,萧红面临的种种问题是当代人依然面临的问题。世世代代都是如此,它们有永恒性,并不随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有一个答案。她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个时代面临的问题。我觉得对于个人而言,要有强大的内心生活和精神生活,因为物质生活让我们渐渐丧失了一种东西。
至于观众能否理解,这是不能强求的。揣测观众的心理当然是可以的,但如果以丧失自我为代价的话,结果可能玉石俱焚。你只能真诚地创作,然后去寻找那些能跟你发生心灵碰撞的人,这个过程是被动的。你并不知道跟你发生共鸣的观众是哪个阶层,在哪个区域,做什么工作。
这种共鸣有点象对待爱情的态度,里边是偶然跟必然交错的一个关系。
问:对于中国电影当下的创作环境,你的感受是什么?
答:中国电影处在一种虚胖的状态,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电影产业发展蓬勃,观影成为集体娱乐方式。但生产的内容比较疲乏,类型少,质量不高。这跟时代环境和意识形态也有关系。大家拼命追逐票房,很多人涌进电影业掘金,就像圈地运动。电影热的好处是机会多,更多人参与到推动电影的浪潮中。在这个资本迅速积累的时期,可能比较多粗制滥造。我们也没有形成艺术电影院线,一些独立的艺术片缺少良好循环的生态环境。
有时候你拍了一个比较私人的电影,可能很容易被淹没。这是很多国家电影发展都面临过的问题。我个人是希望电影有更多类型,观众形成多种口味的,使每个电影工作者都有一个良性循环的小宇宙,形成一个互相喂养的生态环境。艺术片有艺术片的工作,商业片有商业片的市场,大家彼此和而不同繁荣相处,彼此喂养,那样电影才会真正健康发展。
问:从编剧到名编剧,你是否争取到了更大的话语权?
答:如果是指电影从拍摄到完成发片的话,似乎是比以前有更多的话语权。但这个话语权不是真的话语权,真的话语权指的是你可以完全追求自己的电影观,还有良好的宣发环境和受众,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话语权。如果只是指被拍摄成功的话,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假象。成名并没有给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我来说就像是被虚构的另一个自己,我的日常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影响。名气带给我更多的是对我作为职业编剧的确认,是对我自己的身份确认。我可以靠写剧本为生,并且我也有写剧本的素质,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名声并不是象天上掉馅饼一样砸我头上,还是靠写慢慢累积信誉的过程。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140930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