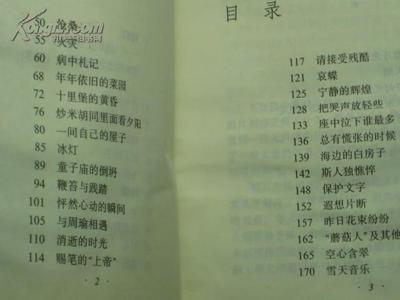采浆果的人
(第十一届小说月报百花奖)
金井的山峦,就是大鲁二鲁的日历。
雪让山峦穿上白衫时,他们拉着爬犁去拾烧柴;暖风使山峦披上嫩绿的轻纱时,他们赶紧下田播种。山峦一层一层地由嫩绿变得翠绿、墨绿时,他们顶着炽热的太阳,在田间打垄、间苗、锄草和追肥;而当银光闪闪的霜充当了染匠,给山峦罩上一件五彩的花衣时,他们就开始秋收了。
金井是个小农庄,只有十来户人家。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从来没有事情能阻止得了秋收,但今年例 外,一个收浆果的人来了。
秋收刚刚开始,一辆天蓝色的卡车摇摇摆摆地开到了金井。这一带的路坑坑洼洼的,所以这辆车虽然不少一只轮子,可走起来还是像个瘸子。
车主是个中年汉子,高个儿,方脸,小眼睛,
大嘴巴,面色红润,说起话来神采飞扬的,一看
就是走南闯 北、见过世面的人。卡车上装着
十来只空坛子。听说他是收浆果来的,金井人
就嘲笑他:"哪有秋后收浆果的?早 过了时候了
!"
车主说:"要的就是这种过了时候的浆果!
你们没听说过吗,头茬的韭菜二茬的姨娘是最
鲜的,我再给它加一条,就是最后一茬的浆果醉
人心!"
车主倒是没说错,盛夏时就熟了的浆果,如
果无人采摘,在其熟得不能再熟的时候,就兀自
静悄悄 地坠到林地上,无声无息地被雨水沤烂
了。而还零星挂在枝头的浆果,无外乎两种命
运,要么因为花开得晚、果做得迟而熟在了秋
风中;要么就是熟得绽裂了,流出 了体内一部
分汁液,减轻了自身的分量,没了落到地上的危
险,而风和阳光的照拂又使它们风干了,成为幸
存于枝头的另一类。这两种浆果被霜一打,甜
得醉人,不 过它们稀少得就像这个时令的蚂蚱
。
车主开出每种浆果的收购价格后,从怀中
掏出两摞钱来,夹在指间,把它们当竹板一样敲
打着,以 说书人的口吻说:"话说这秋菜要是晚
收一天它呆在土里也飞不了,可是这浆果要是
晚采一天,拿现钱的就是别的人了!人家的男人
拿钱买酒你喝白水,人家的女人 拿钱买织锦缎
子你穿粗布,你说这浆果采得采不得?!"
他这一番吆喝,让秋收的人们扔下了手中
的镐、铁齿、镰刀、耙子 等农具。他们纷纷
回家拿起形形色色的容器,奔向森林河谷,采摘
浆果,仿佛牧羊人在寻找失了群的羊。
以往采浆果的都是女人和孩子,男人是绝
不伸手的。可现在男人 也来了,谁不愿意多赚
几个酒钱呢!
浆果与人一样,也是有秉性的。喜静的,生
长在河谷和阴沟里,比如山丁子、稠李子和水
葡萄。而 爱热闹的,则热情奔放地散布在植被
丰厚的森林中,如都柿、野草莓、马林果和牙
各答等。野草莓和马林果是春末夏初就熟的浆
果,所以如今在林中只能偶尔可见它 们已经萎
黄了的叶片,果实却已是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佳
人--芳踪难觅了。在这些仅存的浆果中,最好
采的是牙各答,它们不仅数量为众,耐寒的它们
肌肤仍然光 亮、饱满着,在其喜欢生长的林地
缓坡或者是透出腐烂气息的松树的根部,你很
容易就能在一片浓密地匍匐着的墨绿色的卵形叶片中,觑见它们红艳艳的笑影。有经验的人,会一铲一铲地连叶带果地将其收在铁撮子中,
然后簸掉叶子,使果实匀密地沉淀下来。都柿
果呢,它不像山丁子和稠李子结在树上,让人直
着身仰着头舒舒 服服就能采,矮棵的它们逼着
人必须弯下腰才能摘到果实,那些一弯腰就爱
眩晕的人当然要骂它们了,他们骂得五花八门
的,譬如"小贱种","小娼妇","小混 蛋",可见
他们也是把浆果当 人看待了。
第一天收购上来的浆果,牙各答居多,其次
是山丁子和都柿。收浆果的人果然没有食言,
每个采浆 果的人都领到了数目不等的现钱,平
均下来,每户有三四十块呢,这对于金井的农民
来说,不啻于在荒野中捡到了巨大的银锭,兴奋
得像久违了青草的一群羊,因为 他们从没有在
一天之中拿到这么多的现钱。以往来收购浆果
或者秋菜的人,多是乡里派来的,给他们打的大
都是白条子。白条子是钱的凭据,但它不能当
钱使,就是 一纸谎言,它不能买柴米油盐、烟
酒糖茶,几年下来,金井人学精了,他们绝不做
不给现钱的买卖。
由于开心,金井人家这一天的晚饭也就较
往日要隆重些--无外乎在桌上添了一碗酱豆腐
,一碟腌 牛肉;再奢侈的,烙一摞油汪汪的葱花
饼,炒上满满一盘的鸡蛋。男人们自然要温一
点酒来喝的,女人呢,心目中已然出现了绸缎的
颜色和图案,它们如朝霞一样浸 湿了她们的心
,女人们在这个夜晚对待男人,自 然也比平日
多了几分温柔。
一年一度的秋收本来像根缜密坚实的绳子
,可是那些小小的浆果汇集在一起,就化成了一
排锐利无 比的牙齿,生生地把它给咬断了。
金井的男人中,有个比女人采浆果还要灵
巧的人,他就是王一五。看看他那双手吧,手形
秀气不 说,那十指修长柔韧得连女人的手都自
愧弗如。王一五不爱种地,但他是个农民,不种
也得去种,他下田时脸上就总是挂着霜。农闲
时,他喜欢把装着碎布头的包袱 打开,用它们
拼衣裳。他家没有缝纫机,一切都是手工操作
。他飞针走线时气定神凝,什么事情也惊扰不
了他。他做的衣裳,大约有上百件了吧,没一件
是人能穿得 了的,全都是小衣裳,只有巴掌那
么大,看来只有精灵鬼怪才能穿得。他老婆牛
桂丽见他爱鼓捣这玩意儿,常把破了的衣裳和
袜子扔给他,让他补,王一五就仿佛是 受了羞
辱似的,急赤白脸地将它们撇开,好像人穿的东
西都是俗物,沾染不得。他也因此招来老婆一
顿连着一顿的骂。他们有个儿子,十一岁了,可
看上去只有七八 岁那般大,瘦削枯黄得像棵秋
天的狗尾巴草,人们都叫他"豆芽"。别的男孩
拎一篮土豆能一路疾行,豆芽提着半篮就趔趔
趄趄、气喘吁吁了。别的男孩敢下河摸鱼 上
树掏鸟窝,他却连自家养的狗都怕。王一五爱
做小衣服,豆芽则喜欢用铅笔画画。他爱画花
鸟虫鱼、房屋河流,他从来不画人,说是世上的
人都是丑的,不能入 画。他画了画,喜欢拈着
它四处走,那样子就像举着一个招魂牌。所以
牛桂丽骂她男人时,常把豆芽也捎带上,称他们
是一大一小两个瘪了的猪尿脬。王一五和 豆
芽都喜欢采浆果,看他们进了林中如鱼得水的
样子,金井人就不无 挖苦地称他们是一双花蝴
蝶。
不秋收了而去采浆果,王一五和豆芽开心
极了,他们第一天就采了半瓦盆的牙各答和一
大茶缸的都柿,所以他们家拿到的钱最多,快六
十块呢,牛桂丽终于发现这爷俩儿的缺点在这
时候成了优点,特意割了把韭菜,对上些虾皮,
包了顿饺子犒劳他们。
涂抹着金井秋天的,是一场接着一场的霜
。初霜来时,山上的树叶会微微泛黄。而第二
场、第三场 霜降临后,树叶就有红的了。这时
节你就可以秋收了。最先收的,是那些不禁霜
的蔬菜,比如西葫芦、茄子、倭瓜和萝卜。接
下来是土豆。最后呢,是比较禁霜的大 头菜和
白菜。其中土豆种植的面积最广,每家都要收
获二三十麻袋,它们会被下到地窖里,成为漫漫
长冬中人畜共用的主要食品。所以单单是起土
豆,每户都要用上 四五天的时间。一般来说,
收完秋后,大地会上一场大冻,蓝天的颜色也会
旧下去,变得灰蓝了,清冷的风把林中的落叶吹
得狂舞的时候,雪花也就纷纷扬扬地来 了,它
们掩埋了秋日最后的绚丽,拉开了苍茫的 长冬
帷幕。
卡车就是收浆果人的家,他吃住都在那里
。卡车上不仅有煤油炉和锅碗瓢盆,挂面、罐
头,调料也 是应有尽有。他支起煤油炉美滋滋
地为自己操持晚饭的时候,采浆果的人也就三
三两两地回来了。他将收来的浆果分门别类地
倒进坛子里,然后将钱一五一十地付给 大家。
这时节晚霞在西边的天际灿灿燃烧着,好像天
也在生火做着晚饭。人们拿了钱,心满意足地
回家了。收浆果的人吃过饭,会把炊具归置好,
抽过 几颗烟后,就钻进驾驶室睡了。
三天下来,金井人和收浆果的人混熟了,男
人们晚饭后也就凑过来和他聊天。那人不吝惜
自己的烟,挨个给大家发上一支。他们抽着烟,
在瑟瑟秋风中讲着关乎男女之事的 笑话,快乐
得如同过年。
大家出于好奇,免不得要问那人,花这么多
钱收这晚秋的浆果给谁?那人说:"这浆果可都
是绿色食品!现如今有钱的人吃果子都要'绿色
'的了!"
金井人就糊涂了,浆果不是红的,就是蓝的
,怎么能说是绿色的呢?未成熟的青果才是绿色
的呢。
大鲁二鲁是金井人中惟一还在秋收的人。
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兄妹,大鲁是男的,二鲁是女
的。他们 已是中年人了。他们的父母,也就是
老鲁夫妇,是一对表兄妹,这使得他们生出的孩
子言语木讷,思维迟钝,严重智障。大鲁二鲁自
幼跟着老鲁夫妇学做各种农活, 所以他们十几
岁时,就是家中的主要劳力了。也许是男女有
别的缘故,虽说他们是双胞胎,但大鲁二鲁在相
貌上却并不完全一样。大鲁浓眉大眼,二鲁则
细眉细眼 的;但他们的鼻子和嘴巴长得很相像
,鼻子是扁的,嘴巴很宽,他们爱笑,永远合不拢
嘴的样子,使嘴巴显得更大了。二鲁的唇角还
有颗痣,她常常用小拇指抠它, 好像它是只苍
蝇,要把它拂走才是。可是这样的 "苍蝇"无论
如何是轰不走的。
老鲁夫妇几年前先后去世了。他们临终留
给这对兄妹的遗言就两条:第一,不许睡在一起
;第二, 春天播完种,别忘了秋天下了霜就秋收
。大鲁二鲁牢牢记住了这两点。他们不像其他
人家喜欢用日历,金井的山峦,在他们眼里就是
一个巨大的日历。翻动这日历 的,就是风霜雨
雪。当暖风让这日历透出隐隐的绿色时,他们
就去播种了,而当秋霜将这日历点染得一派绚
丽时,他们准时地去秋收了。
金井有个老女人,她男人在她三十岁时就
瘫倒在炕上了,她既要侍候男人和当时只有六
岁的女孩, 又要独自种植大片的土地,她自此
白了头发,人们就不叫她的本名了,而叫她"苍
苍婆"。苍苍婆不像别的女人遭了难后终日以
泪洗面、唉声叹气,她的头发全白了 之后,她
的心也仿佛一下子跟着变得光明了,她爱说爱
笑了,学会了抽烟喝酒。有一个薄雾的傍晚,喝
多了酒的她披散着白发在村中游走,撞见她的
人都以为看到了 鬼。女人们那时都不喜欢她,
谁都知道她男人是个废物了,她们怕缺乏滋润
的苍苍婆会偷她们男人身上的雨露。但苍苍婆
并没有窃取男人身上雨露的意思,她大约也 是
不缺乏雨露的,她是金井的农妇中惟一热爱大
雾和雨水的人。雨雾天气中别人都死气沉沉的
,她却兴味盎然地在雾中雨中穿行,有时还放声
歌唱着。她从不用雨 衣,任雨水把她打湿,好
像她是一条鱼,与水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三
十年过去了,苍苍婆的女儿已经嫁到乡里去了,
她的男人却依然躺在炕上靠着苍苍婆的服侍而
活着。人们都说苍苍婆心眼好,换做别的女人
,少侍候他几天,他也就一命呜呼了,谁又会追
究她的责任呢?苍苍婆彻底老了,以前她只是白
着头发,脸颊却是饱满 光洁的,如今她的脸颊
塌陷了,眼角的皱纹密密麻麻的,嘴也微微瘪了
,但她的眼睛,却没有老年人的那种混浊,依然
那么明亮,清澈逼人,好像她的眼底浸着一汪
泪,使她的 眼睛永远湿润而明净。
苍苍婆平素爱逗大鲁二鲁,她常说的一句
话是:"大鲁二鲁一个被窝睡吧,生出个小鲁,让
苍苍婆当羊乖乖搂着!"
大鲁正言厉色地回答:"爸妈死前嘱咐了,
大鲁二鲁是不能睡在一块的!"大鲁从不称自己
为 "我",而是"大鲁";二鲁也是这样,她朝别人
家借农具,不说"我要借镐",而是说"二鲁借把
镐"。他们强调着自己的姓名,似乎提醒金井的
人,不要漠视他 们的存在。而事实上他们的名
与姓被大家叫颠倒了,他们的户口上明明报的
是"鲁大""鲁二",老鲁夫妇包括其他人却都叫
他们大鲁二鲁,叫顺嘴了,他们也就在 不经意
间把姓给挪到名字的尾巴上了--那也就成了名
,致使他们好像没姓了似的。
苍苍婆只要见着二鲁,就把目光放在她的
肚子上,仔仔细细地打量一番,末了总要叹口气
,说:"你这肚子里还真是没有小鲁啊。"听上去
分外惋惜的样子。在她眼中,大鲁二鲁是这村
中最可爱的人,老鲁夫妇丢给金井的,不是一对
弱智的孤儿, 而是两只美丽温和的鸟。
二鲁见苍苍婆盯着她的肚子看,就说:"二
鲁没饿着!"二鲁笑着,笑得格外的明媚。
苍苍婆说:"我是想看里面有没有小鲁!"
二鲁似懂非懂地说:"只有大鲁二鲁,没有
小鲁!"
金井人常把这些话当做田间地头的笑谈和
晚饭后的闲聊。这样的话题对男人来说是饭后
的一支烟,而对女人来说是渴极时的一杯凉茶
。
采了三天浆果的苍苍婆终于想到该叫大鲁
二鲁也去挣点现钱,这样的好事把他们落下了,
叫她心里不忍。苍苍婆就在这天晚饭后摇摇
晃晃地去大鲁二鲁家了。
大鲁二鲁收了一天的萝卜,趁着天还有微
微的亮光,将它们一筐 筐地下到菜窖里。
满嘴酒气的苍苍婆亢奋地叫道:"大鲁二鲁
,别秋收了,采浆果去吧,能拿现钱!大鲁过年时
就能买新鞋穿了,二鲁也能买件花衣裳 了!"
大鲁二鲁没有日历,所以他们常常错过一
些节日,比如端午节和中秋节。但春节是不会
从他们眼皮 底下溜掉的,因为除夕的早晨便有
鞭炮声响起,入夜时家家门前又都有点燃的冰
灯。他们过年不像别人家,瓜果糖茶都要买些,
而且人人都穿着簇新的衣裳。他们永 远都穿
着旧衣裳,只不过晚上时包一顿饺子吃而已。
当然,他们也会冻上两座冰灯,一左一右地摆在
门口,让它们充 当暗夜的一双眼睛。
大鲁说:"苍苍婆,爸妈死前告诉大鲁了,下
了霜就秋收,大鲁都点了头了!"
二鲁也说:"春天撒了种,秋天就得收庄稼,
二鲁也记着呢!"
苍苍婆说:"你们真是一对傻瓜,这天响晴
响晴着呢,晚个十天八天秋收,你种到土里的东
西也不能长翅膀飞了;可你要是不采浆果,就得
不到现钱,等你们收完秋去采,收浆果的人早就
走了,你们一分钱也 挣不到!"
大鲁二鲁不为所动,在他们看来,秋收才是
天经地义的事。他们喂了两头猪,四只鹅和十
几只鸡, 家畜们一个冬天吃的东西全靠这些秋
菜。这不像植物生长的季节,你把它们撒出去
放养,它们总能找到吃的。冬天的金井,永远被
厚厚的积雪覆盖着,雪粒就是再像 白米的话,
也不 能当粮食吃啊。
没有劝动大鲁二鲁,苍苍婆只能摇头叹息
。以前她不认为他们傻,这一刻她认定他们的
脑袋里灌了猪屎,实在是臭!
苍苍婆离开大鲁二鲁家时,抬头看了一下
天,她发现星星出来了,一个个跟刚出壳的鸡雏
似的,毛 茸茸、黄莹莹的,新鲜而可爱极了,看
来明天又是一个大晴天。苍苍婆认定星星都有
点化尘世当中愚钝的人的神力,她就求助于一
颗最亮的星星,指点着它说:"今 晚给大鲁二鲁
开开窍吧。"说完,她才略觉心安,想着明天又
可有钱揣进口袋,不由得哼起了小曲。或许是
酒的作用,或许是年纪大了腿脚不那么灵便了,
走着走 着,苍苍婆忽然跌倒在地。她本来能立
刻就爬起来的,可她躺倒后,发现镶嵌着星星的
夜空就像一床蓝地黄花的缎子被盖在她身上,
令她无比陶醉,她就索性多躺了 一会儿,然后
缓缓爬起来,朝家走去。想着家中暗淡的灯影
下,有一个几近骷髅的老男人的脸等着她擦拭,
苍苍婆的泪水就像一群奔着光明而来的飞蛾,
扑了她一 脸。
天刚亮,曹大平夫妇就提着竹篮出了家门
。他们昨天发现了一片隐藏在河谷转弯处的山
丁子,显然 那里无人涉足,树上垂吊的果子比
别的地带的要多得多,他们想独享这片果实,所
以早早就出发了。他们快接近河谷时频频回头
张望,生怕有人跟上他们。人没跟上 他们,倒
是他们家的狗跟来了。曹大平停住,回头呵斥
狗:"滚回家看门去!"那狗脸皮薄,挨了骂后一
缩头,夹着尾巴回 家了。
太阳出来了,阳光充满了活力,它从树梢穿
下来,一直照到地面的 落叶和枯草,好像它的
光芒能刺透泥土,使它们能像种子一样埋到土
里去。如果阳光变成了种子,大约人间一年四
季都是春天了。
曹大平夫妇的心情跟阳光一样明朗。他们
边采山丁子边计划卖浆果的钱的用途。男人说
要买一个电 动刮胡刀,他的胡子长得快,每周
都要刮两三次。用人工的刮胡刀常常失手,弄
得下巴上旧的伤痕未去又添新痕。女人笑着说
:"你的胡子要是麦子就好了,那样我 给你买个
金子的刮胡刀也值得!"曹大平"呸"了女人一口
,说:"我的脸要是能长出麦子的话,也轮不到你
做我老婆了,我起码要找个比你嫩十岁的!"女
人说: "你找个比你小四十岁的多好,连带着把
她的奶娘也收了房!"他们互相打趣着,男人又
说要买一坛黄酒和一顶山羊绒帽子,女人的主
意变得快,刚说完要买花头 巾,想着家里的菜
刀钝得磨不出锋刃了,就说买菜刀,一想到菜刀
还能对付着使,又想添一条毛料裤子了。说来
说去,他们想买的东西足可以开个杂货店了。
两个人 就嘲笑自己不切实际的支出,说到底还
是钱好啊,钱多了,可以随心所欲买东西,他们
羡慕那个收浆果的人,他是多么有钱啊。
他们边说边采着山丁子,不知不觉中,太阳
已经遨游到中天了。这岸的果实已经采尽,他
们就着咸菜疙瘩分别啃了个凉馒头,打算渡过
青鱼河,对岸有一片茂密的透着隐隐红光的山
丁子树,说明挂在枝头 的果实仍然可观。
青鱼河不是流经金井惟一的河流,但它却
是最宽的。这河水流急,深不可测,因而很少有
人在夏秋之时到对岸采浆果。一般来说,青鱼
河被寒风冻僵了之后,才会有人拉着爬犁从它
身上走过,去柳树丛中拾 捡干枯的枝条当柴烧
。
曹大平夫妇决定涉水渡河,也是想把还有
富余的竹篮给装满了。他们折下一根山丁子的
枝干,一方 面用它当拐棍,一方面用它来试探
水的深度。虽然天已经凉了,但他们还是脱下
了外裤和绒裤,把它们搭在肩头,光着腿下河。
他们怕把裤子打湿了,秋日的阳光一 时半会儿
又晒不干它。曹大平左手提着树枝在前,他老
婆右手挎着竹篮在后,男人的右手和女人的左
手十指相扣地紧紧地攥在一起,他们侧身而行,
以削 弱水流的强度。
河水凉得他们直打寒战,好像它是刚由冰
块融化开来的水流。但见河床上阳光飘舞,可
是他们却感 觉不到温暖之气,想来秋日的阳光
早已没了火力了。开始他们还能忍受得住,随
着河心的临近,水涨到他们腰际了,水流的冲击
力加强了,他们有些站不稳,但他们 咬着牙,互
相鼓励,坚持着,虽然他们不敢张望对岸的果实
,但他们知道它离他们越来越近了。曹大平拄
着的树枝,被河水吞吃得越来越多,裸露在水面
上的,只有 筷子那么长了。突然,曹大平的腿
抽筋了,他栽歪了一下身子,水花就扬起巴掌,
劈头盖脸地朝他打来,他呻吟着,惊恐地看着白
花花的水欢笑着从脖颈下跃过。幸 而曹大平
的女人比他高半头,又健硕,她紧紧地拉住丈夫
不撒手,尽管她也栽歪了身子,而且挎着的竹篮
像个顽皮的孩子似的,趁机从她胳膊肘 那儿溜
走了。
装着果实的竹篮最初跌入水中时,它自身
的重量使它充当了石头的角色,沉入了水底。
但是很快, 水流掏空了那些落花般的果实,竹
篮又浮出水面。它被激流推动着,像个小脚女
人,摇摇摆摆地向下游去了。曹大平夫妇的衣
衫也被水打湿了,他们赶紧向回返,相 互搀扶
着哆哆嗦嗦地回到岸边。上岸后,曹大平才发
现搭在肩头的裤子不见了,他想一定是他在水
中挣扎时,裤子充当了叛徒,从他肩头跳下来逃
跑了。女人把自己 的外裤分给他穿,而她自己
,只得穿那条紫红色的绒裤了。他们坐在河滩
上,一个接着一个地打着寒战,想着青鱼河要真
的是一条大青鱼就好了,他们会从家里拿来 斧
头,把它砍得血肉横飞、断肢解体。女人想着
不但没有渡过河去,而且一上午的成果付诸东
流,忍不住哭了。曹大平一开始忍着,但他想起
今天不但赚不到一分 钱,而且装干 粮的竹篮
和自己的裤子也被河水卷走了,备觉凄凉,他也
跟着落下泪来。他们很委屈地离开河岸,踉踉
跄 跄地朝家走去。
曹大平一回去就发烧了,他的女人忧愁地
在灶间把风干的姜捣碎,为他煮姜汤时,那条遭
到呵斥的 狗满怀怜爱地凑过来,用它湿漉漉的
舌头舔着主人滚烫的脸颊,曹大平又一次落泪
了,他觉得自己捡了一条命。他憎恨青鱼河,憎
恨河对岸的果实,憎恨手中握着大 把大把钱的
收浆果的人,他对狗说:"我就是没有炸药包,要
不给你绑上,你把那卡车给我引爆了,把那些盛
浆果的坛子炸他妈个稀里哗啦的!"狗没有迎合
他的 话,仍然舔着他的脸,倒是蹲在灶前续柴
火的他的妻子,听了 这话后满面凄苦地笑了。
晴朗已经持续了一周,收浆果的人带来的
那些空坛子,有五只已经是满的了。他花了二
十元钱,在 李占前家捉了只活鸡宰了,用柴油
炉炖了整整一个下午,满村子都飘拂着鸡汤的
香味,弄得那些饥肠辘辘的采浆果归来的人口
水涟涟。这人倒也不贪嘴,让姓张的尝 口汤,
给姓李的分条腿,又撕给姓王的一只翅膀,很快
,一只鸡就没了踪影。那些尝了鸡肉却没有尽
兴的人,回家后看着鸡鸭鹅狗时难免露出觊觎
的眼神,吓得家畜 们不敢靠近主人,惟恐 刀落
在自己的脖子上。
苍苍婆爱采的浆果,只是都柿。在她眼中,
能让人醉的果实才有人性。稠李子、山丁子尽
管也酸甜可口,却没有享用都柿的那种迷醉感,
苍苍婆就觉得这样的果实太贫乏 了。
都柿确实奇怪,你若是吃上一捧两捧也没
什么,但若是吃上一海碗,目光就会发飘,腿也
软了。据 说当年森调队员勘察森林,看到那一
片片碧蓝饱满的果实,吃起来甜中带酸,酸中又
透着甜,十分解渴,就大把大把地往嘴里扔,结
果吃得一个个醉倒在地,险些成 了狼口中的食
物。七八月间,都柿熟了的时候,外地收购它的
人就来了,收它都是为了酿酒。不过那价格低
极了,四五 毛钱一斤,你顶着烈日的烘烤和蚊
虫的叮咬,一天中采了满满一桶,不 过挣个十
块八块的。
苍苍婆因为贪吃都柿,醉过已不知多少次
了。她年轻的时候,那时她男人还生龙活虎着,
有一回她 进山采都柿,回来时篮子却是空的,

而她自己的嘴唇,却已被这浆果染成黑紫色,好
像她的唇上落着只紫蝴蝶。她见了人只是痴痴
地笑,你无论问她什么话,她只是 拖着长腔软
绵绵地说:"美--啊--"她是把自己的肚子当做
篮子,将都柿全都采到那里去了。她的肚子也
因此成了酒窖,从口腔散发出浓郁的酒香气。
苍苍婆的 男人嫌她醉成这样给自己丢人,很少
让她去采都柿。但你又怎么能管得住她呢?有
一年的八月,金井接连下了几场雨,雨水会催发
菌类植物的生长,苍苍婆对她男人 说,她要去
采木耳,男人就让她去了。可是她早晨出去,黄
昏了也没回来。她男人心焦了,约了两个男人,
提着马灯进山找她。天黑了,月亮起来了,除了
猫头鹰之 外,林中的鸟儿也歇息了。他们左一
声右一声地呼唤她的名字,可就是没有回应。
最后还是苍苍婆的男人醒悟过来,她别是打着
采木耳的旗号,又偷偷吃都柿去了, 因而无声
无息地醉在了山里。于是他们开始在生长着都
柿秧的地方寻找她。后半夜时,果然在一片茂
盛的都柿丛中发现了她。月光照映着她,给她
酣睡的脸涂上一层 宁静安详的白光。她背囊
里只有一小捧湿漉漉颤巍巍的黑木耳,嘴唇已
然被都柿染得一派青紫。她的衣裳还被扯开了
一道口子,没有穿背心的她露出一只乳房,那乳
房在月光下就像开在她胸脯上的一朵白色芍
药花,简直要把她的男人气疯了。他把她踢醒,
骂她是孤魂野鬼托生的,干脆永远睡在山里算
了。她被背回家,第二天彻 底清醒后,还纳闷
自己好端端的衣裳怎么被撕裂了一道口子?难
道风撕开了它?她满怀狐疑地补衣裳的时候,从
那条豁口中抖搂出几根毛发,是黑色的,有些硬
,她 男人认出那是黑熊的毛发。看来她醉倒之
后,黑熊光顾过她,但没舍得吃她,只是轻轻给
她的衣裳留下一道赤痕。一般的女人会为此后
怕不已,可苍苍婆却笑着说: "黑熊见了我的奶
子都不肯吃一口,看来它是没什么趣味的!"
开始的几天,苍苍婆还像规规矩矩的小学
生一样,在林中认认真真地采上一天的都柿,黄
昏时一本 正经地将它交给收浆果的人,换来几
十块钱。可是接下来的日子,当她独自在林中
垂下老迈的腰,手指触及到皱纹累累的已经蔫
软的都柿的时候,她的心凄凉了,想着果实老
了还有人寻觅,女人老了却是无人问津。她尝
了一粒都柿,真是甜极了,这甜让她更觉凄凉,
苍苍婆就很想喝上一碗酒,抑制一下满腔的悲
凉。山上没酒, 她自然把采来的都柿当酒吃,
竟一发而不可收,吃空了盛都柿的盆子。苍苍
婆意犹未尽,索性直接把刚采到手里的果实丢
进嘴里。秋天的阳光雪亮而干爽,像是一把 刚
晾晒好的麻线,无处不在地缠绕着她,让她有纳
鞋底的欲望。苍苍婆在林中穿行的时候,一些
干枯的树叶就被摇晃下来了,它们有的落到她
的头上,有的则滑过她 的肩头,回归大地。苍
苍婆披散着的干涩而苍白的头发上,就有了火
红的鹅掌形的榛树叶,心形的金黄色的杨树叶,
当然更多的,是那些像针一样细而短小的松树
的 针叶。它们簇拥在苍苍婆的头上,像是一群
色彩明丽的 鸟落在了雪野上。
这天晚上苍苍婆是紫着嘴唇回到金井的,
一看她那逍遥的步态,人们就知道她犯了年轻
时的老毛病 了。她将空盆子当草帽一样提着,
并且不时晃悠两下,像个调皮的少女。她的气
力不比从前了,所以即使她哼着小曲,人们也听
不清是什么,跟蚊子哼哼没什么两 样。她刚进
村子,就碰见了拉着手推车从田地归来的大鲁
二鲁,车上堆着七八麻袋的土豆。大鲁肩上挎
着绳子在前拉,二鲁则在车尾推车。他们的脸
被泥土和 汗水弄成了花脸。
大鲁二鲁见了苍苍婆,停下车来,等着一贯
爱跟他们说话的苍苍婆问他们话,也顺便歇口
气。
苍苍婆晃晃悠悠地走过来,她先是用手中
的空盆打了一下装满了土豆的麻袋,骂:"都是
你们不懂 事,你们就那么俊啊,非让大鲁二鲁
把你们从土里起出来,要不他们进山采浆果,能
挣多少钱啊!"接着,她又用空盆打了一下大鲁
的胳膊,骂:"死心眼,就知道 笑!"大鲁确实笑
着,笑得就像刚从乌云中钻出来的太阳。二鲁
不等苍苍婆吆喝她,主动从车尾走到苍苍婆面
前,苍苍婆依旧用空盆打了一下二鲁,打在她的
肚子 上,嚷着:"我算是抱不上小鲁了!"二鲁笑
得更欢了。
苍苍婆就在大鲁二鲁的笑声中叹息着走开
了。她没有回家,而是去了收浆果的地方。她
看着那辆卡 车,说它是只铁鸟。收浆果的人跟
她已经熟了,他逗提着空盆子的苍苍婆:"你采
的果子哪儿去了呀,是不是都让狐狸给偷吃了?
"苍苍婆哈哈笑了,她不无得意地 用左手的食
指点着自己的鼻尖说:"让这只老狐狸给吃了!"
牛桂丽正领着豆芽等着给浆果估价,她说
苍苍婆:"你又偷吃都柿了?醉了吧?"
苍苍婆绷着脸说:"我采的我吃了,怎么是
偷?"
豆芽插话说:"人家说你过去吃醉了都柿,
差点没让熊给舔了,你不怕死?"
苍苍婆啐了一口唾沫说:"我还怕死?我乐
意死,可我死不了!我想着死后变成个小人,到
时你爸给鬼精灵做的那些小衣裳就能派上用场
了!"
豆芽嘻嘻笑了,说:"苍苍婆要是能穿上我
爸做的那些小衣裳,我 用巴掌就能托着你了!"
苍苍婆对豆芽说:"人长得不大,心眼倒是
不少!"
牛桂丽最忌讳别人说豆芽长得小,苍苍婆
的话令她不快,她说:"人小人大有什么,人活着
,身上的零件都管用就行呗!"
牛桂丽这是影射苍苍婆那不中用的男人呢
。苍苍婆听出了弦外之音,但她故作糊涂着,问
收浆果的人,哪几个坛子还空着?那人笑着说:"
苍苍婆,牙各答和山丁子都收足了,就等您的都
柿呢!您看来是不缺钱用啊,全都自己享受了!"
这时候又有三个采浆果的人回来了,一个
说撞见蛇了,一个说看见了一种从未见过的鸟,
它发出的 叫声像小孩子的哭声。另一个嘟囔
着倒霉,眼皮被蚊子叮肿了不说,半新的裤子还
被树枝划了道口子。可是当他们拿了钱后,谁
也不发牢骚了,他们带着喜悦回家, 走前都满
怀同情地看着一无所获、佝偻着腰渐行渐远的
苍苍婆。收浆果的人为了安慰她,曾丢给她一
张十元钞票,让她买酒,苍苍婆捡起钞票,运足
一口气,又把它 吹回地上,苍苍婆说:"钱是什
么,不就是一张落叶么?蚂蚁合伙举过落叶,这
样的叶子它们没见过,留着给蚂蚁们举着玩,当
遮阳伞使吧!"说完,她就一摇一摆 地走了。
"这个苍苍婆,倒清高!"收浆果的人看着她
苍老的背影说。
牛桂丽吩咐豆芽把那十块钱捡起来还给收
浆果的人,她以为他会顺水推舟地送给豆芽。
谁知豆芽举 着钱还给主人时,那人竟接了过去
,揣进口袋,就像一个旅人揣上一张煎饼一样自
然。牛桂丽扯着豆芽回家时就有些不快,她嫌
豆芽没有叫那人一声"叔叔",没有 冲人家笑,
十块钱自然就不会送他了。牛桂丽一旦把责任
归咎于豆芽身上,对他的火气也就一路升级,到
了家门口时,朝他的屁股狠狠踢了几脚,骂他:"
蠢猪!" 豆芽不禁踢,他倒在地上,像球一样滚
了两下,滚出一串屁来,牛桂丽听到屁声气上加
气,她说:"你还说饿呢,肚子瘪的人怎么有屁放
呢,我看你就别吃晚饭 了!"
苍苍婆连着四天空手而归了。想必她进山
时还是下决心要采回都柿的,她不忘了带盆子,
可她回来 时盆子仍是空的,可见她禁不住诱惑
,又让自己的肚子充当了都柿的容器了。中止
了浆果采摘的,除了苍苍婆,还有曹大平夫妇。
曹大平一直病在炕上,他发烧时胡 话连篇,一
会儿说家里的炕洞里钻进了一只绿眼睛的狼,
一会儿又说星星掉下来,砸漏 了他家的屋顶。
他清醒的时候,就一瓢接一瓢地喝水,喝完水总
要骂一句"小妈养的青鱼河",复又虚弱地倒在
炕上昏睡。曹大平的女人唉声叹气的,男人的
病像一 只无形的手,拖住了她的腿。她既不能
采浆果,又不能去秋收,只能守着他。
大鲁二鲁刨完了土豆,又砍了白菜和大头
菜,把它们运回来,腌了两缸酸菜和一缸咸菜,
然后把余 下的菜下到窖里。之后,他们把遗落
在地里的菜帮也捡起来,装进麻袋,拉回家堆在
仓房旁,作为猪饲料。最后,他们踏着更浓重的
霜,去了大草甸子,夏天时大鲁 打了一些猪草,
早已晾干了,他们用绳子把猪草背回来。干草
在他们背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气,让他们觉
得背着的不是草,而是戴着花环的小女孩。
就在大鲁二鲁扛回猪草的那个夜晚,天空
悄然凝聚了一团又一团的乌云,星星和月亮全
然不见了。 乌云越聚越多,夜色浓重,气温骤
降,雪花就像一位端庄、美艳、率性的公主,没
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乘着冬天的雪橇来了。
金井人没人注意到下雪了,因为雪是 在夜里来
的,在森林河谷中奔波了一天的采浆果的 人,
都沉浸在梦乡中了。
雪越下越大,到了清晨,雪深近两尺。当金
井的主妇们推开家门抱柴生火时,发现世界已
改变了颜色。雪没有停的意思,仍然漫天飘舞
着。女人们慌慌张张进屋喊起了丈夫,又吆喝
起了孩子,他们纷纷奔到窗前,看着苍茫的大地
,一个个目瞪口 呆。
金井人一年的收获,就这么掩埋在大雪之
下了。大地彻底地封冻了。
人们脸上满是凄苦的表情。有的女人甚至
扑倒在雪地上哭了起来,哭他们的土豆、白菜
和红红的萝 卜,好端端地就被冬天给糟践了。
他们冬天吃什么?他们的牲畜和家禽吃什么?他
们觉得上了收浆果的人的当,纷纷走出家门,不
约而同地朝卡车停放地走去。哪里 还有什么
卡车的影子,它早已不见了,村路上连个车辙都
没留下,可见他是在雪花 到来前就走了。想着
卡车上那些装载着浆果的坛子,金井人恨不能
戳瞎自己的眼睛。他们认定这辆卡车 是魔鬼
变成的。
卡车曾经停留的地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王一五一家也来了。豆芽跟在父母身后,手里
捏着一张 纸,纸上画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披
散着长发,有着狐狸一样秀丽的脸庞,唇角漾着
笑意,眼睛明亮极了,所有在场的人都认出那是
年轻时的苍苍婆。豆芽并没有见 过那时的苍
苍婆,那时他还没出生呢,可他却逼真地画出了
旧时光中的苍苍婆,让所有见着这画片的人都
大吃一惊。这个声称人都是丑的、绝不能让人
入画的孩子, 终于画了一个人。大人们默不作
声地垂立在风雪中,在他们眼里,豆芽提着的就
是一幅女人青春的遗像。
只有苍苍婆没有来到卡车平素停靠的地方
。不是她没出家门,她出来了,到大鲁二鲁家去
了。她站在他们的院门前,隔着白桦木栅栏,望
着这户惟一收获了庄稼的人家,想着这个冬天
只有他们家是殷实的,她的心中先是涌起一股
苍凉,接着是羡慕,最后便是弥漫开来的温暖和
欣慰。
二鲁推开屋门,她出来抱柴火了。大鲁也
出来了,尽管雪仍在下,他还是拿起扫帚清理积
雪了。他 们抬头眺望着远处金井的山峦,看着
昨天还是花花绿绿的日历,今天就突然变成了
白的,他们相视而笑了。 苍苍婆注意到,二鲁
的脖颈上有一圈火红的东西。虽然离着很远,
无法仔细辨别,但她知道那一定是串野刺莓。
金井的女孩,最喜爱穿这样的项链来戴。野刺
莓多生 长在田间的高岗上,它们春天开花,夏
季结果。到了秋天,它的果实就风干了,像是一
粒粒火红的珠子。看来在秋收的间隙,大鲁二
鲁也采了浆果。只不过他们只采 了很少的一
种,并且为它们做了最美的镶嵌。
《收获》2004年第5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