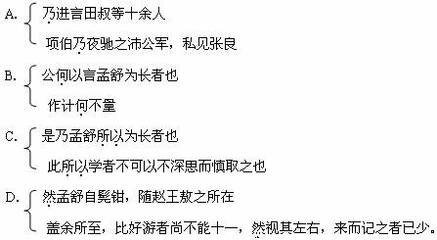抵抗·风格·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内容提要亚文化(Subculture)是通过风格对主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特殊文化方式,往往涉及边缘文化、弱势群体对主文化和权力的抵抗,一直以来都是文化研究的重点所在。如何看待亚文化的抵抗?亚文化以何种方式对社会产生影响?亚文化的风格究竟该如何估量?亚文化如何被主文化收编?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国内学术界目前研究亚文化大都误用或滥用某些概念,致使一些相关研究每每带有“失语”和“错位”之感。因此,梳理、考察并剖析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关键词就显得不可或缺。关键词 亚文化理论 抵抗 风格 收编 |
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指聚集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Contemporary CulturalStudies,简称为CCCS)周围从事文化研究工作的学者,如霍加特、霍尔、赫伯迪格、威利斯、费斯克等。伯明翰学派高度重视亚文化研究,“流行音乐及青春文化”位列CCCS1964年成立后的首批研究项目。[1]CCCS的主干课程“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有5个研究方向,亚文化研究占据了两项:“文化、亚文化和阶级”和“支配文化、附属文化和独特文化和反文化”。[2]伯明翰学派崇尚小组探究和集体合作,重视个案研究、民族志调查和文本分析,多方借鉴西马、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人类学、女性主义等理论,研究了欧美自19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如无赖青年(teddyboy)、光头仔(skinheads)、摩登派(mods)、朋克(punk)、嬉皮士(hippie)等;从197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伯明翰学派出版了《仪式抵抗》、《学会劳动》、《世俗文化》、《亚文化:风格的意义》、《监控危机》、《帝国反击》、《躲在亮处》、《共同文化》、《女性主义与青年亚文化》等十多部亚文化专著,多已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路数和成果构成了亚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库和风向标。考察其亚文化理论,可以为国内青少年亚文化研究提供一些理论资源,而且能为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提供一些研究路数和方法论的参考。
一、抵抗
在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中,亚文化对主文化(主导文化、主流文化、主体文化)和霸权的抵抗是一个核心问题。伯明翰学派的领袖斯图亚特·霍尔在第一部著作《通俗艺术》(1964,与沃内尔合著)里这样描述亚文化的抵抗:青少年形成了特别的风格(特殊的交谈方式,在特别的地方以特别的方式跳舞,以特殊的方式打扮自己,和成人世界保持一定距离),他们把穿着风格描绘成是“一种未成年人的通俗艺术……用来表达某些当代观念……例如离经叛道、具有反抗精神的强大社会潮流”。[3]霍尔敏锐地指出:青少年亚文化形成特别的风格,其目的就是为了“抵抗社会”,这种抵抗有可能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
那么,青年亚文化抵抗的到底是什么呢?伯明翰学派对此的回答是: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不是代际间的矛盾,而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和集体经历的问题(贫穷、失业、住宅拆迁等)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亚文化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如工人阶级、黑人、亚裔、女性的特殊抵抗方式,不仅不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而且恰恰相反,青年亚文化表征了一种反霸权的意识形态,是与他们生活真实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青年亚文化用引人注目的风格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共识的破灭和瓦解。”[4]
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和主导的价值和文化。更为准确地说,亚文化可能产生于经济混乱的地方,或产生于由于再发展引起的社会迁移的语境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生产确实发展和生活条件确实改善的条件下,英国社会所允诺的“富裕”和“中产阶级化”,并没有给青年们的生活带来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并没有消失,阶级差别和贫富分化等不平等依然严重,青年们依然要面对低微的薪水、令人厌烦的的周期劳动和不能接受教育的现状。菲尔·科恩曾精辟地指出:“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母体文化所产生的接踵而至的亚文化都可以被视为基于这一核心主题的不同变体——在传统工人阶级清教徒主义和新兴的消费享乐主义之间的矛盾:部分变化中的社会精英或新出现的游民之间的经济层面上的矛盾。摩登派、帕克族、光头仔、克龙比族,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5]科恩的话意思是: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源于持续不断的社会结构矛盾、阶级问题以及相应产生的文化矛盾,抵抗是为了提出一个“集体解决办法”(collectivesolution),以极端的方式具体再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一观点或许可通俗地概括为: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
亚文化的这种抵抗是对资产阶级的霸权的抵抗。霍尔等人指出:“在与统治阶级的霸权的联系中,工人阶级被限定为附属的生活和文化形式……当然,有时霸权是强大和坚固的,附属阶级是虚弱的、不情愿的和被强加的。但它不会通过限制就消失,它作为附属结构依然存在,经常处于分离和不可渗透的状态,虽然仍然被统治阶级的无所不在的规则和领导所容纳。”[6]这就是说,尽管工人阶级的抵抗在历史中潮涨潮落,但是它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因为它位于一种阶级结构和对霸权文化的反抗的位置中——亚文化就是最明显的表征。
以英国的1950年代出现的无赖青年亚文化为例。无赖青年都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在街头惹是生非,被称为最初的“具有反叛精神的民间恶魔”。他们时常穿着改装过的爱德华式服装在街上闲逛。爱德华(Edward,Teddy是其昵称)式的服装本是为贵族青年所设计,包括一件狭长的掐腰夹克衫,一条窄腿裤,一件时髦的马甲,圆领的白衬衣和打成温莎结的领带,爱德华式服装被无赖青年挪用和改造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紧身直腿裤、厚底鞋、缎子领或斜纹布领的宽夹克、系成“鞋带”式样的领带,服装颜色也进行了大换样,变成了大红大绿的颜色。奇装异服的无赖青年把自己装扮成想象中的贵族青年的模样,以弥补战后工人阶级社区文化被破坏后的失落心情。无赖青年出现在战后英国沉闷的,毫无生气的时期,他们主要来自非技术阶层,被关在英国战后繁荣的大门之外,缺乏学校教育,不能进白领阶层。他们的服装风格“实际上掩盖了从事体力劳动的无技术、半游民的真实生活与周末晚上衣冠楚楚却又无处可去的经历之间的差距。”[7]

值得重视的是,伯明翰学派把亚文化的“抵抗”视为一种寻求“认同”(Identity)。这样,他们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对抵抗也作出了了阐释。霍尔等人认为:流行音乐亚文化——歌曲、杂志、音乐会、节日活动、滑稽戏、与流行歌星见面、电影等等——可以帮助青年人树立一种认同感。[8]“亚文化风格的组成不仅包括团体可以利用的物质材料——为了建构亚文化认同(服装,音乐,言谈),也包括他们的语境(行动,功绩,地点,咖啡馆,舞厅,迷幻剂,晚会和足球赛)。新闻报道在宣传时牺牲了这些东西的用途,记者们特别想弄明白的是:它们怎么被借用和被转换,借此可以开始行动的活动范围和空间,铭刻着东西和物体的风格的集体认同和外表……”[9]。伯明翰学派所谓的“认同”,即“个体将自我身份同至少另外某些身份相融合的过程”。[10]和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著名的“认同”学说大体相近。埃里克森认为的“认同”是指的是“个人独特性的意识感”,“经验连续性的潜意识追求”,是“青春期自我的最重要的成就”,[11]简言之就是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回答“我是谁”、“立于何处”、“何去何从”等问题,包括自我认同、集体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性别认同等。埃里克森认为,青少年亚文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青春期聚集了早年尚未解决和整合的“认同危机”,存在着对成人承担义务的合法延缓期,是最容易发生认同危机或混乱的时期。[12]为解决认同危机,青少年热烈地寻求可以信仰的人、观念和偶像,醉心于时尚的追求。为了体现认同并防御认同感的丧失,他们制造出了各种风格,作为“圈内人”和“圈外人”的标志。青少年亚文化因此产生。[13]
二、风格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往往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往往停留在闲暇领域。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里出现频率颇高的关键词也正是“风格”(style,或译为“文体”)。伯明翰学派是把亚文化看作一种“巨型文本”和“拟语言”,对其“文体”(风格)的抵抗功能和被收编的命运进行解读:“风格问题,这种因时代而产生的风格问题,对战后青年亚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14]“对风格的解读实际上就是对亚文化的解读”。[15]这也正是伯明翰学派的一个核心观点:青少年亚文化制造出各种盛行一时的独特的风格和符号系统:音乐、文学、舞蹈、行动和暗语等,通过风格来协商他们的阶级存在。
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最重要的著作是霍尔等主编的《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Youth Subculture in Post-warBritain,1976)(以下简称《仪式抵抗》)和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The Meaningof Style,1979)(以下简称《亚文化》)。两本著作的书名不约而同地都触及到了“风格”。
《仪式抵抗》中的“仪式”(Ritual,或译为“礼仪”)和“风格”是同义词,即“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许多人类学证据都指出,社会动荡之际或者个人或群落的‘常态’在某些方面觉得受到威胁之际,礼仪活动就随之加剧。”[16]特殊时代的“文化意味”是要依靠“仪式”通过象征化或符号化的“活动”(服装、语言、音乐等)来传达的。”《仪式抵抗》从人种志调查和理论层面细致地探讨了工人阶级文化的危机是如何通过亚文化的风格体现出来的:“我们把注意力首先投向风格产生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亚文化的活动、实践和外观通过一些非常有限而又连贯的形式得以表达。”[17]“亚文化群体开发了群体内部生活的核心关切、惯例和禁忌一系列社会仪式,依靠它们建立了群体的认同……它们采纳和适应着物质客体——商品和财富并把对其进行重新组织化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表达了它们的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的集体性……”[18]。在伯明翰学派看来,无赖青年、摩登族、光头仔等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是种种仪式的聚集,是一种在霸权和反霸权的斗争领域产生的抵抗形式。
赫伯迪格的《亚文化》更是以“风格”为突破口,认为亚文化的颠覆意义正是通过“风格”得以体现:“亚文化所代表的对霸权的挑战并不是直接由亚文化产生,更确切地说,它是间接地表现在风格之中,即符号层面。”[19]“亚文化的意义向来都不乏争议,而风格是对立的定义以最戏剧性的力量相互冲突的领域。”[20]《亚文化》一书的“绝大部分篇幅将用来描述物体被赋予意义的过程,以及这些物体作为亚文化的‘风格’被再次赋予意义的过程。”[21]《亚文化》条分理析地揭示了作为拒绝、挪用、同构、拼贴的风格,风格与黑人、白人的关系,风格与媒体、与摩登派、与摇滚派、与“跨掉的一代”的关系等等。
伯明翰学派所说的“风格”,用费斯克等人的话就是“文化认同与社会定位得以协商与表达的方法手段”。“风格通常被看作是许多类型的事物所做的分类,它也涉及某些事情如何去做,如如何演奏音乐、如何发表演讲、如何穿着打扮等……”[22]风格是亚文化最具有自我吸引力和最可读的特性(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性经济学中的恋物癖),[23]是亚文化群体的“第二肌肤”和“图腾”。亚文化风格不仅是阶级身份的表达,也是文化认同的表述,是一个赋予群体有效性和一致性的强有力的途径,它联系着特定阶级的特定人群,帮助亚文化群体进行内部和外部的自我表述,依赖于某些特定形态的知识与习俗,与布尔迪厄所谓的“习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构成了特别的亚文化资本。“风格”不仅仅是亚文化群体的符号游戏,它更展示、关注、传达了阶级、种族、社会性别等关系。
亚文化风格有着重要影响力,“亚文化风格确实有发挥影响力的时刻,形成其短暂却震撼人心的景观”[24]。赫伯迪格把亚文化风格形象地描述成“噪音”,它干扰了资本主义中霸权的顺利实现,破坏了资产阶级苦心经营的共识:“它干扰了从真实事件与现象到媒体中的再现的有序过程。我们不应低估引人注目的亚文化的表意力量,它不仅作为一种隐喻,象征着潜在的、虚构的无政府状态。它同时还作为一种语意混乱的实际机制,再现系统中的一种暂时阻塞。”“它们明确地表达亵渎神圣的概念”,“惊世骇俗的亚文化以被禁止和反常的形式(逾越服装和行为的规范,违反法律等)传达被禁止的内容(阶级意识,偏离的意识)”。“对共认的符码的违抗会产生相当大的煽动与扰乱力量”,[25]赫伯迪格的意思是说:语言的神圣性往往寄寓了社会制度的神圣性,权威符码的被挪用是一种相当大的挑战——风格(符号)实际上构成了巴赫金所说的“意识形态战场”。
三、收编
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的抵抗风格产生以后,支配文化和利益集团不可能坐视不理,它们对亚文化进行了不懈的遏制和收编(incorporation)。
霍尔等人在《通俗艺术》里已经触及到了青少年亚文化被商业化“收编”的问题。他认为:“商业娱乐市场提供的文化——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折射出业已存在的态度和情绪,同时提供了一个富于表达的天地,一套通过它可以折射出这些特点的符号……”。“十几岁人的文化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和粗制滥造的东西的矛盾混合体:它是青年人自我表现的场所,也是商业文化提供者水清草肥的大牧场。”[26]商业化和大众文化如何对亚文化进行收编与利用,霍尔并没有展开讨论。对亚文化的“收编”进行了学理分析的是赫伯迪格。他在《亚文化》一书中主要着眼于欧美的朋克摇滚,指出:亚文化的表达形式通常通过两种主要的途径被整合和收编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中去:第一种:商品的方式。把亚文化符号(服饰,音乐等)转化成大量生产的物品。第二种:意识形态的方法。支配集团——警察、媒介、司法系统——对异常行为贴“标签”并重新界定。[27]
在赫伯迪格看来,“亚文化与为它服务同时也利用它的工业之间有着暧昧含糊的关系”,这是因为“亚文化主要关系到消费层面,唯独在休闲领域起作用。”赫伯迪格揭示了资本社会里亚文化的一个宿命现象:亚文化群体生产出新的、对抗性的意义的方式,然后这些意义却被资本和市场加以整合和利用,当蔓延世界的商品经济把亚文化符号转化为利润丰厚的商品时,这对亚文化无疑具有毁灭性的打击。“新兴风格的创造与传播无可避免地和生产,宣传和包装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从而必然会导致亚文化颠覆力量的削弱。”[28]亚文化“经由商品来传达信息,致使那些在哪些商品上的意义被有目的地扭曲或者抹除”。亚文化风格以发动符号的挑战开始,以建立一套新的惯例变得僵化而结束。如朋克服开始使用的是最令人鄙弃的和不值一提的衣服材料——安全别针和塑料制品。但是很快这一装束就成为时髦的主题涌入市场,成为旧的惯例——最新款式的女装。当赫伯迪格看到商品化的朋克服装的配件上写着“使人震惊就是时髦”时,他不无悲哀地说:“这一点(亚文化的商品化——笔者注)预示着亚文化一步步逼近死亡。”[29]
和商品化的收编紧密相连的是意识形态收编。赫伯迪格认为,亚文化兴起时媒体等意识形态的反应是复杂的,风格激起了两种反应,除了有恐惧、愤慨、道德恐慌,还有对亚文化的迷恋和兴趣盎然的描述。媒体、唱片公司等意识形态系统一方面蔑称亚文化为“民间恶魔”,一方面尽量抹杀亚文化的“他者性”(Otherness),否定他们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把朋克重新“安置”在家庭里,如媒体有时会致力于描绘朋克家庭的细节活动,把朋克的“他者性”减少到最低;有时会把摇滚歌星说成是开放时代的少数“才华横溢、桀骜不驯”的天才,悄然置换“真实历史的矛盾产物”的亚文化特性。正如霍尔所指出的:“媒体不仅记录了反抗,他们还把这些反抗行动安置在支配团体的意义构架内,那些决定投身于引人注目的青年文化的青年人同时也返回到常识替他们安排就绪的位置。”[30]
20世纪80年代之前,伯明翰学派的学者认为,亚文化群体对商业收编是拒斥的,一旦被收编就意味着死亡,这种看法后来有所改变。如默克罗比在研究“朋克现象”中的“二手衣服”和“旧货市场”时指出:“这种浪漫化的观念(即“亚文化群体对商业化的态度是拒斥的”这一观点)未免太理想主义了。实际上,整个朋克文化都在利用大众传媒宣传自己,并且从一开始就开了一系列商店直接卖衣服给年轻人”。“从那以后,把纯粹的亚文化和被商业污染了的外在世界截然分割开来的旧研究模式已经宣告破产了”。“我们完全不必把这些活动看作成是纯粹商业性的亚文化低潮,远离对传统的反抗;恰恰相反,这些活动正好处于离经叛道的中心。”,麦克卢比的这一观点和费斯克以及威利斯等对亚文化群的“符号创造性”的乐观论述形成了呼应。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因为亚文化难以避免被“收编”的结局,所以亚文化往往显得暧昧而复杂,既横眉冷对也不乏秋波暗送,既抵抗也妥协,既深刻也浮浅。对主文化来说,它既是潜在的对手,也是收编的对象;它是商业文化的对立面,也是大众文化的同谋,被收编的亚文化“半推半就”、“乐见其成”,用令人震惊的“风格”这一独特的“亚文化资本”,成为流行时尚(当下的风格),换得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不同程度地失去抵抗性,与大众文化、主文化也有了相互转化的可能。
以上三个关键词大致概括了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重要观点。伯明翰学派过分强调亚文化风格的抵抗功能,使抵抗具有了“浪漫化”的倾向,对亚文化的收编态度也有些模棱两可,这些无疑都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醒。
注释:
[1]CCCS,First Report,1964:6-7,转引自古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7-58页。
[2]Chris Rojek,Stuart Hall,Cambridge:Polity in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2003,p.71.
[3]Stuart Hall , Paddy Whannel, The PopularArts(1964),Boston : Beacon Press;New York, PantheonBooks,1967,pp..280-282.
[4]Dich Hebdige,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Style,London:Methuen,1979,p.17.
[5]Phil cohen,Subcultural Conflict and Woking-classCommunity,in Stuart Hall,eds Culture,Media andLanguage,London:Hutchinson,1980,pp..82-83.
[6]Stuart Hall, Tony Jefferson, eds , ResistanceThrough Ritual:Youth Subculture in Post-warBritain,Lon-don:Hutchinson,1976,p.41.
[7]Stuart Hall,Tony Jefferson,Resistance ThroughRit-ual:Youth Subculture in Post-war Britain 1976, p.48.
[8]Stuart Hall,Paddy Whannel,The populararts,pp..276-281.
[9]Stuart Hall,Tony Jefferson,Resistance ThroughRit-ual:Youth Subculture in Post-war Britain,p..53-54.
[10]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注,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281页。
[11]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98—202页。
[12]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117页。
[13]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118页。
[14]Stuart Hall, Tony Jefferson, Resistance ThroughRitual,p.52.
[15]Stuart Hall, Tony Jefferson, Resistance ThroughRitual,p.203.
[16]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243—244页。
[17]Stuart Hall, Tony Jefferson, Resistance ThroughRitual,p.177.
[18]Stuart Hall, Tony Jefferson, Resistance ThroughRitual,pp..53-54.
[19]Dich Hebdige,Subculture:The Meaning ofStyle,p.17.
[20]Dich Hebdige,Subculture:The Meaning ofStyle,p.3.
[21]Dich Hebdige,Subculture:The Meaning ofStyle,p.3.
[22]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279页。
[23]Ken Gelderand,Sarah Thornton,eds,The Subcultures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ltedge,1997,p.374.
[24]Dich Hebdige,Subculture:The Meaning ofStyle,p.130.
[25]Dich Hebdige,Subculture:The Meaning ofStyle,pp.90-92.
[26]Stuart Hall,Paddy Whannel,The populararts,p.276.
[27]Dich Hebdige,Subculture:The Meaning ofStyle,p.94.
[28]Dich Hebdige,Subculture:The Meaning ofStyle,pp..94-95.
[29]Dich Hebdige,Subculture:The Meaning ofStyle,p.96.
[30]Stuart hall,Culture ,the Mediu andthe‘Ideological Effect’,in James Curran,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Society ,London:Edward Arnol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University Press,1977,pp..339-346.
[31]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205-206页。
(胡疆锋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北京100073)
(陆道夫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 广州 510669)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