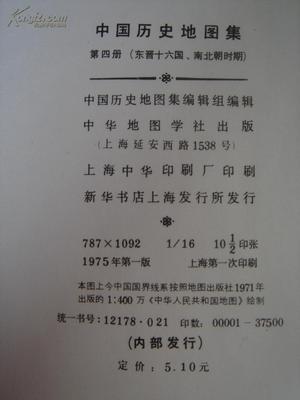所谓礼仪之争,开始时只是天主教内部关于天主教与中国传统关系展开的争论。根据《新天主教百科全书》给“中国礼仪之争”的定义可知,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士人祀孔,二是家人祭祖,三是中西文中关于基督教上帝的译名之争。
一、耶稣会内的“礼仪纠纷”
利玛窦是中国教会的真正创始人,从1597年起担任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会长。中国传教区中的重大方针决策都由他来定夺。特别是早期耶稣会的传教策略都是在利玛窦时代定下来的。利玛窦要求耶稣会士采用中国儒家经典中语言来翻译天主教神学,容许皈依天主教的中国教徒能够继续祭祀孔子和他们的祖先等等。在翻译天主教最高信仰“Deus”名称时,采用了先秦古籍儒书中的“天”或“上帝”称号。后来,他了解到朱熹对“天”的解释,说“天”不过是一种义理,“上帝”也不必是独一的天地主宰,于是又将“天主”、“天”和“上帝”三名并用。
对于利玛窦定下的传教策略,当时的耶稣会士一般是执行的。但在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这种传教策略遭到了新一代人物的怀疑。在利玛窦去世前一年继任为耶稣会中国会长的龙华民(NiccoloLongobardi)就是这些怀疑者的代表。
当时中国的天主教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耶稣会内部,中国传教区受到更多的关注。龙华民的地位也比当年利玛窦显赫得多。大概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同前人的重要性,龙华民全面审视了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策略,对利玛窦的一些做法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他的理由是,当时耶稣会远东视察员巴范济(FrancescoPasio)得到日本耶稣会士的报告,日本人用理学家朱熹的思想去解释“天”和“上帝”,不能代表基督教所称的创造万物的尊神。
1612年,巴范济去世,龙华民联合熊三拔(Sabbathin deUrsis)上书耶稣会日本—中国省会长,要求禁用“天”、“上帝”、“天主”等译名。文件转到罗马,当时著名神学家组成研究小组,经过讨论做定维持利玛窦的原定译名。不过,龙华民并不甘心。他认为,利玛窦的做法是在迎合儒家,而儒家经典里的词语有它特定的涵义。“天”、“上帝”,在程朱理学中有宗教意味,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还原成儒家、佛教、道教,就是异端。如果汉语里的“天”和天主教的“Deus”混同,那么梵蒂冈教堂里的“上帝”就可能和北京天坛上空的“上帝”混同。同时,他也反对会士们容忍中国教徒祀孔祭祖。由于龙华民等人不尊重中国传统,导致与中国地方官员发生矛盾,引起了南京教案,使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一度遇到很大的困难。
南京教案是由南京礼部侍郎沈潅发起的反教会运动。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潅三次向神宗皇帝上《参远奏疏》,参劾耶稣会士图谋不轨,力主严禁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但前两次都未获准。8月30日前后,他又交结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方从哲,逮捕并关押传教士王丰肃(AlphonsusVagnoni,后改名高一志)、谢务禄(Alvarus deSemedo,后改名曾德昭)等30多人,掀起反教会运动。徐光启上书为耶稣会士辩解说:“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指西方传教士)最真切,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1]李之藻在高邮、杨延筠在杭州也都致书南京官吏请求容忍西方宗教。但沈潅又勾结内监,再上第三疏,终于获得万历皇帝谕准驱教。大批传教士被勒令回返澳门。不久,沈潅失势,教禁稍弛,传教士又纷纷内渡。1621年,山东发生白莲教起义,沈潅复升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勾结魏忠贤,指责天主教为白莲教,意在图谋不轨,于是万历皇帝再次下令在南京逮捕和驱逐传教士。传教士有的被迫改名换姓避居杭州杨廷筠家和上海徐光启家,有的被押解澳门。天主教在中国遭到重大打击。
金尼阁是利玛窦的学生和朋友,正是他于1615年把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日记带到罗马,译成拉丁文,向欧洲公布。他还说服罗马教会给予在中国的传教士以适应于当地的传教策略。他于1620年从罗马带来了教廷对中国教徒的宽容策略:平时祷告不必都用拉丁文,可以用中文,但限于文言文;可以设本地神职班,培养本地的神职人员;可以部分地翻译《圣经》的重要章节;行弥撒时不必强求脱帽,以尊重中国官冕阶层的习惯等等。
1621年,耶稣会在澳门着急会议,讨论的结果是,赞成利玛窦的主张。
1628年1月,由于龙华民的坚持,耶稣会在在华传教士召开了“嘉定会议”。嘉定是著名教徒徐光启的学生和儿辈亲家孙元化的家乡。这次会议专门讨论“译名之争”。当时到会的有11名耶稣会士。徐光启等中国教徒列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38个问题,大多是有关中国信徒的祭祖祭孔以及天主的译名方面的内容。龙华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奉行“无神论”的。金尼阁在会议上竭力为利玛窦的传教策略辩护,心力交瘁,因劳得疾,会后不久在杭州发高烧死去。会议议定:废除利玛窦时期使用的“天”和“上帝”,保留“天主”译名。这一决议是双方的折中。不使用儒家经典里现有的“天”、“上帝”,同时也不使用音译,而是另外造了一个儒家经书中没有的“天主”,以示借用的是中国的语言,而不是儒家的概念。龙华民可以被看作因起中国礼仪问题争论的第一人,但这仅仅是在耶稣会内部的争论,并没有扩大到其他修会之间,更没有扩大到中国教徒的生活中。“嘉定会议”决定中国人可以祀孔祭祖,禁用“天”和“上帝”的译名也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1633年,耶稣会再度集会,决议仍采用以往习惯上的译名,赞成利玛窦主张的李玛诺(Manoel DoazSenior)继任为视察员,遂准许会士自由采用“天”和“上帝”。耶稣会内部关于译名之争遂告一段落。
龙华民虽然是引发礼仪问题的第一人,但耶稣会内部的争论起初并没有扩大到天主教的其他修会之间,更没有扩大到中国教徒的生活中。
二、耶稣会同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之间的争执
17世纪30年代,礼仪之争扩大到天主教内部,出现了修会之间的争执。“礼仪之争”正式把法在福建,最早是在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同耶稣会之间进行的争执。方济各会、多明我会是欧洲的老修会,他们的传教方略是到处拿着十字架,宣讲耶稣救世的故事。他们指责外教人的愚昧无知,要他们赶快信仰耶稣。他们认为,耶稣会学术传教方式过于曲折,而且两个修会都蔑视耶稣会向官绅传教的做法,他们主张向平民百姓宣讲教义,甚至不惜标榜对抗。特别是方济各会中的西班牙人,他们受一种征服者文化的影响,这种征服者文化曾经强迫在西班牙的穆斯林与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否则予以驱除。
1632年,多名我会传教士AngeloCocchi来中国,在福安传教。在福建主持当地教会的是全面继承利玛窦传教策略的耶稣会士艾儒略,对中国文化采取了十分开明的做法,包括允许教徒们进祠堂、入孔庙,被当地教内外绅民誉为“西来孔子”。艾儒略的做法引起了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的反对。次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uanBautista Morales)和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Caballero)两人来福安增援。他们到来后,就检讨耶稣会士艾儒略在福建发传教方针,认为过于绕弯费时间。他们要直接向中国宣讲福音。
利安当是个很有造诣的西班牙神学家。他在学习中国话时,一次偶然地问教书的先生王达窦:中国人的祭祀活动有什么意思。王达窦解释说,祭祖仪式就如同天主教的弥撒。利安当听了,马上就想到中国祭孔祭祖都是宗教的祭典。他还请人陪同去观看葬礼,仔细研究后断定祭祀活动是一种宗教礼仪。了解当地教徒祭祀孔子和祖先的习惯后,他便断定:耶稣会神甫们正在容忍教徒们奉行异端。1634年,利安当为了礼仪问题,专门去了南昌,同住在那里的耶稣会副会长阳玛诺(EmmanuelDiazJunior)讨论礼仪的问题。他还进一步北上,到了南京,找人辩论。南京是江南儒家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有利玛窦的许多老朋友,无论教内还是教外都维护耶稣会的说法。南京的天主教徒们认为他多事,辩论过后,竟然把他软禁了6个星期。放出后,派人把他押会福建福安。这次痛苦的经历,使利安当决计要与耶稣会争个明白。
利安当找到了在福建传教的多明我会士莫若翰(Juan Baptista deMorales,也有人译为黎玉范),两人于1635年9月连写两信,要求艾儒略作答。艾儒略没有理睬。利安当和莫若翰分别是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在华的会长。11月,两人决定一起到福州去找艾儒略。而此时,耶稣会的副会长傅泛际(HeurtadoFrancoisFurtado)来福建。利安当、莫若翰、傅泛际和艾儒略在福州进行了3天的长谈。谈后,三个修会分别向本会在欧洲的总会长报告各自对此问题的态度。利安当、莫若翰认定只有天主才能领受到人们献祭的肉食、水果和香火,极力反对中国礼仪。
1635年12月20日和1636年1月21日,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在福州联合召开法庭调查,向中国教徒进行当庭问答。他们在福州附近传唤了11名证人,这些人均是这两个修会劝化的教徒。他们自然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取得调查结论后,利安当决定通过马尼拉,向罗马汇报中国的礼仪问题。1637年,利安当经台湾去菲律宾,途中被海盗和荷兰人捕去,在爪哇拘留了一年,然后才带着报告到达马尼拉。马尼拉的总主教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在当地解决,不要上交罗马,于是组织了神学家和法学家进行合议。但耶稣会的总会长表示:这个问题只有在华的本会会士有资格答复,其他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不要多发言。当时,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在中国各有两名传教士,一共才4名西班牙人,还都集中在福州附近。他们要推翻耶稣会半个多世纪的成果,自然不能接受。在耶稣会表示不合作后,马尼拉主教决定把矛盾上交到罗马。
1640年5月17日,利安当和莫若翰受命一起去罗马。但不知何种原因,利安当并没有前行,留在了澳门,后又去了内地,在济南、杭州等地传教,莫神甫独自去了罗马。
1645年9月12日,教廷的宗教裁判所根据莫若翰的一面之辞,作出了有利于西班牙会士的决定。然后以教皇英诺森七世敕令的形式正式公布,这就是罗马教廷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第一号文件。其内容包括:(1)中国城镇乡村里为庙会、新年、供祭时经常向民众摊派捐款,如不违教义,信徒可以接受摊派;(2)基督徒在敬城隍时可带一个带苦相的十字架,表面上敬拜城隍,内心却应崇敬十字架;(3)信徒不得参加祭孔活动;(4)信徒也不得参加祭祖活动,不得以任何方式为先人立祭坛和牌位。[2]当这个文件发布时,正赶上清军大举入关,整个中国,尤其是福建、台湾地区正处于战争状态。罗马教廷关于中国礼仪的决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和广泛传播。
1654年,耶稣会士卫匡国(MatinMartini)为“礼仪之争”专程赴欧洲向教皇报告教务,带去了本会的申诉意见。他解释说,中国人的祭祀是一种社会性的礼节,而不是宗教迷信。他认为,奉教的学者可以在孔庙里参加领受登科的仪式,因为那里没有祭司在场,也没有崇拜偶像的设施制度,只是用政治和文化的礼仪,承认孔子为先师。至于祭祖,卫匡国认为,应将下层民众的迷信活动和士大夫举行的仪式分开考虑。天主教知识分子在祭祖时供奉果子、肉类和丝绸,奉祭如在,敬死如生,并不真想死者来享受,只是用以表达内心的孝思和感恩。根据卫匡国的辩护,教皇亚力山大第七于1956年3月23日作出了有利于耶稣会的决定:如果中国礼仪的意义如卫匡国所说,中国信徒可以行祭祀之礼,并以中国化方式传教。这是关于中国礼仪之争发第二号文件,它完全倾向于耶稣会。
卫匡国获得的教廷决议很快被耶稣会士传遍中国。1659年,罗马传信部给三位在中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发出指示:不要试图去说服中国人改变他们的礼仪、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思维方式,因为这些并不公开地反对宗教和良善的道德。还有比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者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出口到中国去更为傻的事情吗?不是要出口这些欧洲国家,而是要出口这信仰。这信仰并不和任何种族的礼仪习俗相矛盾,并嘱咐他们尽可能适应当地的习俗。
就在同一年,当利安当路过杭州时,卫匡国把罗马教廷的意见告诉了他。这大大激怒了已成为济南主教的利安当。他派中国大陆上仅有的另一位方济各会士文都辣(BonaventuraIbanez)去欧洲告状,责问1645年英诺森七世教皇的指令是否宣布取消。
1664以后,朝廷支持反教活动,在北京闹出了一次教难。先是命令各地教士来京集中,后来又把大部分传教士驱逐到广州。这时有23位传教士集中广州的耶稣会院里,举行了“广州会议”。1667年12月18日至1668年1月26日,他们在40多天的会议中,对近百年的中国传教活动进行了全面总结。会议中,中国礼仪再次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利安当在会上积极发难,并利用分歧,争取到4位耶稣会士的支持。但在会后表决时,除一人外,大家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继续持妥协态度。利安当在会后开始改变态度,在自己的中文著作中也使用了他曾反对的“天”、“上帝”等词。1669年5月13日,利安当在广州去世。
面对多明我会的责问,新教皇克莱孟九世采取了骑墙的作法。1669年11月13日,圣职部根据教皇的意思发布部令,指出以前颁布的有利于多明我会的第一个决定及有利于耶稣会的第二个决定都是有效的,即由传教士根据当地客观的情况按照自己的良心去判断。[3]文都辣在欧洲告状的同时,新招募了6名传教士于1672年来华。由文神甫带来的年轻方济各会士渐渐地与耶稣会士合作起来。他们请教耶稣会士前辈,双方想办法如何修改中国礼仪,使它能为争论的各方所接受。
三、阎当再生事端
就在争论各方逐渐妥协的时候,来了一批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和教廷直属传信会的教士。再次挑起事端的是来自巴黎大学的神学博士阎当(CharlesMaigrot)。他于1681年来中国,1684年任教皇驻福建代表,1687—1696年任教廷代牧主教,全面管理福建教务。
1692年,两位方济各会士对中国礼仪不知所措,要求阎当明确态度,到底可不可以进行中国礼仪。1693年3月26日,阎当发布命令,要求在他的教区内严禁中国礼仪。该文告宣称,那种认为祭祖祭孔是民间性而非宗教性礼仪的说法,是“似是而非,错误百出”的。当时各地教堂都有仿制的康熙皇帝赐给汤若望的“敬天”大匾,挂在堂内的显要位置。阎当命令统统摘去。阎当还想把他的权威推广到全国,又感到自己势力单薄,就采取迂回的办法,发动欧洲的神学家来支持他。他派自己在罗马的代表查尔马(NicolasCharmot)找到巴黎红衣主教Louis-Antoine deNoailes支持他。这时,1692年回到法国的耶稣会士李明正同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进行辩论。这些神学家对李明《中国现势录》中的神学观点和美花中国儒家、贬低欧洲文明的言论十分反感。1700年10月,经过30次的讨论,法国巴黎大学的神学院认定中国礼仪为异端。教皇虽然没有马上同意巴黎大学神学院的判断,但也不得不引起重视。
由于巴黎大学神学院的教授认为,耶稣会在中国的做法是容忍异端。为了和欧洲反对中国礼仪的对手们辩论,收集资料,李明精心策划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的内容是要求康熙皇帝出具证明,证明中国礼仪不是宗教崇拜。这样会有利于耶稣会在欧洲的争论。1700年11月30日,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张诚等人为了支持李明,他们把请愿书送到康熙手中。收到请愿书的当天,康熙就加以朱批: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这说明,康熙皇帝当时确实是赞同了耶稣会士的说法,同意说祀孔祭祖只是一种“习俗”,是人之常情,而不是宗教活动。
反对派借机扩大事态,指责耶稣会将教会之时事吧请求教廷解决,反而依赖教外的皇帝裁定是离经叛道。迫于各方压力,教皇克莱芒第十一让教廷圣职部全面讨论了阎当提出来的非议。1704年11月20日,圣职部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并作出决定,由教皇发布禁约7条,断然禁行中国礼仪,其要点有四:一是不准用“天”或“上帝”称天主。二是不许在礼拜堂悬挂“敬天”字样的匾额。三是禁止基督教徒祭祖祀孔,否则以异端对待。四是禁止留牌位在家。教皇还于1701年12月宣布派遣多罗主教(Card.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on)将禁令携往东方,调查并解决“礼仪之争”。
四、多罗出使清朝与康熙帝的回应
多罗于1668年12月生于意大利的都灵。其父为当地望族。多罗早年在耶稣会办的大学读书,晋铎后在罗马各法院实习,后为教宗宫廷宫长钱启(BaladassrreCenci)枢机的随员,参加教宗选举会,为新教宗克莱门十一所赏识。在宣布多罗为特使以前,教宗曾召见他,告之将委以出使中国特使事。多罗向降宗坚辞,理由是身体虚弱,不宜长途跋涉,并且对远东传教问题毫无所知。但教宗不许他推辞。1701年12月21日,教宗亲自在圣彼得大教堂祝圣多罗为主。1702年7月2日,教宗申明多罗为教廷出使中国、印度及附近国家的巡阅使,加上等特使衔,具有指挥和解决教务问题的全权。教廷为了表示既不偏向葡萄牙国王支持的耶稣会,也不偏向西班牙国王支持的多明我会,命令多罗主教一行不要搭乘葡萄牙或西班牙的船只,而是请法王路易十四派出两艘船以供专需。7月4日,使团从罗马出发。
1705年4月2日,多罗到达澳门。第二天,他赶往广州。多罗在广州时选定一名遣使会会士毕天祥(Luigi AntonioAppiani)担任翻译和秘书,并对他言听计从。他们住进西班牙人奥斯定修会在广州的会所里,回避与耶稣会士打交道。
康熙对多罗的到来持欢迎的态度。他要求广东督抚要优礼款待,派员伴送来京,又派遣两广总督的儿子同张诚等耶稣会士前往天津迎接。1705年12月4日,多罗带着未经公布的罗马教谕,到达北京。康熙又派大臣前往多罗的住地问候,并询问来访的真实目的。多罗说,一是代表教皇感谢皇帝对天主教的礼遇,二是为罗马和中国建立长久的联系。他并不敢公开来华的真实目的。康熙很想见多罗,但多罗为了要向皇帝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摊牌而左右为难,便拖延觐见。
其实,康熙已从耶稣会士那里得知,解决礼仪问题至少是多罗来华的目的之一。12月12日,多罗的随行医生在北京暴病去世。耶稣会建议葬礼在本会的栅栏墓地秘密进行,以避免本次葬礼上改变中国礼仪。不巧的是,康熙得知消息后,主动赐了一块新的坟地。多罗喜出望外,而耶稣会士知道这是皇帝想借此观察特使对待中国礼仪的态度。康熙派人探得,葬礼和耶稣会原来的样子不同。因此,康熙对多罗的态度已经有了了解。
1705年12月31日,康熙皇帝第一次召见多罗。当时,多罗生病,康熙特差官到北堂用肩舆迎入宫中。为了不使谈判陷入僵局,他并没有马上提及礼仪问题,而是提出中国教区究竟由哪个传教会来主持的问题。他主张今后的中国传教事务应由罗马传信部直属中国代牧区主教管理,免得耶稣会和其他修会之间产生争议。康熙皇帝表示,应该由在中国住了许多年,了解中国风俗民情的耶稣会掌管中国的天主教事务。由于会见没有涉及中国的礼仪问题,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第一次派出的特使十分热情,当时的气氛是很友好的。此后,康熙曾和多罗数次非正式会晤,并召他一起在畅春园打猎、观花灯。
以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多罗一直托病不见康熙,康熙也表示谅解,并要他宽心养病。到了1706年6月29日,康熙同多罗进行第二次正式会见。多罗仍然吞吞吐吐,康熙很不高兴。几经追问,多罗仍然回答此行的目的是代表教皇向皇帝问候。康熙则直接请他转告教皇:中国人不会改变祖传的礼仪,中国礼仪并不违背天主教教理。如果教皇执意要在中国禁止祭祖祀孔的话,所有西洋传教士就很难在中国耽下去了。
次日,多罗在同康熙游畅春园的时候,说自己在京已愈半年,准备回欧洲,另有一位从福建来的主教,通晓中国文化,将由他来继续讨论。多罗推荐的这位主教就是在福建严格禁止中国礼仪的阎当。
阎当是非常有学问的神学家,但他的中文水平十分糟糕,对中国文化也毫无了解。他来京协助多罗工作,带的是两个讲福建话的中国助手,根本不敢见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早已对阎当有所反感,因为他曾看过阎当写的半文不白的书籍。7月22日,康熙主动要召见他,命他到热河行宫觐见。他受旨后十分恼怒,认为是张诚等耶稣会士故意让皇帝招考他。8月1日,阎当在承德行宫觐见康熙。他只会一些福建土话,不会官话,由康熙的亲信巴多明(DominiqueParrenin)当翻译。皇帝问他御座后匾上“敬天法祖”四字为何时,阎当只认得一个“天”字。其糟糕的中文让康熙勃然不怒。次日,康熙朱批道:愚不识字,胆敢妄论中国之道。第三天,康熙又批道: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1706年8月13日,康熙帝作了一个重要的谕批,指责多罗掩盖出使真相,在中国教会中拨弄是非,制造混乱,并申明皇帝对于居住在中国的西洋人拥有管辖之权。
8月20日,多罗请求离京,从运河,经天津、临清、扬州到达南京。在12月17日,多罗到达南京时,也传来康熙皇帝在北京驱逐阎当出境的消息。多罗决定在南京公布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文件。1707年1月25日,他给在华的传教士写信,发出“南京命令”。信中除发布禁令外,还规定会士应该怎样应付皇帝对天主教士的盘问。信中说:如果他们被问到有关中国传统教导、法律、礼仪、一般习俗,他们是否同意这些东西,或者答允不攻击它们,不在口头上或以书面反对它们时,他们都必须答复如下:如果它们是和基督教法律相容的,或者可以与之合法及恰如其分地相符的,答复是可以的,否则不性。如果他们被问到在神律中是否有与中国传统的教导的不同之处,他们必须回答:有许多不同。当要求他们举例说明时,他们可以尽他们们所能想到的,阐明算命、祭天、祭地、祭太阳、祭月亮、祭其他星宿和神灵等视为人文学科和艺术的发明者的意义。基督徒只能祭万物的创造者天主,他们从天主那里得到祸或福。当他们被问到敬祭孔子和祖先的焦点问题时,他们应该作如下回答:不行。我们不能奉献这样的祭品,我们不允许听从神律的人们祭孔和祭祖。等等如果不执行这一命令的将割除教职。
中国礼仪之争捅到了康熙面前,康熙发现他的臣民中至少有10万人听从国外的命令。他决定要为中国教会定一个规矩,使在华传教士绝对服从于他。凡继续在华的传教士须表明遵守中国礼仪,领得印票才准传教。统一发放给由内务府拟定的,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千字文印票。票上写作: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恢复西洋,已经来京觐见陛下。康熙一定要亲自问过后,当面宣誓,才发给印票。康熙对他们解释说,因为你们入了中国籍,不是外人,中国人会更加积极地入教。一是来京不便,二是传教士内部对此意见分歧,只是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耶稣会士来宫廷领了票。康熙对不愿“具结”的传教士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下令将他们驱逐至澳门。康熙还派艾若瑟到罗马宣示旨意,要求教皇收回成命。大多数在华传教士暂时尊从于康熙皇帝,并呼吁罗马能够对教皇的决定作某些修改。
1707年6月29日,多罗被中国人押送到澳门,澳门主教拒绝承认他的权威,结果将其囚禁,直到1710年去世。他的晚年,思想已经有所变化。在他去世的当年,还至书康熙请求谈判。
五、嘉乐使团来华与康熙皇帝的禁教
教皇发现他先前发出的敕令在中国未被遵守,就拒绝了耶稣会士的呼吁,并于1715年3月19日再次发布更加严厉的禁令,禁止传教士再对礼仪问题进行任何申诉。这道禁令被称为《自那一天》(因为禁令的第一句话是“自那一天”)。禁令要求世界各地所有的“中国礼仪之争”,都应该按本规定彻底执行。在内容上,除重复1704年以来的严厉态度外,还增加了一项宣誓内容。这有可能是针对康熙的“具结”而增加的,它要求所有中国的传教士和将要访问中国的人都签署一份誓言,以保证遵守关于中国礼仪的规定和禁令。1716年8月,该禁令文件送到广州,由驻广州的传信部办事处秘密送往全国各省。11月,在北京公布,激起康熙的极大反感和愤怒。诏书公布后,在中国的传教士们都宣誓服从,但一般教徒并不遵行。有不少士大夫因禁止祭孔而无法参加科举考试,就自动离开了教会。有些教徒无法不去祠堂祭祖,也只好不再进教堂。康熙皇帝针锋相对,于1717年谕礼部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
为处理中国礼仪问题的善后事宜,教皇于1719年派遣嘉乐(Mezzaberba)为代表出使中国,进行礼仪问题的调解。
嘉乐于1682年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巴委亚,曾考取民律、教律的两科博士。任宗座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法官,后升教宗国多提和撒批纳两省省长。接受出使中国委任时,他年仅37岁。1720年,嘉乐刚到广州,就受到皇帝派员的盘问,嘉乐回答来华使命是向皇帝问安,请皇帝开恩保护天主教。嘉乐由水陆北上。进京后,在回答来华目的时,嘉乐说:一是请求皇帝允许让罗马直接管理所有传教士,二是请皇帝允许让中国天主教教徒改掉中国礼仪。嘉乐对他来华使命的描绘前后不符,康熙听说后十分愤怒,并下了逐客令。康熙传谕嘉乐:“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2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吧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且尔教王条约之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着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此即准尔教王所求之二事。”[4]
嘉乐在北京见势不妙,就不敢公开教皇的禁谕,反而接受了劝告,在暗中与耶稣会士谈判,拟定了“八项准许”,准备向中国礼仪妥协。其内容是:(1)准许教友在家中奉祖宗牌位,但只许写姓名,两边加上天主教的有关道理。(2)秩序纪念其他亡人,但环境应布置为非宗教式的。(3)准许祭孔,不能用牺牲,可用香火,牌位上不得书有“灵”字。(4)准许在修改后的牌位和死人棺材前磕头。(5)准许在丧礼上焚香点蜡烛,但不许有迷信举动。(6)准许在牌位和棺材前放水果,以资纪念。(7)准许春节和其他节日里在牌位前磕头。(8)准许在墓前焚香、点烛,供水果,但不能有多余的迷信活动。
在“八项准许”的基础上,康熙答应谈判,并先后13次接见嘉乐。前几次接见,康熙的态度温和。康熙向他解释说,中国“供牌位原不起自孔子,此皆后人尊敬之意,并无异端之说;呼天为上帝,即如称朕为万岁,称朕为皇上,称呼虽异,敬君之心则一”。并直接谕示:“尔欲议论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读尽中国诗书,方可辩论。朕不识西洋之字,所以西洋之事朕皆不论。”[5]1721年1月14日,康熙第四次会见之后,要求嘉乐交出《自那一天》禁令,自己找人翻译。康熙看了马国贤等人翻译的禁令中文本之后,了解到罗马教廷自从阎当挑起纠纷以来,教皇的态度没有变化,便批阅道:“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6]1月18日,康熙命令,把重用多年,但此刻站在嘉乐立场上的身边的翻译马国贤、德里格、利国安逮捕关押。嘉乐立即上书康熙,乞求释放被押传教士,表示禁令问题容他亲自返回欧洲,请示罗马再作修改。康熙放人后,双方继续会谈。康熙又接见了嘉乐8次,每次都重申自己的立场。1721年3月1日,康熙最后一次接见嘉乐,当日把一部由朝臣用中文记录完成的《嘉乐来朝日记》交给他,详细地把朝廷对中国礼仪的观点,用嘉乐在华日记的形式告诉欧洲,并请他转交给教皇,同时催他上路。3月3日,嘉乐离京南下。嘉乐使团的其他成员集中扣留在广州,不许入内地,一切等嘉乐回来再说。为了防止嘉乐在欧洲作出不符原意的解释,康熙另外让耶稣会士通过陆路,经俄国传给欧洲一个副本。这个副本在欧洲得以流传。5月23日,嘉乐抵澳门。同年11月4日,嘉乐向全国主教和神圣人员发布了一份牧函,他详细地谈到“八项准许”,并要求传教士们摈除成见,精诚团结,服从教宗的旨意。该函最后说:“八项特准只有必须和有用的时候,才能谨慎地让人获知。无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自己或其他人,以口头或书写的方式透露这份文件。无人可以将这份信函译成中文或其他东方语言文字。如果违反此项禁令将受绝罚。”[7]1723年,当嘉乐到达里斯本时,葡萄牙国王已经向他出示,并怪教廷多事。嘉乐只能说这个副本不全面。这时,罗马教廷已经非常被动。教宗下令圣职部调查嘉乐“八项特准”的由来及性质。
1742年7月5日,教皇发布《自上主圣意》的长篇通教谕,作出最后判断,废除嘉乐的“八项准许”,对中国礼仪采取了严厉的禁止态度。至此,反对祭祖祭孔的主张在中国天主教会之呢一完全占了上风,“礼仪之争”终于告一段落。
六、雍正、乾隆时期实行严厉禁教政策
1722年底,康熙突然患病,在畅春园卧床不起。12月20日,康熙去世,皇四子胤祯继位,是位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雍正。雍正对天主教传教士有着特殊的厌恶和仇视。雍正登基的次年(1624年)就发布在全国禁止天主教的命令,并且不承认康熙发给传教士的“印票”。当时,浙江有人上书,请求驱逐传教士。雍正马上下旨,让礼部议复:“奉旨,西洋人除留京办事人员外,其散处直隶各省者,应通过各该督抚转饬各地方官。查明果系精通天文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遣至澳门安插。其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尽行查送内务府销毁。其所造天主教堂,,令皆改为公所。凡误入其教者,严为禁谕,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众诵经者,从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实心禁饬,或容隐不报,如之。”[8]雍正还召见了在京传教士言明政策:“近在福建,有若干欧西人侵扰我百姓,蔑视我法律,福建官长奏申报,朕当制止乱行。此为我国家之事,朕当负责执行者也。……尔等欲我中国人尽为教徒,此为尔等之要求,朕亦知之;但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徒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舰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中国北有俄罗斯是不可轻视的,南有欧西各国,更是要担心的,西有回人,联朕阻其内入,毋使捣乱我中国。俄国使臣曾请求在各省通商,为朕所推辞,惟允彼等在北京及边境贸易而已。今朕许尔等居住北京及广州,不深入各省,尔等有何怨乎?……现朕既登皇位,朕唯一之本分,是为国家而治事。”[9]
各省传教士50多人,连同5位主教被驱除出境。1732年,集中在广州的35名传教士也被两广总督驱逐到澳门。只有在钦天监工作的20人留用,但不准传教。
雍正不容许天主教存在除主张自己的信仰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在康熙诸子的皇位争夺中,天主教传教士支持的皇子和家族都是失败者,天主教也成了宫廷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根据《康熙实录》,康熙四十七年,原来立的太子被废除后,皇八子同宗族中信仰天主教的苏奴家族比较亲近。雍正登基后,以不遵满洲正道,崇奉西洋之教的罪名,查办苏奴家族,有的被没收家产,有的被革职囚禁,还有的被驱除出京。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教廷不仅禁止儒家礼仪,对满族人信奉的萨满教礼仪也加以禁止。雍正对天主教禁止祭祀满族人的“天”大为不满,斥责其为“图谋不轨”,要严加惩处。
1736年,乾隆登基后,在政治上发展部了一系列赦令,其中包括释放受雍正迫害的康熙诸子,受流放的苏奴家族也恢复了宗室待遇,回到北京。但乾隆对传教士并不尊重,言而无信,多次对天主教进行迫害天主教,严格限制天主教入境。有些传教士只能偷渡进来,进行地下传教。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据1810年的统计,仍有欧籍传教士31名在中国内地16个省秘密活动,天主教徒共有20.5万人。[10]到1839年6月,据报告天主教在中国本部13个省有活动,欧籍传教士有65名,天主教徒30万人。[11]这说明清政府的禁教时弛时紧,天主教传教士仍有回旋余地。正是由于传教士的活动转入秘密进行,致使介绍西方科学的活动也未能延续,特别是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因工业革命而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知识未能引入中国,实在是一大憾事。
1773年,罗马教皇克莱孟十四迫于欧洲各国的压力,下令取缔耶稣会。两年后,中国的耶稣会也彻底解散。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利用中法《黄埔条约》,重新进入中国传教。此时的罗马天主教会对中国礼仪的态度有了某些松动。1939年11月8日,罗马传信部发布了由教皇庇护十一世签署的《人们完全明白》教谕,被中国的传教士称为“中国的解放宣言”。它最终结束了明清以来的“中国礼仪之争”。礼仪之争前后相继上百年的时间,这样有意无意地向欧洲各界介绍了中国的类似、文化、风俗、习惯、中国的各种思想流派,特别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1] 徐光启:《辩学章疏》,《徐文定公集》,卷5。
[2] 顾卫民:《中国与罗马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2000版,55页。
[3] 杨宪富:《中国基督教史》,(台)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133页。
[4] 张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72—73页。
[5] 张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73页。
[6] 陈垣编印:《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嘉乐来朝日记”,故宫博物院,1932。
[7] 顾卫民:《中国与罗马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2000版,81页。
[8] 梁章钜:《浪迹丛谈·天主教》,中华书局,1981年,81页。
[9]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6页。
[10] 《中国丛报》1983年3月,444页。
[11] 《中国丛报》1844年11月,595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