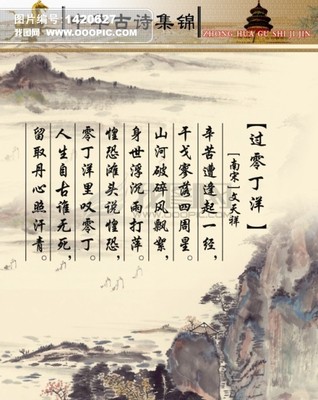原本是最讨厌“只闻新人笑,哪见旧人哭”的了,总觉得无论是感情还是物件都该是“从一而终”的。近来又读了点李叔同的文章,那种佛家的惜缘、惜福之心令我深有同感,他说十分福气要用三分,剩下的七分留与以后用,倘若你够豁达,那不妨散与天下人使用……如此胸怀着实令我感佩。然而前几天听到这样一句话:喜新厌旧乃人之常情。不禁令我一震:是啊,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买衣服,总是一件一件地乐此不疲;吃东西,总是饱腹了之后又变着花样地品尝所谓“舌尖上的艺术”,甚至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蝌蚪火锅、猴脑火锅一类菜肴比比皆是;就连交友也是这样,到了一个新环境就迫不及待地以“适应”为名不断地认识与被认识。我实在不知到这样的“人脉”到底意义何在?
既然人人都嗤之以鼻的“喜新厌旧”事实上大家自己每天都在做,哪有有什么资格以“道德”的名义去指责和批判那些劈腿和有外遇的人呢?当然,有人会说:这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觉得劈腿和外遇已经是道德和人品层面的问题,而日常的“喜新厌旧”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生活之调剂”而已。诚然,二者有区别。可是,这区别事实上也是很小的,并非你所以为的天壤之别。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的一个老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感情是复杂的,是故切莫轻易地对任何一段感情作道德评判。正如杜拉斯笔下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个小时》,谁不为那样无言却又炽热的感情动容?所以,我总不敢对任何有关感情的绯闻去妄言对错。
张爱玲笔下的顾曼桢有一个习惯,一件东西到了她的手里后,她就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她会好好地保存和爱惜它。比如那一双暗红的手套,虽然不是什么贵重之物,然而丢了以后,曼桢还是郁郁了许久。所以当世钧拿着那双半旧的手套还她,曼桢是心动了的,或者说是早已动了的心复又动了。我常常想起曼桢的的这个习惯,因为自己似乎也常常如此小家子气地执拗着,总有一种在时空交错之中遇到了知己的感觉。
唐僧在听如来讲法之时因一步踏错,不慎踩到了一粒米,后世便因这一粒米受了三天病灾。
一个小沙弥和他的师傅同桌吃饭,掉了一粒饭在桌上,没有在意,其师拍桌而起,大怒:“你是有多大的福气,可以经得起这样的暴殄天物?”继而自己捡起了那粒米吃了,拂袖而去……
小时后那首朗朗上口的《悯农》,还有几人记得并真正理解?“锄禾日当午,汗滴和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确实,在农业也科技化了的今天,盘中之餐早已不再如过去那般“来之不易”,可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粒粒皆辛苦”?学习写作的时候,老师说,一个作家,要将世间万物都看做是有灵性的。那么,集天地之灵气又养灵性之人类的“粮食”,其“灵”,想必是丰厚不已的了。
并非真的迷信什么“轮回”与“报应”,只是对于这“轮回”与“报应”,敬畏着。
从去年十二月份开始,开始素食。那一句“如果世界上的屠宰场都是透明的,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成为素食主义者”让我觉得以往的自己是怎样的自欺欺人,说什么“酒肉穿肠过,佛在我心中”,说什么佛家也有“三净肉”,还异常偏爱面粉和瘦肉的混合体——只因那令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吃肉。小时候,听见过村里人杀猪时,被宰的猪那惊天动地的嚎叫,透过密密匝匝的人群,看见了被桎梏着的猪,在死命挣扎,却总也逃不脱那无数只孔武有力的手掌……之后,一个年龄相仿的玩伴指着那案板上被分解得条条块块的“猪肉”对我说,肥肉会咬人的哦。从此我再也不敢吃肥肉。而红黑的纯瘦肉就成了我“自欺欺人”的承载物。
而今,已经是一个素食者的我,对于荤食早已没有了这样“自欺欺人”的幼稚,即便是有时候不可避免地还是会“误食”——比如食堂里一些荤素搭配的素菜,虽然挑出了肉丝,还是会有动物油的成分;比如有时候没挑干净,还是会吃着一些……但此时的我,也不再偏执地去计较了。只因“敬神如神在”、“酒肉穿肠过”、“心诚则灵”。

人生不过从空白中来,行至无果中去。子曰:君子无所争。确实,释然之后,并非颓然地遁隐世外——因为每一个人永远无法真正抛下所有不顾:比如养育之恩、比如前途之想、比如人心万象——而是苏轼那“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的豁达,那“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潇洒……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