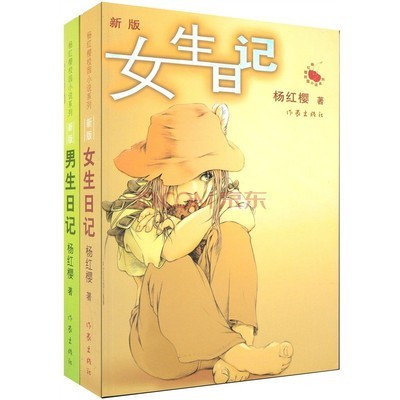于坚的这篇文章是特立独行的散文。它对我们如何发现自然的意义、表达自我的感受,体验生命中深邃的美感和意义,都有很大的启发。
这篇文章是对眼下无病呻吟、千人一面的游记文章的一种反拨,写出了他是如何改变了“对黄果树瀑布这一名词的成见”的过程,写出了黄果树瀑布是如何从扁平的图片,一步步进入他的视野和内心的。这不是简单的先抑后扬,而是作者在对一般旅游景点乏善可陈的认知经验的积累中,因为独特的游历和感受,而走进了黄果树瀑布,抑或是任由黄果树瀑布走进了他的内心。作者的这篇文章不是应景之作,也不是无感而发,而是带着鲜明而独特的个人体验,带着强烈的创作冲动而写出来的性灵之作。因此,他写道:“我抚摸了黄果树瀑布,我周身湿透,我有湿透的话要说。”当一个人觉得有话要说,有一种情绪需要表达时,这样的文章才会鲜活地走向读者的内心,激起读者的共鸣。
作者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写出了对黄果树瀑布的感受。他在一开始是带着抵触情绪的,但是随着他走近黄果树瀑布,“那时我猛然间听见了瀑布的声音,当时我心里一阵激动,黄果树瀑布原来是有声音的。这声音即刻改变了我对黄果树瀑布这一名词的成见,我立即明白我抵达了一个与我在图片上所知道的那个黄果树瀑布毫不相干的地方。”瀑布的“声音”,首先震撼了作者,黄果树瀑布这种“先声夺人”的美,使得本文也因此充满了情感的张力。“我和它立即建立了一种陌生的接触。我越接近它,我的生命和它的肌肤相触的面积就越扩大。”可以说,瀑布的声音,已经征服了作者,已经与作者的生命有了关联。
但是,黄果树瀑布的魅力还远不止此。接下来,作者将瀑布比作“一只弥漫于天地之间的巨手”,“从高处向我合拢过来,它抚摸我,亲近我,拍打我,刺激我,使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张开了,呼吸着水声,呼吸着潮湿。我感受着我的生命在巨大的水声中的惊恐、疼痛;在潮湿中的寒冷、收缩。”这样的体验和感受是作者独有的,也是奇特的。这弥漫于天地之间的“惊恐”和“疼痛”,让他感受到了瀑布原来是一个壮美的“动词”:“另一个瀑布在我的生命里复活了,那时,一切都成为说不出来的动词。”从巨大的声音,到弥漫天地的动词,这都是庞大而自然的力量的显示,是一种震慑灵魂的能量的象征。在一个充满轰响和律动的自然景观前,我们只能心生敬意,充满敬畏甚至恐惧。
作者甚至还来到了黄果树瀑布的背面,看到了在图片上锁没有看到过的立体的瀑布,“在这里犹如置身于水流的内部,看不出丝毫的雄伟、壮丽,你看到的就是水犹如玻璃粉碎那样的运动。”这时,作者与瀑布做了零距离的接触,人与瀑布已经融为一体了。磅礴的声响中,作者写道:“这里是瀑布的声带,唯一的发言者是瀑布,除此之外,任何话都听不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自然对自身的美没有任何言说,却胜过我们人类的万千言语。但是正是这不言的声音,才使我们震撼,才使我们感受到自然界迥异于尘俗喧嚣的力量与美。作者抚摸着瀑布,“和这瀑布之间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关系”。
这样,从听声音受到震撼,到感受弥漫于天地之间的瀑布的动作,体验到生命中的“惊恐”和“疼痛”,“复活”了一个属于作者本人的独特的“瀑布”;接下来,通过在瀑布后面的感受,与瀑布建立了生命的关联。黄果树瀑布,因此从画面上,走进作者的听觉、触觉、所有的感觉,最后走进了作者的生命。
他的表达很独特,是诗意而深刻的。通过这些细节的评析,可以学会怎样去领会文章中的诗意之美,怎样来表达自我的感受。如作者将瀑布比作一个弥漫天地的“动词”,“越走越近,我看见水柱像庞贝城在火山中毁灭时的大教堂的圆柱那样崩裂,轰隆倒塌,栽倒在水里,把水砸出了大坑。水在变形,在死亡,在合成,在毁灭,在诞生……”这样的形容,使得文章有一种宏大的美,这种美的表述又是联想丰富、蕴含着作者对历史和文明的毁灭与诞生的思考和感悟,文字的丰富内涵和极大的语言张力,使黄果树瀑布横亘千古,弥漫宇宙的力量与美扑面而来,同样弥漫于我们的耳目和生命。
作者将他与瀑布的关系比喻成“水和落水者的关系”,“这可能意味着死亡,也可能意味着得救。”这种表述也是很新奇的。作者在瀑布面前,从一个隔岸观水的旁观者,转变成一个投身其中的“落水者”。“落水者”或死亡或得救,死亡是因为体验与感受因窒息而干瘪,得救则是因为生命和灵魂因感悟而脱落旧物、重新鲜活而丰盈。这种诗意而有哲理的比如和想象,让本文具有一种诗意的氤氲和哲理的芬芳。
作者说:“风景化的图片使我仅仅把黄果树看成风景之一,这风景是没有空间、质量、空气和细节的,它们仅仅是祖国的骄傲这一概念的所指。”在很多人看来,游记就是写景,记事,因此,游记文章和旅游景点的宣传品普遍存在着同质化、扁平化的倾向。所以作者才总结出带着我们人人都可能存在的“观景失语症”:“不由自主差一点儿就脱口而出的正是那句老话:哦,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不由得生出一种在旅游点必产生的似曾相识的无聊感。”
这种感受也是带着普遍性的。过去长期将个人生活空间政治化的非正常状态,将个人生活、思想与集体和国家的话语形态强行捆绑,结果导致了表达个人情感和感受的“失语”,甚至人们都习惯于以一种带着集体无意识特征的集体话语和政治话语来表达自我感受和见解。见了美景,没有个人见解,脱口而出“哦,祖国的大好河山!”这就是因为自我意识的缺乏、自我感觉的钝化和说假话大话套话的习惯所造成的。而长期这样重复出现的感觉,就势必会带来“在旅游点必产生的似曾相识的无聊感”,失去对自然和外界鲜活而独特的体验与感受的表达能力。
其实不单是在旅游景点人们经常出现这种无话可说的个人失语和拿假话套话充塞自我意识的无聊感,在写作中,在学习中,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形。比如,学生作文中经常出现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写作套路和言不由衷的话语,还有作者提到的“小学生千篇一律的命题为‘春游某某’的习作的题材,一位满脑袋陈腔滥调的诗人的灵感来源”,都可以归因于这种政治因素和陈旧教育模式对人心灵的桎梏,对人创造力的扼杀。黄遵宪主张“我手写吾口”,袁枚提倡“独抒性灵”,走进自然,让自然走进我们的内心,以自己独有的体验和感受来接受自然,与自然契合,只有这样,你才能写出属于你的游记文章,展现出属于你的自然山水。
附:于坚《黄果树瀑布》原文
黄果树瀑布
于 坚
我在小学时就知道黄果树瀑布。那时老师在提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时总是要提到黄果树瀑布。但我看到黄果树的图片并不会特别地激动,这和看到祖国的长白山、祖国的大兴安岭、祖国的南海这些图片的感觉差不多。风景化的图片使我仅仅把黄果树看成风景之一,这风景是没有空间、质量、空气和细节的,它们仅仅是祖国的骄傲这一概念的所指。
去年六月,我到了黄果树瀑布。入口就是那些图片被拍摄的地点,在这里看黄果树,和图片告诉我们的别无二致。确实是雄伟、壮丽,确实是万马奔腾。不由自主差一点儿就脱口而出的正是那句老话:哦,祖国的大好河山!周围到处是卖旅游纪念品的,这些纪念品和拍风景照片的方法一样,也是按照某种“旅游纪念品”的统一风格制作的,根本激发不起我的收藏欲。我不由得生出一种在旅游点必产生的似曾相识的无聊感。
但那时我猛然间听见了瀑布的声音,当时我心里一阵激动,黄果树瀑布原来是有声音的。这声音即刻改变了我对黄果树瀑布这一名词的成见,我立即明白我抵达了一个与我在图片上所知道的那个黄果树瀑布毫不相干的地方。它提供的东西不是什么形而上的雄伟、壮丽,而是声音。它放射的声波令我的耳膜鼓了起来,我和它立即建立了一种陌生的接触。我越接近它,我的生命和它的肌肤相触的面积就越扩大。它先是侵入我的耳朵,然后灌满了我的耳朵,最后,是震耳欲聋。与此同时,我的头发开始潮湿,我的眉毛和鼻尖开始潮湿;再走近些,我的外衣开始潮湿,我的内衣开始潮湿,我的皮肤开始潮湿,我全身湿透,我像落汤鸡一样里里外外彻底湿透。
那悬挂在高原上的大瀑布,犹如一只弥漫于天地之间的巨手,从高处向我合拢过来,它抚摸我,亲近我,拍打我,刺激我,使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张开了,呼吸着水声,呼吸着潮湿。我感受着我的生命在巨大的水声中的惊恐、疼痛;在潮湿中的寒冷、收缩。越走越近,我看见水柱像庞贝城在火山中毁灭时的大教堂的圆柱那样崩裂,轰隆倒塌,栽倒在水里,把水砸出了大坑。水在变形,在死亡,在合成,在毁灭,在诞生……
那时候我魂飞魄散,“黄果树大瀑布”作为一直统治着我的一个早已干瘪的概念,顷刻间灰飞烟灭。另一个瀑布在我的生命里复活了,那时,一切都成为说不出来的动词,我不能说,我只看见水在动,在响,那不是马在奔腾,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潮湿,把我淹没了。后来,我发现人甚至可以绕过瀑布,抵达它的后面。我看到的黄果树瀑布图片永远只有正面,我一直以为这瀑布是紧紧贴着山体滚下来的,它不存在后面。现在,通过一步一步的接触,我发现它实际和山体之间还有着一条缝隙,人可以从那里穿过。我来到黄果树瀑布的后面,犹如哥伦布进入美洲,因为在中国的任何一张关于黄果树的风景图片中,都不存在这个地点。这里永远不会进入摄影镜头,因为这里太局部,太狭窄,自成一体,与黄果树瀑布正面呈现给人的整体印象无关,在这里犹如置身于水流的内部,看不出丝毫的雄伟、壮丽,你看到的就是水犹如玻璃粉碎那样的运动。这里是瀑布的声带,唯一的发言者是瀑布,除此之外,任何话都听不见,哪怕你在赞美,哪怕你像《圣经》那样说话。
你唯一可做的事就是抚摸。你可以把手伸向瀑布,抚摸它飘散在外的细毛。于是你和这瀑布之间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关系。水和落水者的关系,这可能意味着死亡,也可能意味着得救。
![[转载]【中学语文课文赏读系列】读于坚的《黄果树瀑布》 黄果树瀑布于坚朗读](http://img.413yy.cn/images/30101030/30110540t0125b31ceb67534378.jpg)
我本来永远不会就黄果树瀑布说什么话,这是一个多么俗不可耐的话题,一篇小学生千篇一律的命题为“春游某某”的习作的题材,一位满脑袋陈腔滥调的诗人的灵感来源,我有什么话好说呢?
但我抚摸了黄果树瀑布,我周身湿透,我有湿透的话要说。
1996年3月14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