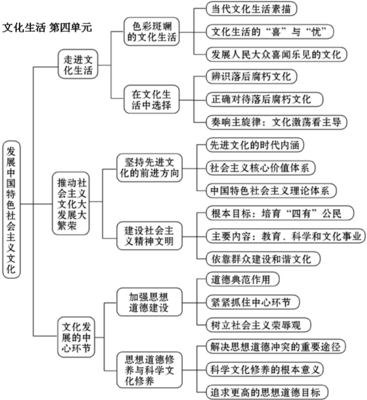吴秀波做客《文化视点》
马东:欢迎来到文化视点,今天啊非常特别,我们现场观众98%是女的,现场出现这么严重的生态平衡的失调,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现场会出现一位非常有魅力的男人,让我们掌声欢迎吴秀波。(掌声尖叫)
马东:这个环境你习惯吗?经常会遇到?
秀波:努力习惯中。
马东:我们是把在这个采访的消息,在你的贴吧里公布了,然后这些都是头两分钟之内报名的,两分钟之后人就满了。(秀波双手合十鞠躬)我们今天要跟秀波谈好多他的问题,我们一阵掌声来欢迎他。我们落座,好吗?
(秀波和马东落座,秀波的座位背对着观众)
马东:行没事,你冲哪都行。随便,咱们就这么聊,你愿意转过去,照顾照顾他们也行?你先转过去带5分钟,他们全踏实了咱们在开始。
观众:你俩换换吧?
马东:可以了,我俩换一换?
观众:对对。
马东:那不行,答应你们一会我俩换个位置。(最后也没换)
马东:来,我们一阵掌声给吴秀波。
马东:你有点不自然。
秀波:不是不是,因为公司的人提醒我坐下来的时候把西服扽扽(den den)。
马东:我们这一个星期呀,采访了很多明星,但你是上场以后掌声最热烈,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她们都是波蜜,另外一方面呢,你最近的关注度确实太高,你上来第一句话说:“我在努力习惯中”,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秀波: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毕竟不是以前生活的常态,然后突然间进入一种新的环境和新的反馈,尽量让自己不起念头。
马东:什么样的念头?
秀波:所有的念头。
马东:人能不起念头吗?
秀波:如果坚持的话,有可能。
马东:为什么不起念头?起念头有什么不好?
秀波:是这样,只是觉得就好像水一样,不管你是在浪尖上还是在底下,你只是一滴水而已。千万别以为这浪头是自己做起来的,是风和月亮。(掌声)
马东:不是每一滴水都能上到浪尖上,风天天刮,月亮也永远在那,但为什么现在是吴秀波在这个浪尖呢?你平常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吗?
秀波:不问。
马东:就跟着这个感觉走?
秀波:对,仅仅而已。
马东:我看你那个经历,其实你是一个经历特别复杂的人。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我看过你十年前的一个采访,那时候你可能是在做音乐呢。你知道咱俩同岁,都是68的。说起这事我就恨,看看人家68年的。(大家笑)你10年前接受一个音乐方面的采访的时候,我发现那时候你就会去谈论一些关于对生命的感悟啊,然后自己的创作状态呀,音乐到底在自己的生活中是什么,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它。。你是那种成熟得很早的人吗?
秀波:我觉得自己可能是一个一直没有完全成熟的人。
马东:成熟在你心目中的标志是什么?
秀波:我只是觉得我还有很多不明白的,我以为成熟可能意味着了解或知道得更多吧?
马东:那在这个标准下,人还能成熟吗?
秀波:其实成熟是相对于某一个时段或某一个阶段的词儿。谁又能说自己真正成熟了?可能在生理年龄上意味着结婚生子是成熟的一个表象,就像开花结果一样。
马东:我们俩谈得很深刻。不谈这个了,换个话题吧。大家都知道一个演员有一部好戏,大家就在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你比如像《黎明之前》,这部戏热的程度咱就不去形容了,在这之后你还在做什么?你的生活状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秀波:跟以前差不多。因为在《黎明之前》可能拍戏拍得稍紧一些,大概一年拍四部戏,11个月在拍戏,然后《黎明之前》播了以后呢,可能相对来讲一年要至少安排出至少两个月的时间来完成现在这些工作。其他的,我在尽量地减少我拍戏的量。
马东:你是那种在这个圈里很多年的,所以一旦自己到了浪尖上的时候,特别注意如何收敛自己。
秀波:其实不是,因为我这人有够。本来就不年轻了,就像你说的似的,咱俩都是68年生人、属猴的,然后突然间在作父亲的时候有了一份好的工作,只是想把这份工作如何做长,并不想在这份工作上做多么大的花活。所以现在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来讲,路的长度最重要,走最重要。(掌声)
马东:太喜欢她们这状态了,只要你说一个句号她们就鼓掌。(大家笑)我在看你这经历的时候啊,我就乐,你知道咱俩有很多像的地方,都是68年出生的,第二都生长在北京,都是在大院里,小时候父亲都不在身边,都有过管父亲叫叔叔的经历,我也有。然后我就在想咱们俩的成长环境是不是一样?因为我要做这个采访,每一段将心比心去看,吴秀波当时在看什么,他今天的心态跟我有什么一样或者不一样,其实我找到了特别多的相同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从小就生长在一个贫乏的环境里,其实那种环境对于我们人到中年以后会有一种影响,比如像我,就像你刚才说的,我有够,这句话就特别对,因为在我这个年纪觉得“有够”是个很难的事,因为再我们从小在那个贫乏的环境里,诱惑太多,你完成这个转变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秀波:其实就现在我们聊天,你也依然有从小生活在北京、68年生人的那种慵懒和不屑,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对那种商业时代的到来感触得特别深,因为我们在八十年代很贪玩,然后在大院里的孩子毕竟不愁吃喝,所以到来后来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才需要去找一份工作,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并不觉得养家糊口有多难,但最后推着你走的根本不是你自己。有时候好像你要装扮成另外一个自己,不停地在别人眼里努力工作,其实自己也不明白干嘛要这样。我就是那个努力想让自己明白为什么要被一个东西推着走?然后我就不是想走那么快。
马东:接受这个采访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秀波:是。
马东:我理解你说的,你说你愿意减少你的曝光,不愿意让那么多人跟着你,但是你的那份工作又决定了必须有那么多的人跟着你,才能证明你的工作干得好。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你能想通吗?
秀波:我最近在努力想。就是说,我们一进来看到这么多的人,因为我知道她们很爱我的角色,但是她们其实并不了解我。然后这件事作为我工作的一部分,我是为了她们来的,但是今天如果想我们俩聊得开心,我们要看不到这些人,完全看不到这些人,所以要放下心中刚才站在那别人鼓掌的念头,咱俩才可以专心地聊下去。而其实咱俩也不熟悉,咱们俩最好的聊天其实是四个人,两个你两个我,大家扪心自问。
马东:哪两个你哪两个我?
秀波:一个表象上的你和一个内心里的你,一个表象上的我和一个内心的我。首先我们要自己和自己先聊起来。这样咱俩才能有话说,其实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要放下的所有东西。
马东:你的这个状态其实和刘新杰这个角色是有反差的,
秀波:这个是后来这个戏播出以后,慢慢慢慢的(发现的)。。。所以我喜欢演戏,演戏像另外一个空间的生活,是一种修行。就是我发现,只要你感受,只要你平等对待,其实人性是相通的。
马东:我没太听懂。
秀波:其实怎么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们有任何没区别。你比如说人类所有的天性,我一个人身上全有,你一个人身上也全有,只不过每个人由于缘分、由于机缘巧合,放大的那一部分不一样。就是说,以前有一个演员问我,他说“吴老师”,他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他要演一个家境很好(的人),突然间家里又来了个孩子,说是他的弟弟,然后他要特别厌恶地把这个孩子轰出去,他就说“我做不到”。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塑料棚子里,夏天的时候在聊天,然后我说“你做得到,只不过你没有放大那一块”,他说“我从来没做过”,我说“我刚才就看你做了”,他说“我做什么了?”,我说“我看见你用剧本在疯狂地打一只蛾子,那是一个独立的塑料棚,有灯光,相对外面来讲,要更暖一些,更亮一些,那只蛾子飞进来,那是他生命的需要,而你拿那个本儿打它,只是因为厌恶和陌生。这跟那个兄弟之间有什么区别?没区别,你把它放大了,或者你真正把它放进你的生活。”
马东:你生活当中一直这么敏锐吗?就是你知道吗?坐你对面会很害怕的。你做的每一个动作,就是潜意识的,不知道能不能被他捕捉到。你最近佛经读得很多是吗?
秀波:那倒不是。我觉得我只认真地看过一本《金刚经》。
马东:我能理解,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理解你这种状态。我是说现在,你知道这是一个访谈节目,其实你不愿意把它当做一个秀场来对待,你愿意回到本心来做一次交流,那在这个交流的过程里面,刚才咱们俩所谈的那些东西,是自己内心的那种的真念,是自己内心的那种想法,但是你用这么娓娓道来的方式说出来,还时不时地照顾一下她们----观众的时候,这个状态是你生活中的状态吗?
秀波:演员是一只猴子,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猴子,就是供大家看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要“为人服务”。我没有答案,我也没有道理,如果今天做访谈,要管我要个答案或道理,去找爱因斯坦。其实采访也罢,访谈也罢,录像也罢,采访可能就是“唉,吴秀波,说说你是怎么回事?来,看看吴秀波是怎么回事?”其实没关系,今天在这我是翻跟头也好,脱衣服也好,聊天也好,我们打架也好,让她们看到就行,是什么就是什么。其实要的就是这个。但是如果你找我要个道理,要个结论,或者说“吴秀波,你照着你自己给自己画张画”,我画不来。你们画,我画不来。(掌声响起)
马东:你们鼓完掌。(大家笑,鼓掌)
马东:在《黎明之前》其他那些男演员,包括林永健还有那几位,都很强,然后其实也很用力,所以你这个角色、你找的那个状态就特别好,一下就把距离拉开了,同时又相得益彰的那种感受。导演是这么要求的吗?刘江是这么要求的吗?
秀波:刘江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也是一个特别清楚的人。首先他是构建这个戏剧社会的主人翁,因为一个导演决定所有的场景、街道、房间、人物的形象,他创造了这个环境和社会;然后其次在我眼里,是无数的缘分、对立面,谭忠恕也好,齐佩林也好,顾晔佳也好,他们有跟我共通的地方,有跟我不同的地方,我特别感激我能找到一种在那个时间我认为比较准确的状态,进入了导演构建的这个世界,我也特别感激所有的演员在这个世界里所展现出的人物的特质,才给了我那些东西。那个戏我演得好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全是他们在做,就是简单地说,如果你在说话,我连听都听不见的话,那就该住院了。我听、我看,然后我想,我在那。
马东:刘新杰这个角色让你掉进去了吗?
秀波:我已经离他很远了,已经过了很长时间。
马东:当时呢?
秀波:当时,非常的舒适。
马东:非常什么?
秀波:舒适,很舒适。你看到的是风吹草动,跟以往不同,以往是疯狂地演了七百场戏,自己一句话没听见。有的时候,有些人晚上愿意去酒吧和人聊天,喝两杯酒,聊了两个小时,第二天早晨记住的全都是自己说的话,别人说的话一句没听进去,我觉得那就有问题。我(演)刘新杰最高兴的是我听见的全都是别人说的话。
马东:我理解你,你说的话的意思是,你找到了你自己和这个角色身上相同的那个频率,所以踩点踩到一块了。
秀波:嗯,有可能。
马东:所以你就舒服。然后整个耳朵、器官全都打开了,接受到各种各样别的演员、还有刘江营造的那种戏的社会的氛围。
秀波:对对。
马东:自己那种舒适的感觉出来了,自己也呈现了最好的一个状态。
秀波:对,它是一个真实状态。
马东:真实状态。你受过特别严格的表演训练?
秀波:我曾经受过。
马东:有用吗?
秀波:嗯。。。我其实特怕伤到所有要去考学的孩子们。
马东:没事。
秀波:我在你们最早给我发的一份简易的采访单子上,看到一个题目,就是他问我:你认为(表演)是随性重要还是演技重要?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其实我们说的随性,仅仅是一个人进入表演过程最开始的一个步骤。表演有没有技术可言?当然有。比如说,就像所有的工种,我首先我要不怕这台机器,我既要照顾到它的画面,但我又不被它产生任何的影响;其次我的戏是演给她们看的,但我在演给她们看的时候,要看不到她们,只看到你;再其次你和我并不认识,这个环境并不真实,但我要把它当成我真实的生活。这些都是要靠训练完成的。但是其实说的简单一些,就是放下,放下生活中所有对立的东西,放下自我,来进入一种虚幻的、虚拟的精神世界的空间里进行交流。其实用这么两句话说,表演课就上完了。但是有那么长的课程,有四年的课程,那是一个表演疯子写了好长时间的书,赶上他高兴了,他都写。但是人的语言有太多的误区,从书本的文字到老师的头脑里,就产生了巨大的误区,再从老师的头脑里转化成文字,在到学生的脑子里,又有巨大的误区,学生的生活和他生活的空间跟他所接触到的知识,有产生巨大的误区,所以我发现,最终从电影学院和表演学院毕业出来的孩子们,最大的障碍不是源于自己的生活,最大的障碍源于自己四年的学习!这是最可怕的。就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反而是他们学来的这些莫名其妙的知识。(掌声)其实,我以为“知识”这两个字特别有意思,我认真地想“知识”这两个字,“知”是一个箭矢的“矢”字加一个口,我知道!你们听我说!我知道!我就等于用一张嘴拿着箭在射你。
马东:用一张嘴拿着箭在射你?我慢慢想,你接着说。(笑)
秀波:而知识的“识”,是一个言字旁,一个只,言而知止,知道只说什么。就是比如我们真的想要一个学生明白表演或者明白一个东西,那个老师必须聪明到知道说到适可而止,而剩下的让他自己去想。你要说了就叫“知”,而不“识”。(掌声)
马东:刘江是这样的人吗?
秀波:其实很多生活中擦肩而过的人都是这种人,都是这种老师。
马东:你说到这,别的我不能肯定,但肯定是回不了中戏当老师了。(大家笑)
秀波:我怕我上课没话说。
马东:人受完教育,应该把所学的知识都忘掉,剩下的是教育成果,你说的这点特别重要。但是你知道你是因为有那么多的生活历练,或者说你是读完那个书以后在社会上有那么多的生活经历,然后把感悟都一点一点在心里积攒,然后能有今天的这种见识。年轻人怎么能有啊?他们去学这个表演是不是本身就是错的?
秀波:我觉得这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学校,怎么可能这个世界让每个人都幸运到因你而失教?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学生要有一颗自己教育自己的心。其实好多事都是这样吧,我以为。我以为中戏、电影学院,然后某一个特定的高材生的班,还有特腐化的幼儿园和小学,和无数人去烧香的庙,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地方,
马东:都是象(?)。我特能理解,他在这说话,他虽然说的很慢,在这想,我在这点头,就是我知道他特怕说,因为生怕自己说出来的东西,跟自己想的那个东西不一样。表达本身就是一个误会的过程,但是又不能不说,要不然我们俩干坐着,坐着干嘛呢?这个过程既痛苦也挺有意思。
秀波:但其实我们俩聊天,如果我们现在真做到后面没人的话,我们俩聊天,我说一半,你想一半。
马东:你生活当中的朋友,你跟他们都是这么聊天的吗?(笑)
秀波:其实我怎么聊都可以。因为我最先聊天先拿眼睛和耳朵聊。
马东:眼神交错,然后张着耳朵听。
秀波:我听的时间特多,我喜欢听。
秀波:我一直以为自己圆滑。
马东:好,太好了。终于让我找着一问题。自己圆滑是什么概念?
秀波:首先我喜欢圆,我不认为这个词完全是贬义词。首先我喜欢“圆”,我不喜欢任何有棱角的东西;然后“滑”确实是我个性上最自我保障的一份东西,北京人叫“滑不溜丢”,你要想攥我,你攥吧,我可能就跑掉了。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吓唬我们家的猫,就是小孩嘛,贪玩贪闹,对一个小动物就追呀追追,直到把它追到厨房的一个角落,它实在没地儿跑了,它的一个表情吓坏我了。就是它那么软的毛,全都根根立着,然后嘴张到最大。它所有的恐惧过后,它是拼命。然后我发现人的骨子里也有这种东西。这样东西我在我的角色里看到过,然后自己也有。我相信你的环境不会给我营造成这样。逼急了的话,哈(大家笑,鼓掌)
马东:其实每一个说自己圆滑的人内心都是方的。你如果内心就是圆的话,不用说,因为你本身就是圆的,所有每一个说自己圆滑、滑不溜丢的人,内心都有一个不妥协的方,见棱见角,是吧?(鼓掌)你角色里见过毛全立着的,你生活中有吗?
秀波:生活中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尤其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非常非常幸运。在我们的幼年时代,全中国人民信仰统一,这是一个几乎我们可能永远再看不到的事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仰统一的环境里。
马东:对。
秀波:然后我们出门在外是如此之安全,一年级的小学生脖子上挂个钥匙,满街疯跑,我们独立,我们有尊严。我们又特幸运地在八十年代感受到那么风花雪月、清新的空气。然后在所谓人说在飞速转变的九零年代或者千禧年代,我们父母即将走了,然后孩子出生,是人生常态的轮回点,我们那么幸运,所以我至少不是个愤青,我以前以为我是,我发现我不是。我非常感恩。
马东:他把我支走了,我刚才问的什么来的?(大家笑)想起来了。所以在我们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不会有被逼急了的时候。
秀波:只有自己对自己的不认可有可能,或者说在生活常态下对亲人的责任感有可能。你比如说对家庭责任,对自我的责任,都有可能。因为我觉得六几年的生人真的是很幸运。
马东:性格问题吧?我们这个年代生的人也有特别刺儿的。。。
秀波:有吗?
马东:有。你是不是想说,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容易有一种优越感,容易有一种闲散?
秀波:对,我觉得更多的是闲散。因为在早期它是一个生活极度平均的年代,我们没有任何压力,然后我们不产生童年的对比心;然后青少年的时候,那时候八十年代可能是建国后最浪漫的一个年代,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的电影风潮,看到很多新的文字,看到了很多新的诗和文化,到现在为止连那个年代的音乐都无法复制,现在那么多的比赛在做着口水歌或者。。,但没有一句讲的是他们自己的。
马东:那是一种被禁锢了很久以后突然释放的一种快感。
秀波:对对对。
马东:你可能有那么大的水量,但是你找不到那个突然释放的快感。
秀波:是。然后等到了九零年代和千禧年代的时候,恰巧我们本身就被摆在了社会栋梁的地方,我们肯定拥有工作,所以我们不恐惧。
马东:你一直心里没有焦虑吗,这整个的过程里面?因为你说你是八年前才重新回到你的影视表演,我知道在那之前你有过很多种职业经历,而且成功的、不成功的,赔钱的、不赔钱的,等等,没让你产生过焦虑吗?
秀波:有过。各个阶段都有焦虑,其实也是一个不停地在追求自由和解放的过程,自我解放。最早期的焦虑是考试,当然我这个不能成功借鉴啊,只是自己聊自己,看这只猴子是怎么样的。第一个面临的不自由和焦虑就是考试,高考也罢、初中升高中也罢,然后我找到了一种解决方式就是不上学。
马东:哎呀,你说到我心里去了。(大家笑)
秀波:于是我就不上学了。
马东: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上的?
秀波:我初中过了以后就不上了。
马东:我想想我。您接着说,您接着说。
秀波:然后接下来带来的第二层忧虑或者禁锢,就是爱情忧虑,当时给自己找的办法就是多谈。(大家笑)
马东:那是没法上学了。(大家笑)
秀波:因为这有一个概率问题,你谈俩,最多成一个;我谈一百个,你能跟我比?(大家笑)
马东:你怎么知道我就谈俩呢?(大家继续笑)
秀波:然后,慢慢的,才进入第三层,真正面临到你离家出走以后你的生计问题。你需要工作。然后那时候就是,那时候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多换。干干这个不成,我再换换那个。
马东:你那时候的状态基本是街上野孩子那种状态。你跟什么人混哪?
秀波:其实说得难听点,就是“有家的盲流”,
马东:实在没得吃了可以回家吃。
秀波:说得好听点,是“大侠”。(大家笑)直到最后焦虑感开始产生就是,因为父母虽然是你的亲人,但他们不依赖于你生活,相反你依赖于他们生活。就算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的工资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系依然完善地存在。然而到我开始组建我的家庭和拥有我的亲人的时候,那才是最大的焦虑和恶梦,因为你发现你要一份真正的工作。
马东:大侠也得有钱,才能当大侠。
秀波:后来我发现大侠还不如一个木匠。(大家笑)
马东:你当大侠的时候很快乐吗?
秀波:当大侠的时候“晕”。
马东:晕就已经是很快乐了。能晕多快乐啊。你当大侠是搞音乐那段时间吗?
秀波:我当大侠的时候什么都干过。搞过音乐,卖过录音机,然后做过服装,开过美容院,开过饭馆。
马东:慢慢慢慢。倒录音机是最开始那个。。
秀波:DA27
马东:就是那个单声道双声道的那个录音机时代?
秀波:录像机。
马东:哦,录像机。就是那个大21小21带子那个。
秀波:对对对对。反正那时候大家知道的,咱们都做过。
马东:搞服装是练摊?
秀波:对。
马东:你在哪练呀?
秀波:我在东四,租柜台。
马东:你自己喊吗?
秀波:瞧一瞧看一看
马东:那不喊。因为东四是这样。当时的东四呢,全是民房,当时最早都是平房,当时我们最羡慕的就是那群住平房的人,尤其是住在街面平房的人。
马东:墙上掏个洞就开门脸了。
秀波:他们直接就把自己家改成了一个可以分拆租售的地方。他在自己的那个小屋里,摆上五六个柜台,以每个柜台平均两到三千一个月的价格往外出租。
马东:哦,就一个屋里面还是不同的柜台,就是租给很多人。
秀波:因为当时都不是那么有钱,不可能租一个整个的屋子,大家都是分租柜台,做到最后有做的好的,他都包下来,两三千块钱意味着当时一个正常人一年的工资。那时候你要一个月付掉。
马东:你也是南方整衣服回来卖?
秀波:嗯,石狮,福建石狮。
马东:挣钱吗?
秀波:挺挣钱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概念啊,因为那个时候首先不知道钱是干嘛用的。
马东:不会吧?
秀波:是是是。就是说以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挣了钱会非常清楚,我买一个房子,最重要的,它既能居住,又能保值;然后我买一辆车,这样我出行方便;我买一个衣服,为什么?因为我天天出去混,我得让人觉得我穿得还不错。那时候花两三千块钱买一BB机,不知道干嘛。
马东:没人呼你。
秀波:没有啊。(大家笑)
马东:然后还得捆皮带上,还得把T恤。。
秀波:捆皮带上不行。
马东:捆哪呀?
秀波:就是西服这有一兜,那么大一BB机别兜里把袢露出来(大家笑),我现在还有一张我那么拍的照片呢。
马东:然后一天到晚就盼着别人呼你。
秀波:自己呼啊。(大家笑)
马东:BB机刚出的时候。
秀波:126.
马东:就是上面一小排液晶的,126的,相当奢侈了,齁贵!刚才你说一两千块钱相当于什么什么,当时那一个BB机就得一两千块钱。
秀波:对。因为那个时候就以为那就是人生的价值,它是一种误区,一种误解。前两天去拍了一个音乐电视,一个品牌赞助的,那年那个品牌做了一个大毛领的西服领的皮夹克,我们叫皮偻,3000多,哈哈。买一件穿,冬天这冷得不行,西服领的皮夹克,你想想,最逗的是穿上这皮偻,打上一条金利来领带。(大家笑)
马东:金利来,斜纹代表勇敢决断。
秀波:现在我们说起来,只有我们能把它当成笑话,其实如果我们能清晰地认识到,那不是笑话,那是生命的正常。
马东:对。
秀波:就跟现在所有人把裤子穿到这,把裆掉到这一样。
马东:一样。表现形式不一样。按你这路子你应该直接会成为一个商人或者叫做个体户。
秀波:咳就是没做好。其实我梦想着成为一个商人,但是没做好。
马东:你知道现在北京有很多很成功的企业或者大的连锁餐厅,都是那时候从一个当初的一个小饭馆那么起来的,很多企业也都是从当初练摊那么一点一点滚起来的。
秀波:对。
马东:你没弄好。
秀波:我没弄好。其实我很佩服有很多的企业有企业文化,坚持着企业的责任、企业文化和拥有企业信仰的那些企业是我特佩服的,那其实对社会非常有益。
马东:当时你没找着这个。
秀波:是没做好,做不到。
马东:所以就跳。
秀波:在不停的跳。
马东:开餐馆,开什么餐馆?
秀波:我开的挺多的。我开过西餐厅,开过酒吧,开过火锅店,开过云南菜。。
马东:挣钱吗?
秀波:开饭馆没挣着什么钱,卖饭馆挣着钱了。开饭馆因为我不精于算计,你以为坐满了就挣钱啊?坐满了不挣钱。坐满了你也得看你的支出。大厨二厨砧板所有服务员的支出、所有开销和房租,以及你店的容量,还有你的菜价,我那饭馆有时候天天满,但就是不挣钱。
马东:你这么不精于算计的一个人,你开饭馆干嘛呀?
秀波:我当时有一个特简单的概念:我会吃就会卖。
马东:我知道什么好吃。
秀波:我以为是这样。
马东:然后那个东西确实门槛低嘛。然后到最后挣钱,是因为特别侥幸在哪?因为这就是占了我是本地人的便宜。大家多少会有些关系,比如找房、办照,我们非常的容易。
马东:这样一个一个开,一个一个卖。
秀波: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的那个外城市的人到北京来做生意,他们非常清晰,而且他们在外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原始资金,他们要迅速地完善店面,他们没有时间,也不愿意过多地去做那些周章。
马东:他们就直接把你的店买下了。你就拿了钱再开一家。
秀波:对,然后再卖。
马东:人坐满了就再卖。
秀波:对。
马东:这挺好。这其实是很成功的一种…你其实是个中高手啊。
秀波:其实现在认真想想,我这应该叫“商务房地产中介”。(大家笑)。我做得更完善一点,我连室内设计(都做了)
马东:把它包装成餐厅的样子,其实是房地产中介。其实这挺成功的,滚起来了吗?
秀波:但是后来也不行了。因为我卖了七家店,我卖到最后,北京已经开始盖新楼了,再盖新楼要求进店的标准完全不同啊。
马东:已经不是你能做到的了,你就转行了
秀波:我就又干别的去了。干嘛去了那时候我?我干别的去了,嗯。(大家笑)
马东:你看啊,就这些经历里边,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每一段经历都是修行,因为你接触人、见识人,掌握一点关节,掌握一点能量储蓄的地方,拐弯抹角地成功搁在自己心里,所以成功不成功不重要,在自己心里留下东西了。所以自己去干点别的去。
秀波:对。
马东:按说你当时的这些状态,你是那种走心的人,这种状态就是挣多少钱、或者钱来钱去,其实对你来说不重要。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你会把所有这些经验积累起来,作为下一步的一个台阶。
秀波:这就是我们彼此的不熟识。你说我是所谓走心的人。
马东:对呀。
秀波:我不是一个天生特智慧的人或者对自己要求特高的人。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低的人。我现在之所以(走心),我不敢说是我的信仰要我走心,我的工作让我不得已必须走心,我做演员不走心不行,不走心你们不看我的戏,我没饭吃。所以在工作中
马东:你是被迫走心的。
秀波:咱们就这么说吧,不能把自己说太好。开始通过八年的演戏生涯开始琢磨了,琢磨人,琢磨心,看到心,然后开始所谓心的行走啊,是挺好一词儿,还有你所谓今天的你可以说“吴老师这是你的见识”,我说“这是吴老师的病态”,咱们舒服点,就是我的这种状态。我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如果在水里的生物,我就是一水母。知道那东西吧?
马东:我知道,就海蜇嘛
秀波:对对对,一点脑子都没有。(大家笑)连捕食都不会,你知道吧?所以如果今天我还有一些东西能放下的话,完全得益于那时候什么都记不住,真的什么都不在乎。就那时候叫混不在乎。浑浑噩噩不在乎。过了就放下,过了就放下,根本没有任何钱或者事业,没有,没责任,那时候没责任哪,而且那时候身体好,死不了,而且生活中还有异性。
马东:那就更死不了了。(大家笑)你当过老板,然后又转回来开始当演员,而且是从小演员开始当起,得益于你说的这个无所谓,过去了就过去了。当演员是因为好玩吗?
秀波:不是,我没有任何退路。我当演员那年我孩子在他妈妈肚子里七个月,我身无分文,一分钱都没有,不当演员,我总不能带着我的妻儿回到我父母哪去。那时候没钱买,还想出名?给钱吗?给钱干什么都行。但是有一条我明白,我不能犯法。因为我不仅要给我儿子一个生活的空间,我还要给他一个尊严的空间,对吧?我不能说你爸的钱是偷来的。所以就是给钱怎么都行。
马东:你这个孩子来得是很突然,是吗?
秀波:(表情)是。(大家笑)
马东:孩子会改变一个人,这是没辙的事。他来了你就被迫得改了。
秀波:必须要改。
马东:那时候你多大?
秀波:那时候34到33之间。
马东:这之前都可以混不吝?
秀波:我现在都不敢想象,如果我没有孩子出生,我现在什么样?现在我估计我在街上狂奔呢。(大家笑)
马东:当演员哪,想过照什么方向发展吗?就是片酬能够越来越高,能够让妻儿生活得越来越好,这是当时一个明确的目的吗?
秀波:就是我当演员的头一到两年、甚至两到三年的心态就是,我们管它叫公共汽车也好,比如一辆拥挤公共汽车,或者说这个车你只要下来就死,而这个车又没有车边上的车壁。
马东:啊,就大平板。
秀波:就说千万别给我挤下去。头一两年、两三年都是这个车。
马东:我明白,经常在印度的新闻上看到这种车。
秀波:千万别给我挤下去,千万别给我挤下去,我干什么都行,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马东:所以努力。
秀波:拼命。
马东:拼命。你拼命什么样?
秀波:我可以不要命,我可以把我这条命拼掉。
马东:演戏?
秀波:演戏!死都行。
马东:现在别人形容吴秀波的这种懒散、慵懒,那时候那样吗?
秀波:我不知道是不是光演戏这样,我相信所有的工作、或者你需要依赖它生存的工作方式,可能都需要带两样东西,一个是和暖的阳光,一个是一把刀。
马东:说说看。阳光。
秀波:因为你要保持良好的心态,这样你才能不纠结,不做太多错误的决定。还有一把刀,这把刀就是用来捅自己的。只要自己做错了,没做好,捅自己;再做错,再捅自己;再做错,再捅自己。。。
马东:你常捅自己吗?(大家笑)
秀波:常常捅自己。
马东:不让别人知道?
秀波:别人也不信哪。
马东:你的性格应该是那种回家自己捅(自己的)。怎么捅?
秀波:就是我几乎可以忘了所有的事,特别专注地想,我究竟错在哪?怎么错的?和如何改正?
马东:如果这个错伤到了别人,给别人道歉吗?
秀波:不是这种错误,都是在表演上出的问题。就是说,比如我把工作演戏当做修行的话,此时此刻也是修行,如果我此时此刻不能真心真意地和你交流,我回去就会拿刀捅我自己。我根本不在乎这期节目播出来是什么样,但我必须要做到真实交流。(大家鼓掌)因为我如果不能真实交流的话,我下次演戏有可能也作秀,那我的妻儿就会没饭吃。
马东:现在身上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吗?
秀波:我觉得应该永远有吧?因为我不是骗子,我要(靠演戏)换饭吃。
马东:所以你身上那种懒散和潇洒只是一面?
秀波:在这时候会没有。
马东:你说的那个拿刀捅自己的过程,在表演里边对自己有用吗?
秀波:有用,不仅对表演有用,我觉得对人的一生都很有用。比如说一个错误在心里形成一个疾患的话,你这一刀不捅进去,它永远是个疙瘩和阴影。拿刀捅进去之痛快呀!
马东:就释放了。
秀波:非常痛快。
马东:你朋友形容你是吊儿郎当,看起来不是那么回事。
秀波:其实以前大部分都吊儿郎当。
马东:表现给他们看吊儿郎当。
秀波:比如现在,如果你的节目可以抽烟的话,我会一定抽烟。
马东:不可以。
秀波:这就是一种让人看起来你吊儿郎当(的状态)
马东:有表演成分。
秀波:没有,就是想抽。
观众:。。。。(没听清)
马东:你们太客气了。
秀波:比如到现在为止我接受了200个采访,前50个不会想抽,前50个都在想:我头发没乱吧?(大家笑)现在就会想抽烟,所以我特高兴,因为我平常只有聊剧本的时候才会想抽烟,现在采访的时候也想抽烟;或者以前特小的时候,我只有打麻将的时候才想抽烟,现在连做访谈节目都能想抽烟,这就是一种进步,对我来说。
马东:其实你保持这种真实状态对你自己特别有好处,或者说你从中尝到了甜头,是吗?头发乱不了没那么重要。
秀波:非常甜,就跟甘露一样。
马东:我想说什么?我一直在想跟采访嘉宾之间找真实感觉,你知道很多人做到这个座儿上的时候,他没办法,有的人是演员,有的人是有身份的,有的人是什么,找这个真实感觉特别不容易。有的人只要灯一灭,镜头一不对着他,马上真实;但是坐在这就不能。为什么不能坐在这的时候也真实呢?
秀波:我形容一下咱们现在的状态啊。我可能是一个恰恰相反的人,我不是说我多好,我是因为工作我没办法,我是开开灯以后我真实,你把灯关上以后,我马上虚伪。(大家笑)
马东:你这么说,你那些朋友不寒心吗?
秀波:然后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你本来需要要用很多种方法、你的职业技能,让这个嘉宾进入一种真实的状态,你好跟他聊。但有的时候你突然碰到一个真实的人,你会问:唉?你为什么这样?你等会儿啊,等我一下,我先扔下再追你去。
马东:我用你的角度再来说说我的感受。我的感受是什么?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是我们能以电视台的名义把一个我们感兴趣的人请到这来,坐在这,然后我跟他真实交流。如果坐在这是假交流,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我真正看重的这个(钱的手势)完成了,所以在中央电视台挣不了多少这个(钱的手势)。(大家笑鼓掌)我要是想这个,肯定不干这个节目了。这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吸引,但是我的痛苦就在于,有的时候别人想的刚刚相反,他认为咱俩坐在这你唱我和,你哼我哈,咱俩把这个事给弄完了,我也能弄,弄完以后我心里边就是。。没劲!不过瘾!我喜欢这份工作就是因为可以真实交流。说实话我也喜欢这样的观众,因为你们知道我们说什么,喜欢我们这种交流方式。有的不是,有的就希望我们一块表演个什么东西,我们也会,但那不是我们想要的。
秀波:绝不!
马东:所以你刚才说灯一灭,你开始进入另外那种状态,所以你真实状态恰恰是通过媒体传播出去的,所以恰恰大家看到的是真实的吴秀波,你生活当中倒不完全是真实的你。你别扭吗?你知道这样的话就变成你的表演不累,但你生活累。
秀波:是这样啊。在表演中如果我的生命够长,我一百个戏我有一百个生命,我演一千个戏我有一千条生命,我死得起、活得起。但是生活不是,有一首唱的“生活就像一条大河”,
马东:我听的那个是“生活是一团麻”(大家笑)
秀波:如果要想在生活中找到真实的自由,是不能向外找的,因为所有人都在你对面,是不能向外找的,得往回走,所以当你把灯关上,我也把灯关上,我自己屋里灯亮着就行。
马东:你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多吗?
秀波:几乎分分秒秒。
马东:就是人生的那个孤独感一直伴随着你?
秀波:分分秒秒都独处吧。
马东:这种孤独感没办法和亲人孩子分享吗?
秀波:这是你自己需要照见和解决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的,孩子也罢,亲人也罢,都是生命中的缘分,如果你觉得有能力,你就去努力工作,让他们尽量生活得安稳,你努力地修行自己,让他们感觉到和暖和善,剩下的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对自己解决。
马东:人生终究是孤独的。
秀波:对。所以有一句和幼稚、很美好和很斩钉截铁的一句话,叫“不去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非常难,怎么可能呢?这条路毕竟是你自己一个人走啊。
马东:不显得太凉点了吗?
秀波:我觉得特好,我觉得特暖,很暖,非常暖。
马东:你孩子能听懂这些话的时候,你会跟他说这些吗?你忍心跟他这么说吗?
秀波:我相信他终有一天不用我说,一定会这么想。就像我们的父亲走之前有太多没有跟我们说的话,但我们今天自己都清楚,然后我们也想,我们究竟是像那个“知”----一个矢一个口说给儿子,还是我们做一个“识”的人,说到哪和不说什么,还是不说吧,适可而止。(大家鼓掌)
马东:这人挺可怕的。做访谈节目特别怕这样的,就是你无话可说。
秀波:不怕不怕,我觉得呆着就呆着。(大家笑)如果有一期节目,45分钟,呆了20分钟,
马东:那叫事故!(大家笑)你是没事,我是要扣钱的。(大家笑)说说音乐吧。
秀波:好。(大家鼓掌)
马东:这是什么时候的碟?
秀波:我的记性非常差,至少是15、6年以前的。
马东:全是你自己写的?
秀波:全是自己写的。
马东:十首歌?
秀波:十首歌。
马东:京文给你出的?
秀波:京文出的。
马东:这些歌你写的,你现在听起来你觉得好听吗?
秀波:我觉得我做这件事对我自己非常有意义。如果我跳出来的话,作为客观来讲,如果听音乐的话,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人的歌,我觉得他的旋律感不好,但是我会喜欢他的真实性,就是非常可观地说。然后我在音乐了欠缺太多的技能,包括音乐创作也欠缺太多东西。因为写歌的这个毛病延续了好长时间,最后写的几句歌到现在我清楚地记得,但是我只写了四句,我就已经把我要说的全说完了,但是我的音乐却无法把它包圆了。
马东:歌词意境。
秀波:我可以唱给你听。(大家鼓掌)
马东:不是我要求的,但是你既然这么主动,我只有答应。(大家笑)拿一个手持来。
(大家要求他去中间的表演台去唱)
马东:不必不必,他说了他是要唱给我听。
秀波:其实就四句,特别简单。(开始唱了)让梦想的鱼在天上飞,让蓝蓝的天永远不要灰,让所有人的眼中藏着幸福的泪水,永远不要再伤悲。(大家鼓掌)
马东:这是你多大的时候写的这四句歌词?忘了?
秀波:不不,记得。这是在我孩子出生前。
马东:生活里阳光都照进来。
秀波:这个歌首先第一句话就很难完成,让鱼在天上飞。(对乐队说)我们先不弹琴啊。(清唱)让梦想的鱼在天上飞,让蓝蓝的天永远不要灰,让所有人的眼中藏着幸福的泪水,永远不要再伤悲。。。那一句能做到?
马东:你唱的是天堂。你闭着眼唱歌脑子里是什么?
秀波:这是我要看到的,因为睁开眼睛看不见了。
马东:他们说你开演唱会什么的都不睁眼,只要唱歌就把眼睛闭上。
秀波:其实刚才拿上这个(手持)的时候,就会成为一种
马东:障碍,不是自己的
秀波:对,它不是一种自我交流,因为我没有什么想跟别人表达的,其实说句不客气的话,就是今天就是自己跟自己聊天。
马东:嗯! 我明白我明白。我也是!(大家笑)
秀波:这样有价值。
马东:对,我明白。音乐是你自己跟自己聊天的一种方式,
秀波:嗯。
马东:我采访过一些创作型的搞音乐的人,它是一种生理需求,你说不让他写歌,他能憋死。就是当它有那个创作冲动,其实写小说的人也是这样,或者画画的人也是,这是他的生活方式。他不这样就跟人不走路,血液循环就憋得慌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你唱歌特别好,他们说你曾经在歌厅里就是那种唱歌会感动很多人的那种人。
秀波:曾经有过。
马东:天赋。
秀波:还有需要。我以为还有需要。
马东:今年春节过了的时候,你们经济公司跟我通过一个电话,就说秀波要推一张唱片还是单曲,或者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晚会呀让你。。你知道这事吗?
秀波:我昨天在拍摄现场,我的经纪人说,吴老师,我给你听首歌?然后给我听了首歌。我说这歌干嘛?她说这歌我想放在你的什么写真集里(笑)。我经纪公司有一群特可爱的人,一群特可爱的女人和一个男人,(大家笑)他们像妈妈和姐姐一样努力经营着你,让你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创造最大的价值。一开始我会抵触,就尤其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和我的经纪公司的经纪人认真谈了一次,经纪人傻了,就是本来聊今年的工作安排,她说你今年的工作安排是什么?我说今年的安排不拍戏(大家笑),休息,然后什么都不做。宴西眨了眨眼睛,说吴老师,那你再想想?(大家笑)特别好。其实是我不对。
马东:肯定是你不对呀。(大家笑)
秀波:是我不对。所以我感恩他们为我做的一切。如果我觉得这项工作不好,一定是我的心态不好,没有任何一件事是不好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有对错,如果没做好,只能是我没做好。所以他们拿来一首歌,我听真挺好的,我会尝试去录,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自己觉得满意。
马东:你刚才说,比如今年我不拍戏,然后你又说了,这是你不对,其实从我们大家知道和喜欢的吴秀波来讲,这是你不对。从你个人来讲,或者说从一个人的自我的那个角度来讲,这挺好的,或者说这有一种力量感。你能不能做到?
秀波:其实水流碰到的一个坎。水流到这它要自由,它碰到这个坎它就想往边上拐,其实你只要水漫过去,仍旧可以流过去。流过去你发现哪都是河床,流在哪都一样,怎么修行都是修行。
马东:这事你想通了?今年还拍戏?
秀波:我想通了才来这。(大家鼓掌)
马东:那这种情况下,唱歌和音乐还会带给你享受吗?
秀波:依旧会,会给我带来满足和自我交流。自我交流真是太有意思的一件事,因为自我交流会很难,因为你无法想象你说:“吴秀波!”“哎!你好。”不行,烦死了。很难,你看不见自己,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想象着自己在这或者在那,然后产生很多迷幻的感觉。
马东:老有一种感慨:这孙子谁呀?(大家笑)
秀波:我觉得这很重要,很重要。
马东:这不算精神分裂吧?
秀波:我以为自我交流可以产生信仰。
马东:只是产生幸福,因为它让你
秀波:也产生方向。
马东:又没的说了。他可以让自己看见自己,这种自我观照是何其重要。我们很多人老把信仰当作和宗教相关的一种说法,其实我们在这谈论的不是宗教,是人的自我内心的一种。。。说修行就偏宗教了。
秀波:生命过程的需求。
马东:是自我认知的一种需求。人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你总得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到这个世界上来?能干嘛?怎么走?
秀波:而且它是客观存在的。
马东:你怎么写歌?
秀波:这个。。这个。。
马东:你会乐器吗?
秀波:不不不,这个问题太大了。就是我不会乐器,我也不识谱,所以你要说我怎么写歌,回去容我想一个月想明白这件事。反正就假设在某个时段这个人在谈恋爱,一直在谈恋爱谈恋爱谈恋爱,然后他对这个人所有的感受和想表达的东西又说不出来的时候,或者自我有某一种方向感要去的时候,他,就是我,就会唱出几句,包括刚才唱那四句也是。就是我看到了,但又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你就要用比喻的方式来给自己一个观照,你怕你自己有一天忘记看见了那个方向,然后突然间就出来这么四句歌。这么四句歌好像是四个情景,鱼在飞;天是湛蓝的;每个人在流着眼泪,但是因为幸福在流泪;然后看不到那些伤悲,也不存在喜悦,他是一个和暖的感受。
马东:拿录音机给自己录下来。
秀波:那不用,如果记不住的话,忘了也罢。
马东:然后唱给别人听?
秀波:更多的时候是洗澡的时候唱给自己听,然后开车的时候唱给儿子听。
马东:你唱别人的歌吗?
秀波:也唱,很多人写歌,我最后不写歌不做音乐,那时觉得一听别人的歌,人家写得太好了。
马东:干嘛非得超过人家?
秀波:是我不允许自己再卖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要贩卖的话,人家种出来的西红柿那么大、红的,你种出来的这样(用手比划小得可怜的形状),怎么卖?
马东:跟儿子关系怎么样?
秀波:我是他,他是我。我是他们,他们是我们。
马东:你 这么忙,有时间陪他们吗?
秀波:我怎么说呢?如果你不打我的话,我说句特形而上的话啊,我分分秒秒和他们在一起。
马东:是得换一句。
秀波: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工作是我生命中特别大的一份需要,所以我一定要去工作。然后我跟我儿子是这样,就是说我只要一回来,我们就在一起,在一起玩。说点三级的,我们家有一大浴缸,回来最高兴的事就是把浴缸放满水,跟我俩儿子一块在浴缸里,六只小鸭子。。。好多人都说,哎呀老出去工作的人会不会跟儿子生疏?马东特简单,咱俩这么聊两次天,咱俩都不会生疏,何况我儿子呢?(大家爆笑)
马东:这是我听到的最该打的一句话。换个话题,换个话题。我知道你们特想让我问吴秀波的感情问题,听我说。。
观众:不想!不想!
马东:你们也不问?
观众:不问!
马东:咱们都不问。就让这个话题过去。因为吴秀波今天跟我分享的这些故事,关键是他打开的他的内心,我觉得已经足够灿烂,也足够满足我们了。谢谢吴秀波。(大家鼓掌)
采访日期:2011年6月1日
来源:百度吴秀波贴吧的秀于琳整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