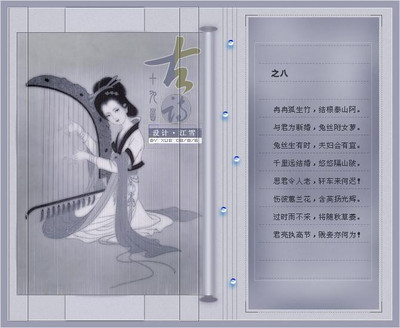周德东是中国名列前茅的恐怖作家之一,基本他的作品我都看过~长篇《我遇见了我》《三减一等于几》《天惶惶地惶惶》《门》等作品,喜欢周德东的可以去下载看,因为篇幅过长在这里不作介绍了~这次介绍的是周德东中篇中的经典~虽然很少被提及~但恐怖效应不输给他的任何一部作品~有时间的恐怖文学爱好者没事看看咯~映画感也是很强滴说~

第十二夜(一)如果早知道会有那样悲惨的结果,张葛怎么都不会带着小毫到玉黄山森林公园去玩。 小毫是张葛的女友,她的体重只有40公斤,很瘦弱,身上总是凉凉的,好像不产生热量一样。平时,她说话的声音很小,总是没有底气的样子。 张葛和小毫已经在一起同居两年了,只是一直没领结婚证。 张葛在一家企业办公室当秘书,惟一的特长是总结写得好。小毫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出纳,整天跟钞票打交道。可以说,他俩都不是什么浪漫型的人。这天,张葛却突然心血来潮,要领着小毫去野游。 “去哪?”小毫似乎没什么兴趣。 “玉黄山森林公园,听说那里很好玩。”张葛说。 玉黄山森林公园离市区有60公里,张葛和小毫都没有去过。 “会不会很危险呀?”小毫问,她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 “旅游景点有什么危险?” “等到五一放假吧。” “放假的时候人太多,没意思。我们分头跟单位请两天假,明天就去。” 他们是上午出发的,太阳很好,他们的心情也很好。只是,张葛从厂里借的那辆吉普车略显破旧,没有暖气,而且窗子漏风。小毫死了,死于体温过低。 本来,她的尸体应该放进医院的太平间。可是张葛却坚持要把小毫放到家里去。 他说他要单独守侯她一夜。 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回到了家。 他们的房子是自己买的,从建行贷的款,十年按揭,现在还不到一年。 家里真暖和,进了门,一股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尽管这个家很简朴,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但是对于张葛来说无比亲切。 墙上的那些小饰物都是小毫买回来的,甚至椅子垫都是她亲手缝成的,可此时她蜷缩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她的表情很详和,医生说,死于体温过低的人都是这样的。 那张床是张葛自己设计的,很宽大,很舒适。两年来,那上面承载着他们的恩恩爱爱,缠缠绵绵。可是,他亲爱的小毫很快就要变成一撮灰,装进盒子里,那盒子跟她的首饰盒一样大…… 天渐渐黑下来,小毫的脸一点点陷入了黑暗中。都说死人可怕,张葛却没有一点恐惧,他轻轻抚摩着小毫冰凉的额头,一边流泪一边喃喃地说着情话。 他觉得,他的小毫一定听得见的。 此时,他的心中悔恨不已。平时,他的方向感就不好,经常领小毫走冤枉路。而小毫总是默默无声地跟着他,从来不抱怨,他就是她的方向。 为什么要去森林公园呢?为什么要离开管理处朝森林深处走呢?为什么让她留在车里呢?那时候她已经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了啊…… 男人应该给女人带来安全和保护,可张葛觉得,他不但没有做到,反而把小毫害死了。 哭着哭着,张葛累了,趴在床头打起了瞌睡。 在半梦半醒之间,他感到身边有什么东西在软软地动,他睁眼一看,身边竟然是一堆堆的绿毛,很多的大眼睛,很多的爪子,很多的腿,都在缓缓地动着。 是那种叫不出名的动物!有很多个,它们毛烘烘地依偎在一起,紧紧围住了张葛! 张葛大骇,一下就醒了,摸了摸,身边什么都没有。 他长长出口气,伸手打开灯。 屋顶的吊灯很暗,里面的灯泡多数都坏了,只剩下了一只或两只。苍白的灯光照在小毫的脸上,显得有几分恐怖。 就在这时候,他看到小毫的眼皮好像微微动了一下。 张葛的身上像过了电一样,头发都要竖起来了,心中的悲伤被巨大的恐惧替代。 他忽然想起了一条新闻,那是他在《南方都市报》上看到的,写的是广东顺德市乐从镇一家酒楼发生的事情。酒楼的员工小陈宰杀一条泰国眼镜王蛇,他把蛇头砍下来扔在地上,就忙着剥蛇皮什么的。大约十分钟之后,他忙完了,用钳子准备把那个蛇头夹起来,扔进垃圾箱,那蛇头突然跳起来,恶狠狠地咬住了他的右手无名指……小陈被送进佛山市一家医院后,仅仅几分钟就陷入昏迷,停止了呼吸。一般被毒蛇咬伤只需注射一支解毒血清,可是,医生为小陈注射了6支解毒血清尚未脱离危险…… 这个新闻曾经让张葛感到很恐惧。它将改变我们的某些常识。 假如,你打开一个垃圾箱扔果皮的时候,看见一个脖子被剁得参差不齐、流着血水的蛇头,它盯着你,突然跳起来咬住你…… 那么,有个人就可能在半夜里突然摸到被窝里有一团凉凉的软软的东西,还慢慢地蠕动着,开灯一看,竟是一条没有脑袋的蛇。 那么,在鲜血浸透黄土的法场,一个被砍掉的人头,在大家都散去后,就有可能突然滚到最后一个要离开的人脚前,眨着眼珠说:“请慢走……” 那么,你虽然死了,你的大脑就有可能还保留着意识,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怎样被推进了太平间…… 那么,小毫现在能不能听见呢? 仔细看,小毫静静地躺着,像一根木头。 张葛安慰自己说,一定是自己太累了,产生了幻觉。 大雪过后的小城,更加静谧。夜深了,除了窗外的一只乌鸦,都睡着了。那只乌鸦在叫,声音很丑陋,很缓慢,很孤单。 又过了半天,张葛看见小毫的腮部又动了动,那是上下牙在错动,这次他看得很真切,想欺骗自己都不可能了!他一下跳起来,后退了一大步,紧紧盯着她的脸,眼皮都不敢眨一下。 他首先想到这是小毫的鬼魂在作怪。她恨他,因为他的判断失误使她丧了命,所以她在奔赴黄泉的半路上又折回来,想害他。可是,她为什么不像传说中的诈尸那样一下跳起来把自己掐死呢?难道她真的活过来了? 张葛又恐惧又激动。他在用他那有限的医学常识在思考,一个人的身体机能和各个器官都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就被冷冻了,遇到温暖之后,可以缓过来吗?难道奇迹出现了? 他轻轻叫了一声:“小毫……” 小毫没反应。 他又叫了一声:“小毫。” 她的眉毛微微皱了皱,很痛苦的样子。 张葛觉得,她一定是听到了,也许她的大脑还不能支配神经,想睁开眼睛却无能为力。从那表情上可以感受到,从阴间到阳间的路有多么漫长。 “小毫!”这次他的声音大了许多。 这一次,小毫一点点睁开了眼睛。她在苍白的灯光下朝两面看了看,最后眼睛定在了张葛的脸上。 这世界死寂无声。“我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小毫问。 她说话了!张葛觉得她的话没有一点质感,像一缕雾气。 张葛朝她迈了一步,站在离她近一点的地方,眼睛紧紧盯着她说:“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去玉黄山玩,迷路了,我们在大雪里奔走……” “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然后呢?” “后来我们找到了吉普车,我把你留在了车里,一个人去找森林管理处。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却不见了。大家开车找了你一宿,在天亮的时候发现了你,可是你已经……昏过去了。” 张葛没敢用那个“死”字。不管她是人是鬼,那个字都是她所忌讳的。 小毫的眼圈一红,说:“我好像想起了一点儿。这么说,我们得救了?” 张葛上前扶着她坐起来,感到她的身子很凉:“对呀!我们得救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张葛半开玩笑地说:“我也怀疑我是在做梦,咱俩互相掐一下。” 她低头看了看紧紧蜷缩在一起的手说:“我的手怎么没有知觉?还有我的脚趾!” 张葛拉过她那像鸡爪一样的手,感到冰凉渗入了骨髓,像死人一样。 “一会儿吃点阿司匹林,你现在要加快血液循环。”他轻轻为她揉搓着,眼睛一直看着她的脸。 她疼得叫起来。 揉搓了一会儿,她的手和脚竟然都有了点血色。这时候,张葛已经有点信任她了。他试探着说:“小毫,真是奇迹!其实,我们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 “我已经怎么了?”她直直地看着张葛。 张葛停下手,考虑了一下,终于鼓足勇气说,“你的心脏都已经停止了跳动……” “什么?”她的声音蓦地大起来,根本不像她平时静悄悄的性格。 这时候,灯一下灭了,房间一片漆黑。 张葛的心跳如鼓。他和小毫谁都看不见谁。他偷偷朝后退了退。 “你是说我死了?”小毫在黑暗中问。 “医生这样说。”张葛低声说。“你等等,我去点一根蜡。” 他哆哆嗦嗦地摸到抽屉,摸到蜡和火柴,点着。烛光一跳一跳的,这房间显得更鬼气。 小毫还坐在床上,她满脸迷惑,问:“那我怎么又活了?你摸摸,我的心是跳的!” 张葛把蜡固定在茶几上,走过去伸手摸了摸,她的心软软地跳着。 “这是命不该绝,你又活过来了!”张葛说。 小毫木木地说:“又活过来了……” 夜深人静,睡熟的人类缓缓滑进另一个阴虚的时空;清醒的幽灵悄悄融入这个真实的世界。 这时已经过了半夜。 “我很饿,你赶快炒点肝给我吃。” “不行,你现在只能吃流食,再补点维生素。”张葛说。 说完,张葛来到厨房煮牛奶。 他的耳朵一直聆听着卧室的动静。 现在,他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卧室里的这个人将跟他一起生活下去,可是,她到底是人还是鬼? 说她是人,可她的的确确是死了,至少死了十几个小时了,这一点毫无疑问。 说她是鬼,可鬼的脸上怎么会有血色?心怎么又会跳? 张葛简直受不了这种大喜大悲的刺激了。 他决定,明天领她到医院去看看,他相信科学。假如在她身上确实发生了奇迹,那么也应该让医生为她检查一下,看看内脏有没有什么被损坏。 老实讲,他的心中一直没有彻底放松对小毫的警惕。他在心里努力回忆着今天的每一个细节,分析着她的每一个表情。 当他端着牛奶进了客厅的时候,看见小毫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那姿势就像没起来过一样。她的脸在闪跳的烛光里显得更加苍白。 好久没下雪了,干冷。好在张葛和小毫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张葛那件是蓝色的,小毫那件是红色的,很醒目。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玉黄山。 那是一片原始森林,没有人工景观。他们离开管理处那几栋砖房,朝森林深处开了大约5公里,下了车,吃午餐。 张葛特意给小毫带了一些炒肝,那是她最爱吃的东西。 四周的群山此起彼伏,树木连绵不尽,没有人迹。这时候,天变得灰蒙蒙。 吃完了饭,两个人正准备四处转转,小毫突然指着不远处说:“张葛,那是什么?” 张葛一看,一棵树的后面露出一个动物,长得很怪,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它,大家可以先想象一个狐狸的样子,但这个狐狸身子前倾,前爪离开了地,呈半直立状,好像要站起来;皮毛是绿色;减去两只耳朵,还要去掉一个尾巴;另外,它的眼睛更大,大得有些恐怖。 这个不知是什么动物的动物,距离他们只有30米左右,它静默地看着他们,那双过大的眼睛里充满和人类的意会神通。 小毫紧紧靠在张葛的肩头上,害怕地说:“它,它会吃人吧?” 张葛假装轻松地说:“怕什么?我过去把它赶走。” 然后,他捡起一根树枝,大步流星地朝那东西走过去。尽管他的表情恶狠狠,其实他的心里很怯。 那东西一动不动,冷冷看着他走近。 张葛走着走着脚步就慢下来。 这时候,他感到有冰凉的东西落在脸上,抬头看,漫天的雪花降落下来。 他终于在离那个东西十几米的地方停下,不敢前进了。 他和它对峙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小毫在身后看着他。他一个男人,如果退回去,那实在很丢人。于是,他想吓吓它,就大声喊了起来:“嗷!嗷!嗷!” 那东西无动于衷。 他又举起那粗粗的树枝掷过去,打在了它旁边的树干上,那东西连头都没扭一下,继续看着张葛的眼睛。 张葛有点慌了。 突然,他发现那东西抬起一条前腿(它那姿势太像人了,应该说它抬起了一条胳膊),朝管理处方向指了指,好像是在命令他们赶快返回。 张葛感到,这里很可能有什么危险正等待着他们。他快步退回去,对小毫说:“上车,我们快离开这里。” ……后来,张葛才知道,那个东西指给他们的其实是死亡的方向——他认为它指的是管理处的方向,其实正好相反。 雪越下越大,整个森林一片白茫茫。 张葛开车行驶了很远,却不见管理处的房子,而且四周的景象越看越陌生——他不知道,这时候,他已经驶上了一条荒凉的伐木公路,一点点驶向了森林腹地。 他的心越来越沉重,眼睛死死盯着雪花飘飞的前途。 两个人都不说话,他能感到小毫不时地转头看他的脸,她急切地想从他的表情上判断出目前的情况有多糟。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雪越下越厚。 他们的车不断地打滑,越走越艰难,终于陷在一个雪坑里,出不来了。张葛一会儿挂前进挡,一会儿挂后退挡,油门踩得震天响,却越陷越深。 他终于停止了努力,依靠在座位上,看着前方,脸色极其难看。 小毫颤颤地问:“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我们下车走吧。” 小毫早就没了主张,她乖顺地点点头。接着,两个人裹紧羽绒服,弃车步行。 张葛把吉普车上的红色座套扯下来,撕成了很多条,走一段路就在路边的树上系一条,做记号。 他们在大雪中向前奔走,脚也乱,眼也乱,心也乱。天已经快黑了,可他们一直没有看见管理处的影子。死亡的阴影像夜色一样越来越浓。 小毫说:“赶快打电话求救吧。” “手机根本没信号。”说完,他安慰小毫:“没事的,管理处就在前面。” 小毫望着远方白茫茫的雪说:“刚才我们就不该离开车……” 张葛一下变得很暴躁,他吼道:“你别抱怨了好不好!” 小毫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张葛立即有点后悔——小毫太娇弱了,她受不了这种寒冷。他伸手为她扫了扫羽绒服上的雪花,温和地说:“对不起……” “我太冷了。” 张葛就带她躲到一个避风的地方,然后把脚都插在对方的胳肢窝里,互相温暖。 他们坐了一夜。那一夜,小毫一直在哆嗦。终于,天边出现了一丝暗暗的白,张葛拉起小毫,拍掉她身上的霜雪,继续走。雪丝毫没有要停止的意思,天黑得像压了一口锅。 张葛虽然长得并不高大,但是他很健康。他一直很清醒,至少还没有忘记在树上系布条。 而小毫却越走越沉默。这时候,那不知是什么动物的动物又出现了,它半直立在前方的雪地里,距离还是大约30米的样子。雪很白,衬出它古怪的剪影。它的眼睛射出绿莹莹的光。 张葛倒吸一口凉气。 它转过身,朝前方跑去,好像牵引他们继续走,到一个什么地方。 张葛盯着那个动物,惊怵地说:“小毫,我觉得,它是在害我们!” 小毫呆呆地望着那个动物的背影,没有表情。 “现在,顺着布条朝回走,必须找到车……”张葛说。 这时候,小毫竟然不抖了,她的脸上都是霜雪。她无神地看了看张葛,没有说话,默默跟在他后面,朝回走。 她似乎对能不能找到车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他们又走了很长时间。张葛回头叫了一声:“小毫……” 小毫愣愣地朝两边看了看,然后直直地盯着张葛,疑惑地问:“你叫谁?” 她那眼神让张葛一下恐惧起来:完了,她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了。张葛把小毫紧紧搂在怀里,眼睛湿了。 雪仍然不紧不慢地落,人间一片雪白,老天似乎在编织一张巨大的裹尸布。渐渐地,雪已经深过了他们的膝盖,走起来十分艰难。 当张葛看到那辆抛锚的吉普车的时候,激动得叫出声来。他拽着小毫的手,快步冲过去,把眼看就要冻僵的小毫抱进车里,然后手忙脚乱地发动车,想制造一点热量。可是,那车却像被死神买通了一样,怎么都打不着火了。 这车四处漏风,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如果两个人都在这里等,那等于坐以待毙。 张葛想了想,说:“小毫,你坐在这里不要动,等我去找救援……” 小毫疲惫地靠在椅子背上,沉沉地闭上了眼睛。 张葛喉咙一酸,下车走了几步,又不放心地回来,在车窗外喊:“你千万不要动!你千万等我回来!” 小毫眼睛都没有睁开,懒懒地朝他挥挥手。 张葛走了。他判断,昨天一定是方向走反了,这一次,他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天快黑的时候,张葛竟然找到了森林管理处!可是,当他们开着车,带着熟悉森林路径的管理员,还有急救医生,找到张葛的吉普车的时候,小毫竟然不见了! 张葛一下就傻了。 救援车在森林里搜寻了一夜,在次日天快黑的时候,终于在一个雪窝里把小毫找见了。 小毫缩成小小的一团,张葛怎么叫她,她都没有回应。 医生检查了一下,说:“她死了。” 张葛含着眼泪蹲下身,果然发现她的心跳和呼吸都已经停止了,她的身子跟雪一样冰冷。她已经50多个小时没有吃任何食物了。 张葛抱着她,欲哭无泪。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