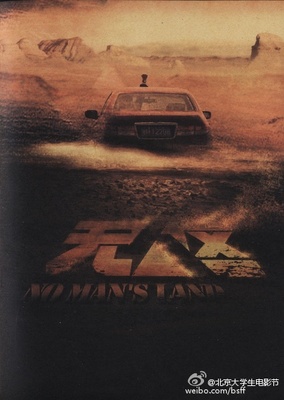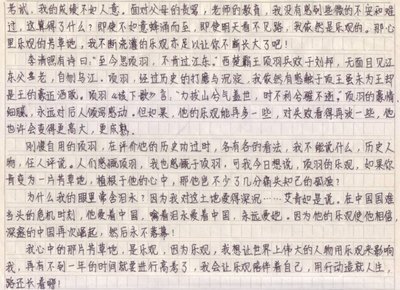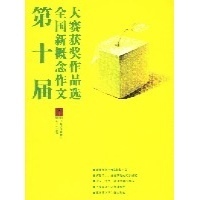研究生组优秀奖:
池艳萍:《视点的疏离,从“悬念”到“惊讶”——论电影<万箭穿心>对传统情节剧叙事继承上的异变》
视点的疏离,从“悬念”到“惊讶”
——论电影《万箭穿心》对传统情节剧叙事继承上的异变
池艳萍
电影《万箭穿心》根据湖北作家方方同名小说改编,通过讲述李宝莉一家人的十年光景,塑造出坚强又泼辣的女主人公李宝莉这一人物形象,在2012年众多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许多关注。导演王竞说:“我们想让观众思考你觉得这个牺牲是神圣的吗?李宝莉的悲剧有没有她自己的原因?”在此构思下,电影在情节安排,人物关系和结局上都做了调整。一方面是为将小说中的文字表达转化成影像表达,且要适应电影时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导演自己对故事的思考。这不是一个照搬照抄小说的电影,导演利用小说的故事来向观众发出他的疑问。
传统情节剧一般强调一次情绪的完整释放,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再次确定,但这不是影片《万箭穿心》想要做的方向。《万箭穿心》取材一般中国观众再熟悉不过的家庭问题情节剧,在叙事结构上延续了传统情节剧的基本元素,不论是在早期的中国电影还是当下盛行的电视剧中家庭问题情节剧都屡见不鲜。《万箭穿心》以不同的叙事视点,对主人公做了更深层次,不同角度的挖掘,新瓶装旧酒,使观众产生了不一样的观感体验并引发出了对李宝莉这个人物的思考,这也正是导演构思的实现和影片的成功之处。
现实主义情节剧,一种传统的延续
情节剧是一种中外皆有的电影类型,它从戏剧发展而来。西方学者将情节剧称作“一种大众化浪漫形式用以表现道德人物在压抑的社会情形中的斗争内容”。本文谈的传统情节剧指中国传统情节剧,中国传统情节剧一方面有一般情节剧的基本特点,即它在叙事上包含大量戏剧化情节,强调激发观众情绪,有一定的娱乐性,叙事上吸收了许多好莱坞经典叙事法则。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在取材上偏爱家庭题材,思想上充分继承了中国自古以来“文以载道的要求”,情节上重视因果联系,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做基础。《万箭穿心》中李宝莉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心态也反映了这种传统道德观,这是李宝莉作为一个生活在90年代的中国女人的合情合理的表现。1923年《孤儿救祖记》的出现奠定了中国传统情节剧的叙事路径,在近一百年的光景里,从擅长拍家庭伦理情节剧的张石川主张“营业上加一点良心”到蔡楚生情节剧里的社会问题再到谢晋的政治伦理情节剧,中国的情节剧影片一直都有紧贴社会环境紧贴现实的传统。《孤儿救祖记》以一个充满巧合纠葛的三代人之间的家庭误会故事来批判了封建遗产制。《万家灯火》有对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财富悬殊巨大的直接描绘,都有对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的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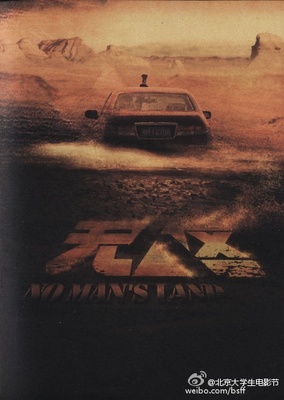
《万箭穿心》以武汉做故事背景,从90年代的工厂改制讲到20世纪初经济全面发展,人物与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并受到时代的左右,正如观众清楚的知道《孤儿救祖记》里的清末民初和《万家灯火》里的抗战结束环境信息,特定的时代也会给予剧中人特定的身份。《万家灯火》里的胡自清面对堕落腐败的国民党官员不肯同流合污但又使全家捉襟见肘。而90年代选择离婚依然是个相当招人非议的行为,马学武的偷情被捉放到今天社会环境下也不见得还有影片中对人物的压力,而他正好又是在经济改革中的浪潮中。马学武原是工厂中的小领导,是个知识分子,与李宝莉在社会阶级上有差别。马学武和周芬在一起是和谐的,而李宝莉和建建在一块也是很自然的,这与他们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这种身份阶级上的差异在传统情节剧中不难发现痕迹,特别是这种知识分子丈夫与没文化的妻子的人物身份设定,从杜十娘和李甲到张忠良和素芬数不胜数。《万箭穿心》中这种身份差异还表现在空间上,李宝莉在汉正街上是随意且自由的,而在她自家新房中被框定在有限范围内的,我们甚至没有透过李宝莉的视点看到过整个房间内的全貌,她在这个家里一直有她不能去的“禁区”,她和她所在环境隔阂。影片如传统情节剧一样,严守线性时间,除了后半段小宝视点下的闪回,情节按因果联系紧密相连,有很戏剧化的情节,如小宝在高考前一天冒着大雨赶到建建处找李宝莉的戏,但以较克制的情绪结束。《万箭穿心》继承了传统情节剧的基本叙事元素,导演且以与传统情节剧不同的视角进行叙事。
视点的疏离
男人移情别恋背叛了他的家庭和他的妻子,他消失或死亡,他的女人含辛茹苦十年撑起家庭,养大了男人的孩子,赡养了男人的母亲,最终却被扫地出门。《万箭穿心》线性时间上的线索并不等同于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故事。移情别恋而后消失的男人,忍辱负重自我牺牲的女人,从《秦香莲》到《一江春水向东流》里,这种人物关系并不新鲜,然而因为叙事的视点不同,我们对电影人物投射的情感也不相同,对故事的理解也大相径庭。波德维尔说:“在任何情况下,观众体会剧情、产生期待或组织情节内容时,都受到叙述者说什么和不说什么的限制”。这里提到的故事叙述者并不等于视点,但是当观众透过镜头观看银幕上的故事时,已经不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行为。导演正是从分利用视点在电影中的功用,来讲自己的故事。
戈德罗在热奈特的聚焦法上对电影视点从认知和观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他将观看分为内视觉聚焦和零视觉聚焦,前者即我们通常称为人称视点且可以进一步再分为原生内视觉聚焦和次生内视觉聚焦,后者指代所谓上帝视点。观众被设定在“眼睛-摄影机”的假象轴上以不同方式观看获得的认知,信息获取的角度与量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其情绪的积压与释放,以及观众如何去把握故事整体。
传统情节剧中通常观众获得一次完整的情绪释放的方法是通过对故事悬念的形成到释放,观众此时以上帝视角观看,他知道的比影片中人物知道更多的信息,他在心理形成一杆好与坏的标尺,“他”会极度厌恶片中的反面角色,对故事中的“正面角色”抱有同情,在因果轮回报应不爽的铁律下,事实被揭露出来,或以悲剧或大团圆的封闭式结局。《一江春水向东流》里观众知道素芬正在打工的东家正是她不见了的丈夫,而人物自己不知道,观众在等待这一事实的揭露的过程中对人物的喜恶确定下来。所以在传统情节剧中视点与观众的关系的极为亲密的,它满足观众一些想知的信息。观众被置于导演安排下能够全知全能的零视觉聚焦(上帝视角),在确定人物关系和价值取向后,等待情绪的积累与释放。上帝视角引发观众内心的悬念,当结局最终在传统伦理道德认可的方式下出现后,他之前的焦虑情绪在妥善安置中释放出来。《一江春水向东流》里观众掌握了导演精心安排下的“一切”,张忠良是可恶的,素芬是可怜的,当素芬以女佣身份出现在张忠良家里时,观众等待着这颗炸弹的爆炸,张忠良的花天酒地,素芬在他人屋檐下讨生活的场景都催化了观众的情绪,当素芬跳江自杀,观众的情绪在零视觉聚焦的带领下获得宣泄。
《万箭穿心》中导演则采用内视觉聚焦(第一人称视点),极大部分镜头我们都是跟随李宝莉的视点去观看影片。这里虽然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视点但却不是以镜头来取代李宝莉,而是采用的是次生内视觉聚焦。戈德罗认为“它的定义依据是画面的主观性被衔接、被语境化所构成这一事实。与银幕上出现的一个目光相衔接的任何画面都属于此类,只要某些‘句法的’规则得到遵守,就像正反打镜头”所以我们看见的不仅是李宝莉所看见的,我们还看见了“李宝莉”本身,这对观众认知李宝莉极为重要。导演王竞说:“所有镜头都是相对“被动”的、跟着李宝莉的举止和动作,她往那儿看了,镜头才甩过去;李宝莉拿东西了,镜头才跟过去,从来没有一次镜头会跑到李宝莉前面去。”通过镜头的的“跟”,观众在看片中受到的是一次次“惊吓”而不是“悬念”。当我们看到李宝莉女儿身却比男人还蛮劲十足时,我们被她惊吓到,当粗线条如李宝莉这样的女人却想出报警捉赃,我们再次被她惊吓到,当李宝莉在丈夫死后决定去当扁担还,硬是十年如一日,我们还是忍不住要吃一惊,而当李宝莉自行选择离开时这个女人带给我们的除了惊吓还引发了我们对这个人物的思考。次生内视觉聚焦限制观众的信息获取,以这种方式疏离观众,打断我们的惯性思维,包括我们的惯性期待。在李宝莉捉奸的这场戏里,镜头紧跟着李宝莉,观众不知道马学武和周芬在谈论些什么,也不知道宾馆房间内的马周二人具体在做什么,透过李宝莉的听觉才获知房间内两人的行为。观众获取的故事信息虽然相对被限制住,但对李宝莉的人物形象了解却更客观,因为镜头向一台监控器一样一直跟着她,客观的看着她,观众对她的认知也更全面客观。而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导演分别给了很多场戏来表现张忠良的奢靡生活和素芬的贫困生活,强化双方间的对立矛盾,所以我们也不会去思考素芬是否也有放荡不羁的某一面存在,我们知道就是导演反复强调的,即她是个好女人。
影片中马学武自杀后,对李宝莉报警捉奸行为何时会被揭露出来的悬念也因为内视觉聚焦的视点淡化,情节后半部分的线索围绕李宝莉的扁担生涯,一度使观众遗忘之前保留的那个悬念,只通过李宝莉的只言片语得知她与儿子大宝关系的疏远,而我们到最后影片也不知道马学武母亲是否知道是当年是李宝莉报的警。因此当大宝毅然决然要求李宝莉净身出户时的惊讶大于悬念,对十年艰难的扁担生涯也换不回儿子对自己错误的理解的惊讶。内视觉聚焦对被拍摄的主体的多方面展现,带有记录性,导演选择这样也是要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对李宝莉这个不断让我们“惊讶”的人物的思考上,同时也为观众从更多角度解读李宝莉提供可能性,这种“惊讶”在翻新我们对人物已经获得的信息,每一次的“惊讶”都让我们从不同角度去认知李宝莉-妻子,母亲和女人。
“他”的困境
在疏离视点下,影片展现了李宝莉的多个身份,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以及作为一个女人。萨特说:“他人即地狱”,他人的自由选择会危险到我们自身,甚至会逼迫我们做出本不希望的选择。马学武选择去偷情使怒上心头的李宝莉选择去报警,马学武的自杀又逼迫李宝莉选择自己一人去撑住整个家庭。而在此之前,李宝莉选择对待马学武的方法,也让马学武活在了地狱。这里的李宝莉并不作为“她”,她也只是别人眼中的一个“他”。影片中的这个地狱里很难有明确划分出对与错、善与恶,伦理道德的标准在这里是暧昧的。这点上与我们看到的传统情节剧有根本变化,传统情节剧强化伦理道德的标准,观众的问题都能在这个标准下找到准确答案,主要体现在传统情节剧绝大部分都是闭合式的结局,人物的命运最后都会被给予了一个确定的位置。《万箭穿心》中多次提到的房屋风水问题,也是用来淡化是与非,黑与白的绝对性,更加反映人物对自身命运的不可操纵,始终处在“他人”的选择中。与原著小说侧重李宝莉和儿子大宝这条线索不同,导演消减了儿子的戏份,李宝莉与丈夫和与儿子的两部分正好平均的划分了全片时长,导演并不想在影片中塑造一个明显的反面人物去限制观众的判断,他要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复杂性。
影片表现作为女人的李宝莉这一点在家庭题材的情节剧中也不同,传统情节剧表现的要么是女主人公水性杨花的性格,而母亲的情欲在传统情节剧则表现的较晦涩或回避。导演王竞说:“原著小说的价值观其实和电影很不一样,小说描写李宝莉偏向英雄主义”李宝莉家中阴盛阳衰,男女性别颠倒,李宝莉在电影后半段更是一个做男人工作的女人,导演并不想塑造一个道德理想化的人物,他要时刻提醒观众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弱化她的英雄色彩,让李宝莉不是一个“特别”的人,而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表现出这个女人本该有的情欲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电影以一场不协调的情欲戏开场,一段未知的情欲故事结尾,“他”的困境始终无法根本解决,只能选择与其共存。对于无法言对错,只能谈包容的家庭生活,伦理道德本不是教条,在自我价值与家庭牺牲中,观众对李宝莉的思考也是对自身生活的反思。
常言道:“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一个相同的故事却可以通过不同的叙事方法中能带给我们不同的体验与思考,《万箭穿心》的叙事手法为家庭题材情节剧这一古老又传统的类型影片重焕生机获得发展提供了的更多可能性。
参考书目
1. 大卫·波德维尔,《电影艺术》【M】兴国图书出版社公司
2. 安德烈·戈德罗,《什么是电影叙事学》【M】商务印书馆
3.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对话王竞:关注社会现实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