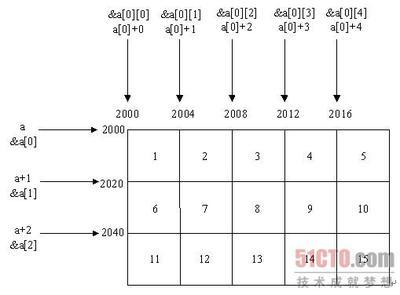http://hi.baidu.com/ɽ�����/blog/item/e0007b08cf1623376b60fbce.html
山上悟空的空间
本空间以探讨哲理、民生和易医为主,欢迎探访和分享。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和夫人许鹿希的人生故事
2011-02-13 21:18
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近日正在央视1台热播中,它首次详细反映了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科学家研制两弹一星的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剧中有不少场面介绍了邓稼先和夫人许鹿希的感人事迹,特令人受教育。但电视剧不竟是经过艺术加工提炼的,现实中他们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现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许鹿希的访问录,从另一侧面看看银屏外的邓稼先和夫人许鹿希的真实人生…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和夫人许鹿希的人生故事 记者:倪既新
我从未遭遇过如此冷峻拒绝的采访对象 我同许鹿希相识,缘于1992年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之时。 杨振宁有个与之有着半个多世纪友谊的朋友邓稼先。邓稼先是中国的两弹元勋,当时已不在世,我要表现杨振宁与他从中学时代开始的亲如兄弟的情谊,收集和拍摄具体独到的素材,就必须要找许鹿希了。 1992年4月初,我去北京为拍摄踩点。为了和许鹿希取得联系,我一边采访其他对象,一边从早到晚往她家和医科大学办公室轮番打电话。那时候,在北京打电话还很不方便,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找电话机。但是连续两天始终没有人接听,直到第三天一早,我从北京西绒线胡同的招待所出门前再试,才听到话筒里传来她平静的声音。原来之前她出差去了,这时刚回到家里。我立刻十分激动地说明自己的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冷淡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听她的语气,要马上挂断电话了,我就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我们的诚意,而且已经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 怕好不容易接上的联系又“掉线”,我越说越详细越急迫,但是,我说了半个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我只好硬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的韧性坚持,最后,她沉默了一下,答应我第二天上门去见一面,不过规定在中午11点半,就是她午餐前的时间。“我12点吃午饭,这之前你必须走!”她语气干脆地说,接着又补充一句:“你得带介绍信来。” 在采访中遭遇这样冷峻的拒绝,在我还是第一次。但正因为这样,使我要探个究竟的好奇心反而更强烈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才知道了意外的背景 第二天一早,在去许鹿希家之前,我先顺道访问了也在西绒线胡同的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三十一中学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校友会的一位老教师接待了我。听到我就要去采访许鹿希,她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光是出了个纪念性的小册子,就为他们家找了很多麻烦: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知能挣多少大钱,也不会这么早死了!”三十一中在校内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不料十几岁的娃娃们也疑问不少,说:“像他这样值吗?”老师们痛心疾首,大声问:“都是这样的价值观,今后国家发展靠什么?”显然,许鹿希对采访的冷淡态度与这背景是大有关系的。 许鹿希的家在北太平庄的一个大院落里,很普通的平顶式住宅楼。进了门只见里面水泥地,白灰墙,裸露的管道和电线,像是没有经过什么装修一样,更没看到有成套像样的体面家具和摆设。 许鹿希把我引进一间显然是待客的房间,那里除了两个布沙发,两把钢管椅,一个写字台,一个小书橱之外,最醒目的就是一幅直接贴在墙上的毛笔字:“两弹元勋邓稼先”,那是张爱萍的手迹。下边有一张装在小镜框里的邓稼先半侧遗像,斜靠在书橱顶上。 相比之下,倒是许鹿希的外表更出乎我的意外:如果不是她在开门的时候说“我就是许鹿希”,我就不会直接认她,因为她那件驼灰色的对襟外衣,那头随意梳拢的齐耳直发,那个肤色黝黑的面容,看去绝对像个劳动妇女,与我头脑里预先勾勒的“元勋夫人、名门之后、大学教授”的形象相去实在太远了。
好在,面对面时的许鹿希,比昨天电话里温和亲切多了;一坐下来交谈,感受到她内在的思想情感,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体会了。果然,一说邓稼先和杨振宁的友谊,她立刻变得言辞委婉语意绵长,成了性情中人,再也没提昨天给我的时间限制,以至我起身告辞时,已过了下午一点半,而她则完全忘记了吃午饭。 许鹿希向我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邓以蛰、杨武之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同住清华西院宿舍,9号、11号更是紧近邻居。邓教美术史,杨教数学,性格很合得来。邓稼先的妈妈和杨老太太都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关系也很好,所以两家是世交。 邓稼先出生于1924年,比杨振宁小两岁。他们两人生性都很顽皮,兴趣也一致,两人都曾在西南联大读书,但因为中学时杨振宁跳了一级,大学里要比邓稼先高三级,就更是一个大哥哥了,所以邓稼先对杨振宁很亲密。 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费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很近的普渡大学,这样他们来往就很方便。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当即回国了,那时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之后两人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是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许鹿希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邓稼先?杨振宁说,中央情报局是不可能去编一个名字恰好与邓稼先同音的。”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到上海之后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说到这里,许鹿希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轻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惨,那些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很多人遭了殃。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有个很有贡献的炸弹专家钱晋,他们拷打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年轻的一批搞光后就轮到高层的了。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侥幸得救。 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其实,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这样的巧合真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简直太绝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虽然最初知道拒绝采访,然而一开口谈这个话题,她就一泻难止了。这让我怦然心动。 谈论原子弹,邓杨两人是那么神秘地心照不宣 许鹿希以轻松的语调说了件轶事:最初见面,杨振宁问邓稼先在什么地方工作,邓稼先说“在北京之外”,“什么单位呢?”“京外。”杨振宁不明究竟,后来到上海就问弟弟杨振汉“京外是什么单位”,杨振汉听了大笑说,“哪有这个单位啊!” 许鹿希说:“实际上,那之前杨振宁早已知道稼先是搞原子弹的了。后来两人见面什么都谈,杨振宁就是不再问稼先有关单位的事情了。”直到最后,在离开北京去上海回美国的飞机舷梯旁,杨振宁突然问送行的邓稼先:据说中国搞原子弹有美国人参加?邓稼先为难地推说:快上飞机吧,我以后告诉你。因为邓稼先肯定和否定都不行:肯定吧,不是事实;否定吧,那就证明他自己也在搞,所以知道。 “其实杨振宁是在测试稼先,”许鹿希笑着解释。事后邓稼先马上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要尽快答复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没有外国人参加。邓稼先连夜写了封信,交专人送到上海。这时上海市革委会的头头们正在为杨振宁返美饯行,送信的人在宴席上把信交给杨振宁,杨振宁打开一看,知道是中国人自己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搞成功了这样的大事业,顿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为了不至失态,他马上起身到洗手间去了。 对于这件事,在后来的拍摄中,我专门询问过杨振宁,他的回答也是这样的。 许鹿希说,那以后,杨振宁每次来中国,当邓稼先和他在一起时,总是杨振宁口若悬河地讲,邓稼先在一边静静地听。因为杨振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进展,什么都是公开的;而邓稼先恰好相反,什么都是保密的,他不得不谨慎开口,生怕泄漏任何一点“天机”。所以,往往是邓稼先简单提问,杨振宁滔滔回答。 邓稼先留下了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 许鹿希非常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有好几个他们相识的人,相同的病,动手术后又活了二三十年。但是邓稼先因为长期从事这工作,骨髓里就有了放射线,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背上的出血瘢有面盆那么大,嘴里全是血,耳朵里也是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 许鹿希特别给我解释说:中国的核试验,外面知道都是成功的,其实有好几次失败,而且事故很严重。那种时候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如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这是一次后果严重得难以预测的事故,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线侵害。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决定性的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的习惯,在上吉普车前返回时,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之后,邓稼先怕许鹿希担心,从没给她看过这张照片。现在这张,是她在赵副部长那里见到之后自己翻拍的。 许鹿希说:“外国情报说中国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而我们自己则说进行了46次,那多出的一次,就是指降落伞没有打开的这一次。后来核弹照原样重做一个,降落伞打开了,也就成功了。”
她说只有中央军委下命令她才接受拍摄采访 两个月后,我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 那天夜里,我给许鹿希打电话落实第二天的拍摄内容和要求,我说除了拍信件和照片,最主要的是要请她讲一段话,说说杨振宁与邓稼先青少年时代的友谊,和杨振宁回国时要求见邓稼先而无意中救了他的事情。想不到许鹿希又断然拒绝了:“这绝对不行!”并严肃质问:“你上次怎么没说要拍我?”意思是如果我上次提出来,她早就回绝了。 她说:“在杨振宁的片子里决不能出现许鹿希!不论你怎么说,我都拒绝!即使杨振宁来动员,我也坚持自己的意见,相信他是会尊重我的。我坚决不拍,因为我不是搞原子弹的!”她又说:“照片不能出我的家门,你们只能在我家里把它拍完。” 第二天我们去许鹿希家,见了面,她却又是那样温和与善解人意。她已准备好了七张照片和两份信函的复制件,不但给我们开电风扇纳凉,还端上了冰镇西瓜。指着一张他们夫妇在医院里与杨振宁的合影,她深情地说,这是邓稼先最后一张照片,当时他正在大出血,嘴角上还有擦不净的血痕。这张照片对她是最宝贵的纪念,她绝对不让它离开自己一步。 我见她这么平和,就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绝情”地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 没有办法,我们只得作罢。等大家坐下来休息时,许鹿希又谈笑风生了,还为她昨天和刚才的坚决拒绝道歉。她表白说:“希望你们理解我们这样一拨人,因为如果为了多赚钱,为了有好的房子、好的家具,那邓稼先肯定不会回国的。我自己也两次去美国,前不久又去了日本,我完全可以留在那里,那里的工资是国内的一百倍……所以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说我们不但能够理解,而且更看重她这样的风骨和人格。 邓稼先应该正确地被表达 许鹿希语调沉重地感叹:“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应该被很正确地表达的。但有些人的方式我认为很不妥当,对不理解的人我很害怕。譬如人家要把邓稼先搞原子弹的事拍成他与我许鹿希的爱情故事,就有人这样点过题。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是怎么谈的恋爱?我只回答是世交。我不愿理睬这些专门搞花絮的俗气的人,所以我坚决不答应拍。稼先是个很庄严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被歪曲成儿女私情。我现在开放一点了,是为了给可信赖的人留点真实的东西。” 许鹿希说,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说着说着她就和他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前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她回答说:“你一定要这样写,那你就去写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且你不能用邓稼先的名字。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
许鹿希说:“有的人会求之不得,会巴结上去。你们能理解吗?能理解我的个性吗?我认为要纪念未必要用这种形式,因为另外的人也很棒,不一定要以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 回程路上,我一想到她几次三番地说“希望你们理解”,心中不禁有些悲哀:他们平时竟然就这么不被人理解?以至她总是担心我们也理解不了他们…… 在杰出科学家的颁奖会上,她用邓稼先的照片遮着自己的脸 后来,1995年秋的一天,我在谈家桢家的书桌上见到几本“求是科技基金会”的年度纪念册,其中1994年和1995年两册的几张照片中,获奖科学家的行列里都有许鹿希,但是她的形象很特别,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都举着一个装有邓稼先侧面照片的小镜框,严实地遮着自己的脸。虽然匆匆浏览,但还是给了我深深的触动。 许鹿希出席的是求是科技基金“杰出科学家”的颁奖仪式。这个奖是由香港查济民家族出资设立的,规定只颁给在世的有贡献的科学家。但是1994年那一届,十个大奖得主中却有邓稼先这位已去世(1986年)的,评委们一致认为,在中国的核科学中,论功劳贡献,不颁给邓稼先很不合理,所以尽管他已去世,也要给他这个荣誉。许鹿希是代邓稼先去领奖的。 后来香港求是基金会也给我寄来了整套的纪念册。再细看其中许鹿希举着邓稼先的头像遮住自己面孔的照片,我仍然为之感动。我当即给许鹿希打了个问候致意的电话。在话筒的那一端,她显然有些动情: “那天我举照片得罪了好多记者。他们非要我把照片放下来,说应当正面的显示自己。我没有照办,所以有好多记者不高兴,拉我,要我放下来……宴会上,杨振宁和夫人坐在主桌,他们特意来找我,找了好久才见到我,说你怎么坐在这里?意思是太边上了吧。他们夫妻俩同敬了我一杯酒,杨振宁说非常理解我当时的心情,他们的酒不是光敬我一人的。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他们也是希望,这时候邓稼先如果自己能来……” 两弹一星表彰大会上扑伏在椅背上抽泣的人就是她 1999年9月18日,北京召开两弹一星功臣表彰大会。在中央电视台所作的实况转播中,会场里始终洋溢着昂奋、激动人心的气氛。但是突然间,一个插入的镜头,使我看到台下的座席里,有一位老年妇女,突然扑伏在前排椅背上抽泣起来。当时我心里马上有一个反应:这会不会是许鹿希? 事后,我打电话到北医大解剖学系找许鹿希,她的学生挡驾说,老师不接受任何采访。我再三说明来历,他就要我报出名字,十分钟后再打去。再去电话,他说老师愿意与我交谈,告知了另外一个号码并提醒我,许鹿希最近心情很不好。 在电话里我首先提到上面这个猜测,许鹿希回答说:“那是我。” 许鹿希沉默了一会,似乎是在平静情绪。她说她也不知道是哪位摄像师拍下的:“当时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周围。事后非常后悔,我应当背过脸去,人家都高兴,我怎么哭起来了呢?同这个场合不合拍的,挺抱歉……” 她再三问我“这印象不好吧?”那胆小纯真恰如一个孩子。我说,这有什么不好,你的心情大家都能理解的,而且看了很感动。她这才说,“邓稼先那工作是一个人用一生去做也值得的,别人都这样鼓励我。有个美国朋友打来电话安慰我说:‘请你一定坚强地把自己维护好,好好过日子,邓稼先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老哭。’我听了很感动。许多老同志也打来电话,没有一个责备我的。当时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这虽然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但到今天我还感到抱歉,应该是高兴的呀!” 我们在电话中足足谈了两个小时,我问了她好几个问题,她都详尽地回答了。 她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有人问我:当时你是不是高兴得跳起来了?我回答“不是的。”因为平时家里人的心都提在嗓子眼上,这时只是松了一口气,心放入肚子里去罢了。这28年,对稼先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对家属也是非常残酷的损伤,这点旁人是无法体会的。在外国,搞核武器的科学家是轮换的,而我们中国是同一批人搞到底,从原子弹到氢弹到中子弹。作为家属就这么长期的提心吊胆着,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狂喜。这次发奖只是感觉到,他如果还在世那多好!在世的人非常高兴,非常快乐,唯独我这样的家属心情不一样。所以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像别人一样狂喜过。 我知道,当邓稼先领受任务神秘“消失”的那一年,许鹿希才30岁,而家里既有双方的老人,还有两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许鹿希是许德珩的女儿 当年正好是她母亲诞生一百周年,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她的父母。她说,父母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回忆到这些事,我心里就难过。许多人认为我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家的小姐,生活一定非常优越,其实正好相反。我父亲年轻时主张抗日,所以被捕了,经过宋庆龄、杨杏佛营救才出狱。五四运动时他是北大学生会主席,也被捕过;后来又被北大解聘教授,到别处去教书,为之家里生活很困苦。我是家中长女,弟弟小我一岁,所以许多事情得我做。当时我们一家的经历,不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以理解的。许德珩虽然没有像领袖那样去打仗,但是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不受欺负做了很多工作。所以他后来会那么支持邓稼先搞原子弹。 许鹿希还说,按北方一般的习俗,是常要叫女婿到家来干活、向老人问寒问暖的,而邓稼先非但做不到这一切,还去向不明,还要家人成天为他提心吊胆。之前,我父亲尽管不知女婿在搞原子弹,但知道是搞国防武器,在做保密工程,他又不能问,唯有把好烟好酒留给稼先…… 我又提到当年在北京三十一中学听到的介绍,许鹿希说,那老师说的情况确实有的:很多人不理解,说自己如有邓稼先这本事,早去换钱了。1971年杨振宁回国时,许鹿希家里还没有电视机,就有不少人问:你为什么不去向杨振宁要一个? 说稼先是傻瓜的人确实很多,不光当时,到现在还有。我家两个孩子早已习惯,由人去说。他们觉得父亲是了不起的,有这么大的学问,要不是做这事,吃了放射线,可以多活好多年。因为稼先的父亲20岁得了结核病后来还活到了81岁,母亲活到70岁。稼先却只活了62岁…… “我们的孩子是新一代,他们也考虑人生有个值不值得的问题。现在在美国的女儿,不满15岁就插队去了内蒙古,说到当时边界上集结了前苏联的百万军队,她立刻就理解爸爸了,认为爸爸的一生很值得,那个事业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机会去贡献的,他使国家有了脊梁骨……”说到这里,话筒那边传来许鹿希轻轻的欣慰的笑声……
摘自《档案春秋》2009年第7期 |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