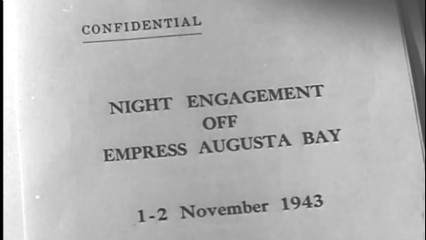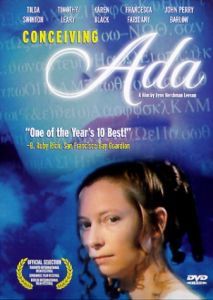坦诚地说,我并不太喜欢克里姆特的油画作品,里面的东方元素:图案与花纹,外在了些,而且,它们阻隔了画面整体气韵的贯通,背景与人的关系处于高度的对比之中,尽管画家也尽力将人物造型纳入其装饰性框架中,消解体积与空间,融合写实与合理的夸张,但复杂的构想有时不一定抵得上单纯,过多的细节已经消弱了作品整体的力量。克里姆特诠释生命主题的手法并不能不算明确,但笔触和色彩却有可能被过于主题化的内容遮蔽,而绘画之美在语言本体丧失的情形下已经是南辕北辙了。
我非常喜欢克里姆特的速写,流畅中有滞涩,轻盈而不薄气,形的趣味,线的趣味在他的大多数“正而八经”的作品中反而看不到了。克氏速写之造型有一种内敛和简洁的品质,他用复线和看似多余的线条来建构形体,衣褶上的图案在速写中是随意而生动的,一旦落实到布面油画,完全被固化和精致化,先前“写”的痛快淋漓没有了,这和我们平时的某些创作草稿和“正式”创作有类似的关系对比。克里姆特描画生命盛衰的主题作品,意象繁多驳杂,暗喻着各种心理的、精神的和生命的变化。速写没有承担这样繁重的主题,因而轻盈灵透。速写用线条——最简洁、抽象的语言使人看到了思想和情绪的畅快、自由和洒脱。速写草稿中的生命冲动不顾一切地奔涌而出(这里面深埋着一个艺术本质的问题——见性情去雕饰),看似随意自由,实则法度谨严,鲜活饱满。最重要的是,速写时画家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创作什么,以忘技巧、去心智而达自然放松的境界。在此,功利远去了,目的被溶入自由之中。
如果说歌颂人间情感(母女、情侣)或性爱是克里姆特作品产生观看兴趣的“刺激物”,我倒认为那是一种误解。当然,对于普通观者和专业人士,兴趣不可能一样。克里姆特在他的前辈达芬奇、伦勃朗、安格尔等人对形态的解悟基础上,又显出构图和动作上有意为之的“形式意味”,线条的独立价值更为凸显,线之自由组织,增加了主观色彩,线条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力度也随之加强。达芬奇、安格尔速写中的线条多是顺向展开、客观表达,我们赏析的是理性的缜密和严谨;克里姆特速写充满情绪的宣泄,我们欣赏的是感觉的敏锐和意趣的勃发。克氏速写外轮廓求整,内部线条强化冲突和对比,比如折笔和断线,因此丰富而不琐碎,整体而不空洞。克里姆特速写的缠结比他的独幅油画更具有原始的力量。在观看的一瞬间,我不是被他画的形体和动态吸引,而是被线条的不断冲突与协调往复间的张力所迷醉——他唤醒了我对速写作为艺术的知觉和兴趣。复线产生的错觉可能是最能延长审美观看时间的,同时它使对象变得更值得玩味和更“复杂”。在局部认识的缓慢性和在整体意象认识的瞬间性之间,我们得到了审美意韵的最大化享受。他的笔触在纸上划过,时快时慢,不舍不分,敏感而轻快,唤起种种情感和思绪的畅游。速度带给我的感受同样敏感而轻快。是的,速度决定我们感知和体验到的内容和形式。笔端形象既浑然整体,又支离破碎,那些不确定、不完整定然产生了多义性,我读解的“自由”也定然在里面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不雕不琢的语言通常更能轻松且深刻地负载文化奥义。线条是最灵活、最丰富的语言形态之一。线条固有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使它所指称的物的具体形态附加为“文”化。我想,融入主观意识的艺术作品其主旨在于通过个人能力发掘对象深层的精神特质,克里姆特做到了这些。其速写有一种缠解的冲突感和整体体式的夸张性,很多线条算不上简洁,相反倒有点“罗嗦”,恰恰是那些看似不符合常规的线条构成了对僵化、平庸形式的疏离与超越,摆脱了对人物的机械模拟,复线——这种新的语言关系建构起速写的厚度和韵味——这两者,也正是无论中国或西方的画家都孜孜以求的。文艺复兴的线性传统就存在于克里姆特速写所确立的意义之中,巴洛克时期的涂绘风格也影响到了他的速写。克里姆特利用了线条间或线条本身的歧义,利用人们的误解、误读,我把这种因人们的误读而可能生成的语义称为“误义”或“随机义”,是将解读权部分交给阅读者,让语言“自语”。中国画中的复勾或补笔就有同样的功用和效果,从倪瓒、傅抱石、黄胄那里我们看到了这种方法的魅力。
在速写世界里,我钟情好几个画家。罗丹的速写结构随情感流转,颇似中国画的狂草,太过流畅和飘逸,像风一样飘过,稍纵即逝,里面没有冲突,一切都那么顺畅。克里姆特的速写情感随结构进行,有点像中国书法中的行书,线条的形态丰富到了极致。席勒也是我喜欢的一个画家,他是克里姆特的学生。席勒速写的知名度远远大于乃师,但我更喜欢克里姆特的。席勒与乃师比较,太过夸张,克里姆特不用夸张就可打动读者。席勒用速写的方式画油画,用油画的方式处理速写,强烈得近乎神经质,尽管他早期的造型能力也颇了得,但就速写而言,他直接跨越到极度夸张的境地,其实用线条驾驭形体的能力是逊色于他的老师的。席勒的速写常常一笔勾出,方笔与圆笔要么对比太强,缺少过渡,要么细节过于具体,用笔也没有乃师的轻盈。克里姆特似乎更关注外轮廓的造型意味,而对细节则减少或作抽象化处理。席勒速写缺少复线形成的意味感,有些作品形体夸张,线条流畅得近乎油滑,既已失去乃师的朴实,便距离艺术之厚味越来越远了。就像以符号化处理“大创作”画面一样,克里姆特也是将速写人物做符号化的处理。尽管席勒有意识夸张人物形态的张力,但他面对和描画出的更是一个真实的个体。人物的表情形态遮蔽了对语言本身的欣赏。无论中西,高明的画家谙熟如何以混沌求丰富,以虚无求实有的道理。画面中说的特清楚的常常是技术部分,只是状物,说不清的那一部分就是艺术了。就像作诗,句子的韵律,绝对不是在于只由铿锵的字眼之连续所形成的外表,但它却是依着那被一种微妙的交互关系所含着的思绪之曲线波动的。克里姆特的速写有体块的厚度与持重,也有线条的流畅与飘动。其丰富性可比肩任何一位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的速写作品。克氏速写没有调子的铺陈,代之的是对结构和平面感的趣味,这与西方绘画的发展是同步的。自印象派以来出现的结构主义、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等类型都有平面化的共同特征。而这种变化恰恰受东方绘画观念和形式的影响。
克里姆特速写中的断笔,与中国画的笔断意连既相似,又不尽相同。中国画不是在交错或并置中进行,断则断矣,用“意”去联结。克里姆特利用了线之虚实和方向的变化,似断而非断。但两者都着眼于线自身的趣味以及由此生出的风格。这种变通,成就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丰富世界。线条一派生机,在挥洒中出现一些滞碍和重复,其韵自此生矣。就像诗歌中词语的错位所产生的张力与美感,令人回味。中国画论中尝言:“有画法而无画理非也,有画理而无画趣亦非也。画无定法,物有常理,物理有常,而其动静变化机趣无方,出之于笔,乃臻神妙。”克里姆特速写在动作和线条的组织上出现了动静变化、机趣无方的鲜活性,互存互补,相生相克。又,《淮南子》云“画者谨毛而失貌”,这是对只见局部而忽视全局的作法的批评。克里姆特的速写整体大于局部,即使有局部的细节刻画,但非面面俱到,可谓略其形而得其神。张彦远下面这段话同样拉近了中国画家和西方画家的距离:“夫画物特忌形貌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以中国画家的视角来看,神、意、言、象,这四点在克里姆特速写中都得到了完美统一。
与其说我迷恋克里姆特的速写,不如说我被线条的韵致和趣味感动。顺便一提,并非克里姆特的所有“正式作品”都被他夯实了。比如1917年创作的《孩子》就颇得速写之韵致,充分利用了底色,有“无画处皆成妙境”之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