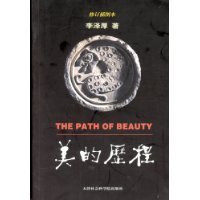悼朱光潜先生
朱光潜先生逝世了,我应该写点什么,却不知道写什么才好。凌晨四点钟,我坐在屋里发呆,四周是那样的寂静。我和朱先生是所谓“论敌”,五十年代激烈地相互批评过,直到朱先生暮年,我也不同意他的美学观点。这大概好些人知道。但是,我和朱先生两个人一块喝酒,朱先生私下称赞过我的文章……这些却不一定有许多人知道。那我就从这写起?
我那第一篇美学文章是在当时批朱先生的高潮中写成的。印出油印稿后,我寄了一份给贺麟先生看。贺先生认为不错,便转给了朱先生。朱回信给贺说,他认为这是批评他文章中最好的一篇。贺把这信给我看了。当时我二十几岁,虽已发了几篇文章,但毕竟是言辞凶厉而知识浅薄的“毛孩子”。这篇文章的口气调门便也不低,被批评者却如此豁达大度,这相当触动了我,虽未对人常说,却至今记得。贺先生也许早淡忘了,但不知那封信还在不?当然,朱先生在一些文章中也动过气,也说过重话,但与有些人写文章来罗织罪状,夸张其辞,总想一举搞垮别人,相去何止天壤?我想,学术风格与人品、人格以至人生态度,学术的客观性与个体的主观性,大概的确有些关系。朱先生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地写了特别是翻译了那么多的东西,造福于中国现代美学……这是我非常敬佩而想努力学习的。朱先生那半弯的腰,盯着你看时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带着安徽口音的沉重有力的声调,现在异常清楚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因为自己懒于走动,我和朱先生来往不多。在“文革”中,去看过他几次。我们只叙友情,不谈美学。聊陈与义的诗词,谈恩斯特•卡西尔……虽绝口不涉及政治,但我当时那股强烈的愤懑之情总有意无意地表露了出来。我把当时填的一首词给朱先生看了,朱先生却以“牢骚太盛防肠断”来安慰、开导我。并告诉我,他虽然七十多岁,每天坚持运动,要散步很长一段路程,并劝我也搞些运动。朱先生还告诉我,他每天必喝白酒一小盅,多年如此。我也是喜欢喝酒的,于是朱先生便用酒招待我,我们边喝边聊。有一两次我带了点好酒到朱先生那里去聊天,我告诉他,以后当妻子再干涉我喝酒时,我将以高龄的他作为挡箭牌,朱先生听了,莞尔一笑。
“文革”后,朱先生更忙了,以耄耋之年,编文集、选集、全集,应各种访问、邀请、讲学、开会,还要翻译维柯……于是我没再去朱先生那里了。最近两年,听说朱先生身体已不如前,但我消息既不灵通,传闻又时好时坏,加上自己一忙,也就没十分注意。
如今,一声惊雷,先生逝去。回想起当年情景,我真后悔这十年没能再去和朱先生喝酒聊天,那一定会痛快、高兴得多。但这已经没有办法了,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不能重复。只是记忆和感情将以更丰富的形态活在人的心底。而这也就是死亡所不能吞噬的人类的有活力的生命和生命的活力。

一九八六年三月七日晨五时匆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