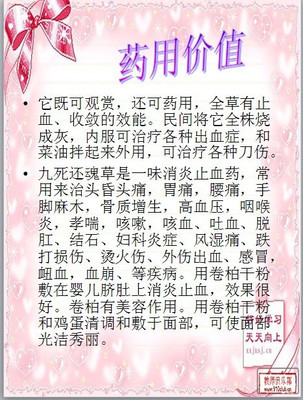周梦蝶诗集:还魂草
周弃子序
叶嘉莹序
I 山中拾掇
■天窗
■ 九行
■ 朝阳下
■ 守墓者
■ 濠上
■押摆渡船上
■ 树
■闻钟
II 红与黑
■ 一月
■ 二月
■ 四月
■ 五月
■ 七月
■ 十月
■ 十二月
■ 十三月
■ 闰月
■ 六月
■ 六月
■ 六月
■ 六月之外
III 七指
■ 菩提树下
■ 豹
■ 山
■ 逍遥游
■ 行到水穷处
■ 骈指
■ 托钵者
IV 焚麝十九首
■ 寻
■ 失题
■ 还魂草
■一瞥
■ 晚安,小玛丽
■ 虚空的拥抱
■ 空白
■ 车中驰思
■ 穿墙人
■ 你是我的一面镜子
■ 一瞥
■ 关着的夜色
■ 绝响
■ 圆镜
■ 囚
■ 落樱后,游阳明山
■ 天问
■ 燃灯人
■ 孤峰顶上
■ 周弃子序
列市尘纷万蚁驰,冷摊兀坐一人畸。
长贫不碍殷求友,太瘦真怜苦作诗。
尚想蝶魂归觅我,曾闻豹语死留皮。
梦蝶属题重刊还魂草,丙辰秋闰弃子漫笔
■ 叶嘉莹序
我是向来未尝为任何人任何书写过序文的,然而两天前,当周梦蝶先生要我为他即将出版的诗集《还魂草》赶写一篇序文时,我竟冒昧地答应了下来。其一,当然是有感于周先生的一份诚意;其二,则因为我原是一个讲授旧诗的人,而周先生居然肯要我为这一本现代诗集写序,则无论这一篇序文写得如何,至少不失为新旧之间破除隔阂步入合作的一种开端和首试;最后,一个更大的原因,则是因为我对周先生之忠于艺术也忠于自己的一种诗境与人格,一直有看一份爱赏与尊重之意,因此,虽明知自己未必是为此书写序的适当之人选,也依然乐于作了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承诺。
周先生之要我写序,也许因他曾偶在报刊中看到过我所写的一些有关旧诗词之评赏的文字,其实,批评古人的旧诗词,与批评今人的现代诗,并不尽同,一则因为旧诗词的作者,已属无可对质的古人,则我信口雌黄之所说,在读者而言,纵未必尽信其是,然也不能必指其非,而对今人之作,则我在论评之间,就不得不深怀着一份惟恐其未必能合作者原意的惶惧;再者,对于旧诗词的阅读和写作,我是早在30年前就已开始了的,而对于现代诗,则我不仅从来不曾有过写作的尝试和经验,即使阅读,也仅是近二、三年来,偶然涉猎浏览过一些极少的作品而已,虽说美之为美,天下有目之所共赏,我对于现代诗中的一些佳作,也极为赏爱,但如说到论评,则刺绣之工既不尽同于编织,缰辔的控持,也必然不同于方向盘之操纵,如今我欲以一向惯于论评旧诗词的眼光来论评现代诗,则即使不致如扣盘言日之盲,似乎也颇不免于燕说郢书之妄了。
以我习惯于论评旧诗词的眼光来看人,我以为周先生诗作最大的好处,乃在于诗中所表现的一种独特的诗境,这种诗境极难加以解说,如果引用周先生自己在「菩提树下」一诗中的话「谁能于雪中取火,且铸火为雪」,则我以为周先生的诗境所表现的,便极近于一种自「雪中取火,且铸火为雪」的境界。
我在为学生讲授旧诗词的时候,常好论及诗人对自己感情的一份处理安排之态度与方法,由于其对感情之处理与安排的不同,因此诗人们所表现的境界与风格也各异。如果举一些重要的诗人为例证。则渊明之简净真淳。是由于他能够将其一份悲苦,消融化解于一种智能的体悟之中,如同日光之融七彩而为一白,不离悲苦之中,而脱出于悲苦之外,这自然是一种极难达致的境界;其次则如唐之李太白,则是以其一份恣纵不羁的天才,终生作着自悲苦之中,欲腾掷跳跃而出的超越;杜子美则以其过人之强与过人之热的力与情,作着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至于宋之欧阳修,则是以其一份遣玩的意兴,把悲苦推远一步距离,以保持其所惯用的一种欣赏的余裕;苏东坡则以其旷达的襟次,把悲苦作着潇洒的摆落,以上诸人其类型虽尽有不同,然而对悲苦却似乎都有看一种足以奈何的手段。此外更有着一种从来对悲苦无法奈何的诗人,如「九死其未悔」的屈灵均,「成灰泪始干」的李商隐。他们固未尝解脱,也未尝寻求过解脱,他们对于悲苦只是一味的沉陷和耽溺。另外更有一种有心寻求安排与解脱,而终于未尝得到的人,那就是「言山水而包名理」的谢灵运,大谢之写山水与言名理,表现虽为两端,而用心实出于一源,他对山水幽峻的恣游,与对老庄哲理的向往,同样出于欲为其内心凌乱矛盾之悲苦,觅致得一排解之途径。然而佛家有云:「境由心造」,若非由内心自力更生,则山水之恣游既不过徒劳屐齿,老庄之哲理亦不过徒托言筌,所以大谢诗中的哲理。若非自其「不能得道」作相反之体认。而欲于其中寻觅「得道」的境界,就未免南辕而北辙了。
至于周先生的诗作,则自其48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孤独国》,到今日准备出版的第二本诗集《还魂草》,其意境与表现,虽有着更为幽邃精致,也更为深广博大的转变,然而其间却有着一个为大家所共同认知的不变的特色,那就是周先生诗中所一直闪烁着的一种禅理和哲思。周先生似乎也是一位想求安排解脱而未得的诗人,因之他的诗,既不同于前所举第一种之隐然有着对悲苦足以奈何的手段之诗人;也不同于第二种之对悲苦作着一味沉陷和耽溺的诗人;如果自其感情之不得解脱,与其时时「言哲理」的两方面来看,虽似颇近于大谢,然而若就其淡泊坚卓之人格与操守来看,则毋宁说其更近于渊明。周先生之不同于大谢者,盖大谢之不得解脱之感情,乃得之于现实生活之政治牵涉的一份凌乱与矛盾,而周先生之不得解脱之感情,则似乎是源于其内心深处一份孤绝无望之悲苦。再者,大谢之言哲理,只不过是在矛盾凌乱中的一份聊以自慰的空言,而其所言之哲理,并未曾在其感情与心灵之间发生任何作用,而周先生诗中的禅理哲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