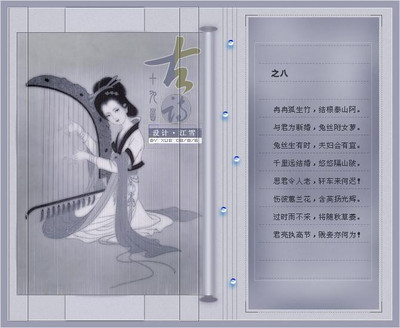古诗十九首之七“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
接 片
原 片
局部放大
译文:
皎洁的明月照亮了仲秋的夜色,在东壁的蟋蟀低吟的清唱著。
夜空北斗横转,那由玉衡,开阳,摇光三星组成的斗杓,正指向天象十二方位中的孟冬,,闪烁的星辰,更如镶嵌天幕的明珠,把仲秋的夜空辉映得一片璀璨!
深秋,朦胧的草叶上,竟已沾满晶莹的露珠,深秋已在不知不觉中到来,时光之流转有多疾速呵!
而从那枝叶婆婆的树影间,又听到了断续的秋蝉流鸣.怪不得往日的鸿雁(玄鸟)都不见了,原来已是秋雁南归的时节了。
京华求官的蹉跎岁月中,携手同游的同门好友,先就举翅高飞,腾达青云了,而今却成了相见不相识的陌路人。
在平步青云之际,把我留置身后而不屑一顾了!
遥望星空那"箕星","斗星","牵牛"的星座,它们既不能颠扬,斟酌和拉车,为什麽还要取这样的名称,真是虚有其名,
然而星星不语,只是狡黠地眨著眼,它们仿佛是在嘲笑,你自己又怎麽样呢?
想到当年友人怎样信誓旦旦,声称著同门之谊的"坚如磐石";而今"同门"虚名犹存,"磐石"友情安在叹息和感慨,炎凉世态虚名又有何用呢?
赏析一:
这首诗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诗中所描述的是什么季节?明明景象都是秋天的景象,然而却说是冬天。到底是冬天还是秋天?二,前八句似乎全是在说景物,后八句则明显是感受,情感抒发。前、后八句有什么联系?仅仅是即兴有感吗?
第一个问题是关键,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很早以来,人们就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而所做的一概都是去努力否定“孟冬”指冬天。
注《文选》的李善指出,“汉之孟冬,今之七月也”。也就是说,这里的“孟冬”不是冬天,而是“七月”。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历之前,汉朝都是沿袭秦朝的历制,那时是以现在的十月为岁首,那么,照此算来,孟冬正好是初秋的七月。所以,这首诗可能作于西汉初年。这个论点影响甚大。
其实这个说法不能成立。把每年的十月当作一年的开始,并没有改变季节和月份的名称,该称呼什么还是什么,这些都没有变。即使是西汉初年,孟冬还是孟冬,还是指初冬,而不是孟秋七月。所以,李善这番功夫是白费了。
叶嘉莹先生则指出,诗中“孟冬”是指天空中的一个方位,仅仅“玉衡指孟冬”并不能判断是在什么季节,要想判断季节,还必须知道玉衡是在夜晚什么时辰指向孟冬的。经过一番推算认为,“玉衡指孟冬”指的是孟秋七月的夜半以后到凌晨之前这一段时间。
假若诗中人在初秋的后半夜看天,那么他看到的北斗星的斗柄就指向“孟冬”的方位。这样,似乎解决了诗中的季节矛盾。
但是,将季节确定为孟秋七月,与诗中的景象并不完全相符。蝉鸣、白露降等开始于初秋的立秋节以后,但玄鸟(燕子)南飞却是中秋的白露节以后的事。诗中说燕子南飞,则时间起码是中秋以后。这个现象初秋七月就解释不了了。
至于“促织鸣东壁”所示的时间,《礼记》曰:“季夏之月,……蟋蟀居壁”,《诗经·七月》则说:“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在我床下。”从这些记载中可以推知,蟋蟀随着天气温度的降低,会逐渐挪移自己的居住地和活动范围。季夏,也就是六月,热风退,温风至,夜晚在野外就有点冷了,于是,蟋蟀开始居住在墙壁中。一直到七月,白天活动还是在野外。进入八月,就只能活动在屋檐下的范围内了,当然晚上所居仍然是房屋的墙壁。到了九月,蟋蟀就会进入房间,活动与居住都在房间里。十月就只能在床下呆着了,借人的热量。从七月开始,就鸣叫了。
所以,七月时促织晚上是住在墙壁内,但不一定是东壁。东壁,日照向阳,乃是稍为寒冷时的选择,刚刚住进时的墙壁不会是东壁。可能,八月时会住到东壁,面朝外,主要在屋宇下活动;也可能九月时进入房间后也住在东壁,而在屋内活动。所以,“促织鸣东壁”更可能是八月或九月。
燕子与促织两个例子足以推翻季节是孟秋七月的说法,从而,叶嘉莹先生所认为的后半夜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我认为,将“孟冬”解释为天空中的一个方位显得有些牵强,毕竟“孟冬”直接的就是季节的名称,而将其视作方位那就是一个拐了弯的专业术语了。一首诗里突然出现这么专业的名词总嫌突兀,尤其是对明白如家常话的古诗十九首来说。
当然,还有其它类似的解释,比如金克木先生认为是指孟秋或仲秋(即七月或八月)下弦月夜半至天明之间的这段时间;也有认为该诗作于王莽新朝期间,当时用殷历,按此推算,“孟冬”正好是指九月。
这些解释,目的都是试图将“孟冬”指初冬的字面意思推翻,代之以种种深奥的、繁琐的、曲折的内部变换,以使得时光向秋天的景象靠拢,以达到消除“孟冬”时节与种种秋景的矛盾的目的。所有人都是在这样做,虽然做法不一,但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到一起来了。
但是,即使上面的某一人真能解释通了,真的将矛盾给解决了,本诗就弄明白了吗?照样不明白。那样的话,本诗就是前后两截的了。前边八句与后边八句没什么直接联系,彼此关系游离而恍惚,一种飘忽的个人性的见景抒情、即兴感发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说词,唯一说得上的所谓联系。现代人可能会这么作诗,但古人不会,古人讲理,不像现代人这么恍恍惚惚地抒情。一首诗不会是不讲逻辑,两截子的。即使“孟冬”能够被变换成“秋天”,还是没弄懂这首诗,于诗的内涵还是隔着一层。
何况,历史上种种试图将“孟冬”解释成“秋天”的努力,都是失败的。这个事实表明:“孟冬”就是指初冬,冬天的季节与秋天的景象的矛盾是存在的,也是不能被取消的。
好在“孟冬”不能被解释成“秋天”,好在这个矛盾还存在。因为正是这个表面看起来的矛盾,才是理解本诗内涵的关键。诗人正是借由这个矛盾来说他想要说的话。
俞平伯、朱自清等正确地推断出当时应该是九月立冬以后,肯定了“孟冬”就是立冬,但他们却对诗中明显的秋天景象与立冬季节的矛盾视若不见,或者可能是有意地弱化、消解了这个矛盾,导致诗人的真意最后还是被蒙了起来,虽然只差一点就揭开了。这很遗憾。
诗中有一句关键的话谁都没注意,这句就是“时节忽复易”。什么叫“复易”?易,更易,变化;复,再一次,重复。“复易”那就是变了两次。假如说季节变化,那只能说“时节更易”、“时节忽易”,而不会说“时节忽复易”。只有在较短的时间段内时节连着变了两次才会这么说。
这是关键的一句。可惜历代的读诗者都给读成“时节忽更易”、“时节忽变易”了,将“复易”当成了“变易”、“更易”,将变了两次给读成了一次。这,当然就读不懂诗了。
“时节忽复易”,时节忽然两次更易。在所涉及的时间段内,很快地变了两次。由秋至冬是一次,立冬了又变回秋天之气候,则又是一次。这就是两次。
所以,季节是立冬了,那北斗星何其历历醒目,确实是立冬了,立了冬了。然而却出现了秋天的气候和景象:白露沾野草而不是白霜;秋蝉尚还在鸣叫;燕子刚开始南飞或刚飞走不久。按《礼记·月令》讲,这叫“孟冬行秋令”。那上边说:“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所以,这是名与实的脱节,实际的气候与季节之名已经不一致了。不一致的原因是因为实际上的气候又“复易”,又变回去了,“实”发生了变化。前八句都是渲染这个的。后八句也是在讲这个。全诗都是讲这个的。
好了,将外边喧闹着的历史公案解决了以后,我们可以进入到诗本文中去了,去静静体会。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这两句是渲染氛围的,夜被月光充满,被鸣叫声充满,构建出一个典型的秋季月夜环境。
这里,“皎”是动词,与下句的“鸣”为对文。明月澄澈明亮于夜光之中,促织鸣叫于东壁。促织,蟋蟀。东壁,东边的墙壁,这里当指房间的东边墙壁。
蟋蟀居于东壁,说明晚上有些寒冷,但还不是特别冷,特别冷时,蟋蟀会住在人的床下。秋天的天气还不太冷。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玉衡,这里代指斗柄,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五至七星。北斗七星形似酌酒的斗,第一星至第四星成勺形,称斗魁;第五星至第七星大致成一条直线,称斗柄。由于地球绕日公转,从地面上看去,斗柄的指向每月变一方位,于是古人根据斗柄所指的方位来辨别节令。
孟冬:冬季的第一个月,初冬。孟、仲、季分别表示每个季节的三个月。
“玉衡指孟冬”,天上标示季节的斗柄已经指向了孟冬,季节已经是初冬了。
众星,这里是指北斗七星。为了强调说明季节变换,为了肯定“玉衡指孟冬”,所以这里是指北斗七星本身。另外,月夜中一般的星星都很难看见了,不可能有“众星何历历”,但北斗七星总是那么清晰可见,即使在月夜,所以,北斗星才被人们用来指引方向、定位。历历,清楚,分明。
“众星何历历”,北斗那七星一个个那么清晰分明,清清楚楚的。
这两句强调说明:可是时节已经是到了冬天了,已经立冬了。你看天上北斗星那么清楚地照耀着哪。
矛盾出现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于是,紧接着要说明,要解释。
白露,“立秋”节后白露降,“霜降”节后即为白霜而非白露。所以,一般在立冬前半个月的“霜降”节开始,就没有“白露沾野草”的现象了,而这时还有这种现象,说明“时节”又变回到秋天去了。于是,“时节忽复易”——本来刚刚立冬,季节从秋天变到了冬天,可是忽然又再次变回秋天了。从这句诗里可以猜测,可能“立冬”节后有一个极短暂的变冷的时间段,比如一半天,但很快就又恢复温度,回到了秋季,所以当时的景象还都是秋天的景象。
“时节忽复易”是对前此各句的总结与说明,将立冬的季节与促织鸣叫、白露沾草的秋景矛盾揭示出来。
“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
玄鸟,燕子。逝,不见,不再露面。适,往。“玄鸟逝安适”,燕子飞走不见了,它们去了什么地方?
中秋、白露节之后,燕子开始南飞。这里提到燕子,用“逝”字,说明燕子已经飞走了,但可能飞走的时间不很长。从白露到立冬,整两个月时间,按正常年份燕子到了这立冬之时,早已经飞得没影了,人也就想不起两个来月前燕子南飞这回事来。诗中提到燕子南飞,说明燕子刚飞走不是很久,还让人们记得。这自然是因为天气暖和,燕子也就不急于南飞了。同样,秋蝉本来立冬前就已经死了,要不是天气暖和,哪里还会鸣叫呢?
立冬了,秋蝉还在树上鸣叫呢,燕子也才飞走没几天,也不知它们飞到了什么地方。
这两句是仍在强调秋景的存在。表面看来是重复、加重,实际上,在一二句渲染氛围、三四句点出季节、五六句揭示矛盾之后,实在需要七八句再次强调一番,以塑造热闹的秋天印象,而将立冬的季节印象尽量压低。这样做是为全诗服务的。
前八句都是写景。从诗中来看,应该是诗人在月夜自己的庭院外看到的景象,听到的蝉鸣、蟋蟀叫。这无疑可以视为写景,但却不是我们所习惯了的写景,也不是从景象里兴发什么意趣,而是“用景”,用构造的景象说明问题。诗人构造了一个向前推延的时间、季节进程中突然产生了紊乱的错位了的环境。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同门就是同在一个师门的同学,同学的关系当然很亲密,并肩前进,携手同行,有“携手”之好。
翮,位于翅膀前部的长羽,底部是长长的硬管,顶部是毛羽,左右各三根,共六根,称为“六翮”,是鸟儿飞行的主要力量所在。《韩诗外传》有曰:“夫鸿鹄一举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同门友飞黄腾达,象鸿鹄一般高飞起来了。可是,却“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就象行人丢弃脚印一样,把我给丢下了。
这四句当然是诗人自己实际的感慨。被昔日的携手好友抛弃,悬殊的今昔对比之下,感慨自然是有的。
友谊关系的向前推延出了问题,过去的友谊推展不到新的情况下了,友谊延续不下去了。就象前面的气候,在时间过了立冬之后,竟然也是推延不过去,仍然在秋天里呆着不变。从这点上来说,二者是一样的。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南箕,星名,形似簸箕。北斗,北斗星,形似酌酒之斗。牵牛,牵牛星。轭,驾车时套在牲口脖子上的曲木。牛拉车时都要负轭,不负轭就是不拉车。这几句直接来自《诗经》。《诗经·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杨;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睆彼牵牛,不以服箱”。服箱就是拉车。
名为箕而不能簸米糠,名为斗却不能舀酒,名为牵牛又不能拉车。南箕、北斗、牵牛都是虚名,都只是虚名罢了。
“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良,正常传延,正常进程,事物的正常演变进程。在先天规定的本质轨道上生存延续,在正常的轨道上传延。
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孟子说的是先天的本性,凡是来自于先天本性的能力就叫良知良能。
同样,当我们说“良心”时,指的就是我们的先天善良本性,本性善良的心。
我们说“良民”,那是指安分守己不乱来的百姓;“良家”,清白人家,守规矩人家也;“良医”,那是生命在正常轨道上传延的保证,他们专门负责去除扰乱生命正常轨道的疾病;“良药”是治病的,将病去掉而令身体重新在正常轨道上延续;“良性肿瘤”之所以“良”,就是因为它还是正常轨道上的产物,并不危及生命,所以闹不成“癌症”;所以我们要“除暴安良”,除去那些横生的、暴乱于正常状态的东西,安抚良善顺遂者。
古代,妻子称丈夫为“良人”,孟子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离娄下);百姓也称那些支撑国家的德高望重的大臣、那些国家栋梁为“良人”;那些好朋友、带你走正道的朋友叫“良友”。良,实在是人生的保障。失去了正常,失去了“良”,生命也就陷入紊乱,并将很快终结。
甚至,我们对这种正常的顺延有更大的期待和指望,我们也将“良”用于其它的方面,只要是让我们感到事情在顺延着呢就行,虽然有点“很……”的意思,但那也只是在顺延的路上走得稍长了点而已,并不是没走正路。《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默然良久”,《史记·商君传》“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只要属于是被人关注下的正常的顺延,都是“良”,时间长点也无妨;“你用心良苦,我受益良多”,我能感受到你那为我好的一番苦心,那从深远处贯穿而来的苦心,你这番苦心给我的益处啊,那可是多得很,一直在往上堆积,至今还在不断地向上叠加着呢。
所以,我们说,良,就是正常传延,正常运转,在本来的应该在的轨道上继续,使传延不断。不能这样,就是不良、无良。所以,我们说“良”有好、善的意思。
作为名词,那就是正常的进程,正常的传延,正常的应有的延续不断。本诗这里,正是这个意思,“良”在此是个名词。
事物演变变化的进程本身,也就是“良”的力量一般都很强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抵抗外界因素的干扰,维持自身的稳定。也就是说,这个“良”一般都是如磐石般稳固。假如这个“良”不是这样,“‘良’无磐石固”,那么,事物就会发生紊乱,短暂的紊乱,或长期的动荡,乃至灭绝。没有这种内在机制的稳固,外在的一切都将发生变化,所产生的就不再是所预期的正常的东西了,过去的用于形容正常的“名”就与实际的东西不相符了,这时,这个“名”也就是“虚名”了。
“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本来保证向前推延的力量就没那么大,本来正常的进程就没有象磐石那么稳固,还执著于那虚名又有什么用处呢?
四季轮转,正常更替,但今年“时节忽复易”,气候在入冬后返秋,冬天的虚名已不足以描述当下的秋景,这是四季轮转的力量小于某种外来因素而导致了紊乱。过去的同门之友发迹后,“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不再拿我当朋友看,过去的朋友关系推延不到现在了,只能说明本来的交情就没有磐石般稳固,只能说本来交情就不深,经受不住飞黄腾达的考验。这时还执著于这个朋友的虚名又有什么用处呢,只好算作白交往一场了。这时的虚名,就象天上的南箕、北斗、牵牛星,也就只是个虚名罢了。
原来本就有这般虚名存在。那我也就罢了吧。
用大段的景物季节来为自己排遣,用天上的星宿来纾解被遗弃的痛苦,诗人在努力使自己升华上来。还有淡淡的悲哀,些许的感叹,但也仅止于此。
着眼于实质,而不务虚名,这无疑有助于人放下很多毫无意义的东西。
赏析二: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诗人此刻正浸染着一派月光,这是谁都可以从诗之开篇感觉到的。胶洁的月色,蟋蟀的低吟,交织成一曲多么清切的夜之旋律。再看夜空,北斗横转,那由“玉衡”(北斗第五星)、“开阳”、“摇光”三星组成的斗柄(杓),正指向天象十二方位中的“孟冬,闪烁的星辰,更如镶嵌天幕的明珠,把夜空辉映得一片璀璨!一切似乎都很美好,包括那披着一身月光漫步的诗人。但是且慢,让我们看一看“此刻”究竟是什么时辰?“严玉衡指孟冬”,据金克木先生解说,“孟冬”在这里指的不是初冬节令(因为下文明说还有“秋蝉”),而是指仲秋后半夜的某个时刻。仲秋的后半夜!--如此深沉的夜半,诗人却还在月下踽踽步,显然有些反常。倘若不是胸中有着缠绕不去的忧愁,搅得人心神不宁,谁还会在这样的时刻久久不眠?明白了这一层,人们便知道,诗人此刻的心境非但并不“美好”,简直有些凄凉。由此体味上述四句,境界就立为改观--不仅那皎洁的月色,似乎变得幽冷了几分,就是那从“东璧”下传来的蟋蟀之鸣,听去不也格外到哀切?从美好夜景中,抒写客中独步的忧伤,那“美好”也会变得“凄凉”的,这就是艺术上的反衬效果。
诗人默默无语,只是在月光下徘徊。当他踏过草径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什么:“白露沾野草。朦胧的草叶上,竟已沾满晶莹的露珠,那是秋气已深的征兆--诗人似平直到此刻才感觉到,深秋已在不知不觉中到来。时光之流驶有多疾速呵!而从那枝叶婆婆的树影间,又有时断时续的寒蝉之流鸣。怪不得往日的燕子(玄鸟)都不见了,原来已是秋雁南归的时节。这些燕子又将飞往哪里去呢?--“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这就是诗人在月下所发出的怅然问叹。这问叹似乎只对“玄鸟”而发,实际上,它岂不又是诗人那充满失意的怅然自问?从下文可知,诗人之游宦京华已几经寒暑。而今草露蝉鸣、又经一秋,它们在诗人心上所勾起的,该是流离客中的几多惆怅和凄怆!以上八句从描述秋夜之景入笔,抒写诗人月下徘徊的哀伤之情。适应着秋夜的清寂和诗人怅惘、失意之感,笔触运得轻轻的,色彩也一片渗白;没有大的音响,只有蟋蟀、秋蝉交鸣中偶发的、诗人那悠悠的叹息之声。当诗人一触及自身的伤痛时,情感便不兔愤愤起来。诗人为什么久滞客中?为何在如此夜半焦灼难眠?那是因为他曾经希望过、期待过,而今这希望和期待全破灭了!“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在诗人求宦京华的蹉跎岁月中,和他携手而游的同门好友,先就举翅高飞、腾达青云了。这在当初,无疑如一道灿烂的阳光,把诗人的前路照耀得五彩缓纷。他相信,“同门”好友将会从青云间垂下手来,提携自己一把;总有一天,他将能与友人一起比翼齐飞、邀游碧空!但事实却大大出乎诗人预料,昔日的同门之友,而今却成了相见不相认的陌路之人。他竟然在平步青云之际,把自己当作走路时的脚迹一样,留置身后而不屑一顾了!“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这毫不经意中运用的妙喻,不仅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同门好友“一阔脸就变”的卑劣之态,同时又表露了诗人那不谙世态炎凉的多少惊讶、悲愤和不平!全诗的主旨至此方才揭开,那在月光下徘徊的诗人,原来就是这样一位被同门好友所欺骗、所抛弃的落魄者。在他的背后,月光印出了静静的身影;而在头顶上空,依然是明珠般闪烁的“历历”众星。当诗人带着被抛弃的余愤怒仰望星空时,偏偏又瞥见了那名为“箕星”、“斗星”和“牵牛”的星座。正如《小雅·大东》所说的:“维南有箕,不可以颠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皖彼牵牛,不以服箱(车)”。它们既不能颠扬、斟酌和拉车,为什么还要取这样的名称?真是莫大的笑语!诗人顿时生出一股无名的怨气,指点着这些徒有虚名的星座大声责问起来:“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扼!”突然指责起渺渺苍穹中的星星,不太奇怪了吗?一点也不奇怪。诗人心中实在有太多的苦闷,这苦闷无处发泄,不拿这些徒其虚名的星星是问,又问谁去?然而星星不语,只是狡黠地眨着眼,它们仿佛是在嘲笑:你自己又怎么样呢?不也担着‘同门友’的虚名,终于被同门之友抛弃了吗?"----“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l"想到当年友人怎样信誓旦旦,声称着同门之谊的“坚如盘石”;而今“同门”虚名犹存,“盘石”友情安在?诗人终于仰天长叹,以悲愤的感慨收束了全诗。这叹息和感溉,包含了诗人那被炎凉世态所欺骗、所愚弄的多少伤痛和悲哀呵!
抒写这样的伤痛和悲哀,本来只用数语即可说尽。此诗却偏从秋夜之景写起,初看似与词旨全无关涉,其实均与后文的情感抒发脉络相连:月光笼盖悲情,为全诗敷上了凄清的底色;促织鸣于东壁,给幽寂增添了几多哀音;“玉衡指孟”点明夜半不眠之时辰,“众星何历历”暗伏箕、斗、牵牛之奇思;然后从草露、蝉鸣中,引出时光流驶之感,触动同门相弃之痛;眼看到了愤极"直落"、难以控驭的地步,“妙在忽蒙上文‘众星历历’,借箕、斗、牵牛有名无实,凭空作比,然后拍合,便顿觉波澜跌宕”(张玉谷《古诗赏析》)。这就是《明月皎夜光》写景抒愤上的妙处,那感叹、愤激、伤痛和悲哀,始终交织在一片星光、月色、螺蜂、蝉鸣之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