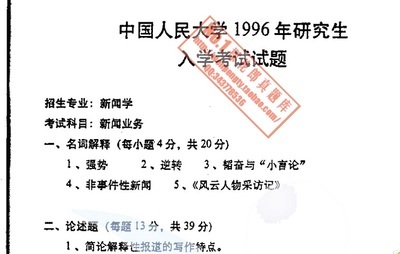用白色石头雕成的吴玉章半身像安放在人文楼的正中。今晚,当教二草坪上的舞台陷入狂欢之中的时候,吴校长深邃的眼神,将穿透那两层玻璃门,静静地注视着这一片喧嚣。
他是个布尔什维克,他又不完全是个布尔什维克。
一
62年前的今日,中国人民大学诞生在铁狮子胡同1号,那个有着古典框架与格局的摩登院落。
中共党务系统最高负责人,中共的二号人物刘少奇出席了那天的建校典礼。从那时起,这所学校成为中共高层最为倚重的人才储备基地之一。
图1 1950年10月3日人大开学典礼
然而,在1950年到1966年的十六年间,这一所以培养“党的干部”为宗旨而被广泛称为“第二党校”的学校,并没有培养出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反而,这十六年里,她已经开始对延安传统的反动。
随着私立中国大学、私立朝阳大学等院校相继并入人大,她的正红底色开始改变。
1957年,对于中国人民大学而言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那一年,仅仅发了几句牢骚的葛佩琦成为全国高校系统首先被批判的大右派;那一年,一个法律系的弱女子林希翎在五月的整风高潮中成为叱咤人大北大的才女,最终被刘少奇钦定为右派。官方认定承继自延安的红色大学,却变成“反右”政治运动重要的漩涡中心,人们开始发现摆脱干部培训学校性质之后的大学,开始出现桀骜不驯的反叛者。
此前的1955年,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谢韬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随后的二十多年里始终命途多舛。虽然在老乡吴玉章校长的保护下,他勉强保住了中共的党籍,然而从就读成都金陵大学时就开始的跟随中共追求自由、进步和解放的梦想已被无情碾碎。两年后,法律系林希翎曾为谢韬案张目,也被作为划成右派的证据。
二
如果说私立朝阳大学、私立中国大学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是人大历史上第一次清流的涌入,而北大新闻系并入人大则为这所学校未来新的伟大篇章奠定基础。
苏联专家把新闻作为意识形态和统治技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大学原隶中文系的新闻专业被整编到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是1958年。
这一帮北大新闻系学生中,有的至今仍然活跃,譬如钱理群;当然也有更多的湮没无闻。然而,历史将无可争议地记载,这些学生中最让人钦佩的那一位,苏州吴县的彭令昭,她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林昭。
她是地道的北大人,却在铁狮子胡同一号度过了几年有些幽暗的岁月。1957年“反右”运动中不经意的出头,让这个曾经积极参与土改的昔日左翼青年,一步步成为那个时代众人皆醉之下的独醒者,成为反对独裁的圣女和先知。吴玉章曾经为了保护她,批准她回上海养病。为了保护林昭、林希翎这样的女子,吴玉章在使用权力时没有吝啬。
图二 吴玉章在陕北

总体而言,这个时代的新闻系是黯淡无光的,如同她身后的这个国家,满目疮痍。这个时代的新闻人无从记录,只能在恐惧之下彻底蛰伏。诚如新闻系1978级校友张善炬1989年所写的那样:“多苦多难的中国记者,回首前四十年,至少有三十年是在痛苦地背叛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痛苦地闭上眼睛篡改历史,历史会报复新闻的。”
而在当时的人大,聋哑的又岂止是一个新闻系,每一个专业都被时代大潮裹挟着,丝毫喘不过气来。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曾联合组织调查组,实地考察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情形,由于调查组未能得出支持中央做法的结论,曾任人大副校长的时任北大副校长邹鲁风遭遇批斗,含恨自杀。而参与调查的人大师生也多受牵连。曾经担任人大第一个“学院”——计划统计学院院长的李震中,事后曾写文章回忆此事。在权力的淫威之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已经成了极端危险的事情。
三
1966年,经历过辛亥革命和大革命的老人吴玉章走到生命尽头。
在自贡拉板车的谢韬,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泪如雨下。二十多年前,在成都锦江边明媚的日子,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与谢韬结下不解之缘,从成都到北京,出身于谢韬出生地邻县荣县的吴玉章,始终给他巨大的帮助和支持。
图三 抗战时期的成都华西坝
吴玉章无疑是个忠诚的老党员,然而他却不是对权力百依百顺的人。从谢韬、到林希翎、再到林昭,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尽力,但终究不能力挽狂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体制的异数。
就在他去世的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濒于关停。昔日宣布学校开幕的国家主席已被打倒,这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起来的“新型大学”,也被亲手创建她的最高权力搞得体无完肤。
此时的她,不是俄语里的布尔什维克,她是少数,是异数,是“两校”之外需要被取缔的对象。学校变成军营,知识让位于暴力,曾经稳定的秩序一夜间被彻底打乱,师生和校友被蹂躏和践踏。
吴玉章走后第九年,东北乍暖还寒的春日,张志新以最惨烈的方式被执行死刑。1979年,张志新平反,这个曾在俄语系进修的弱女子也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精神图腾。这所因权力而生的大学,因为像她这样的斗士而开始有了独立自强的脊梁。
图四 张志新
四
中国人民大学在1978年重生。
那一年有许多人进入这所学校,而今像马凯这样的已身居国务委员的高位,然而有更多的78级校友,并不为人所知。
胡舒立当年要报考北大中文系,因为人大恢复重建,需要抽调一批精干的学生来到新闻系,阴错阳差她成了人大新闻系的学生,二十年后,她被外媒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她所在的媒体树立起中国传媒业的新标杆。
张善炬是她的同班同学,上大学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图五 青年张善炬
在今日中国,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生前只是西南边陲贵阳一家报纸的“调研员”。但在三十多年前,他是新闻系耀眼的一颗星。“一时间,在我们那里,没有谁真的会觉得别人的文章是比自己好的”舒立写道,“不过,很快还是有了公认的第一支笔,其作文、作业争相传阅,这就是张善炬”
1979年秋,北京西单“民主墙”被官方取缔。张善炬在新闻系教室墙报上,仿李斯“谏逐客书”一文写了“谏拆墙书”。舒立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内容:
文章先是坦言:“值今樊笼方开,言路初通,‘文革’创伤,余悸犹存之际,拆墙之举实为因噎废食之下策,塞堵言路之门,将使民望而却步,退而不敢开口”;“区区西单小墙,长不过百步,宽不到三米,纵其全文大多‘反动’,亦不必如此惊惶失色。数百报刊、十万尖兵、九亿人众皆‘愚民’乎?”进而激辩:“且人之有心,思也;人之有口,言也,拆其墙,毋能禁其言;禁其语,毋能鉗其心。昔‘四人帮’堵耳、鉗口、蒙眼、割颈、砍头,何术不用其极,然终无补于事。古人云:‘只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前车之鉴,宜应戒之。”再有劝喻,列举古人先例后论道:“而今公仆治国,理当胜越古人,现文件宪法,无不大书民主,电台报章,亦在鼓吹鸣放。望言必信,行必果,莫学叶公之好龙,贻笑后人。”结语恳切陈情:“诸位立法委员得闲暇时,似可探究西单墙之社会根源及根除之法,拆墙法虽尽善尽美之至,仍属舍本逐末、饮鸩止渴之小技耳。万望三思。”她进而写道,同学们当场点评此文“大胆文章,切中时弊,一片忠心,光可鉴人”,外系外校来访者络绎不绝。最终这篇小文很快被系领导从教室的后墙上取了下来。
自由的空气已经吹进双榆树的校园,而僵化的管制阴云未曾散去。面对胡耀邦亲自干预的“林希翎”案,中国人民大学也能“顶住压力”,坚持不改正对林希翎的“右派”结论。这样一个红色党委治下的学校,如张善炬这样的年轻人的执着和独立,其实殊为不易。
五
中文系的吴思曾讲述过那些年他在校园里听过的讲座,譬如刘宾雁的。二十多年后《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到人大新闻系,发现85后的年轻人对这个名字已经陌生。
那些年的许多记忆,都在人大的校史里被悄悄抹去。然而有一场运动的故事却在每个世代进入校园的时候都被提起,那边是“归还校舍运动”。1979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游行到新华门前,要求文革期间占据校园的第二炮兵部队机关从校内撤出,还人大学生图书馆等等。
彼时,人大校园里就连食堂都没有,学生们都只能露天吃饭。
人大学生的诉求最终得到满足,二炮机关退出了校园。人大校方自诩说,“归还校舍运动”是1949年以来中国内地唯一一场成功达成目的的学潮。
十年之后的人大和人大人,不再有十年前的幸运。
1989年6月5日,四川成都人肖杰在南池子被枪杀,彼时的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四的学生。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萧峰杰”,当年的运动领袖也还用这个名字称呼他。现在没有人知道,当时人大校园里最为活跃的学生领袖为何会在清场后一天才遭遇不测。我们只知道的是,他当时已“视死忽如归”,他向他的父母留下一封遗书:“爸爸妈妈,如果我在壮志未酬之前就被消灭,您们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20多年来只是为这个社会、这个民族养了一个带血泪的流星吧。”他在那一场疾风骤雨里表现得决绝:“我的理想、我的信念1、我的事业在召唤着我,虽然死神也隐在它们的背后向我招手,但我却不能不义无反顾地迎着它们走向前去。我没有其它道路可供选择,因为我的信念,我的使命,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决定了我必须走这条人间最艰难险恶的路。”
同是成都人的吴国锋,先于肖杰被枪杀。他是新津县三十多年来第一个考进人大的学生,就读于86级工业经济系。那天喧嚣而恐怖的晚上,他骑上自行车背上相机进了城,等待他的却是死亡。曾经在人大东门上悬挂的条幅“行动起来,救我中华”也在这些死亡之后,被定格在那个躁动的春夏之交。
人们知道的是,除了他以外,还有多位人大学生乃至教工子弟的生命,在那个夜里戛然而止。几年之后,他们的母亲在一个有着丧子之痛的人大教师的主导下集结起来。
远在贵州的张善炬,是夏也成为报社的整肃对象,受到留党察看处分,被免去《贵州日报》编委、总编室主任的职务。他遭遇整肃,主要源于他所写的“记者的快乐与痛苦”一文。前文中引述的“历史会报复新闻的”等句子,便出自此文。
后人不免会感概,张善炬和肖杰,同样两个来自西南的新闻系年轻人,相隔十年,有着些许相似却又不同的经历。张善炬工于写作,勤思苦学;肖杰热心社会,举办很多校园沙龙,直至参与到那场运动。同样的一腔热血,同样的报国理想,都随时代跌宕而遭遇挫折。
图六 肖杰在广场上(图中持旗杆者为肖杰)
六
一位老师上课时说,他觉得中国人民大学最伟大的一段时间,就是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
那段日子对于不少人大的学生而言,是青涩而复杂的记忆。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一个当时眉目清秀的少年,跻身非法组织“ Gao ZiLian”的常务委员,他正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却摊上这么一档子事情,背着处分离开了人民大学。
他有一个同学,从本科生到福特班,一直到研究生和他都同班。那是个爽朗的东北姑娘,没有任何政治主张,但却在4月27日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她说,她并没有任何关于政治的想法,也没有任何特殊的诉求。她只是相信,上街的人越多,参加的每一个人都越安全。在那一天,她把自己的命运和上百万人的命运相连接。她愿意用她的付出,换“法不责众”下的顺利过关。
5月4日,一场谈话冷却了这场运动的滚烫。以为滚滚热潮即将结束的一批毕业生,踏上去深圳实习的路程。那一位东北姑娘就是其中之一。在深圳呆了几天,这一批人又转往广州。
5月13日,风波又起,当北京又一次人山人海,这一群实习者在离北京距离遥远的南国。他们急切地渴望回到北京去,却发现京广线已经中断,停运几日。他们无从回到北京,只能焦急地等待,那里的消息。来自东北的那位女研究生已经结婚,她的老公在北京中建总公司工作。离开老公的日子,她忐忑着,因为她的老公总是会去送水果和馒头,给那些学生。
那个日期终究还是来了,她的丈夫在国贸工地上班,她听说那也是枪声四起,流弹飞溅。最后,一切还是结束了。她的丈夫,安然无恙。
那位她的同班同学,担任非法组织头目的男生,在那天晚上跑到教务处主任家里。教务处主任对他说,今天晚上你哪儿也别去了,他就在那里躲了一晚上。说起来他原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但是分配得却很差。回想当时人民大学的校方,用尽一切力量保护这些学生,这个男生后来被发配到西北,这样的结局,对他而言其实并不算坏。
南巡谈话的第二年,那位在春夏之交初到广东的女生,和她的丈夫拥有了自己的公司。那位当年背着处分的同学,在那个东北姑娘号召下,来到了全中国最不讲政治的城市——深圳。如今,那当初叛逆的少年,已是这间公司的高管。2009年,这一家公司在深圳上市,同班的两个同学都有了亿万身家。
其实在那个年代的许多人,并不像这个“头目”那样幸运,张善炬便是一例。1982年,甘惜分力主将张善炬留校,却因为那一篇“谏拆墙书”而遭到当时“左派”干扰。1988年,《贵州日报》拟提张善炬为编委时,人大新闻系党总支竟然去信一封,强调张“文字水平较高,但思想上需要提高”“在政治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云云,还附了“谏拆墙书”抄件,张善炬入编委会因此受阻。要知道,彼时他是贵州时任省委书记胡锦涛最为信任的记者。
不少人说人大待学生宽厚,但恐怕只是其中一个断面。人大校园里的确有许多在内心中燃烧着蠢蠢欲动热情的人,但也有死守斯大林主义的老不死的“布尔什维克”,追求真理还是驯服于权力,这一场斗争从这所学校诞生的那天起便成为其主旋律,至今仍在上演着变奏。
七
2007年5月,1990级的中文系研究生项立刚在初夏的校园独自走过,想起那些记忆里的从前。1990年,项立刚和本科新生原晓娟在校园里相识。两年之后的冬天,他们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这个校园里承载着关于他们爱情的最初记忆。
图七 项立刚、原晓娟相恋的宿舍楼
原晓娟后来做了时尚杂志的编辑,又参与一本美食杂志的创办。她是个美食家,到世界各地饕餮,并将美酒珍馐以图片和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可惜命运弄人,2006年33岁的她被确诊胃癌。她名叫“鼠尾草”的博客有很多读者,她坚强的抗癌经历让人感动,也让人唏嘘。
她供职的杂志社因为她生病的缘故,2006年年底和她解除了劳动关系,直至在2007年4月病故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她的身份是“自由撰稿人”。此后,项立刚为她维权,最终达成庭外和解,杂志社付出70万元,原晓娟的家人另凑了一点钱一共捐建了三所希望小学。
项立刚、原晓娟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和轰轰烈烈,除了原晓娟的早逝,像他们这样的一家在人大毕业生中是很平常的。项立刚拥有自己的事业,原晓娟挚爱着美食和生活。而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项立刚也坚持着自己的底线。
项立刚、原晓娟相恋的时候,另一个人大校友开始走入人们的视线。或许,他是人大历史上最有名的校友,他名叫王小波。他是1978级学生,却因为九十年代开始大规模出版的作品而名声大噪,“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是他的代表作。他用自己独道的写作手法,讽刺着苦难和荒谬。这位经历复杂的文学天才,被誉为是中国的“卡夫卡”,他身上的人文气质,告白着一种与布尔什维克的集体主义彻底悖逆的精神。
图八 王小波
八
前几天,一个政客正式被宣判政治生涯的“死刑”。一年半以前,他曾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在前呼后拥中签署中国人民大学和重庆市的合作协议。这所大学曾经对他的迎合,学校校长多次赴重庆的谈笑,乃至于校内所谓学者对“重庆模式”的鼓吹和推销,似乎仍历历在目。
我想起了五六十年代这所学校曾有的如日中天和关停解散。对于大学而言,因为权力而得来的一切,如同过眼云烟。
2009年8月,张善炬因癌症病故。同学们在唁电中把他称为“大写的新闻人”、“志士、猛士、战士”,今天的校史馆里不会有那一封“谏拆墙书”,今天的新闻学院不会告诉学生她曾有过怎样二逼的党总支。然而公道自在人心,我们为这所大学感到自豪的唯一源泉,是这些未曾因权力和金钱折腰的前辈,是那些摆脱了“布尔什维克”传统的独立文人。
张善炬曾经送给自己老领导一幅挂画,上题“上善如水,大真无争”。做官做到多大,赚钱赚到多少,话筒举得多高,其实都不太重要。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独立人格。张善炬短暂的生命,用这幅挂画诠释出“无欲则刚”的精神境界。
周濂于2005年来到人民大学,做了一名哲学系教师。
他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很有趣,叫做《我们都是一小撮》。他用语言解构了“人民”二字:“在一个充满着差异性和趣味性的多元主义社会里,我们应该把“人民”放进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把“审判我就是在丑化人民”以及“代表人民审判你”这样的说法放到微博笑话语录里。”
“由于某种幸运的巧合,我们碰巧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一小撮,只有成为世界的一小撮,才能真实地看清世界。”周濂如是说。
这时候,我明白了“非布尔什维克”的真意。“布尔什维克”不止是一种体制的象征,也是俄文中间“多数派”的意思。“人民大学”从某种程度上便来源于“布尔什维克”,来源于“布尔什维克”扶植的中国革命,来源于以“布尔什维克”建构的社会大多数——“人民”。62年来,这所学校始终带着一股“布尔什维克”的气息,被苏俄革命扭曲了的“布尔什维克”气息。这里,有太多人以“人民”的名义迎合权力,以“集体”的名义抹杀个性,以“政治正确”为由打压人格的独立。
然而,我们骄傲的是,在这六十多年里这所学校有那么多“非布尔什维克”。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我坚持要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
我坚信,大学的光荣并不会源于金戈铁马的革命历史。只有自由和独立,才是大学真正值得珍视的旗帜。
转自校内网元淦恭的日志,原题为《非布尔什维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