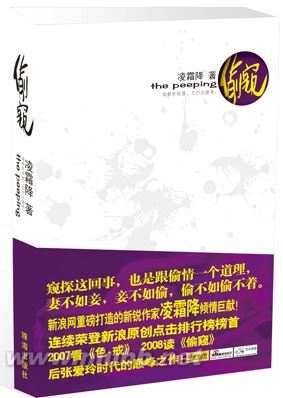采写/张涵予 摄影/李达
视频/郑无边 编辑/赵晓梅
来源/《心探索》杂志66期
【Who is 赖声川】
赖声川:1954年生于美国华盛顿,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博士。台湾著名舞台剧、电视、电影导演,曾任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院长、美国斯坦佛大学客座教授及驻校艺术家。1984年创立剧团“表演工作坊”,现为表演工作坊艺术总监,被誉为“亚洲剧场之翘楚”。
【Who is 丁乃竺】
丁乃竺:赖声川的夫人,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教育学硕士。戏剧制作人。“表演工作坊”行政总监。
赖声川喜欢喜剧,他喜欢用让人发笑的方式,讲哪怕是悲伤的故事。老友说他就是个“老嬉皮”,对物质看得很淡,自由自在,我行我素。受益于巴赫的严谨,爵士的即兴,他用这两味元素把戏调和得十分精妙,又家常又深刻,又随意又严谨。研习佛法多年,他对生命的探索早已融入每一部戏的机理,不经意间就触碰到观者的情感神经,笑和泪一秒间转换。悲喜交叠,情理相宜,他做戏的技艺已经炉火纯青。
但他说自己不是大师,他只是把实相搬上舞台,把故事摊开,让剧情自己流进观者心里。他说戏剧不是假想的呈现,而有让人观照自身,重新咀嚼生命的可能。
演员孙强一人饰演了《如梦之梦》中“五号病人”和“伯爵”两个角色,此后扮演《海鸥》里的作家“果林”,他说赖声川跟每个演员讲一句话,“去怜悯你的角色”,这句话让他在表演上受益匪浅;扮演青年版顾香兰的女演员谭卓至今提起“如梦”剧组来眼泛泪光,她对这一群兄弟姐妹们充满感情,说最难忘每次演出完赖导都带着所有演员在后台给这部戏中的角色和观众做回向,向他们表示感谢,把爱传出去。
契诃夫有两句话对赖声川影响颇深: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吃饭睡觉聊天甚至做很无聊的事,为什么舞台上总是在杀人谈恋爱?在我们吃饭或聊天中,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命运在另外一个地方被决定。
他因此而顿悟戏剧的真意,戏剧要把“生命”搬上舞台,“让一切流动起来,那就是我们的能量”。
赖声川的戏,“相声”系列嘲讽政治,《暗恋桃花源》探讨混乱中的秩序,《十三角关系》关心婚恋情感,《宝岛一村》回顾错位的历史,《如梦之梦》直面生死谜题,到现在借《海鸥》表达一种生命态度,他越来越放松,借助戏剧与社会做深层的联结。
戏剧为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他却说“在我心里,老婆永远第一位,女儿第二位,戏剧、佛法排第三。”
赖声川和太太鹣鲽情深是圈内佳话。他说他们至今无话不谈,彼此间没有秘密。他们的关系一直在演化,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走来一起成长,早已结成知己。
丁乃竺说一无所知的人一无所爱,爱是种能力,需要去了解生命的知识。赖声川说人生需要学习,而最大的学习是放下自己。
“生命太浩瀚了,我们人是怎么一回事,世界、人类、历史又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我们活着干什么。当两个人都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个世界就很大,而不会拘泥于房租学费这些问题。”
喜剧的忧伤
中世纪的神话传说中,独角兽是一只独立安静的动物,喜欢纯洁美好的事物,自由徜徉在森林里。一次,赖声川的朋友跟他做一个小游戏,让他迅速说出一只动物,他脱口而出独角兽。朋友回说那只独角兽就是你。赖声川说自己的个性确是如此,只愿意走自己的路,甚至必须有所不同。
于是,从不改编他人戏剧的赖声川,这次带来了剧场界公认难搞的契诃夫的《海鸥》。契诃夫曾郑重在剧本封面上写下“四幕喜剧”几个字,即使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甚至此后无数大导演,依然茫然说那明明就是一部悲剧。
赖声川却说,喜剧不是关于得到,悲剧也不是关于失去,你得放掉既定的概念,才可能走进契诃夫;他也说,当你能看懂契诃夫,也就能看到日常生活表面下的波澜起伏了。
问:很多观众说看不懂契诃夫,您觉得要想看懂他需要哪些能力?
赖声川:其实什么人都可以看懂契诃夫,但是可能要改变一点看戏的概念问题。因为他的戏里会有人睡着,有人可能就在吃饭,聊一些无聊的事,它不是你平常看的好莱坞电影或者连续剧那样的说故事方式,不是你对戏剧期待中的一切,契诃夫把那些都抽掉了。
还有,可能得稍微在人生方面有一点体验吧。但这个体验不见得是你看破人生或者参透人生什么的,而是说,如果你能看懂契诃夫,也许你就有能力坐在路边看交通和人群在你面前走动,然后你可以感觉到一种美感。或者你回家看到你家人的一种互动,你看到这个人可能有一些话想说但藏了三年都没有讲;那个人呢,可能默默地做了一些事情是让你高兴的然而你没看到;另外一个人可能一直在逃避一些什么事情,可是表面上装的很正常。如果你在生活中能够看到这些细节的话,你看契诃夫的戏你会感觉到是很过瘾的一种对生命的描写。
丁乃竺: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契诃夫,就是很难懂,甚至很多人觉得他的东西很闷,很无聊。长久以来,契诃夫说《海鸥》是个喜剧,可是别人怎么看都是一个没有什么高潮迭起的剧。我是一直到后来赖老师开始用他的方式来解读契诃夫,我才开始了解那一种黑色幽默,了解到他是站在更广更深刻的一个角度,其实是一个很悲悯的东西。(他)在看这些人,这些人是这样子的荒谬,这么搞笑。
赖声川:它其实是一种被抽离和被结构的黑色幽默,你得拉远了看,看人类这个动物,他会搞出各种游戏,然后玩各种游戏来伤害自己,不是很好笑吗?然后才会产生一种悲悯,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机械反应。这个里面有一种美感,它是属于契诃夫的美感,是一个对生命更深的体认。
问:可能这也是很多人不能理解您说它是喜剧的原因,大家对喜剧的定义和理解往往是令人捧腹大笑并且有个圆满结局的一种作品。
赖声川:说实话我也不完全赞成它是一个喜剧。但如果二选一的话,悲或喜,你选悲,对于导演来讲它会陷入一个无解;如果你选喜,它就有机会变成一个非常丰富有意思的作品。你会看到他们中一些人的错误,然后看到这些错误你会笑,笑完了之后你会有悲悯,这是另外一种看待人生的态度。
问:您原来的戏剧似乎每一部剧都会关注一个社会议题,现在演契诃夫,您关心的社会议题是什么?
赖声川:哈哈,很善。它其实更大,它在讲人生,它不是讲任何一个社会的议题。但是你要是找,非常多。尤其跟艺术有关,跟演艺界有关,跟名望有关。妮娜是一个乡下姑娘,她想成名,你想这跟我们现今社会有多么大的关系,她多么想能跟一个有名的作家混到一起,那就等于名利这条路完全打开了,但后来尼娜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契诃夫一百多年前讲的事情,我觉得跟今天完全吻合。
丁乃竺:所以其实讲起来,我们以前都解读妮娜就是最纯真的一个人,但是她的纯真里面她又不是那么纯真,因为她曾经对名望那些东西那么向往,所以她会陷入果林这样一个大名人。最后那一段我觉得很感人,她跟康丁讲,她的生活其实到最后是要撑下去,真的非常黑色非常无奈。她的生命才20几岁,她已经觉得这个生命是要撑下去。
智慧的源头
赖声川常说,智慧首先在于练习如是——看到事物的原貌。看见落日的时候,不会想到某位作家的描绘,不立刻下结论说有多美,赶忙找出相机拍照;看见一杯水的时候,不去想为什么有一杯水,装在什么容器里,它有没有价值。不要去分析它。他将之称为“一个净化的过程”。而净化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在放弃已经使用习惯的概念的同时,也放弃了这么多年来概念所赋予你的安全感。
“一个人能不能积累智慧,主要是看他懂不懂得‘如何看’这个世界,如何看自己的动机,如何看自己的习性,如何看自己的生命经验。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我的戏好看,有种复杂的联系在里边,因为生活中许多积累也不是那么直接,而是含蓄的。我在其中求一种没有分别心的状态。”
问:您常常说创意可以教,只要具备智慧和技艺。但技艺好学,智慧难得。您觉得智慧要怎么教呢?
赖声川:嗯。其实智慧其中一个来源就是从去除概念开始,看契诃夫的剧也是同样,你如果存在一种强烈的概念是关于什么叫戏剧,那你看的时候可能就碰壁了,你就看不懂。如果试着去掉它,那在这方面你就得到了很多智慧,就能看得更宽广。
我们从小就养成接受各种概念的习惯,通过这些概念,学习、整理这个世界,但是慢慢地,我们就只是把新的所见,装在旧的抽屉里,这样看到的世界再多,不过是投射那个过去的我而已。这样就限制了创意的组合和发生。
其实做创意,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可以说就是自己出一个问题,自己来答。这个模式其实是某一种连接的模式,怎么把几个不同的东西连在一起,我在书里面也讲到,其实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创意,就是把A跟B连起来。这个连接是不是所谓的因果关联?万物一体?我自己非常欣赏《如梦之梦》这部戏,它把观众和演员连接在一起,把观众连接到更大的东西,你把这东西叫全人类也好,叫宇宙、道也好,我一直向往的目标是做这样的戏。
问:您说过《如梦之梦》是第一次您把佛法真正拿到戏剧里面来讲,对此您以前是很谨慎的,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赖声川:我觉得可能是找到了一个方法把它戏剧化吧。因为哲学这个东西你如果只是拿出来讲,我觉得观众马上关掉,他不要听的。你如果要跟他说教,任何说教,甚至任何剧中的主题意识,观众都是要关掉的,他不是来听道理的,他来看戏是来感受,然后情感投入,从情感投入中从剧情和人物中他能够有所感悟,所以可能在“如梦”里我找到了一个方式,把一些比较哲理化的东西变成戏的一部分让你无形中就可以感受它。
丁乃竺:我觉得可能也跟那个戏的整个灵感是在菩提迦叶得到的有关。当赖老师做出说要把观众放在中间,就像那颗菩提树一样,所有表演者环绕它的决定开始,这个戏就从这个灵感就开始整理出它的一个方式来,就可以来传达他自己对生命的一种看法跟信仰。
问:您二位会不会很希望透过戏剧来传达你们的一些感悟或者学佛的心得?
赖声川:不一定哎,要看到一些适当的机会才行。其实身为一个学习佛法的人,我们是不随便推荐给人的,一切都要看缘分。我觉得佛法是真的蛮深,它深到真的是可以超越契诃夫的深(笑),所以人家看不懂契诃夫又怎么看得懂佛法。她(指丁)常常讲,佛法的难就像量子力学一样难,那你在一个戏中要怎么讲量子力学,你怎么让观众去了解量子力学所有的理论?对佛法是一样的,它就是那么难的东西。
丁乃竺:因为它在讲探索生命的真相,只有真正对生命真相有兴趣的人,才可能对佛法感兴趣。我们这个行业很特殊,每年定期有一个作品跟大家见面,对创作者而言他其实不可避讳的,一定会把自己的生命态度呈现出来。你可以说它是佛法,也可以说它只是生命态度而已。我觉得在赖老师所有的作品里面,比方他对于悲喜剧的处理,这些都是在反应他对生命的一种看法。我这些年看赖老师的作品,可能“如梦”是最大的一个转折,因为我自己觉得那是因为灵感来自于菩提迦叶,所选择的题材跟生死有关,于是他就非常直接地碰触到了生跟死的问题,生死问题本身就与信仰相关。
梦回桃花源
赖声川说,生命真的太浩瀚了,当你能真实体会每一刹那里的一切,就会发现,我们个人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网状结构中的一小环而已。宇宙间万物相互依存,没有一样东西独立存在于世。
这些细微的体会是他戏剧创意的来源,也是他很多作品中呈现出的生命态度。他常常与太太一起进行闭关修习,对生命真相的探寻,是他们结成知己的根本原因。
问:我知道您二位常常会一起做一些闭关活动,能否分享一下去年去不丹圣地修行的经历?
赖声川:哦,那是很特别的一个圣地。去那里的过程非常艰困,车子要走两天,爬山要走三天,所以一共五天去五天回来。但是到了那个地方就很特别,因为那里人烟罕至,它太难去了,我们自己去,这个过程我们很受启发。我们在那边等于有一个十天的闭关。
问:您说的启发能不能跟我们分享,是怎么样的启发?
赖声川:那里没有水电没有通讯,你没有任何一点一般生活里边的干扰,然后你就被逼着去面对平常逃避的最重要的东西。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忙碌,从早忙到晚,说我没时间这样没时间那样,其实在逃避嘛。逃避什么?逃避自己!逃避与自己相处的时间。一般人要是不理解的话,日子可能就这么一直过下去了。
佛法里边讲,能不能最起码了解到我们的心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人的心是非常伟大和了不起的,它就一直在这么运作,但是我们都不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没有看着它,没有管着它,没有能控制它。那个地方真的非常非常艰难,去到那里,住在很简单的环境里,但是看到的是最壮丽漂亮的山水,有非常好的空气,好像进到了桃花源。那个地方曾经很多伟大的修行者在那里修行过,你就会感觉到充电充饱了,再回到这个世界上。
丁乃竺:在那里所有东西都还原到人类最根本的状态。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厕所,是别人好心在野外帮我们搭了一个。晚上我们抬头就看得到星星,下雨你得撑把伞去上洗手间。那个过程真的非常非常辛苦,那个辛苦我一辈子没有经历过。路没办法走,全部是泥巴、岩石和树根。而且它那个纬度很高,到最后你需要手足并用爬上去。
赖声川:我们去之前一直在问这个地方怎么样,网上找不到一张照片,表示这个地方没有被拍过。
丁乃竺:很特别。我觉得最特别的一点是你很自然会感觉到我们这些文明人平常认为自己很能干,到那边才知道自己多么的无用。就是所有你习惯的一切都没有了。我们连生火都有困难,不丹人就帮忙。我看他们好能干,一下子噼里啪啦,火就生起来了。到那种时候,你就会回到最根本的自己。
赖声川:我们走的比较慢,好比说你五点钟要到达目的地你就可以休息了,但我们到七点还没到,然后天已经全部黑了。然后你可以想象,天已经黑了,全部泥巴地,很滑的岩石,你必须在黑暗中走,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你不知道目的地长什么样子。然后带的人,你会碰到一些人你就问,嗳,还有多远,哦,快了快了。那是?很快很快,二十分钟,结果三个钟头都还没到。有的人你会问他怎么样,他会说很近很近。多久?哦,大概四个钟头。哈哈。
丁乃竺:他们对时间的概念跟我们都不一样。后来我们都不太敢问了,因为问了就很失望。
赖声川:因为真的山中无甲子,根本没有时间的观念。他们那边真的从来没有人需要在几点钟要到达什么地方,他们就大概就好了。也不测距离,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在黑暗中走路的经验也是很特别的,因为你想嘛,我们在黑暗中可能有一点手电筒的光,可是你照不到多远,在黑暗的深林中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不知道目的地长什么样子,其实这是蛮棒的经历,在都市里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丁乃竺:我觉得人经常应该有一段时间真的回归到最自然的状态,当你把这一切都卸下的时候,你会真正面对自己。
赖声川:你会发现它好不重要啊。手机又怎么样,没电了,也没搜讯了,那怎么样?我们后来手机只用来做手电筒用。其实蛮好笑的。
问:现在常常早上起来第一个动作是看微信,有点机械化了。
赖声川:我就在幻想如果所有手机都是外星人的话。它们已经征服我们了,有一天它们会真的起来。因为我们已经变它们的奴隶了。
爱的艺术
赖声川夫妇初次相遇的故事是一段佳话。三十六年前,在那间叫“艾迪亚”的咖啡馆里,赖声川正抱着吉他弹唱,丁乃竺跟朋友走了进来,赖声川抬眼看到:好熟悉的感觉,心想,就是她了!
演员黄磊曾经这样写:赖声川和丁乃竺的关系很让人感动,他们互相呵护。丁姐是个非常全面的人,把赖老师照顾的很好,但两人在一起的时候,赖老师会给丁姐披衣服、夹菜,他想得很周到。台湾演员金士杰则说:他们俩人好像一个人,丁乃竺身上有一半的赖声川,赖声川身上有一半的丁乃竺。
两人共同经营“表演工作坊”整整三十年。从回台做戏剧拓荒,到创造亚洲剧场奇迹,这对工作搭档亦曾数次面临大的挑战。赖声川为辛亥革命百年制作音乐剧《梦想家》一事因为政治原因倍受谩骂和攻击,丁乃竺说这是他们夫妻俩遇到的最大挑战。最终他们选择沉默面对,“不辩解需要更大的勇气,也许这是最好的修持‘忍辱’的时刻。”丁乃竺说,“我们之间最特别的,就是我们在各种上坡下坡,都愿意彼此互相扶持。这一点特别珍贵。”
问:您二位的婚姻是戏剧圈公认的模范夫妻。很多修行的人说最难的修行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很多人在关系方面都有各自的问题,这个部分您二位有什么建议?
赖声川:我觉得双方一定要多沟通。而沟通的先决条件就是关心嘛。你要关心对方,你才会想跟她沟通。如果你不关心,或者关心减少了,就变冷漠了。但是我觉得这两者是互相的。就是你有沟通的愿望,那个关心就会增长。
丁乃竺:还有我觉得倾听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去听他,而且是听到他的内心的需求。因为我发现很多人讲沟通,他就是要表达自己,他并没有在听。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大部分人都认为别人想法跟他是一样的,觉得我们应该看法一致,你怎么没有明白我呢?你这个不明白就是表示你不关心我。但其实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同一个家庭,相同的父母,生下来的小孩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释迦摩尼佛曾经讲过,没有两个人看颜色是相同的,我看到的红色跟你看到的红色是否是同一个红色?所以其实无法比较。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简直把我打了一棒!原来我们连看颜色都无法确定是不是一样,我们只是共许它为红色。
我们如果开始了解这一点,我们才可以开始知道原来我们是有着不一样,但是又有着一些共通性,所以我们要沟通,所以我们要来倾听。这个时候才有沟通的可能性。
问:所以好的关系真的需要双方都来学习。
丁乃竺:对,爱是要学习的,是一种能力。我很感谢德国的心理学家弗洛姆在1953年出的一本书叫《爱的艺术》,很触动我。我也让我的孩子们看过,我希望每一个年轻人都可以看了这本书才去谈恋爱。他讲到了爱的几个条件,包括你能不能主动地给予。
很多人说给,他其实不想给,是很被动的,或者他有一些目的,我给你是因为我想要得到更多。但我们在爱的能力里,强调一种主动给予的能力。在主动给予之后就是一种真正的关怀,比方我说我爱一朵花,但是你们没有看到我照顾一朵花的话,那不叫真正的爱,那只是我喜欢看到花给我的感觉而已。真正在爱当中,他必然愿意承担责任。
爱当中很重要的是知识,一无所知的人其实一无所爱。我们常常听到很多老夫妻说,我太了解这个人了,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一听他这么讲我就知道他已经不了解她了,因为你要知道生命随时在变化,社会和环境在变化,你自己也在变化。
还有一个是尊敬,在爱当中,必然要有尊敬。一般人讲尊敬就是下对上,可是尊敬这个词的英文是respect,拉丁文中叫“我能如实地注视对方”,你是怎么样,我就接受你。而我们很多人所谓的爱,是想象中的一个对象,于是你在爱这个人的时候,你恨不得他能变成你所想要的那个人。这个不是真正的尊敬。
在我生活中早期的时候,包括对我的孩子,我有时会想,如果他能怎样就好了,但是我会马上回来看自己,我发现那是我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这个孩子或者对方的问题。
问:赖老师,丁姐对您的生活最大的影响或者改变是什么?
赖声川:这个太多了,很难一次讲清楚。她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基本上你需要什么,她都能给你。
问:哆啦A梦?
赖声川:对,她就是。那所以,我还能,我不需要说别的了。哈哈。
问:丁姐呢,赖老师对您的影响和改变是什么?
丁乃竺:我觉得赖老师对我而言,他就是个很纯的人,很纯粹的一个人。我从一开始认识他就觉得他是个很敏锐的人,他的感官非常敏锐,比如耳朵,连鼻子都很敏锐,比如他听到好的音乐,他的那种感动我就会想,哇,真的(太特别了)。他有一颗很美的心,有点像小孩。对我的影响当然就是我很希望他能保持那颗真心。一颗很纯粹的心是很重要的,我们当然要保护它。
问: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梦想和想要做的事情?
丁乃竺:我很奇怪我从很年轻时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支持别人的人,一个supporter,我就是觉得自己擅长做这个。我不是很喜欢站在人前面。
问:现在我们常说女性要去实现自我,实现女性的价值,这个跟学习奉献和给予,您觉得有冲突吗?
丁乃竺:我觉得没有冲突,因为我刚刚讲说我自己觉得我属于可以支持别人的人,一个supporter,所以我的工作已经是圆满了。如果有一个人觉得她有一个梦想,她当然应该去尽量走向她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支持别人。哈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