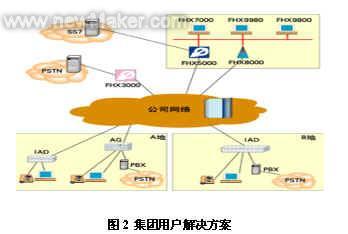王充闾散文风格论
(以下三篇文章是“辽宁省社科联科研立项资助项目、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研究支持项目”的研究成果。已收入《走向文学的辉煌—王充闾创作研究》(王向峰主编)一书,拟定于中国作家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一个作家作品风格的形成,标志着其创作的成熟。成熟就意味着个人作品的高度的独立性和明晰的辨识度。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只有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才会在作品的丛林中凸显出“我的作品”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歌德也认为风格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所以说,作家作品的风格是真实可感的艺术存在,对风格的探讨和研究就是要揭示出这种艺术存在,用理论话语使其明朗化,从而给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在共时的文学场域以及在历时的文学发展史上定位。因此,对于当代著名散文作家王充闾的创作进行理论研究时,对于其散文风格的探讨也是不容回避的课题。可以说,王充闾的散文创作风格既是稳定统一的,又是丰富多样的。作品风格的丰富多样性和稳定统一性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在艺术风格的形成问题上首要的当然应先具有稳定统一性。然而,作家风格的稳定统一决非意味着停滞、凝固或贫乏。大凡高明的、有追求的作家总是“本调”强烈却又毫不单调的。艾青说,一个伟大的诗人,他不仅在题材所触及的范围上有广泛的处理,同时在表现的手法以及风格的变化上有丰富的运用。布封也说过这样的话:“随着不同的对象,写法就应该大不相同;就是写表面上似乎最简单的对象,文笔固然要保持着简单性,但另一方面却也还不能千篇一律。一个大作家绝不能有一颗印章,在不同的的作品上都盖着同一的印章,这就是暴露出天才的缺乏。”[1]王充闾的散文创作并不满足于单一题材,单一风格的重复,而总是不断自我超越,创作出风格多样的作品。因此,本文首先对王充闾不同题材的散文创作风格进行辨识,然后概括出他的散文创作的主导风格,即“本调”。一、历史文化散文的冷峻通透在王充闾的多种类型的散文中,历史文化散文是最能展现他深厚的文学、史学和哲学功底的一种。从更广阔的视界看,他的历史文化散文是在中国具体的文化、文学语境中诞生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精神产品的生产潮流是由文化精英们引领的,90年代以后,“新时期”文学的强劲势头很快过去,一个短暂的充满诗意的时代终结了。诗歌和小说所需要的时代激情与想象力,逐渐被市场、消费和日新月异的物质世界所消磨,人们的注意力投向了层出不穷的物质潮流。国家经济、政治的核心指向GDP的增长幅度,精神世界的事情被暂时搁置,知识分子式的乌托邦精神不再时髦。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心疲惫不堪的人们无心于形而上的追问与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追求,而将自我放纵于肉体的狂欢和感官的刺激之中。人们只专注于当下的现实利益纷争,而没有兴趣关注历史。人们进入了一个断裂无根的处境中,进入了一个“集体无思时代”。我国的这种时代的思想状态再加上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传入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出现了大量没有深度平面化的文学作品。这使中国的文化精英们感到忧虑,于是他们试图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精神,从而在学界引发了一场“国学热”。这场“国学热”在文学界则表现为历史小说创作和历史文化散文创作的兴起。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孕育出来的。显然,王充闾对那种消解诗性、消除深度的文学创作是不赞成的。他说“随着社会的日益商业化、物质化,随着传统的理性和诗性的消解,随着文化价值取向的世俗化,有些人往往满足于官能刺激和‘众声嘈杂’现象,从而阻窒了深度的精神阐扬和艺术开掘。但是,作为一种内在追求,我仍是乐此不疲,在散文创作中,执著地追求诗性、哲思、历史感的结合。”[2]王充闾的这种文学追求突出的体现在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中。综观众多作家的历史文化散文,可以看出他们在创作理念上具有某些一致性,即:追求文、史、哲的融合,用诗性话语在叩问历史的沧桑中对历史进行深度的意义拷问。但是虽然是同样的文学题材,在进入个人化的写作之后,便会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风貌。谢榛《四溟诗话》有一段话:“作诗譬如江南诸郡造酒,皆以曲米为料,酿成则醇味如一。善饮者历历尝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苏州酒也,此镇江酒也,此金华酒也。’其美虽同,尝之各有甄别。何哉?做手不同故尔。”[3]作诗如同造酒,作文亦然。以王充闾和与他并肩南北的余秋雨作比较,两人同是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但风格却有所不同。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常以个人想象回到历史现场,复活历史人事,将自我深入历史之中,注重抒发个人性的感受(从文章处处出现“我”就可看出),如此使其散文洋溢着浓郁热烈的个人情感;而王充闾则在状写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时,以一种清新雅致的美学追求和冷隽深邃的历史眼光,渗透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在美的观照与史的穿透中,寻求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实现对审美世界的建构,对意味世界的探究。因此,他的散文少了余秋雨散文的那种激情洋溢,多了冷静的理性思索。这样他的历史文化散文呈现出一种冷峻的独特风格。对此,著名评论家谢友顺说,与余秋雨的煽情比起来,王充闾要显得冷静很多。冷静,并不等于内心就趋于一片静寂了,这是王充闾的可贵之处。他不机械地追求回到事实中的历史现场,他走的是以诗证史、以诗言思的话语道路。正因为这种冷静的创作心态,王充闾就像一位站在高处俯瞰历史现场的旁观者,更能清醒的洞悉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人物的命运,仿佛一切尽在他的“法眼”掌握之中,可谓“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这种对于历史人事入木三分的洞察力和条分缕析的理性阐释,使其文章呈现出一种通透的风格。王充闾说写作历史文化散文的时候是一只脚站在往事如烟的历史尘埃上,另一只脚又牢牢地立足于现在。他立足于现在而与历史倾心交谈,但他的宗旨绝不是简单地再现过去,而是从对过去的追忆、阐释中揭示它对现在的影响和历史的内在意义,从而开创一片“以史明思”的审美境界。王充闾在散文创作中将史、诗和思三者融合在一起,在诗性的叙述中对历史进入哲学层面加以反思。他以深邃而敏感的洞察力发现隐在喧哗的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并以高人一等的智慧对这些规律做出明晰的解释。现列举几例如下:有限与无限。当年在开封东北处的陈桥驿,赵匡胤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赵宋王朝。但仅仅三百多年后,大宋未帝赵昺在蒙元铁骑的追逼下于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王充闾来到陈桥驿后,想起这段历史,大发感叹。在《陈桥崖海须臾事》中,他说:“古往今来,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存在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交叉点上,无论人们怎样冀求长久,渴望永恒,但相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却只能是电光石火一般的瞬息、须臾。生命的暂住性,事物的有限性,往往使人堕入一种莫名的失望和悲凉。但这又是难免的,因为只要生活在具体的时空里,每一个个体的人与事就难免显现出真正渺小和空幻。为了摆脱这一根本的局限性,超出生命长度,得到更多更多,无数英雄豪杰费煞移山气力,耗尽无涯岁月,到头来总不能如愿以偿,最后只好望望然而去。”存在与虚无。《叩问沧桑》中汉魏故都洛阳当年是何等的繁华,可是如今那巍峨的宫阙、高耸的城墙,金碧交辉的画楼绣阁、古刹梵宫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风烟之中;还有那石崇的豪华别墅金谷园,当年是飞阁凌空,歌楼连苑,而现在一切一切,都已荡然无存;面对着北邙山,王充闾感叹:“无论生前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最后统统地都在这里碰头了。像元人散曲中讲的,‘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纵有千年铁门槛,终归一个土馒头。”王充闾纵观历史,思量世事,发现了一个令人嗒然无奈的事实:“是非成败转头空。”历史的循环。在《“无字碑”》中,王充闾写到了南唐后主李煜之死。李煜降宋后,却未能得善终。在他生日那天,宋太祖亲自派人去为他祝贺生日,并亲赐下有毒药的御酒。李煜奉旨饮下后,不久便气绝身亡。这一天是七月七日,王充闾惊奇的发现李煜出生恰好也是七月七日。宋太祖一生凶残猜忌,恶行甚夥。可是一个半世纪后,他的嫡亲子孙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落到金太宗的手里,其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比后主李煜还要惨重。后来王充闾在《土囊吟》中写到:“历史的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像宋太祖不问任何情由,只因‘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便蛮横地灭掉南唐一样,金太宗攻占汴京,扑灭北宋,也是不讲任何理由的。而且,要后主和道君皇帝都是诗文兼擅,艺术超群,‘好一个翰林学士’,却都不具备做皇帝的雄才大略。”“但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赵佶之流的败亡,自身没有责任。恰恰相反,他们完全都是咎由自取。可以说,赵佶的可悲下场,他的大起大落,由三十三天堕入十八层地狱,受尽了屈辱,吃透了苦头,都是他自已一手造成的。”《狮山梵影》写了明初朱元璋、朱棣、朱允炆祖孙、叔侄三代君王的行藏、史迹与传说。朱元璋在当皇帝之前曾有一段在皇觉寺当和尚的经历。朱元璋死后,册立太子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允炆的即帝令朱棣颇为不满。后来,朱棣竟然举兵攻占南京,夺了帝位。而建文帝朱允炆在亡命途中,竟然也跑进庙里做了和尚。关于这一有意思的历史循环,王充闾说:“乃祖僧为帝,阿孙帝作僧。这倒不是朱家与佛门有特殊的夙缘,更非一场简单的历史游戏,其间存在着制度方面的深层原因……肇祸的根源乃在朱元璋身上,正是分封诸王制度造成了干弱枝强、指大于臂,最后祸起萧墙,无法收拾。”文化和人性的悖论。王充闾说“古代的知识分子大致有三类:在朝的,在野的,周旋于朝野之间的。不管哪一种,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总的说,最后都是悲剧性结局。入世的实现了儒家经邦济世的社会价值理想,获得了政治的权力、地位,却丧失了自我,失去了人生的自由与安宁;出世的获得了个性自由与人格尊严,进入纯粹的精神世界,却放弃了知识分子固有的社会理想和人生抱负;第三种在穷达的张力之种苦撑着,周旋着,也并没有人生的快活。”王充闾在散文创作中,塑造了这几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一种是积极入世的,如《孤枕梦寻》中的陆游、《用破一生心》中的曾国藩;一种是隐逸避世的,如《忍把浮名换钓丝》里的严光、《寂寞濠梁》中的庄子;还有一种是入世中出世,或者从出世中寻求出路的,如《青山魂》中的李白,《春梦留痕》中的苏轼。这几个不同知识分子类型的代表,在王充闾的笔下,都是悲剧人物。王充闾不满足于单纯地讲述人物的悲剧事件和悲剧形象,也没有替主人公大发悲凄之感和自己的悲悯之情,而是以冷峻的目光在文化和人性的深度上积极探究产生悲剧的原因。他把产生悲剧的原因归结为文化的悖论及它内化到个体的人后所发生的人性的悖论。黑格尔在《美学》中说,艺术家所选择的某对象的这种理性必须不仅是艺术家自己所意识到的和受到感动的,他对其中本质的真实的东西必须按照其全部的广度和深度加以彻底体会。王充闾学贯古今中外,另外加上长期从事政务,他看待问题总能保持清醒而通达的认知。所以面对历史人事悲欢,他没有随之情绪化的大喜大悲,而是透过历史表象深入到历史本质之中,对其进行冷静的思考和透彻的阐释。如此,他的历史文化散文创作既有同题材散文创作所具有的深邃厚重的特点,同时他以冷峻通透的风格而独树一帜。二、生活情感散文的醇厚绵密古印度婆罗多弁尼的《舞论》提出“情”是“味”(美、风格)的灵魂,并以八种艺术“情味”代表八种风格。黑格尔则把艺术情趣称为“情致”,他说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的来源。可以说,没有情趣便没有风格,而情趣美是作家在特定的情绪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作家进行创作时,往往由于作家个人的人性气质和创作习惯等原因而趋于遵循一定的审美情态。依据心理学所公认的关于人的三种典型情绪状态,我们把作家进行艺术创作时的审美情态也分为三类:激情、热情、情境。激情是激烈而沸腾的情绪状态,处于这种情绪状态的创作主体因遭遇环境的强烈冲击,心潮翻卷,汹涌起伏,不能自已;与激情相比,热情是较为深沉的情绪状态。这种状态下的艺术情趣一般比较幽邃醇厚,例如杜诗不象李白那样掀雷激电,倒海翻江,而是显得沉郁顿挫、情深趣远。鲁迅的风格也不像郭沫若那样滚烫灼人,而是寓炽热于冷峻。他认为情感太激动时不宜创作,而惯于“静思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4]将冷静的观察,深沉的思索和绵厚的情感镕铸成完美的艺术作品,给人以荡气回肠,忧愤深广,余味曲包的审美情趣;情境,是一种比较持久和弱型的情绪状态。在这种情绪状态下,主体的创作心境与客观的环境相和谐,怡然自得,宛如一泓静宓的池水,几乎看不到情感波澜,最宜产生花鸟缠绵,幽鸟鸣琴的审美佳趣。如果将王充闾的生活情感散文创作的审美情态加以归类的话,应是“热情”这一种。王充闾的生活情感散文大多是怀旧型和追忆性的。由于空间的变更和时间的沉淀,炽烈的情感已经澄静下来,隐在心灵深处,变得绵密而厚重。那么在处于此种创作情态之下,王充闾的生活情感散文呈现出一种醇厚绵密的风格。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里所言:“我们不难看出一切风格都表示一种心境,或是松弛或是紧张,或是激动或是冷淡,或是心神明朗或是骚乱惶惑。”[5]王充闾经历了一个具有严重的情感创伤性的童年,在他的有关童年风景、人事的散文中,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山河的破碎,苦难贫困的生活境遇,多位亲人的相继亡故。可以说,他的童年世界是“悲惨的世界”。但是他的散文中却没有个人撕心裂肺的悲情宣泄,只是似乎不动声色的将往事娓娓道来,文字的表面不见飞扬四溅的情感浪花,但是读者却能够体会到文字背后汹涌着的情感深流,因此这种隐在心灵深处和文字深处的深厚绵密的情感最能感动人心。在《望》中,他用血泪之笔讲述了在短短的几年内大姐、二哥、大哥相继死去的情景。他的大姐爱读《红楼梦》,甚至读的泪眼模糊,食不下咽。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姐姐后来不知患了什么病,留下一个刚刚两岁的女儿故去了。他的姐夫是一个电话接线生,姐姐的死让人悲痛欲绝。王充闾在散文中描绘了当时的情景:一天,他托起两岁的女儿,凄然地交给我的母亲,然后长跪在地下,连着叩了几个头,呜咽地说:“妈妈,给你增加了拖累,实在是对不起。原谅我这个不肖的儿男吧!”就在这个风雨凄凄的当晚,鸿飞冥冥,一去便再无踪影,始终音信杳然。这样,母亲便怀抱着我和外甥女这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我们整天嚷着要奶吃,母亲眼含着泪水,敞开衣襟,把两个已经瘪的乳头分给我们一人一个。可是,由于吃不到实惠,两人又同时哇哇地哭叫起来。屋漏偏遭连夜雨,在家人还笼罩在姐姐死去的悲伤之中的时候,二哥又得了结核菌突然病倒了,最终也离开了人世。二哥写一手好字,家里的墙上留有他的墨迹。每次,“妈妈眼望着墙上的字迹,想起来就痛哭一场。为了免去触景伤怀,睹物思人,父亲伤情无限地花费一整天时间,用菜刀把墙上的字一个个铲掉,然后再用抹泥板抹平。”接着,大哥患了疟疾,庸医误诊,下了反药,出了身冷汗后,便猝然断气了。如此重大的打击,母亲再也撑不住了,“病倒了三个月,形容枯槁,瘦骨支离,头发花白,终朝每日以眼泪洗面。”但是母亲特别刚强,常说“任可身子骨受苦,绝不让脸上受热。”他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接下去,作者追忆了有关母亲和“我”的一幅幅场景:母亲知道误会“我”偷拿家里铜钱后的悔慰、起早贪黑的为“我”做可口的饭菜、在昏黄的灯下为“我”缝补衣袜、“我”上县中学临走时的叮咛,其中含有多少心酸,多少欣喜,多少期盼。“我”终于没有辜负母亲的心愿,有了理想的工作,但是却很少有时间去陪母亲,结果母亲孤独得离开了人世,这让“我”内心充满了永久的悔恨。若干年后,作者依旧自责:“‘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现在,只能抱憾于无穷,锥心刺骨也好,呼天抢地也好,一切一切,都无济于事了。”《望》主要是追忆母亲的文章,而《“子弟书”下酒》则是追忆父亲的文章。由于生活的不幸,父亲经常借“子弟书”来排遣愁苦,常常是唱着唱着,“父亲就声音呜咽了,之后便闷在那里抽烟,一袋接着一袋,半晌也不再说话了。”在这里,作者并没有站在父亲的角度为其抒情,但其中复杂的情感读者又都能体会到。本来父亲滴酒不沾,但是由于心境不佳,常常是借酒消愁,醉了就大唱“子弟书”。对于父亲,王充闾没有写关于他一生的重大事件,也没有直接的抒发个人情感,只是抓住他的爱好和一些生活细节娓娓道来,但是每一位读者都能体会到文章中的感人力量。《青灯有味忆儿时》记述了儿时私塾条件的艰苦、学业的紧张以及塾师刘璧亭先生对自己的严厉又慈爱的启教,也追忆了自己被塾师的榆木板子击打的疼痛,描红临贴、对句作文的辛苦、体悟及和“嘎子哥”扮演的种种恶作剧。由于时空的变化,作者与事件产生一种若即若离的审美距离,无论是凄苦还是欢乐都已不那么强烈,在回忆中都已变得醇厚有味。正如文中所言:“经过了数十载的岁月冲蚀、风霜染洗,当时的那种凄清与苦闷,于今已在记忆中消融净尽,沉淀下来的倒是青灯有味、书卷多情了。”此外,《碗花糕》中我与嫂子的感情,《我的第一个老师》中我与“魔怔”叔的感情,《节假光阴诗卷里》中我与“书”的感情,《故园心眼》中我与家乡的感情都在王充闾散文文本的底层缓缓流淌,形成了深厚而绵长的情感暗流。众所周知,情感是散文创作的法宝之一,无“情”则无文。艺术创作中,在要求情感真实的前提下,具体如何表现情感却不拘一格。有的文章直抒胸臆,激情澎湃,有的文章则委婉含蓄,深情内敛。王充闾的生活情感散文的情感表现属于后者。所以无论写亲情、写友情、写乡情、写爱情、写师生情,他都让这此情感积沉在文字的底层。如果说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对情感采取淡化方式的话,那么他的生活情感散文采取的则是深隐的方式。将情感淡化是为了排除情感对认知的干扰,保持审视和分析问题的客观性与明晰度;将情感深隐是为了避免情感在文字表面激荡时所造成的挥发,保存更加饱满厚重的情感含量和力度以撼动人心。所以前者呈现出冷峻通透的风格,而后者呈现出醇厚绵密的风格。三、智性散文的剀切深微文学创作是情感过程和认识过程同时作用的审美创作活动。情感过程以认识过程为基础,认识过程指导和制约情感过程。情感过程以审美的情感态度和情感评价的形式出现,产生艺术的情趣美;审美认识过程则着重于对生活底蕴和本质的真的追索,表现为识度美。对于王充闾而言,这种识度美不仅表现在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中,在他的智性散文中表现的更加突出。如果说王充闾的生活情感散文更多的表现醇厚绵密的情趣美的话,那么他的智性散文则更多的表现出剀切深微的识度美。文学作品的识度美与作品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作家柯勒律治在《关于风格》一文中,认为真正伟大的风格必须有“巨大的思想力”。歌德将识度美看成风格纯正的重要标志。他把创作分为单纯的模仿、作风、风格三个等级,认为对自然单纯的模仿只是在“风格的外围进行劳作”,作风也仅是攫取生活现象,只有风格才使作家“跨进真正的圣殿的大门”,而“风格是奠基于最深刻的知识原则上面,奠基在事物的本性上面。”[6]真正的文学风格不能没有识度美,更确切说,风格不能不以识度美作为基础。作家的思想认识能力是风格识度美的内在依据和先决条件。不具备高卓精审的观察、感受和认识生活的能力,作家就会在杂乱无章的生活现象面前踌躇不决,难以突入生活底蕴,抓住事物和事件的本质。叶燮《原诗》提出“胸襟”是“诗之基”的主张,还把作家反映现实的主观条件概括为才、胆、识、力四个方面,认为“识”是其余三者能否充分发挥的关键,说“使无识,则三者俱无依托”,又说“识明则胆张”,“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也不随古人脚跟”。[7]袁枚也说,创作“其要总在识”,有识“则不徇人,不矜已,不受古欺,不为习囿。”[8]作家对生活的审美认识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始终,如果没有独特而先进的个人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就不可能比别人“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万般事使得王充闾炼就了超凡的认识能力,使其智性散文作品达到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1986年初至1987年未,应《人民日报•海外版》约稿,两年间共发表随笔杂文40篇,如《李煜与爱因斯坦》、《镜子上面有文章》、《陆放翁为海棠鸣不平》、《以貌取人的教训》、《皮格马利翁效应》、《换个角度看问题》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王充闾的智性散文所达到的思想深刻性和论说的明晰度,记述有板有眼,论说有根有据,行文有声有色。比如《换个角度看问题》,王充闾首先从日本的一本畅销书《怎样进行创造性思维》中的一个故事写起,从而引出了关于换角度看问题的话题,并以苏轼和长沙女子郭六芳的诗和鲁迅评《红楼梦》的一段话来说明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就会产生不同结果的事实。接下去他写道:“事物本来是复杂的,多向的,因此,应该从多种角度去考察:解决问题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应该从多方面去探索。主体考察、审视思维客体时,只有从多角度、多侧面进行多向思考,才有可能获得全面、正确的认识。”然后,他列举的大量的例子反复说明如果不会变换角度来看问题,就会陷入死胡同;反之,善于多角度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就会开创新的境界。整篇文章将话题分析得深入透彻,给予读者极大的思想震撼和启示。1987年11月,王充闾出版了《人才诗话》。在这部智性散文集中,他从历史现象分析进入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就人才的培养、磨练、选拔、深造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的看法。如颜翔林先生所言,王充闾的人才观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人才学范畴,上升为对人的生存意义、生存价值、人格设计、审美情怀、生命智慧等方面本体论、存在论、价值论视角的认识。可以说,就这一问题的运思,很少有人能达到王充闾这样的关切和深刻的程度。因此,他的智性散文总体上呈现出剀切深微的风格。四、山水散文的清醇健朗《清山白水》是王充闾山水散文的代表。他的山水散文从其风格韵致上看,王向峰先生将其概括为清醇健朗。他进一步解释:“《清山白水》的清淳,是说其中有清真淳厚的质地;说其健朗,是说散文有立命于上述基点上的主体情思的刚健明快。这二者的艺术统一,是美的质地与显象之间的审美化成。”[9]《清风白水》里的大部分山水散文,王充闾绝没有停留在对山水景色的客观摹写的层面上,而是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审美情感和哲学思索投注到自然景观之上,从而创作出具有生命情感温度和哲学思想深度的审美的人化自然。在山水散文中,他常常将自我生命的存在形式,与山水景物实行审美想象性的物我浑融,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从而使主体生命精神在山水中畅怀适意,逍遥以游,忘却现世的痛苦与烦恼,获得纯粹的审美形式的体验,宣泄生命存在的感性冲动,达到对个体自由的提升,并升华出一种诗性生命的美感。这既契合中国道家的山水精神,又接近西方生命哲学的人文情怀,使两种哲学话语在王充闾散文所描摹的山水意境中得以对话和交流;另一方面他的山水散文中灌注了儒家的哲学精神内核,通过观鉴山水,寄寓了主体积极进取、兼济苍生、修齐治平的道德理念。在《雅隆河,一首雄奇的史诗》中,王充闾首先从夜色中的西藏着笔,为读者勾勒出一幅静谧、苍凉、浩渺的图景。他说,西藏“传奇的史事,特异的风习,迷人的景色,随处都可以引发雄奇的意境和奋发的情思。”接下去作者将视野和笔触锁定在“雅隆河”,又由此引出的关于文成公主的史话:“为着汉藏友谊、祖国大业,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女,以其宏伟的抱负、非凡的胆识和卓绝的献身精神,毅然离开温柔定富贵之乡,踏上了雪裹冰封、山高峻岭的险程,来到荒凉、落后、风习迥异、言语不通的西藏高原,充当促进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致力于吐藩王国的政治建设、民族发展与社会进步,实在是旷古未有,难能可贵的。”由此可见,王充闾在对山水景观的描绘之中,往往融入儒家的道德情感和伦理精神,使山水意象和意境表现出昂扬向上、刚健明快的气韵。《清风白水》写了如诗如梦、如烟如画的九寨沟的山水胜境。淙淙飞瀑、飒飒松风、关关鸟语、唧唧虫鸣、七彩碧波、杜鹃花萼、地衣松萝、原始森林共同营造了“充盈着质朴的美、粗犷的美、宁静的美的梦之谷、画之廊。”作者创设了一个如同童话和神话的艺术世界,破除一切现实存在的拘役,以一种超脱的自由感将自我的个体生命融入到大自然的母体之中,在散文创作中达到了天人合一的道家审美境界。就像作者在文中所言:“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假日,真像裸体的婴儿扑入母亲的怀抱,生发出一种重葆童真,宠辱皆忘,挣脱小我牢笼,返回精神家园,与壮美崭新的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综上所述,可见正是儒家、道家等多种主体情思蕴含在清真淳厚的山水意象和山水意境的创设之中,使其山水散文呈现出清醇健朗的风格。五、散文语言的古奥雅润英国文艺理论家德•昆西在《风格随笔》中说:“……需要一种技巧,以便使旋生旋灭的东西驻足停留,使蕴藏在内的东西体现于外,使变幻不定的东西成体成型,使暧昧模糊的东西明确具体化,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作者如何去驾驭体现观念的唯一手段的语言。”[10]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品的风格,当然也是离不开文学的根本材料——语言的。对于王充闾的散文来说,无论是历史文化散文、生活情感散文、智性散文还是山水散文,最终都是通过语言来书写的。尽管不同题材的散文有着不同的风格,但是在王充闾的散文语言运用上却有着古奥雅润的一贯风格。彭定安先生认为王充闾的“整体语言家园,是由以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话语为基础,又消化-吸收-融会中国古典-诗词语言,并以同样方式吸取了现代西方文学-学术话语,汇合三者,而形成他的新的散文叙事话语-语言世界”[11]他的概括是相当精当的。具体说来,王充闾的散文语言有如下几个特点:(一)中外诗文片段直接引文。王充闾语言特点之一就是他常常在散文创作中,随手拈来一句或一段中外诗文片段,融入行文里,然而却丝毫不显孤兀,因为它不露痕迹的化入他的散文整体话语之中,化为自己表情达意的语言因素。这样的例子在他的散文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比如王充闾写黄昏,仅开头一段四百多字中,就引了谢眺、王维、泰戈尔、高尔基、莫泊桑、赫尔岑、夏洛蒂•勃朗特等众多中外作家描写黄昏的诗文。现摘选《清山白水•黄昏》中的一节如下:黄昏、夕照,景色是迷人的。自从人类把自然风物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宇宙间的各种景观有了独立的美学意义之后,便有无数诗文咏赞它,描绘它。南北朝诗人谢朓的“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成了传诵千古的吟咏江南春晚的华章;而唐代画家兼诗人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则是一幅典型的北方风景画。在现代作家的笔下,夕照、黄昏更是多姿多彩。它具有美的形象,泰戈尔说:“黄昏时候的天空好像穿上了一件红袍,那沿河丛生的小树,看起来更像是镶在红袍上的黑色花边”。又是富有音乐感的。高尔基说,当太阳走到大地里面之后许久,“天空中还轻轻地奏这晚霞的色彩绚烂的音乐”。而且还有性格,有情感,在莫泊桑笔下,“那是一个温和而软化的黄昏,一个使人灵肉两方面都觉得舒服的黄昏”;在凡尔纳笔下,“太阳在向西边的地平线下沉之前,还利用云层忽然开朗的机会射出它最后的光芒”,“这仿佛是对人们行着一个匆匆的敬礼”,赫尔岑些得更是富有良知,“这魅力的黄昏,过一个钟头便会消失了。因此更其值得留恋。它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在别人还没有厌倦之前叫他们珍惜自己,便在恰当的时候转变成黑夜。”与原来黄昏竟是这样的充满情趣,莫怪夏洛蒂•勃朗特称许它是“二十四小时中最可爱的一个小时!(二)古典韵味的现代话语。王充闾的散文中散发出一种古香古色的味道,他常常化用古典诗词中的字句,而用现代语言的语法规则言说出来。关于这一点,读过王充闾散文的人都有体会。每一篇,每一节都是例证,由于篇幅,此处不好引证。不过,单看文章的标题,我们就可以体会到王充闾散文语言的古雅气息,有的题目就是直接引用或按照七绝或五绝的格式自创出的诗句。如:人生几度秋凉、千载心香域外烧、用破一生心、桐江波上一丝风、陈桥崖海须臾事、纳兰心事几曾知、春梦留痕、青眼高歌、终古凝眉等。此外,他的散文中所散发出的古典韵味还体现在行文中出现大量的古代称谓和古诗句式。古代称谓。王充闾散文中有大量的古代称谓的词语穿插于语句之中,比如:“诗人傲睨一世,目无余子,而对普通民众,倒显得比较可亲可敬。特别是晚年,他在皖南一带结识了许多普通劳动者,像碧山的山民胡晖,五松山的田妇荀媪,宣城的酿酒工纪叟……通过他的生花妙笔,农夫田媪、牧竖樵苏、行役征人、孤孀弃妇、撑船汉、捕鱼郎、采菱女、冶铜工,都留下了鲜明的美好印象。”(《沧桑无语•青山魂》)古诗句式。王充闾有着浓厚的诗语情结,这不仅表现为他直接引用大量中外古今的诗文片段,还表现为他借鉴了中国古典诗词文赋精短严整的句式。比如“过去看到一些描写隐士生活的诗文,往往是北窗高卧,长松箕踞,或者寒林跨蹇,踏雪寻梅,都是逍摇自在的很。”(《寂寞濠梁•忍把浮名换钓丝》)这里就借鉴了《诗经》中常用的四字句式。此外,他还善用中国古典文赋中三字动宾短语句式。比如:“攀悬梯、穿石窟、钻天窗、走屋脊、步回廊、跨飞栈……”(《沧桑无语•劫后遗珠》)“……说唐婉命注孤鸾、克双亲、损夫寿、折子息,使陆母尤其厌恶,于是断然下令逐出家门。”(《沧桑无语•梦寻》)(三)学术色彩的诗性话语。王充闾散文语言中充斥着大量的诗话、文论话语和具有学术色彩的话语。比如在《清风白水》这篇散文中,他一开头就化用了中国古代诗话中的话语:“诗文讲究风格,古人形容苏东坡的词风豪放,说是像关西大汉执铜琶铁板,唱“大江东去”,而柳永的词则是缠绵悱恻,如二八女郎手执红牙玉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接下去说:“风景区何独不然!”其实是想把诗论泛化到现实的自然界之中。在讲到九寨沟“多的是古艳动人的神话传说”,他没有马上进入神话传说的讲述之中,而是进行了一番关于神话的产生的议论文字:“它们以原始思维的想象和幻想、虚构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出藏族劳动人民在征服自然的劳动、斗争、爱情生活中的经验、理想、感情和愿望。这种特异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形成,当然和它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环境,脱离原始状态较晚有直接关系。”讲完了一个神话后,又是一大段关于神话作用的议论文字:神话传说在民族的古代生活中,并不是一堆无机物的沉积,而是经常发挥着弥补生活中的不足的积极作用。有人说,梦是一个受压抑的愿望的满足。那么,神话则是贫弱民族的财产,——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却又无力实现的事情,就以代偿的形式付诸余生梦想,久而成为神话。因此,透过这些神话传说,不仅可以捕捉到历史的影像,而且,能够窥见远古先民的世界观、宇宙观、价值观,察知他们的真实感情和精神世界。以上从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生活情感散文、智性散文、山水散文和散文语言上进行了一番风格上的辨识。从中我们看出王充闾的散文风格是多样的,而且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任何一个作家总有一个主导风格,它贯穿在作家的所有作品之中,统帅和支配着其它的非主导风格,决定着作品的基调。正如明人胡元瑞评杜诗“正而能变,变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调,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12]那样,王充闾的散文创作也是不断的突破原来的题材、情趣和手法,但是其“本调”是一而贯之的。如何察其“本调”?我们知道,风格具有凝聚性特点。它植根在作品形象所显示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血肉联系中。这血肉的联系有个总的枢纽。它和作品中所有部分都水乳交融、息息相通。例如:题材的新颖性,主题的深刻性,思想的明确性,人物的形象性,情节的曲折性,环境的典型性,结构的精巧性,语言的生动性,风采的绰约性,情调的魅惑性,韵味的蕴蓄性等,都从各自角度,对着同一目标,射出形象的光束。这许许多多的光束,经过巧妙的组合,凝聚成一个焦点,这便是作品的总特点,也就是作品呈现的总体风格,即“本调”。依此,我们融合王充闾各类题材的散文的风格,然后找辨识出各类风格交集,这个交集就是:深邃冷峻、清醇雅致。这就是王充闾散文创作风格的“本调”。注: [1]布封:《布封文抄•写作的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页[2]王充闾:《沧桑无语•文学创新与深度追求》,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91页[3]见《历代诗话续编》下,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1184页[4]鲁迅:《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未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28页 [5]丹纳:《艺术哲学》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486页[6]歌德著,王元化译:《自然的单纯模仿•作风•风格》,译林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7]叶燮:《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8]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点校本,第84页[9]王向峰:《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散文的审美化境创造》,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10] 托马斯•德•昆西 著,黄丹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11]王向峰主编:《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散文的审美化境创造》,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354页[12]胡震亨:《唐音癸签》,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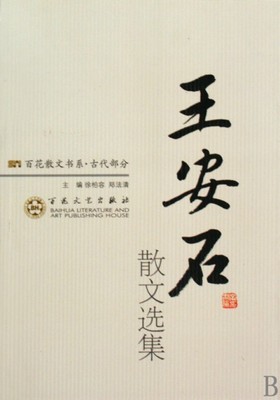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