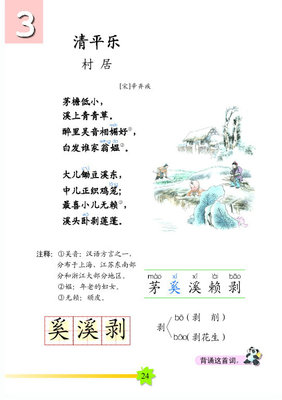也许有一天清晨
蒙塔莱(意大利)
也许有一天清晨,走在干燥的玻璃空气里,
我会转身看见一个奇迹发生:
我背后什么也没有,一片虚空
在我身后延伸,带着醉汉的惊骇。
接着,恍若在银幕上,立即拢集过来
树木房屋山峦,又是老一套幻觉。
但已经太迟:我将继续怀着这秘密
默默走在人群中,他们都不回头。
(黄灿然译)
灵魂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波兰)
我们知道,我们不被允许使用你的名字。
我们知道你不可言说,
贫血,虚弱,像一个孩子
疑心着神秘的伤害。
我们知道,现在你不被允许活在
音乐或是日落时的树上。
我们知道——或者至少被告知——
你根本不在任何地方。
但是我们依然不断地听到你疲倦的声音
——在回声里,在抱怨里,在我们接到的
安提贡来自希腊沙漠的信件里。
(李以亮译)
一首有关暴风雪的诗
马克·斯特兰德(美国)
来自圆顶城市的圆顶阴影,
一片雪花,一个人的一场暴风雪,轻轻的,潜入你的房间
向你坐着的椅子的扶手飘来,就在你
从书本中抬眼那一刻,它刚好停落。这便是
整个的经过。无非是个肃穆的醒悟
面对瞬间,面对注意力的起落,短促的,
时刻间的一刻,一场无花的葬礼。无非是
除了心头的闪念——这首有关暴风雪的
在你的眼前化为乌有的诗篇,将会归来,
还有多年以后,有人像此刻的你那样坐着,口中念叨:
“是时候了。空气已准备好。天空已敞开了一个口子。”
(沈睿译)
我对世界还有一丁点儿惊奇
曼杰什坦姆(俄罗斯)
我对世界还有一丁点儿惊奇,
惊奇于孩子和冰雪,
笑容绝不做作,恰似道路,
也不像仆人那样顺从。
(汪剑钊译)
晚熟
米沃什(波兰)
迟至近九十岁那年,
一扇门才在体内打开,我进入
清晨的明澈。
往昔的生活,伴随着忧伤,
渐次离去,犹如船只。
被派诸笔端的国家、城市、庭园、海湾
离我更近了,
等待更完美的描述,并胜于往昔。
我并未隔绝于人们,
悲伤与怜悯加入我们。
我持续地诉说,我们已经忘却我们都是王的
子民。
因为,我们来自一个地方,那里,我们并不区分
对与错,也不区分现在、过去和未来。
我们如此不幸,在漫长旅途中接受的
赠礼,我们只使用了很少一部分。
来自昨日与数世纪之前的瞬间——
一次剑击、在光洁的金属镜子前
描画眉毛、一次致命的步枪射击、一艘小帆船的
船身触礁碎裂——它们栖居于我们内部,
等待着实现。
我一直就知道,我会成为一名葡萄园工人,
所有男人与女人都同时居住于那里,
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胡桑译)
沉默
凯瑞安(美国)
沉默不是雪。
它不能变厚
变深。一千年
的它比纸张
还薄。因此,
当我们觉得象
大象被困时
我们一定
全错了。
(原野译)
在我们的房子里
威廉·斯塔福德(美国)
回家晚了,一盏灯低低地燃着,
沙发上皱巴巴的枕头,
水槽里的湿盘子(夜宵),
每个孩子的房间里
克制、缓慢、安然的呼吸——
突然我就站到了门道里
我又看见了这个地方,
这一次,夜还是那么宁静,房子
还是那么安全,只有我的呼吸
轻轻浮在空气中——
在我站立之处,空无一人。
(马永波译)
远方
西默斯·希尼(爱尔兰)
当我回答说我来自'远方'
关卡那个警察厉声说:'哪个远方?'
他还没完全听清楚我说些什么就以为
那是这个国家北部某地的名字。
而现在它——既是我居住过又是我
离开了的地方——仍然有很长距离要走
像花了很多光年从远方而来
又要花很多光年才抵达的星光。
(黄灿然译)
手
胡安·赫尔曼(阿根廷)
你不要把手放在水中
它会像鱼一样游走
你不要把水放进手中
这会引来大海
还有岸
就让你的手随其自然
在自己的空气中
在手中
没有开始
没有结束
(姚风译)
生如夏花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
生命,轻薄不休
轻浮不倦
一
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与心灵
向收割中的镰刀孤独灵魂敞开
决绝地重复,但也是重复着最终
在沙漠绿洲中摇曳的福祉
我相信我是
生如夏花之灿烂
不枯、不败、火热、妖冶、放肆
心率和呼吸承担繁琐沉重的负载
百无聊赖
二
我听见音乐,来自月亮与胴体
辅之以极端唯美的诱饵,捕捉袅袅余音
充实紧张的生活,但也充实单纯
总有一些记忆遍布大地
我相信我将
死如秋叶之静美
盛而不乱,姿态如烟
即使枯萎也保留着傲骨和清风的肌肤
隐匿于世
三
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着
爱是一池挣扎不息的蓝绿色水藻
仿佛落寞的微微爆裂的风
通过我的血管出血
多少年来坚守信仰
四
我相信所有人都能听见
甚至预见了分离,我遇见他们的另一个自我
一些没能把握的时机
离开后东行西走,至死注定不能返回无地
瞧,我戴在我头上的簪花,沿途一路盛开
常常错失某些事物,但也深受风霜雪雨的感动
五
般若波罗蜜,尽快尽早
生命美如夏花死如秋叶
还在乎拥有过什么
(伊沙、老G译)
选编:苍劲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