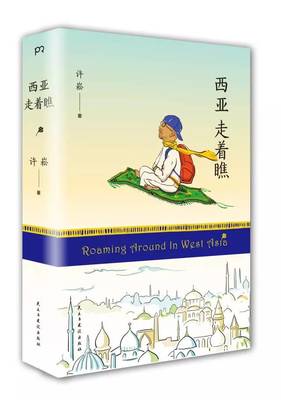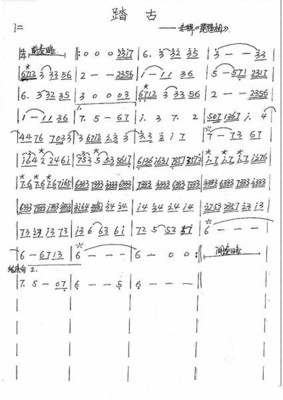我想,是时候给大家一个交代了。
《西亚走着瞧》书稿大体上已经完成,还缺一个序言和需补充及改写的几个章节。2010年3月结束的这次旅行,转眼已经三年多。这次实在是够慢的,应该认真抱歉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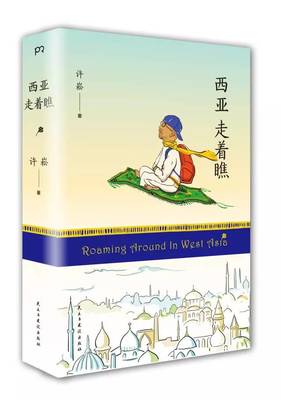
横竖是慢了,我也不赶了。早早晚晚几个月是小事,不留神出来一个以后自己会觉得丢脸的东西,才让我害怕。
大概是生活在大理的缘故,有很多想法跟以前不同了。关于《西亚走着瞧》,一年多前开始有个念头萌发,后来摁也摁不住,索性就从了那它,不挣扎了。那么,我就在这里说说我想做的事。
现在实体书店快要完蛋了各位都听说了吧?一方面是来势汹汹的电商,一方面是越来越方便的电子书,书店的经营者处境越来越困难,其中以小型的独立书店为甚。如果不是爱书者,谁又会在这个时代去经营一家独立书店?房租时时在涨,读者日日萎缩,网上发疯般打折卖便宜书,还有人把本来就利润薄如纸的小书店当成网上书店的样板间。
虽然很多人的阅读现在都停滞在140个字,但是我想,总还会有人愿意读书的吧?“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还不算很过时吧?总还有人是需要书店的吧?那么,大家一起想想办法让开书店的街坊坚持下去吧。
我的想法是,《西亚走着瞧》将不再通过传统的发行渠道发行,也就是说,新华书店之类的书店里不会看到这本书,而当当亚马逊什么的也不会有,也许会有某家淘宝店在线上销售,但是书价永远不会打折可能还要另加运费。我最希望的是,全国所剩不多的小型独立书店里能看到《西亚走着瞧》的身影,并且祈祷在没有电商竞价的压力下,这本书能让小书店看到一点希望。
如果以后有多一些作者愿意以这种方式出售作品,久而久之也许小小的独立书店里就会有一个角落,是网上买不到或者网上也不会更便宜地买到的书。这点小小变化,也许就能吸引更多人去小书店看看、去小书店买书。任何生意靠顾客的恻隐之心活着都是不靠谱的,得有点不可替代的价值服务于大众才行。
当然,我不敢奢望一本小书对大局能有什么影响更别说改变了,上面那些描述是我的理想而已。堂吉诃德是疯的,他分不清现实和幻象。而我自认为不仅能认识现实而且还承认现实。只是,我跟老堂一样,一样的不服。
是的,不服。
听了太多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以后,对这句话也开始不服。也许存在确实就是合理的,但存在未必就是正当的吧?这个世界总还有变得更好的余地吧?面对不堪的现实不一定就要低头吧?反正,我不服,即便胯下没有马、手上没有剑、身边没有桑丘。
那么,我就去跟风车战一回了。不过是本书而已,我输得起,也浪费得起。
这次没有出版社在背后帮忙,所以成书还要请各位等待些时日,请多担待。
下面是《西亚走着瞧》第三章,没校对没编辑过,请先凑合着看看吧——
3.
一早醒来,我大脑一片空白地走到街上去。我不想吃早饭,不想买东西,不为见什么人,不为去什么地方,自己也不知道想要去哪里。没有目的地的话,怎么走都是对的,只需跟着人潮迈步即可。我在一个个街口木然地直行或拐弯,用一种比“磨蹭”还缓慢的速度步行,最后不期然地走到它的面前,站定。
它是一座不起眼的白塔,在加都的街巷中这样的白塔众多,这一座不算大也不算好看,只有刚到尼泊尔的游客兴许还会多看几眼,两天以后就会熟视无睹。但它在我眼中是不同的。我在过去几年中时不时就会翻看下它的照片。直到此刻,我才终于醒过来,明白原来自己是出门来寻找“回忆”的。
加都有我太多的回忆了,整个泰米尔到处都是我游荡过的地方。但是这座小小的白塔对我意义非凡:它是我“战斗”过的地方,我靠它的庇护躲过一劫。
我对于如何界定“危险”的标准还算保守,不容易一惊一乍。对遭遇过的所谓“险境”,既不会太过多愁善感,也不至于因此就豪气冲天。旅行中警惕性会提高、人会变得更敏感实属正常,但被人多看两眼就以为要被打劫,事后还长吁短叹地宣扬自己如何逃得一命,未免有点夸张。即便夸张,那种事情拿来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给大家助个兴还不是问题,但如果自己都当了真,怕就有点过了。以我比较个人的标准,大部分我听到和读到的“危险”,距离真正的危险都差得老远,多是“自己吓自己”和“自己骗自己”的某种古怪结合,或者纯粹是只为了“吓吓别人”或者“骗骗别人”。
我曾经总结过,旅行中真正危及生命的危险其实不多见,可一旦来临——很不幸——却难以防范。那些真正的危险很少出现在旅行者的博客中,基本上都出现在报纸的社会新闻版或者电视台的晚间新闻里。看那些新闻时,早年间我还会固执地认为“那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觉得哪怕是遇到同样的处境,我也一定能逃出生天。后来看到的类似新闻越来越多,那份心存的侥幸和自信终于灰飞烟灭——那些遭遇了海啸、山难、瘟疫、战乱和其他乱七八糟的天灾人祸因而遇难的人,比我聪明的、比我强壮的、比我灵活(这点我就算了,别比了)、比我意志坚定的比比皆是,我除了有信心在遇到饥荒时比别人饿死得慢些以外,什么都比不上人家,凭什么能幸存?
更令人沮丧的是,就算比人聪明、比人强壮、比人敏捷、比人坚强、比人更能忍饥挨饿,都不一定是能跻身幸存者的行列。在灾难中,有一个极不靠谱的因素,却每每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分开了生死,隔绝了阴阳,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它的名字叫“运气”。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的那个下午,我啥都没带,只随身带着相机和难得跟我在一起的“运气”。
二零零六年对尼泊尔来说,就如同一九四九年之于中国。
尼泊尔王室始于公元一五五九年,第一代君王叫德拉比亚·沙阿,因此称作“沙阿王朝”。这个由廓尔喀人建立的小王国在一七六八年统一了尼泊尔,开始了长达二百四十年的统治。
然而,尼泊尔注定不得太平。在沙阿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倒有差不多一半时间(前后一百零五年)是被英国人撑腰的首相家族控制着,等到赶跑了英国佬以后,王室才重新夺回了权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后的对决当中,大势已去却不肯认输的首相还扶持过一个三岁的儿皇帝。这位小国王确实出身王室,首相把他捧出来是为了废黜他爷爷。可想而知的,爷爷情绪很激动,闹得首相一家卷铺盖滚蛋不算,闹得这个孙子也一直只能坐冷板凳,直坐到五十一年后王室实在没人了才轮到他上台。孙子很争气,坐上王位后以非常手段报复社会,转眼间就把祖宗攒下的二百多年基业败得干干净净。
这孙子就是尼泊尔的末代国王贾南德拉是也。
任何朝代,不分古今中外,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昨天还以为自己会千秋万代的,今天忽然就只剩些渣渣摆在古董店里卖给游客。
君主制很久以来就已经不时髦了,哪怕是保留了王室的国家也以君主立宪为主流,纯正世袭独裁的、真正意义上的君主国家现在只剩了三个——沙特阿拉伯、文莱和阿曼。所谓“君主立宪”么,就是全国人民把那一家老小从生到死从头到脚养起来,对外让他们负责红光满面地接待外宾以显得咱们的国家很礼貌很得体,对内让他们负责时不时传点花边新闻让供养人高兴高兴。但是,如果负责脸面事务的娱乐明星们不识时务干涉起国家大事来,供养他们的群众随时就会翻脸。
尼泊尔王室对于君主立宪这回事心态不太端正。从一九五一年开始,他们想要表现自己开明进步了就立个宪,嫌乱臣贼子人太多说话太吵了就把人轰走自己独裁,如此翻来覆去。幸亏尼泊尔群众识大体顾大局,一直忍气吞声过着日子。一九九六年,有个叫普拉昌达的中年人终于觉得这么忍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就另想了办法——普拉昌达领着一群兄弟走进尼泊尔西部的山区,造反了!
虽然我没有查到任何资料,但我还是确信他们带进山去的随身行李里有《毛泽东语录》,因为他们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拉起了自己的队伍、喊出了自己的口号。他们的那句口号身为中国人的我们听着都耳熟极了。他们说,要“农村包围城市”。
这支队伍的正式名称是“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一般被人称为“毛派”。
十年以后,也就是二零零六年,我第一次到尼泊尔的那回,普拉昌达同志的队伍已经无比壮大。仅仅用了十年时间,“毛派”就占据了尼泊尔的大部分国土,是否会取得胜利不再是问题,问题是何时取得胜利。国王和他的士兵们可怜巴巴地躲在屈指可数的城市里,每月盘点一下“最近人家又搞掉了我们多少武器装备多少人”。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国王用机关枪和装甲车控制着的城市也不太平。被赶出议会大楼的那些人不肯乖乖回家洗衣服带孩子,而是到处跟亲戚朋友和邻居讲国王的不是,然后大家发现小国家就是好办事——原来全国都是亲戚朋友或邻居,没人帮衬的只有国王一家人。被国王赶到街上来的党派一共有七个,现在好了,以前拍着桌子对骂的人如今成同党了,改叫“七党联盟”了。可想而知的,心怀不满的亲戚朋友和邻居们人数太多了,屋子里待不下,大家只能到街上去转来转去。
反正,当时的尼泊尔局势一句话就能说完:贾南德拉国王无比坚决地把所有人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再把所有的敌人都团结在了一起放在自己对立面。我简直都怀疑这国王是不是想要自杀又没勇气自己动手。
零六年四月份我和小郑同学从印度回到尼泊尔,正好降落在一个暴风眼中。前阵子的游行示威刚刚告一段落,街上的亲戚朋友们中场休息回家炖鸡汤补身体去了,国王抓紧时机马上宣布宵禁。
所以说,我基本上是回尼泊尔坐牢来的。
宵禁不是闹着玩的。宵禁的意思是,理论上如果你胆敢把脑袋从家门口伸出来,对面的武警就敢对着你把子弹射过来。
我投靠的龙游客栈,里面住着一堆百无聊赖的同胞。大家被国王软禁在一起,靠每天学习祖国各地的不同麻将习俗打发时间。
对于尼泊尔人的好客、热情和友善,大概每个到过尼泊尔的外国人都会有深刻印象。正因为此,我和龙游老板大勇坚信宵禁期间上街转转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虽然外面老百姓都消失不见,只剩了穿蓝色迷彩制服的武警和绿色迷彩制服的国防军,可毕竟那些当兵当差的娃娃们也是老百姓家里来的,我们相信自己断然不会被人一枪爆头或者拖走暴打。一般而言到了国外尤其是不发达国家,遇到军警最好不要去惹是生非,尼泊尔却是难得一个拿到“全民好人卡”的国家,哪怕去跟他们的警察撒泼打滚也问题不大。
我和大勇被关得无聊死了,把说理和骂街的常用英语单词复习了一遍,就出门去找武警撒泼打滚,也好消遣一番。然而我们连这点小小心愿都没法达成——人家尼泊尔武警根本不对我们来硬的,嗓音都不会提高一点;正相反,人家低声下气地劝我们回去好好坐牢,表情和语气都像是欠了我们钱。
作为一个贱命之人,比如我这样的,还真看不得别人对我低声下气,出去了两趟就泄了气。想想人家身为国家机器的一份子混到这份上也不容易,弄不好等天亮了尼泊尔人民搞个自己特色的三反五反还要被秋后算账,再去为难人家有点说不过去。结果就只好在院子里憋着。
憋了一个礼拜,到四月二十二那一天,大家都憋坏了。
我关于四月二十二那天的记忆是从午后开始的。
因为一直在龙游院子里待着,我慢慢就现了原形,重要特征是穿着打扮起了变化。我随身衣物当中带着一身泰国买的桔红色渔夫裤和白色薄纱上衣,出门爬个山远个足啥的不合适,好处是穿着舒服,适合举止平和的小范围活动。
那天我就穿着这么一身在房间午睡。当院墙外的吵闹声把我弄醒时,我真真切切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如果你习惯了在一片安静祥和中像僵尸一般活着,可能也会跟我一样觉得喧嚣声是只应该出现在梦中的。
等分辨出那些声响真实存在并且强大到有效地破坏了我的睡眠(一般而言我睡觉怕光不怕吵),我简直是从床上弹跳起来的,动作快得血液都跟不上,差点又一头栽倒。
于是我裹着一身完全不得体的衣衫,穿着一双不合脚的拖鞋,钱、钥匙、证件什么都没带,只把相机抓在手里就冲出去了……
院子里空无一人。
龙游不是个沿街的院子,平日里街上一般的噪声不会骚扰到我们,宵禁的日子里更是安静得有点过分;这天街上的动静居然能把我吵醒,可见得那声音能有多大!
我冲出房门,冲下楼,冲出院子,冲过胡同,冲到街上,冲进了一支“嘉年华”的队伍中。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哈,这下好了,国王下台了!!
那会儿即便有人解释给我听“国王还是老大呢!还在王位上坐着呢!”,大概我也不会信。我眼前的这支五彩斑斓的队伍,他们鼓掌,他们敲鼓,他们载歌载舞,跟“示威”、“抗议”之类的词汇所表达的悲愤情绪一点不沾边。他们完全不像是要去推翻一个政府,而像是全体中了乐透彩的大奖,吃饱喝足了正要去领支票。这一定是胜利游行!
我承认,我是个对悲伤无感却很容易被欢乐传染的人。身边所有人都快哭死了我都憋不出眼泪,但如果是一群欢乐的人在周围,我按捺不住就想冲上前去跟他们一起蹦蹦跳跳。所以,我像个听到魔笛召唤的孩童一样,蹦着跳着就窜进了游行的人潮中,蹦着跳着就跟着人群一起去了。
狂欢节游行虽然在巴西才是世界级的,不过毫无防备地撞进去的那种惊喜大概巴西也给不了我。《城市画报》曾登过一篇仇敏业先生的文字,标题为“旅行是热烈收集意外的过程”,一语道破了旅行中那些可遇不可求的欢乐之可贵。
我跟着可遇不可求的那一大群尼泊尔群众在泰米尔狭窄的街道上狂欢,试着学他们喊的口号学他们跳的舞。我周围的人对我友好极了,只要一端起相机他们就冲着我欢呼,冲我拗出各种造型。队伍里跟大家格格不入的是几个零零散散的外国通讯社记者,他们如临大敌地穿着防弹背心或带着头盔,有些人还在上面印着醒目的白色“PRESS”字样,以表明自己的记者身份。
队伍很长,不见首尾,难以估算到底有多少人。泰米尔的街道很窄,两辆小车错身而过都困难,游行人群就被拉成了更细长的一支队伍。时不时的,住在沿街楼上的人还会洒点水下来,每次都会引起人群的一阵大声欢呼,显然是在表达祝福而不是砸场子。
走过几条街道交汇的小广场时,我才遇到了今天的第一批武装警察。警察们全都没有武器,随身只带一根南亚特色的细棍子,肩并肩地站成了一道人墙。游行人群没有要跟警察冲突的意思,很是“合作愉快”地沿着警察人墙拐进了另一条街,仿佛事先大家都商量好了似的。
然后我就看到了那座白塔。
从街口拐进来走到白塔旁边,大约花了三分钟时间。当走到白塔旁边,我听到两声闷响,当天的狂欢派对就此宣告结束。
像是一柄利斧斩落,由欢呼和歌声组成的快乐喧哗戛然而止,瞬间切换成惊恐的尖叫和无数人夺路奔跑的脚步声。原本向前的人潮,现在忽然转身,洪水般向我冲来。那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秒钟。
或许是我受了刺激的瞳孔急速扩张让我看见了更多,或许是对那个瞬间后来我默默地回忆过太多遍,以至于那一秒钟像电影胶片那样,随时能一格一格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闷响声过后,在我前面的人潮全体伏低了一下,呈现出一种近似于浪潮的波动,令我一下子觉得“咦怎么突然长高了?”。接下去,组成浪潮的水滴们全然不顾水滴应该遵循的物理规则,刹那间掉头向后狂奔。站在我前排的一个中年男子,转身过来仍保持着低头的姿势奔跑,一边口里还狂呼着什么。要不是我躲避及时,他会一头撞进我怀里。
人在应急状态下,表现跟平时很不一样。平时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先思考一番,然后中央再指挥地方按部就班行动。可真的遇到这样紧急事态,那些“慢着,让我先想想”的人弄不好就会成为被人撞倒在地然后再遭踩踏的受害者。不过,好消息是,面临危险时真正因为太冷静而遇难的人为数不多,我们大家都是正常的人类嘛。
所谓正常的人类,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左右大脑都有一个叫“杏仁核”的东西(也有翻为“扁核桃”、“杏仁体”或者“脑扁桃体”的),在大难临头之时会果断地接管我们。当恐惧突然来袭,杏仁核会立刻激活大脑里一大堆平时里“养兵千日”的化学物质,诸如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可的松之类,造成的变化是血液会从胃部之类无关紧要的部位抽走,以支撑猛烈增加的心跳和呼吸,代谢系统里的糖分像是被点燃了一般,一切都为了“逃命要紧”这一神圣目标服务。所有这一切都在电光火石间发生,平常以“思考”为主导的大脑体系暂时退居二线。
坏消息是,在以情感为主导的杏仁核控制下,人会一下子变成弱智。我们都听说过那些不会游泳的溺水者的故事,他们在有人来救援时的表现毫无理智可言,看起来更像是要跟救命恩人同归于尽。在很多案例中他们也确实做到了。究其原因,正是杏仁核搞的鬼。
这就是我说的“运气”了。运气好的话,杏仁核激发的“超人”系统能让人发挥异乎寻常的体能,帮助人逃出生天;运气不好的话,杏仁核指挥下的人会用最愚蠢的方式撞进死亡的陷阱里。但面对突发危险,到底需要你的超人体力还是你的冷静思考,没人能预知;而且,在需要克服因恐惧而产生的情感本能时,即便潜水员和飞行员也只能以自己的行业特性为基础做针对性训练,跨行业就毫无用处。
因此,登山的、航海的、走荒原的、从高处往下跳的,所有的“探险”都需要训练,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克服杏仁体触发的情感本能。这不仅仅事关自己的命,也事关同伴的性命。在别的事情上,处理不好“理智和情感”最多心灵受伤;出门在外时,“理智和情感”相关的是生与死。
我说自己那天运气好,是因为我的杏仁核只发作了一秒钟。只一秒钟,就在人群要扑倒我的当口,我“嗖”一下往左边蹿出五米,然后——安全了!我躲在白塔背后了!
白塔挡住了一切冲撞我的可能。我背靠着白塔站着,双腿瑟瑟发抖。
人群在狂奔,有个人一动不动躺在我左前方十米左右地方。游行队伍溃败了,尾随着他们的是手持盾牌和木棍的蓝制服们。武警们只要追到近处抡起就是一棍抽下去,街上一片哭爹喊娘声。
接着,我当街哭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催泪弹的滋味。
催泪弹的烟雾是慢慢弥漫开的,从味道判断主要成分是辣椒粉。你可以回忆一下在厨房里闻到呛人的辣椒气息是个什么感受,再想象一下把那股辣椒油烟中的油腻去掉,变成干的纯的辣椒粉滋味,强度浓度上再乘个十倍,大概就比较接近了。
催泪弹的目的是驱散人群,不是为了杀伤目标——除非被直接击中。躺在我十点钟方向的那位仁兄就被其中的一发催泪弹直接砸在脑袋上,当场昏迷。
示威的队伍逃散了,武警四处追逐殴打落伍的人,不管对方是不是女人或者孩子。一个小兵冲过来转身看到我缩在白塔下,挥起木棒就要给我来一下。我当场就吓得说都不会话了,哆哆嗦嗦想要表明身份,可一个词都蹦不出来。幸好小兵看到我脖子上挂着个相机,硬生生收住了已经在往下落的棍子。
群众退走,武警追赶;武警之后,才是记者。刚才游行队伍中的头盔防弹衣记者们重又出现。不过他们也就只有按几张快门的力气,马上跟我一样也蹲到路边哭了起来。
我心里那个恨啊……
对于这种事情,置身事外的人很容易说出“要冷静要冷静”之类的话,而站在那里挨过两发催泪弹以后,世界观立马就改变。两声枪响之前,我是个游客,是个“虽然不关我事但有热闹看当然要看看的”游客;两声枪响之后,我马上坚决站到了革命群众的一边——不用跟我讲什么大局,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被人用催泪弹伺候,而且只差五米就砸到本人脑袋上,老子当然情绪很激动!
这是个太容易的选择了。一边是国家机器的高墙,一边是手无寸铁的鸡蛋。高墙当着我的面把鸡蛋砸碎在街道上,而鸡蛋却在忍着自己的眼泪擦拭我的眼泪。当我和一群记者坐在地上,一个十岁大小的小男孩走过来站到我们面前,手里抱着一瓶水挨个给我们清洗眼睛。他和我们一样流着泪。
我哭得更厉害了,又怕自己嚎啕起来于是紧紧咬着牙关,连句“谢谢”都说不出口。
等再次站起身来,这回轮到那群来自各个国家的记者们来令我刮目相看。
警察的冲锋已经停止,人群早就消失无踪,街道安静下来,只剩一个声音在吼叫着怒骂。
叫骂声出自一个穿黄色T恤的记者。此人年纪长相都跟“豪斯医生”差不多,现在看来脾气也是。他孤身一人走进武警队伍中,梗着脖子面对面痛斥他们中间肩上有两颗星的、军阶最高的现场指挥官。可怜英语中骂街的词汇实在有限,气得直哆嗦的“豪斯医生”用来用去也只有“纳粹”“杂种”“法西斯”“反人类”这么几个有限的词,完全没有限制级内容,听得我直着急。
“豪斯医生”的大意是,身为纳税人供养的武装力量,居然不经警告就向人群发射催泪弹,居然当街驱逐殴打妇孺,“你还是不是人啊?!”。
这样的场面大概不是第一次发生,看起来像是已经被人骂惯了的指挥官铁青着脸一言不发,连脸上的唾沫星子都没有伸手抹一下。
另一边,一群记者围在那个伤者身边在做急救。伤员头部重创,粘稠的鲜血流了一地。记者们能做的很有限,只是清洗和包扎伤口,但是那样的场面真令人安慰。救护车很快呼啸着开到,装上人,又呼啸着开走。
救护车走了,武警又站成了一道警戒线,记者们在警戒线外忙碌,逃散的群众在远处隐约还能被看见,却不再能集聚起来。隔在武警和老百姓之间的一百多米街道上,散落着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拖鞋。
人家穿着拖鞋来找你讲理,你对着人家先丢催泪弹再冲上去打人家老弱妇孺,这样的政权还是让它完蛋吧;人家穿着拖鞋来找你讲理,你逼着人家的子弟对着家人丢催泪弹再冲上去打人,这样的政权还是让它完蛋吧。我一边在拖鞋堆里找东西,一边在脑子里诅咒打手。
我默默地骂了十来分钟,终于从一地的拖鞋中找到了一枚催泪弹的弹壳。
这枚弹壳后来被我带回中国,放在了我的书架上。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