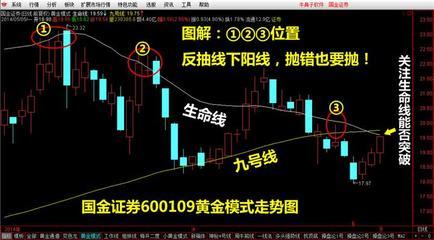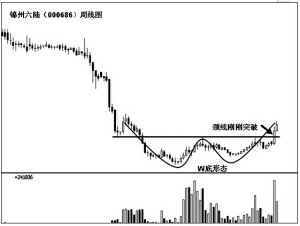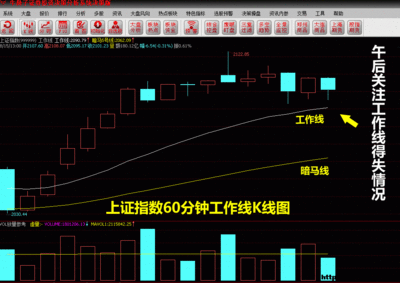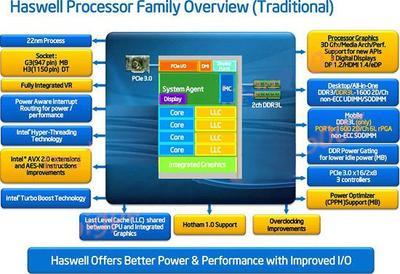齐白石的两大弟子
马河声
要说的齐白石的两大弟子分别是李苦禅和李可染,他们在齐门弟子中无疑是影响最大和成就最高。
苦禅,可染,他们的名字注定只能是艺术家。苦,这个字,不要说老百姓,皇上也唯恐避之不及呢,跟这个字沾上边,敢保证百分之九十没有好果子吃。胆敢将它用到自己的名字里,据我所知,李苦禅是历史上第二个,第一个是清代的石涛,又称“苦瓜和尚”,李苦禅是不是因为太过崇仰他而立名以明志:你既然是苦瓜和尚,我就愿苦心参禅。甭说,有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石涛谁都崇拜,不要说李苦禅,齐白石都愿做他的走狗呢。问题是,这么不同凡响的名字,李苦禅究竟是如何想到的,以他后来的艺术作为和成就看,与这个“明志壮举”实在有点不甚匹配,虽然,李苦禅是一个大画家---是一个“名气很大”的画家。我读过李苦禅传记,他是一个在人格尊严上令人肃然起敬的画家,爱唱京戏,能粉墨登场,会拳脚,对日本鬼子很不客气,他的一生无疑是为艺术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即所谓的艺术人生。但要细细地考究起来,至少在艺术追求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上,与他这个不同凡响的名字还是差距很大的。他的画很“世俗”,一点“禅”味也没有,更体味不到“苦禅”的境界,他的画太粗糙、太蛮憨,也许还有一点大气,但全然没有细腻,一览无余,让人没法回味。所以,在上个世纪的艺术里,李苦禅实在是可有可无,说这话尽管有些于心不忍。
再说李可染,又是不同凡响的名字,名也,命也。李可染这个名字决定了他与绘画的终生结缘,谁也没法摆脱,这样的名字只有在艺术界念出来“天动地摇”,如果放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里边就十分地不顺口,说不定能让夏青、罗京、李瑞英他们咬了舌头,这就是宿命。当然,马河声这名字也只能在文化艺术圈混混,没办法只能放明智了,虽然也常做“委员长”之梦,但醒来还是很踏实地走到画案前舞弄咱熟悉的各种毛笔。李可染也认命,而且认得很彻底,他在绘画上野心勃勃,不仅要“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还要“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李可染如果不以其作品留芳百世,就会因这两句话流传千古。
李可染拜齐白石为师时已经四十多岁,齐白石也超过了八十岁,现在回头看李可染那个时期的作品,无论山水还是人物,还真不负齐白石的抬举,遗憾的是后来越画越糟糕,“勇气”倒是可嘉,但究竟“打进去”了多少“功力”,没法细究,大略看是“刚得意便罢手”,倒是“打出来”太多,元气淋漓,精神饱满是需要的,但过了头就有点“生猛”,用当下的话说就是太给力了。他和李苦禅翻到同一条阴沟,就是“一览无余”。
且看齐白石当年是如何当面“鼓励”他的这两位得意弟子的,说李苦禅“将来不享大名,天地无鬼神矣”;说李可染“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书画可以横行也”,“可染弟画此幅,作为青藤图可矣。若使青藤老人自为之,恐无此超逸也。”这样激情推许的话,不济人就害人,现在看是后者。实非白石老人之过也,是他们没有将这个金针度好。对弟子如此真诚地“过誉”,除了对齐白石作为一个大师级人物嘉勉后学的殷殷情怀和气度表示崇敬外,实在为老人的话没搁到实处而惋惜,更为这两位弟子有违师望而遗憾。
前人之长,后人可师;前人之失,后人可鉴。我尊敬李苦禅、李可染,他们从大师的羽翼下确实挣脱出来了,但是没能成为参天大树,更不要说矗立成山峰,这是人的局限,也是历史的局限,也是命。如果要总结这两位大画家的致命缺失,那就是:缺乏文骨。
2011.8.27.凌晨四时二十分于长安懒园匆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