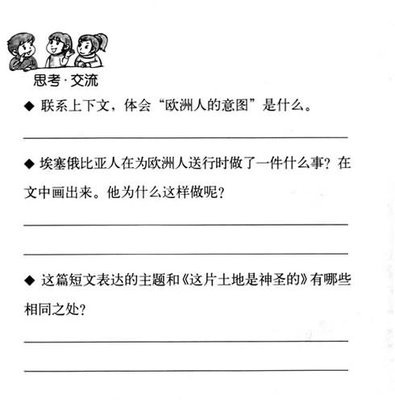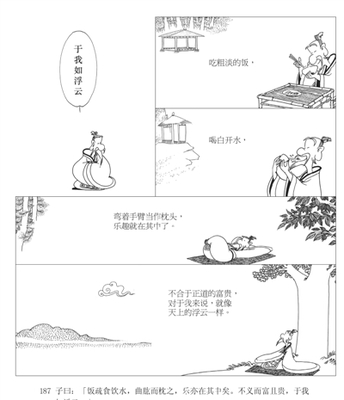刊于《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3期
(未删减版)
——兼谈乐籍群体、教坊体制对昆曲和传统曲牌的意义
程晖晖
摘要:魏良辅,一位在戏曲史和音乐史上功勋卓著、彪炳千秋的人物,其身份、生平和其对昆曲的贡献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笔者在此综合多种学说和材料,进一步提出他是乐籍中人,从乐籍文化视角对他的身份、隶属机构、生卒年代和籍贯作多层次研讨,并提出对昆曲和传统曲牌创承的一点看法,指出曲家魏良辅精神的可贵之处。
(本文为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课题[1]《中国传统音乐曲牌索引及其统计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课题号:11CD101)
关键词:魏良辅乐籍 教坊 昆曲 曲牌 创承
一、关于曲家魏良辅身份的两种观点
魏良辅是一位在音乐史和戏曲史上功勋卓著、彪炳千秋的人物,关于他的生平、身份和对昆曲的贡献,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热点,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都出现了多篇有关魏良辅的专论,笔者对这些成果进行梳理,发现对曲家魏良辅的生平和身份存有大致两种说法。
其一认为曲家魏良辅是身份低下的普通艺人,和同时代的官员魏良辅是两个不同的人,他的生卒年代只可根据现有多种史料进行推测。认同这一观点的学者以顾笃璜、徐朔方为代表,典型论著有顾笃璜《关于魏良辅——与蒋星煜同志讨论》[2]、流沙《魏良辅的生平及其它》[3]、沈沉《魏良辅辨》[4]、徐朔方《曲家魏良辅不是那当官的魏良辅》[5]等[6]。
其二认为曲家魏良辅原是嘉靖五年江西籍进士,生于1489年,卒于1566年,活了78岁,历任户部主事、户部员外郎、兵部武选司郎中、广西按察司副使、湖广右布政使、山东左布政使,精通戏曲,从官位退下后钻研昆山腔,终以戏曲闻世。持此观点的学者以蒋星煜、谢巍为代表,典型论著有蒋星煜《魏良辅之生平和昆腔的发展》[7]、谢巍《魏良辅身世略考》[8]、朱受群《曲圣魏良辅》[9]等。特别是一些戏曲和音乐知识普及性著作往往采用这个观点,如近年来刘建春、姜浩峰《中国昆曲地图》[10]、黎孟德《音乐讲读》[11]等。此外,目前在“百度”网站键入检索词“魏良辅”,可看到“百度百科”的“魏良辅”条目也持此说法,同样的还有“维基百科”等知识资源网站。
除了这两种说法外,还有学者指出曲家魏良辅是瞽者、是医生的身份特征,但都没有做专门论述,只是一带而过。因此大致而言,有关曲家魏良辅身份学界只存在上述两种相互间有着争论的观点,并形成研究热点。相比较这两种观点,持曲家魏良辅为艺人者在数量上更多一些,摆事实、讲道理更充分一些,说服力也更强;但认为魏良辅是官员者由于多被知识普及性著作和网站采用,所以影响也很大,笔者认识一位音乐专业本科毕业生,毕业工作数年后仍记得当年高考辅导课上老师说魏良辅活了78岁,可见所受熏陶之深。
学界至今在对曲家魏良辅身份的认识上还存在难点和疑点,学者苏兴先是于1962年发表《关于魏良辅》一文,论证魏良辅可能是当过山东左布政使的新建魏良辅,但时隔近40年后的2000年又在《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札记五题》中摆出曲家魏良辅和山东左布政使魏良辅或不是同一个人、或是同一个人的观点,没有确证哪个观点合理,最后指出了该项研究的问题所在:“总之,只从一个角度肯定或否定,以现有资料而论定与否,都嫌过早。还要等一等其它资料的发现,或许才有可能下最后的结论[12]”。而从对曲家魏良辅身份之讨论所引发的籍贯问题,也被朱恒夫、王基伦收入了1998年版《中国文学史疑案录》:“魏良辅到底是哪里人,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是沈宠绥误记,还是魏良辅确实从南昌迁移到昆山或太仓,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谜。[13]”
笔者认为,在曲家魏良辅身份研究方面学界缺乏必要的阶段性总结和共识,比如1998年的《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说“曲工魏良辅不是当官的魏良辅,看来已经成了共识[14]”,但显然没有求得真正共识,这也是信息还不够发达所致。今天看来,“官员说”明显是不能成立的,官员魏良辅和曲家魏良辅是同时代同名的两个不同的人。持“艺人说”者已经将有关魏良辅的史料几乎全部搬出来在文中再行抄录(如曹徵明、周文康《魏良辅生卒年蠡测》,因此本文在论述时不再全面铺排史料),并通过多重角度反驳“官员说”,提出曲家魏良辅即是那当官的魏良辅之多种不符合逻辑性(如沈沉《魏良辅辨》),其考证缜密、视角丰富,但“艺人说”的论证多集中在对“官员说”的批驳上,对曲家魏良辅艺人身份的论证还显得薄弱。持“官员说”者史料基础均来源于单线条的江西魏氏家谱,虽然考证出这上面记载的魏良辅的生卒年代和历任官职,却无法证明此魏良辅就是彼魏良辅;当然,蒋星煜先生曾经身体力行做过“逆向考察”式的田野调查,获得魏氏家族后人的口传说曲家魏良辅和进士魏良辅是同一个人,这种研究精神诚然可嘉,但所获证据却显得异常孤薄,并和现存多种有关曲家魏良辅的确切史料记载产生矛盾。在此,笔者于《魏良辅辨》四条反证的基础上(本文限于篇幅恕不赘述)再补充两点显而易见的反证:
1、持“官员说”者一致认定以戏曲、音乐闻世的明代魏良辅就是那个江西籍的嘉靖五年进士,此外别无他人,那么据此说所本的魏氏家谱,进士魏良辅生于弘治二年(1489年)卒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这应该是非常确切的;而《南曲九宫正始》中记录,作者钮少雅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左右弱冠年纪往谒魏氏时魏氏已死,据多位学者推测那时魏氏刚去世没多久。虽然学者董每戡认为其时魏氏可能去世已久[15],但另有一条记载万历间魏良辅携提琴“入洞庭奏一月不辍”(清毛奇龄《西河词话》)的史料说明曲家魏良辅一直活到万历年间,这也是经多个研究者所考证承认的。由此可证官员魏良辅生卒年代线索与曲家魏良辅的生平事迹不符。
2、文徵明手抄本《南词引正》标明曹含斋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为《南词引正》作跋,这至少能确切无疑地说明此书是“娄江尚泉魏良辅”在嘉靖二十六年之前所做,其时魏在戏曲上已经取得成就,然而此前直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卸任,那个做官的江西籍魏良辅却都在娄江之外的地方(有的“官员说”者还认为此魏良辅是嘉靖三十三年后才去娄江钻研戏曲的[16]),也并没有材料能说明其籍贯娄江(其族谱史料反证其籍非娄江也)或曾来过娄江;即使一些持“官员说”者举出史料,推测进士魏良辅从山东左布政使位上卸任后来到弟弟魏良贵在太仓(辖娄江)任苏松兵备道的府上居住并研究戏曲且从此再未归乡,那也是嘉靖二十七年之后的事情了。这一点持“艺人说”的学者也强调过。由此可证官员魏良辅的经历和曲家魏良辅的史料有很大出入。
以上辨析了两种观点,指出“官员说”的错误之处,但学界至今在曲家魏良辅身份上还没有形成定论,笔者则以为,造成“魏良辅之谜”的原因,诚然是由于资料缺乏、现有史料零碎且松散,但更重要是研究视角还不够理想,没能从新角度解读现存史料。在此笔者试图通过乐籍制度切入既有研究,把曲家魏良辅放在封建王朝乐籍文化的背景下,进一步论证“艺人说”,提出曲家魏良辅是乐籍中人的说法(其实中国传统社会中承载着乐文化的艺人主脉就是乐籍中人),从这个视角对他的身份、隶属机构、生卒年代和籍贯做多层次的新研讨,并对昆曲的创承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二、曲家魏良辅是乐籍中人
从乐籍视角出发,可以发现能解读出魏良辅的身份实质是乐籍中人的材料不少。
明代宋直方《琐闻录》中有一条史料:
野塘,河北人,以罪发苏州太仓卫。素工弦索,既至吴,时为吴人歌北曲,人皆笑之。昆山魏良辅者,善南曲,为吴中国工。一日至太仓,闻野塘歌,心异之,留听三日夜,大称善,遂与野塘定交。时良辅年五十余,有一女,亦善歌,诸贵人争求之,不许,至是竟以妻野塘,吴中诸少年闻之,稍稍称弦索矣。野塘既得魏氏,并习南曲,更定弦索音节,使与南曲相近。[17]
以往的研究经常使用这条史料,但很少注意“吴中国工”这个字眼儿,其实对曲家魏良辅的这一称谓,恰恰说明了魏的乐籍身份,“国工”一词可以指工匠、棋手、画师、乐师等工伎阶层,此处意即国家乐工或“音乐国手”——具有国家级水平的乐工;“吴中”一般指苏州、姑苏,明代即苏州府,“吴中国工”的意思是曲家魏良辅为名籍在苏州府教坊的国家乐工、音乐高手,而乐工在传统中国社会,其实质身份就是乐户,隶属乐籍(中国传统“乐”文化涵盖音乐、曲艺、戏曲、舞蹈等多种技艺门类,在籍乐户即由这多种门类的专业乐人构成)。传统社会的在籍乐户,都是官属性质,地位极低,相当于国家奴隶,所谓“唤官身”是也。这国家奴隶不光在皇宫服役,也遍布于地方官府,他们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在京师有太常、教坊,在地方则有地方教坊,最小、最低一级的单位是郡县教坊,再上一级是州府教坊、两京教坊,最高机构是宫廷教坊、太常,其间构成了级属关系,由此形成网络统辖着从地方到中央的天下乐籍。由唐至清,这种制度一路延续下来,具有一致性[18],今天的陕西眉县还有教坊村,包括南教坊、北教坊和教坊堡三个行政区域单位。乐籍中人,并非祖籍在哪里就在哪里服役执业,也非固定在某一地执业服役,而是根据“轮值轮训”制度[19],分番往来于京师、州府和郡县,经常要“走南闯北”。有些高级别官员别配有乐户,这些乐户会随着官员任职属地的变化而流动。但不管乐籍中人祖籍在哪里、居住在哪里、服役执业在哪里,都是国家官属乐人,为官方“直属”。所以,即使是居住在郡县、州府的乐户,也隶属于国家,也经常要赴上级机构执役;而宫廷乐师,也会到地方领命[20]。因此,“吴中国工”一称内涵丰富,不仅说明魏良辅的乐籍身份,而且指出了他的名籍所在和服役区域,但这个“吴中”,很可能并非其祖籍所在地。
还有一条明代史料也从称谓上直接说明了魏良辅的乐籍身份:
伯起善度曲,自晨至夕,口呜呜不巳。吴中旧曲师太仓魏良辅,伯起出而一变之,至今宗焉。[21]
“曲师”是传统社会里对资历较高或从事教曲的乐籍中人的称谓之一,等同于女乐的“妓师”,和“乐师”、“乐工”、“乐人”、“乐户”等称指的是同一个群体。隶属乐籍之人,相当于奴隶,社会地位极为低下,多被人呼来喝去,连名字也多有不雅驯者,其生平身世很少有人记载,即使有记载也不会被以尊重的口吻书写。通观曲家魏良辅的史料,都符合这种情况,而且多把他和其他乐工并列记载,这一点多位学者都考证过。如明末清初的余怀说:
良辅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缕心南曲,足迹不下楼十年。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度为新规……吴中老曲师如袁髯、尤驼者,皆瞠乎自以为不及也。[22]
这里的“老曲师”袁髯、尤驼,不仅从“曲师”称谓上能直接看出他们是乐户,而且可看出其名字应来源于各人的外貌特征,这实是一种蔑称、贱称,带有谐谑、嘲弄的意味,恰恰符合乐籍中人的社会处境,此种现象在乐户中俯首可拾,如元《青楼集》中记载的男性乐人名字:田眼睛光、李牛子、李鱼头、冯蛮子、马二、李四等。而同为“曲师”的魏良辅在文中被与袁髯、尤驼“相提并论”,可见魏的地位也不高。吴梅村诗《琵琶行》:
里人度曲魏良辅,高士填词梁伯龙。[23]
这里把“里人”对应“高士”,里人也就是居住于市井里巷之人,身份自然不如“高士”,可见魏良辅与贵富的梁伯龙地位悬殊,考虑到乐籍中人日常一般居住在市井里巷,我们从中也可推断其为乐籍中人。这句诗描绘了专业乐工与文人在创承音乐和文学上的互动,点明了两者之于艺术的关系。
前引《琐闻录》史料还包含一则重要信息,即张野塘与魏氏的联姻,以往学者只是从中得出魏良辅招罪民张野塘为婿因而社会地位较低或魏良辅重视人才、礼贤下士的结论,但笔者以为这里非常值得重新详细解读一番,因为这条史料向我们鲜活地展示了乐籍制度的家庭组织和技艺传承特点,从而更充分地说明魏良辅的乐籍身份。我们知道,乐籍中人在家庭组织上有一大特点,即行内通婚、同色为婚,技艺世代相传,整个家族成员都是专业贱民,且多是罪罚贱民。张野塘“以罪发苏州太仓卫。素工弦索,既至吴,时为吴人歌北曲”,说明他是受罪罚的乐工,符合乐户的渊源传统,被发配到太仓卫,一般说他是“戍卒”,则可能属于军中乐户。而魏良辅的女儿“亦善歌”,此是承袭家传技艺。有关魏良辅女儿的史料极少见,但她确实是昆曲发展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女性,维系了一个乐籍家族的承上启下。清人陈维崧(其年)《赠歌者袁郎》诗云:
嘉、隆之间张野塘,名属中原第一部。是时玉峰魏良辅,红颜娇好持门户。一从张老来娄东,两人相得说歌舞。[24]
“红颜娇好持门户”直接说明了魏女实为在籍女乐,由“红颜娇好”的女乐主持养家糊口是贱民乐籍家庭一大被社会强加的突出特征。在籍女乐是声色娱人的,《琐闻录》记载诸贵人争求魏女就应该不是求娶为正室而只是侧室甚至仅是求“包养”之,实属社会地位悬殊的两个阶层之结合,因此品格清高的魏良辅才“不许”——虽然在世俗眼光看来,嫁给权贵或包养给权贵似是明智之选,因为通过与权贵结合这种途径能求得经济资助或可事先使女乐脱离贱籍从而脱离苦海,而嫁给乐户张野塘则是终不脱贱民身份的“自甘堕落”。张魏能够联姻,绝不仅仅是魏良辅个人意愿的选择,这两户同是乐籍贱民,“门当户对”,那么从社会制度上就保证了张魏能够联姻,此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了魏良辅不畏权贵择张野塘为婿的主动权。细品《琐闻录》史料的片言只语,可想象出其中包含多个复杂曲折的事件,此中魏良辅坚毅、勇敢、专注于艺术、精神独立不流俗的可贵品质充分彰显。而“野塘既得魏氏,并习南曲,更定弦索音节,使与南曲相近”、“一从张老来娄东,两人相得说歌舞”则描绘出两户乐籍联姻后对专业的共同创承,以致直接推动了昆曲的发展。魏良辅女儿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见一斑,但可惜传统男权社会的历史对她几近“失忆”。至于魏良辅和张野塘的后代,明末张采《太仓州志》“物产”章中专列一条云:
弦子提琴。州著歌吹,故二器极精工,价比他制倍十余。按吾州魏良辅开昆腔一宗,嗣有瞽者张野塘以弦子著,长子张八传父技,次子张九又工管,其提琴则推杨六,吹箫则推上百户,皆擅绝。今惟杨六在。然他邑习弦子提琴,犹问太仓师法。[25]
由此可知魏良辅的外孙、张野塘的长子张八和次子张九都承袭了家业,符合乐户家族内代传技艺的特征;且此处书写的张八和张九的名字与很多乐籍中人同样不够雅驯,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乐户所具备的特征。以上所举几种史料都是历代乐籍资料中值得珍视者,生动地说明乐户在戏曲和音乐创承上的突出特点和伟大贡献。
此外还有一处往往被学者忽视的实证,即苏州老郎庙供奉魏良辅为戏神的材料,这条材料在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和顾聆森《再论魏良辅声腔改革——就昆曲语音、昆曲地位答戴和冰先生》[26]中都被一笔带过,但没有进行更多的探究。《清嘉录》记载苏州老郎庙是乐籍祭祀之所:
苏州老郎神庙梨园公所:苏州昆剧行会。据《清嘉录》卷七:“老郎庙,梨园总局也。凡隶乐籍者,必先署名于老郎庙。庙属织造府所辖,以南府供奉需人,必由织造府选取故也。”[27]
老郎庙、咽喉神庙都是乐户祭祀本行业神的所在[28],也是业内聚会、应差暂居的“梨园公所”、“伶人公所”之所在,“凡隶乐籍者,必先署名于老郎庙”——这也说明传统社会中戏曲艺人的主脉是乐户,又如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描写南京的老郎庵:
他这戏行里,淮清桥是三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水西门是一个总窝,一个老郎庵。总寓内都挂着一班一班的戏子牌,凡要定戏,先几日要在牌子上写一个日子。鲍文卿却是水西门总寓挂牌。他戏行规矩最大,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齐上了庵,烧过香,坐在总寓那里品出不是来,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一个字也不拗的。还有洪武年间起首的班子,一班十几个人,每班立一座石碑在老郎庵里,十几个人共刻在一座碑上。比如有祖宗的名字在这碑上的,子孙出来学戏,就是“世家子弟”,略有凡岁年纪,就称为老道长。凡遇本行公事,都向老道长说了,方才敢行。[29]
“有祖宗的名字在这碑上的,子孙出来学戏,就是‘世家子弟’”,这些材料都显示出老郎庙、老郎庵之于乐籍中人的关系。上述苏州的老郎庙“其成立年代大抵在清康熙中叶至雍正十二年间。初名‘喜神庙’[30]”,《吴门表隐》记录了此庙所奉之神:
喜神庙在镇抚司前,向在郡庙傍,乾隆初移建,祀翼宿星君。神少年称老郎,实后唐庄宗,(徐腾照诗注。)因兴梨园,故祀之。(六月十一日神诞。)亦作唐明皇,又谓鬼山神耆童,(《山海经》。)又云颛顼子老郎,(其神有洪涯、叔孙通、雷海青、黄幡绰、万宝常、魏良辅、李龟年。)为伶人公所一在。[31]
可见隶属乐籍的戏曲伶人所奉之神大多是乐户中之杰出者,这里记载的唐以来近世之神除唐明皇、后唐庄宗是精通音乐的皇帝外,雷海青、黄幡绰、万宝常、李龟年都是隋唐技艺超群的著名乐户,魏良辅列入他们的队伍,足证其乐籍身份,也可见其影响之深、贡献之大,直让人奉以为神。
以魏良辅是乐户的视角回看学术界的“官员说”,若讲曲家魏良辅和嘉靖五年进士魏良辅是同一个人,也有一定道理,像蒋星煜先生推测进士魏良辅做官后很可能因犯事被罢免再去搞音乐和戏曲,从乐户的特征看也能说得通;因为乐户的一大来源就是罪罚之人,许多乐户过去都是有罪的官员或其后代,一旦入乐籍,即成贱民,一般连家谱都不能入,历史对其“前世今生”的记载就会出现语焉不详。如果这两个魏良辅是同一个人,可能的解释就是他先当官后被打入乐籍,惟此才能打通官员和乐户如隔几重天的社会地位。不过,由于前述几点反证,则完全推翻了曲家魏良辅是那个进士魏良辅的可能。他们不是同一个人,而是同一时代重名重姓的不同的两个人。而魏良辅祖辈是否乐户、如果不是那么入籍前他的身份如何、入籍前是否为官?在新的可证资料发现之前,我们还无从解答。
根据上述论证,可见学界“艺人说”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先前学者们在“艺人”上的论证还稍嫌欠缺,因此没能形成定论;且此说没有揭示传统社会中承载乐文化的艺人主脉之实质,没有对曲家魏良辅的身份进行更深层次研讨,虽然论述了魏良辅地位不高,但没有深究这种现象的原因。曲家魏良辅在戏曲、音乐上成就如此之大、对文人士夫影响如此之深、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如此之高,但竟然没有一篇关于他的传记传世,而其毕生音乐经验的总结——《南词引正》也不能独立的而只是附录于他人文集中刊行(这一点多位学者也已探讨),如果曲家魏氏不是乐户身份,在中国文化历史上肯定说不过去。由于乐籍制度视角的切入,我们在发掘和解读史料时会有更多收获,对曲家魏良辅生平的解读,还有赖于将来进一步的发现。
三、曲家魏良辅与南教坊[32]
如前所述,教坊有逐级隶属的关系,形成了自中央到地方的网络体系,明代有宫廷教坊,下有两京教坊、州府教坊、王府教坊,最下一级则是郡县教坊,乐户及其名籍在这些机构和地方进行流动,从而促进了音乐传播。由于乐籍中人的“官属”身份[33],即使他们居住在郡县,也是“官身”、是“国有”的,比如“吴中国工”、“锡山老国工”等,都是持“地方户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按照乐户的执业特征,既然魏良辅为“吴中国工”,居住于娄东(其时属太仓州),那么平时他肯定要到太仓州教坊、苏州府教坊以至国家最高音乐机构宫廷教坊和太常执役的。
朱元璋开国后,在都城建立教坊司,后世还保留着教坊司题碑,司中人员有七百余人之多,《秦淮志》引夏仁虎《回光寺观明教坊司题碑》一诗:
乐官山下葬诸伶,却忆当年雷海青。七百余人同禀食,幸生开国免飘零。[34]
永乐迁都北京后,原教坊司在南都保留了下来,成为两京教坊之一——南教坊,亦称“南京教坊”、“南都教坊”、“金陵教坊”,主要管理南中国的音乐事务和乐户名籍,是南中国最高音乐机构,其规模和重要性可与北京教坊媲美,两者并称“两京教坊”[35]。祝允明《猥谈》:
奉化有所谓丐户,俗谓之大贫……官彀之而征其淫贿,以迄今也。金陵教坊称十八家者亦然。[36]
“金陵教坊”即是南教坊,可见永乐迁都后,南教坊还是不断发展的,甚至有十八家之多,又如名画《南都繁会图》[37]生动描绘了南教坊戏曲演出的盛况。南教坊所处环境也很美丽繁华,《客座赘语》:
余犹及闻教坊司中,在万历十年前,房屋盛丽,连街接弄,几无髋地。长桥烟水,清池湾环,碧杨红药,参差映带,最为歌舞胜处。时南院尚有十余家,西院亦有三四家,倚门待客。[38]
明代南教坊由各色乐工构成,如万历时期之繁盛,据邓之诚《骨董琐记·教坊司题名碑记》:
南京古物保存所,有万历辛亥教坊司题名碑记,凡二十一色,有俳长、色长、衣巾教师、乐工等称。[39]
这二十一色之多的人等都是隶属南教坊的乐籍中人,其中的女乐多有资质杰出者,《万历野获编》:
丁酉南教坊马四娘(注:即马湘兰),年过五旬。畜妓十余曹。[40]
自吴人重南曲,皆祖昆山魏良辅,而北调几废,今惟金陵存此调。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云中,……今南教坊有传寿者字灵修,工北曲,其亲生父家传,誓不教一人。寿亦豪爽,谈笑倾坐,若寿复嫁以去,北曲真同广陵散矣。[41]
《情史》:
金陵教坊妓齐锦云者,能诗,善鼓琴。[42]
但这些乐工女乐由于乐籍身份,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板桥杂记》:
乐户统于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签牌之类,有冠有带,但见客则不敢拱揖耳……[43]
而包括苏州府在内的14个府级单位都直隶于南京,苏州府教坊直接由南教坊管辖,那么曲家魏良辅“吴中国工”之称号也应该主要是赖南教坊所赐。魏良辅作为“吴中国工”,按轮值轮训制,应去过北京宫廷教坊执役,但以南京教坊的重要性和就近原则,肯定去南教坊的次数更多,平时更是主要在苏州的府县教坊活动。乐籍中人既然在各级音乐机构流动,那么各地怎么安置这些前来执役的在籍“外地人”呢?清代则设立了相当于梨园会所的“局”,如苏籍昆班乐户的“昆局”有“京局”、“南京局”、“湖广局”、“山东局”、“台湾局”、“福建局”等[44],乐籍制度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延续性、稳定性,那么明代亦必如此,明代潘之恒《鸾啸小品》有一则评当时专业艺人的表演:
吴侬之寓秦淮者,坐进此道,吾以观微的之……作诸事评。[45]
“吴侬之寓秦淮者”即说明名籍在苏州的乐户歌者到秦淮居住、执役。潘之恒还讲到南京演员由于“多游吴”进而“吴曲稍进”[46],这里的“游”对乐籍中人来说并不是象今人那样的“自由行”,他们到外地有“公务”在身,是要去执役的,“游”只是个好听的说法而已。由于教坊网络的存在,明代南都成为音乐汇集和返播的中心,特别是对其直辖地区苏州的集中和辐射,如《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载:
武宗南巡(1519年),自造《靖边乐》,有笙、有笛,有鼓、有数落、吹打诸杂乐,传授南教坊。今吴儿遂引而伸之。[47]
南京是南中国的区域中心,南教坊又是南中国音乐文化的管理中心,《顾曲杂言》说南教坊曲师顿仁“尽传北方遗音,独步东南”,另有学者“详细考证了南戏弦索官腔在南京教坊产生的过程,及其南传至福建泉州及广东潮州对泉腔梨园戏的影响”[48],这些就是南教坊对于南中国地方教坊进而对南中国戏曲的意义之例,南北音乐文化在南京得以集中与返播。明末南教坊衰落以至不存,“甲申(1644)秋,南教坊不足充下陈,私徵之远境[49]”,但清代乐籍制度延续下来,教坊网络依然布局天下,南京教坊依然是音声技艺荟萃的中心,唐甄《半塘红行》:
杨家歌舞第一部,夜夜醉倒金樽前,中有南京教坊妓,低蹙蛾眉暗理弦。新翻宫词随手弹,月落才度十三篇。其人姓李名不记,我常戏唤女龟年。[50]
李良年有一首长篇古体诗,以此赠送并赞美曲师丁老,题曰《丁老行》,文曰:
吾生不见南中全盛日,秦淮丁老三叹述,达官戚里多欢娱,碧曲锦缆凌晨出,三十六曲青溪边,教坊名部分甲乙,沙嫩清箫绝世工,顿老琵琶更无匹,脱十娘家盛歌舞,碧纱如烟香满室,写生麦纸郁青缥,定情红笺擅诗笔,解貂秉烛千缠头,锁革夸铢衣金作袒。是时法曲选梨园,丁老排场推第一。[51]
“南中全盛”,多因秦淮乐籍文化之盛,而其中在籍女乐功不可没。
有学者推测为《南词引正》作跋的曹含斋、作校的吴昆麓和魏良辅之间有交往[52],这也是有可能的,而且还有他们是在南京相识交流的可能。虽然经考证曹为金坛人、吴为毗陵(今常州)人,和魏良辅都不在一个地方,但前二者是参加南京乡试的同年,后又可能在南都为官、进行文人雅集,也就有可能和赴南教坊执业并以改革昆山腔闻名的魏良辅在南京相识并切磋艺术,也就是说南教坊为文人和乐户提供了一个认识交流的绝佳平台。曹、吴在南京参加评品金陵乐籍中女乐的“莲台仙会”,也是一次戏曲研习的雅集,影响很大,不知作为乐户的魏良辅是否参加,但可以肯定的是,当魏良辅改创昆山腔后,其成果必然被南教坊所取用,潘之恒在《亘史》“艳部金陵”中记载了南教坊对魏良辅改革后的昆山腔之推崇,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