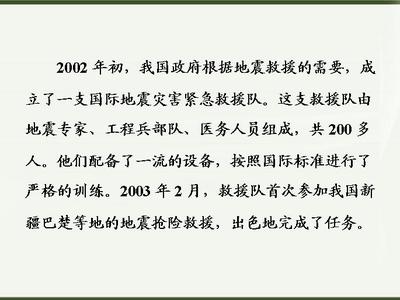内容提要本文对研究中国礼乐制度既有之理念进行梳理辨析,认定中国礼乐制度并非在战国时期因“礼崩乐坏”而终结,并非秦汉以下两千年礼乐发展无制度保障者,中华礼乐文明在确立之后延续了三千余载。中国礼乐制度实际上是以《周礼》为本、依“五礼”的演化脉络,纵贯起来把握更显清晰。作者提出中国礼乐制度四阶段论,即两周为礼乐制度确立期,汉魏、南北朝为礼乐制度的演化期,隋唐为礼乐制度的定型期,宋元以降直至清代为礼乐制度的延续发展、随着封建社会解体直至消亡期。本文对于一些与礼乐制度相关的理念进行辨析,认定礼乐制度是随五礼理念之演化、规范下三千年来所展现的丰富性整体脉络。
关 键 词中华礼乐文明三千年礼乐四段论转型国乐以雅为称华夏正声胡汉杂陈五礼用乐丰富性
我在《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1]一文中提出了中国礼乐四阶段的理念。当然,这种理念还有待学界的批评。
自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音乐文化便越来越被赋予了多种功能性的内涵,因用途各异而彰显不同功能性特征,特别是礼制以及与其相辅相成的乐制规定性,在构成中国礼乐的同时,也与另一种音乐文化的形态相对应,这就是俗乐。因此说,纵观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实际就是由两大板块构成,即礼乐与俗乐。
有一种认知,即中国社会自春秋以降“完成了从神本文化转换为人本文化的过程,成为以人为本的社会了”[2],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却略显以偏概全。其实中国传统社会中礼乐与俗乐是具有张力的两极,在社会生活中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哪一极都不可或阙者,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显现人们对某一极更为看重或称偏重,但在中国传统乐文化中,礼乐与俗乐其实都是不可偏废,这样的形态贯穿中国传统社会始终。
就礼乐说来,两周文献所及,祭祀被视为国家理念中头等重要的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者,祭祀涉及天神、地祇、人鬼,国家祭祀必定有仪式,而与祭祀仪式相须以为用的乐当然成为乐中最为重者。但礼制涉及社会上层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绝非仅仅限于祭祀之礼,礼制绝非仅适用于庙堂,我们说,在朝堂与厅堂等场合的礼制仪式中,其乐显然不能够完全等同于祭礼——坛庙之用者,如此显现礼乐的丰富性内涵,这就是在多种礼制仪式中所用的乐应该属于礼中用乐的道理。
一直以来,中国音乐史学界在探讨礼乐文化时存在着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首先是中国礼乐制度是否限于先秦或称两周,所谓“礼崩乐坏”之后礼乐制度是否消亡;其次是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来认知,礼乐制度在两周是为成熟还是确立;从乐与礼结合的视角看,礼乐制度究竟在何时定型;何谓雅乐,作为“国乐”的雅乐能否完全等同或称涵盖了礼乐,礼乐与雅乐有怎样的关系,礼乐有怎样的丰富性内涵;两周礼乐与后世礼乐的相通性和差异性何在,鼓吹乐究属何种性质;在历史长河中,礼乐之乐队组合是否单一,礼制下的乐制有怎样的显现;《乐经》何指,是否仅仅为文本的意义,若不仅如此,从乐的本体形态上释解应该怎样把握;如果以中国为礼乐文明来认知,礼乐是否仅仅只是局限在宫廷?不如此,那么从宫廷到各级地方官府中具有上下相通性的礼乐是什么,又是怎样的体制保障其实施;中国为礼乐之邦,中国礼乐制度是否仅仅限于两周,秦汉以降是否有礼乐的存在,如果有礼乐的存在,是否有制度的保障。这种保障是否为礼乐制度的整体延续,还是仅仅存有礼乐之理念,而无礼乐的具体实践;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理念之中,礼乐究竟有怎样的功能性意义,礼乐是否为传统音乐文化主流的组成部分;当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再回首,却发现既往之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无解或称含混、或称不到位,极大地阻碍了我们对传统音乐文化的整体把握与认知。
在我们既往的研究中,说到礼乐制度,一般就是指两周时期,无论是音乐学界还是大学术界大多如此。但有一点,中华文明以“礼乐文明”相称,中国是为礼乐之邦,何以对礼乐文明只谈两周而不论其后两千年?是否秦汉以降这礼乐文明消失,或称出现断层?如是,则中华礼乐文明又该如何认知,是否中华礼乐文明、中国礼乐之邦只在两周者?如果不是这种状况,讲中华礼乐文明自凸显之后延续数千年,那么,这数千年的礼乐文化是否一直贯穿着制度的约束或称规范?如是,这是否都称为礼乐制度?在数千年的礼乐制度延续过程中,有着怎样的起伏变化?这是既往的音乐史著作中没有很好回答的问题。
我近期在做的两个课题之一是“以乐观礼”(另一课题为《中国乐籍制度研究》),我力图将中国礼乐文化置于历史长河中有着更为全面的审视,以把握礼乐制度确立之先的样态和确立之后三千余载的发展演化轨迹。如果说,中国礼乐制度确立之后有着三千载的贯穿,而不是随着战国的结束而消亡,那么,就应该审视礼乐制度有着怎样的起伏变化,厘清其发展演化的脉络。在这种意义上,我将两周定为礼乐制度的确立期。虽然周公制礼作乐使礼乐制度彰显,经历了八百年又由于所谓“礼崩乐坏”似乎使礼乐制度消解,其实这只不过是显示了礼乐制度第一个“周期”的变化,诸侯以降各等级所僭越的是“周之礼”,坏掉的是“周之乐”,但国家必有礼乐之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非但没有降解,而是被后世统治者不断加入新的理解与诠释,并有制度和音乐本体实践上加以保障,因此,从整体意义上讲,礼乐制度其实是经历了一次转型。这种转型包括理念上的变化,诸如国家祭祀中所用的礼乐“六代乐舞”不再相沿、也不相传,是随朝代更替而改变,所谓“秦、汉、魏、晋代有加减……有帝王为治,礼乐不相沿”(《魏书》)。这里的礼乐显然是指雅乐之涵义。应该明确的是,所谓礼乐不相沿者,并非礼乐不再,而且这礼乐依然要有国家制度作为保障者,并且不断发展,这就是所谓转型的道理。
从乐队组合上也显示这种转型的意义。两周时期由于金石乐悬作为制度下重器,在士以上阶层中虽然依制排列的方位有异、数量多寡不同、却可以普遍拥有,所谓“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4],这就造成乐悬拥有者无论哪一种样式的礼乐、甚至俗乐都会使用这样的乐队组合形式,魏文侯所谓“古乐”、“新乐”有可能在一种乐队组合中完成。正是这种乐队使用的同一性,使得人们难以辨清礼乐的分类意义,以及在某些场合礼乐与俗乐的异同。秦汉以下,当金石乐悬失去了制度规定性普遍拥有意义上的支撑,不允许再如两周时期那样社会上层人士的普适性使用,从重器理念上金石乐悬只允许在宫廷以及王侯使用,地方官府中的各级官员逐渐排除于拥有乐悬的行列而改用鼓吹,这就意味着制度规定性的变化。我们之所以认为礼乐制度并未消解,恰恰是基于礼乐观念已经确立,从制度规定性有新的释解,而且使用礼乐既有延续又有变化的意义。

我将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定为礼乐制度的演化期,这样讲是因为这一时期有转型的特征,没有定型而为后世全盘接受和效法的整体把握。礼乐制度确立的两周时期,《周礼》、《仪礼》、《礼记》“三礼”中记载分类意义上礼的仪式更多是在前两种著述中,《礼记》多是礼乐思想之诠释。然而,前两种礼书所载礼的类型虽已有后世五礼之称谓,但整体上看却是更显宽泛,《周礼·大宗伯》中的记载可以明确这一点,而且《周礼》与《仪礼》所述又有不同。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宫廷太常系统实际上一直在对礼制加以改造,如此具有“合并同类项”的意义,在反复与游移中逐渐向五礼归拢[5],换言之,即是将两周时期所用更多礼的类型归至五礼类下,正是这种类归,也从另一层面显现出两周时期礼制为“确立”而非“成熟”的意义。
从用乐的角度讲来,更是可以显现这一时期处于演化的过程之中,这一时期与两周最大的差异在于鼓吹乐的出现。近期学界有多篇研究汉魏以降鼓吹乐与五礼之关系和涉及鼓吹乐相关机构的文章可资借鉴[6]。应该明确的是,文献记载鼓吹乐起于汉代军中,其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的类型,诸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学界多有考辨,如此也说明鼓吹乐形成之后的演进。可以看到,从军中之乐到宫廷用乐,乃至各级官府普遍使用并设置机构管理还是有一个过程。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尚未有哪一部礼典明确鼓吹乐在礼乐中的定型使用,这也是我们认为秦汉至南北朝是为礼乐制度转型、演化期的理由之一,毕竟作为鼓吹乐之起始就是中原乐器与周边民族乐器共用、所谓“胡汉杂陈”的样态,能否在礼乐中使用或称制度规定性的普遍性还是有一个“被接受”、“被规定”的过程。
我们的另一个认定为演化期的理由在于,秦汉以降那种金石乐悬作为士以上社会人士普遍拥有的制度规定性不再,这大概是那些视拥有乐悬为礼乐标志物的研究者认为礼乐制度消解的一个动因。然而,这种“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7]的乐队组合并非不存在,只不过不再具有两周时期被广泛运用的普适性意义,这种乐队组合更多用于宫廷和王府一级,这就显得越来越小众化,虽然至高无上,却有些“不食人间烟火”,马王堆、南越王、洛庄等汉墓中出土的乐悬可以明确反映这一点,这是我们所讲从乐本体上认知礼制变化处于演化期的道理。当然还应该考虑到《魏书》中所表述的那种“礼乐不相沿”亦不相传者,这也是转型演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乐的视角认知并从礼制上综合考量,隋唐可视为礼乐制度的定型期,亦可称之为成熟期。这样认知出于以下考量。我们看到,《隋书》记载时人理念对礼乐之定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先是隋人在承继南朝旧乐时认定了“华夏正声”的存在:“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並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於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於内地。及平陈后获之。髙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虽赏逐时迁,而古致犹在。可以此为本,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其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其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箏、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五人”[8]。这里敏锐地提到了清商曲为“汉来旧曲”,无论乐曲还是乐器都是为“华夏正声”(项按:从乐器上看,琵琶与箜篌两种似有外来乐器之嫌,但就乐器史研究讲来,这琵琶有秦琵琶一类,箜篌亦有从南向北传的卧箜篌者[9],与西域传来的竖箜篌并不相同。亦有观点认为,乐器中凡是单字的即为中原产生,而复合之称谓则属外来。此说有道理,但从后世的雅乐所用乐器的文献记载来看,这两种乐器多不涵盖其中,可以认为这里是从大关系上讲华夏正声,一旦有了这种理念之后还有进一步甄别的步骤),这种理念的出现对后世无论乐调的承继、乐曲的创制以及乐器的使用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华夏正声理念的提出,对后世功能性用乐、特别是礼乐中雅乐乐队组合,以及从乐律、乐调、音乐创作等层面把握华夏、中原之“正宗”传统的作用怎样考量都是不过分的。正是这种理念之形成,大有廓清华夏自身与周边融入(既有外族亦有外国者)之意,泾渭须明(能否完全做到另当别论,至少从理念以及形式上如此)。如是我们看到,与该乐队组合不同的鼓吹乐队则呈现“胡汉杂陈”的样态,一旦这种理念确立,则有豁然之感,两种不同的乐队组合如同泾渭,虽有同场相用,却是分工有自独立而存在。前者用于礼乐中的雅乐,或称成为雅乐专用乐队组合,更多在于宫廷;后者则用途广泛,从军中走向宫廷,既而在官府中普遍使用,并成为礼乐中除吉礼用乐之外所有礼制类型以及卤簿中必须使用者——这是制度的规范性!把握这一点,也是我们认定隋唐为礼乐制度定型期的重要理由。
《隋书》中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理念“雅乐为国乐”。所谓“国乐以‘雅’为称,取《诗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10]。礼乐与雅乐之关系,一直是没有说清楚者。所谓不清楚,似有一层窗户纸却一直没有被捅破,虽然此前也对雅与正之关系多有论证。当国乐一词与雅乐相联,又是一种豁然。如此可以回答并辨清礼乐与雅乐之关系等诸多问题。究竟礼乐与雅乐的概念哪一个为大呢?显然应该是礼乐概念为大,即礼乐涵盖了雅乐,雅乐是为礼乐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之所以将礼乐与雅乐的概念混用,更多还在于讲话与认知时的语境,即在某种本来就是礼的场合,独有雅乐在场,如此说法不为错,但从整体说来,辨清礼乐与雅乐的关系还是非常必要。
《隋书》中的认定使得一个上千载没有说清楚的概念得以明晰,这是文献中首次出现“国乐”的概念。所谓国乐,应该是在国家重要的仪式场合代表国家形象而以乐的形式存在者,诸如我们现在的国歌具有同样的含义。那么,在此为何不用“国歌”而用“国乐”呢?在下以为,这应该看到历史之语境,毕竟早期所谓乐的概念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如果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理念与之相联系,那么,在国家最为重要的大事——祭祀仪式中所用、又是有着特定承祀对象的乐当然是指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乐舞。在当时的语境中,这种乐舞显指“六代乐舞”,如此,这六代乐舞即是周的“国乐”,《周礼·春官·宗伯下》中由大司乐所掌对应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考所用的“云门”、“咸池”、“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即是“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11]。在国乐中既有乐之旋律,又有“颂”之歌辞,还有舞在其中。用于国家祭祀,代表国家形象,一份庄严、一份肃穆,有特定之风格,这是典型的雅乐形态。至于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国歌一词出现较晚,应该是近世的理念,我们通过检索《四库全书》,至少在唐宋之前没有与之明确对应关系者。随着社会的发展,音声技艺形式越来越显现出各自的独立性,从三位一体到歌舞乐既有关联又有明确的各自指向,即便在雅乐的使用中,也将舞作为单独的创作而加以使用,如此可以称之为“雅舞”者,诸如《大唐开元礼》中在“十二和”之外又有“文德之舞”、“崇德之舞”、“钧天之舞”、“文和之舞”、“光大之舞”、“长发之舞”、“大成之舞”、“大明之舞”等等,从一体到分立,却又综合使用,当然,以两周的理念这些都应综而归之于礼乐之雅乐目下。如此,雅乐自秦汉以降成为一朝一代不相沿袭、因时而定的、在用乐上代表国家形象者,这应是雅乐的实质内涵。
[1] 项阳:《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汉唐音乐史国际研讨会”(2009年10月西安)参会论文,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3-12转50页。
[2] 孙玄龄著:《声响中华》第2-3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3] 《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十七》,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电子检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4] 《周礼注疏·卷二十三》,刊《四库全书》全文电子检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5] 学界对于这个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可参见梁满仓先生《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6] 河南大学刘斌硕士学位论文《六朝鼓吹乐及其与五礼制度的关系研究》(2006年打印本)中文献索引目录记载较为详尽;另外,《音乐研究》2009年第5期有黎国韬《汉唐鼓吹制度沿革考》的新论。
[7]《国语·周语》卷三,参见《四库全书》全文电子检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8] 《隋书·卷十五》,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77-378页。
[9] 参见李娜:《卧箜篌起源探微》,刊《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72-78页转85页。
[10] 《隋书·卷十三·志第八·音乐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92页。
[11] 《周礼注疏·卷二十二·春官·宗伯下》,《四库全书》全文电子检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