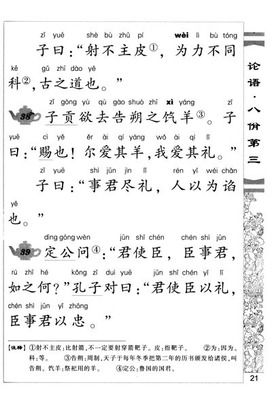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一千两百名举人于燕京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背景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参加乙未科科考的各省举人正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的《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银二万万两的突然消息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籍贯台湾省籍的举人们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内地十八省与中国东北、台湾举人接连响应,共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行省与奉、台举人,与数千燕京官民集于“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光绪帝。

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依汉代孝廉,皆乘公家车辆赴京师惯例,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又称为“公车”。
主要内容
公车上书内容反对签订《马关条约》,主要主张如下:
1拒和应战2迁都西安 3锻炼新军 4维新变法。
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结果及影响
上书被清朝官方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组织强学会,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史称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
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激励了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思考中国如何救亡图存于欧日列强帝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公车上书全文:
呈舉人康祖詒等,為安危大計,乞下明詔,行大賞罰,遷都練兵,變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國命,呈請代奏事: 竊聞與日本議和,有割奉天沿邊及臺灣一省,補兵餉二萬萬兩,及通商蘇杭,聽機器、洋貨流行內地,免其釐稅等款,此外尚有繳械、獻俘、遷民之說。閱《上海新報》,天下震動。聞舉國廷諍,都人惶駭。又聞臺灣臣民不敢奉詔,思戴本朝。人心之固,斯誠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涵濡煦覆,數百年而得此。然伏下風數日,換約期迫矣,猶未聞明詔赫然峻拒日夷之求,嚴正議臣之罪。 甘忍大辱,委棄其民,以列聖艱難締搆而得之,一旦從容誤聽而棄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豈忍上負宗廟,下棄其民哉!良由誤於議臣之言,以為京師為重,邊省為輕,割地則都畿能保,不割則都畿震動,故苟從權宜,忍於割棄也。又以群義紛紜,雖力擯和議,而保全大局,終無把握,不若隱忍求和,猶苟延旦夕也。又以為和議成後,可十數年無事,如庚申以後也。左右貴近,論率如此。故盈廷之言,雖切而不入;議臣之說,雖辱而易行,所以甘於割地、棄民而不顧也。 竊以為棄臺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舉人等棟折榱壞,同受傾壓,故不避斧鉞之誅,犯冒越之罪,統籌大局,為我皇上陳之。 何以謂棄臺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棄臺民,即可棄我,一旦有事,次第割棄,終難保為大清國之民矣。民心先離,將有見土崩瓦解之患。《春秋》書「梁亡」者,梁未亡也,謂自棄其民,同於亡也。故謂棄臺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日本之於臺灣,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島已割。諸夷以中國之易欺也,法人將問滇、桂,英人將問藏、粵,俄人將問新疆,德、奧、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啟。有一不與,皆日本也,都畿必驚;若皆應所求,則自啖其肉,手足腹心,應時盡矣,僅存元首,豈能生存?且行省已盡,何以為都畿也?故謂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此理至淺,童愚可知,而以議臣老成,乃謂割地以保都畿,此敢於欺皇上、愚天下也,此中國所痛哭,日本所陰喜,而諸夷所竊笑者也。 諸國知吾專以保都畿為事,皆將陽為恐嚇都畿,而陰窺邊省,其來必速。日本所為日日揚言攻都城,而卒無一砲震於大沽者,蓋深得吾情也。恐諸國之速以日本為師也,是我以割地而鼓舞其來也,皇上試召主割地議和之臣,以此詰之,度諸臣必不敢保他夷之不來,而都畿之不震也,則今之議割地、棄民何為乎?皇上亦可以翻然獨斷矣。或以為庚申和後,乃有甲申之役,二十年中可圖自強,今雖割棄,徐圖補救。此又敢以美言欺皇上、賣天下者也。 夫治天下者勢也,可靜而不可動,如箭之在棔,如馬之在埒,如決堰陂之水,如運高山之石,稍有發動,不可禁壓,當其無事,相視莫敢發難;當其更變,朽株盡可為患。昔者辛巳以前,吾屬國無恙也,自日本滅琉球,吾不敢問,於是,法取越南,英滅緬甸,朝鮮通商,而暹羅半翦,不過三四年間,而吾屬國盡矣。甲午以前,吾內地無恙也,今東邊及臺灣一割,法規滇、桂,英規滇、粵及西藏,俄規新疆及吉林、黑龍江,必接踵而來,豈肯遲遲以禮讓為國哉?況數十國之逐逐於後乎?譬大病後,元氣既弱,外邪易侵,變症百作,豈與同治之時,吾國勢猶盛,外夷窺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無歸,外患內訌,禍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無日矣,今乃始基耳。症脈俱見,不待盧扁,此舉人等所為日夜憂懼,不憚僭越,而謀及大計也。 夫言戰者,固結民心,力籌大局,可以圖存;言和者,解散民禮,鼓舞夷心,更速其亡。以皇上聖明,反覆講辯,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必當獨斷聖衷,翻然變計者。不揣狂愚,統籌大計,近之為可和可戰,而必不致割地、棄民之策;遠之為可富可強,而斷無敵國外患之來。伏乞皇上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而已。 何謂鼓天下之氣也?天下之為物,譬猶器也,用其新而棄其陳,病乃不存。水積為淤,流則不腐;戶閉必壞,樞則不蠹;砲燒則晶瑩,久置則生鏽;體動則強健,久臥則委弱。況天下大器日摩洗振刮,猶恐塵垢;置而不用,壞廢放失;日趨於弊而已。今中國人民咸懷忠義之心,非不可用也。而將吏貪懦,兵士怯弱,乃至聞風嘩潰,馴至辱國請和者,得無皇上未有以鼓其氣耶?是有四萬萬之民,而不善用之也。 伏念世祖章皇帝手定天下,開創之聖人也,而順治十八年中,責躬之詔屢下。穆宗毅皇帝手定艱難,中興之盛功也,而同治元、二年開罪己之詔至切。天下臣民,伏讀感泣,踴躍奮發,然後知列聖創定之功所由來也。《傳》謂:「禹、湯罪己,興也勃焉。」唐臣陸贄謂:「以言感人,所感己淺,言猶不善,人誰肯懷?」今日本內犯,震我盛京,執事不力,喪師失地,幾驚陵寢,列聖怨恫。皇上為人子孫,豈無有震動厥心者乎?然於今經年,未聞有罪己之詔,責躬咎厲,此樞臣輔導之罪,宜天下之有望於皇上也。 伏乞皇上近法列聖,遠法禹、湯,時下明詔,責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厲天下,同雪國恥。使忠臣義士讀之而流涕憤發,驕將懦卒讀之而感愧忸怩,士氣聳動,慷慨效死。人懷怒心,如報私仇。然後皇上用其方新之氣,奔走馳驅,可使赴湯蹈火,而豈有聞風嘩潰者哉?此列聖善用其民之成效也,故罪己之詔宜下也。 皇上既赫然罪己,則凡輔佐不職、養成潰癰,蔽惑聖聰、主和辱國之樞臣,戰陣不力、聞風逃潰、剋扣軍餉、喪師失地之將帥,與夫擅許割地、辱國通款之使臣,調度非人、守禦無備之疆吏,或明正典刑,以寒其膽,或輕予褫革,以蔽其辜,詔告天下,暴揚罪狀。其餘大僚尸位、無補時艱者,咸令自陳,無妨賢路。庶幾朝廷肅然,海內吐氣,忭頌聖明,願報國恥,此明罰之詔宜下也。 大奸既黜,典刑既正,然後懸賞功之格,為不次之擢。 將帥若宋慶、依克唐阿,疆吏若張之洞、李秉衡,諒山舊功若馮子材,皆有天下之望,宜有以旌之。或內綜樞柄,或外典幾疆,以鼓舞天下。夫循資格者,可以得庸謹,不可以得異材;用耆老者,可以為守常,不可以為濟變。不敢言遠者,請以近事言之。當同治初年,沈葆楨、李鴻章、韓超皆以道員擢為巡撫,閻敬銘則由臬司擢撫山東,左宗棠則以舉人部員賞三品卿,督辦軍務,劉蓉且以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陝西巡撫,用能各展材能,克佐中興。若漢武帝之用才,明太祖之任吏,皆用不次之拔擢,不測之刑威,用能奔走人才,克成功業。伏讀《世祖章皇帝聖訓》,屢詔舉天下之才,下至山林隱逸,舉貢生監,佐貳雜職,皆引見擢用,此誠聖主鼓舞天下之盛心也。今日變甚急,天下未為乏才,而未聞明詔有求才之舉,似非所以應非常之變也。夫有非常之事變,即有非常之才應之,同治中興之臣,率多草澤之士。宋臣蘇軾謂:「智名勇功之人,必有以養之。」伏乞詔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撫、兩司,各舉所知,不論已仕未仕,引見擢用,隨才器使。昔漢高之於樊噲,每勝增其爵級;其於韓信,一見即拜大將。凡有高材,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懷國恥,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報皇上,故求才之詔宜下也。 夫人主所以駕馭天下者,爵賞、刑罰也。賞罰不行,則無以作士氣;賞罰顛倒,則必至離民心。今聞日本要我以釋喪師之將,是欲以散衆志而激民變也。苟三詔既下,賞罰得當,士氣咸伸,天下必距躍鼓舞,奔走動容,以赴國家之急,所謂下詔鼓天下之氣者,此也。 何謂定天下之本也?自古都畿皆憑險阻。自非周公盛德,不敢以洛邑為都,故婁敬挽輅,漢祖移駕,宋汴梁無險,致敵長驅,徽、欽之辱,非獨失德使然也。方今旅順已失,威海既隳,險阻無有,京師孤立。近自北塘、蘆臺、神堂、澗河,遠自山海、撫寧、昌黎、樂亭、清河、蠶沙,處處可入,無以為防守之計。此次和議即成,而諸夷窺伺,皆可揚帆而達津、沽。《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既失矣,國何可守?故今日大計,必在遷都。 請以前事言之。我朝當道光之時,天下全盛,林則徐督粵,鄧廷楨督閩,疊敗英酋朴鼎查、額爾金之兵。而移師天津,即開五口,而償二千萬矣。其後道光二十九年,咸豐六年,咸豐八年,皆始戰終和,借京師以為要挾,諸口益開,巨款累償。暨庚申之變,我文宗顯皇帝至為熱河之狩,焚燒御園,震驚宗廟。至今萬壽山營繕雖新,餘燼尚在。由是洋人掉臂都畿,知吾虛實。此事非遠,皆諸臣所目擊,前車易鑑者也。尋五十年來,吾大臣用事及清流進議者,不深維終始,高談戰事。及震動津、沽、宮廷惶駭,則必以戰無把握,輸款求和。於是尸位無恥之流累借和議以容身。朝廷雖深知主戰之直,必不見從;亦明知議和之非,俯徇所請。蓋實患既至,非復空言所能抵塞。故外夷所累藉以脅制者,皆以吾京師近海之故。彼雖小丑,無求不得;吾雖大勝,終必請和,亦既彰明較著矣。用事者既不早為自強之謀,又不預作遷都之計,夷釁既開,虛僑空談,相與言戰,乃稍敗衄,震動畏縮,苟幸得和,乃至割根本之地、棄千萬之民而亦為之,其不智而失計亦甚矣。 以今事言之,吾所以忍割地、棄民者,為保都畿,安乘輿也。微論將來外夷繼軌,都畿終不能保,乘輿終必致驚,而以區區十里之城,棄千里之地、十兆之民以易之,甚非策也。以後事料之,諸夷知我之專保都畿也,咸借端開釁,陽攻都畿以索邊省,我必將盡割沿邊十餘省,以保都畿,是棄天下萬里之地、數萬萬之民,以易區區之都城也。 夫王者有都以治天下耳,豈有割天下以保都城而恃為至計哉!以五十年來前後今事考之,吾之款和輸割,皆為都畿邊海之故,其事易徵,其理易明。昔者苟能自強,雖不遷都,猶可立國;今日雖欲自強,而外夷連軌,計不及待。故非遷都,智者無所騁其謀,勇者無所竭其力,必將坐困脅割盡而後已。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國,豈不痛哉! 故今日猶言不遷都者,非至愚病狂,則甘心鬻國。大臣既不能預鑑於前,而至辱國,又不補救於後,必至喪邦。皇上聖明,試以詰難諸臣,當無從置喙,或下群臣集議,當亦從同,而後宸衷獨斷,定議遷都,以安宗廟而保疆土,無逾於此。 或謂我能往,寇亦能往,我遷都以避,寇深入以爭,自古遷都之謀,皆遂為偏安之計,此明臣于謙所以力爭,而庚申所以止議也。不知古今異形,今昔殊勢,外夷政由議院,愛惜民命,用兵甚慎,不敢深入,與古不同,今日本用兵已可概見。我即遷都,可以力戰,雖沿邊糜爛,而朝廷深固,不為震懾,即無所脅制,主和者無所容其身,主戰者得以激其氣。豈不鑑於五十年事,而尚以為孤注哉!獨不畏徽、欽之辱乎? 或謂國君有死社稷之義,此尤不達經義之讆也。夫國君者,諸侯之謂,以社稷受之天子,當死守之,猶今地方有司,有城池之責比耳。若天子以天下為家,四方皆可建都立社,何一城之為?明莊烈帝既為迂儒所誤,明社遂屋,豈可復以此誤我國家哉!且一朝而有數都,自古為然,商七遷,周營三邑,漢室二京,唐世兩都,及明祖定鼎金陵,永樂乃遷燕薊,以太子留守南京,宮殿官僚,悉仍舊制,擇有司扈從行在,廟社官署,隨時增修,永分兩京,可以為法。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熱河、遼瀋,則更迫強敵;南入汴梁、金梁,則非控天險;入蜀則太深;都晉則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近雖水利不開,漕運難至,然都畿既建,百貨自歸,若藉機器督散軍,亦何水利之不開哉? 夫京都建自遼、金,大於元、明,迄今千年,精華殆盡。近歲西山崩裂,屢年大水,城垣隳圮,閭閻房屋,傾壞無數。甚者太和正門、祈年法殿無故而災,疑其地氣當已洩盡。王者順天,革故鼎新,當應天命,謂宜舍燕薊之舊京,宅長安為行在。然人情樂於守常,難於移動,以盤庚遷殷,誠論至煩「三誥」,以魏文遷洛,世臣猶有違言。 蓋世臣大家,輜重繁多,遷徙不易,聽其變舊,庶免阻撓,自非大有為之君,不易破尋常之論。魏文南征,永樂北伐,皆借巡幸留而作都。皇上既講明利害,遠之防諸夷之聯鑣,近之距日本之脅制,急斷乃成,亟法漢高,即日移駕,奉皇太后巡於陝西,六龍西幸,萬人歡慶。幸當講和之時,民心稍靜,擇親藩之望重者留守舊京,車駕從容西狩,擇百司扈從,以重兵擁衛,必不慮宵小生心。日人雖欲輕兵相襲,數日乃抵津、沽,而我大雲集都畿,猶可一戰,彼豈敢深入內地,飛越四天門、潼關之險哉?然後扼守函、潼,奠定豐、鎬,建為行在,權宜營置,激厲天下,妙選將才,總屯重兵,以二萬萬之費改充軍餉,示之以雖百戰百敗,沿海糜爛,必不為和。日本既失脅制之術,即破舊京,不足輕重,必不來攻,都城可保。或俯就駕馭,不必割地,和議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戰矣。故謂遷都以定天下之本者,此也。 何謂強天下之勢也?凡兩物相交,必有外患,獸有爪牙之衛,人有甲冑之蔽,列國並立,兵者,國之甲冑也。昔戰國之世,魏有武卒,齊有輕騎,秦有武士。楚莊投袂,屨及劍及,即日伐宋。蓋諸國並騁,無日不訓討軍實,國乃可立。今環地球五十餘國,而泰西爭雄,皆以民為兵,大國練兵至百餘萬。選兵先以醫生視其強弱,乃入學堂學習佈陣、騎擊、測量、繪圖。其陣法、營壘、器械、槍炮,日夕講求,確有程度。操練如真戰,平居如臨敵,所由雄視海內也。日本步武其後,遂來侮我。而我猶守大一統之舊制以待之,不訓兵備,至有割地款和之事。今日氛未已,不及精練,然能將卒相知,共其甘苦,器械精利,壯其膽氣,亦可自用,選將購械,猶可成軍。 夫用兵者,用其氣也。老將富貴已足,無所願望,或聲色銷鑠,精氣竭衰,暮氣已深,萬不能戰。即或效忠,一死而已,喪師辱國,不可救矣。近者楊芳失律於粵城,鮑超驕蹇於西蜀,令彼再如為兵時跳身坐炮眼上,豈可得哉? 此趙惠王所以致疑於廉頗,光武所以不用馬援也。伏讀《聖祖仁皇帝聖訓》,亦以老將氣衰不能用,此真聖人之遠謨也。惟少年強力,賤卒懷賞,故敢萬死以求一生。故選將之道,貴新不貴陳,用賤不用貴。且外夷戰備日新,老將多恃舊效,昧於改圖,故致無功。今請更練重兵,以待敵變。都畿根本至重,必有忠勇謀略下士愛民之督撫,如李秉衡之流者,專督畿輔之軍,假令便宜,令其密選將才十人,不拘資格,各練十營,日夜訓練,厲以忠義,激以國恥,擇其精悍,優其餉糈,以為選鋒。既有李克用之義兒,李成梁之家丁,緩急可恃,得此五萬,都畿可守。再有將才,可以續練。前敵之宋慶、魏光燾、李光久,宿將之馮子材,並一時人望,可咨以將才,假以便宜,悉用選鋒,厲以仇恥,沿邊疆臣,亦宜選振作有為之人,不宜用衰老資格之舊,各選將才,各練精兵萬人。並飭紳士各自團練,遇有警迫,堅壁清野,並請敕下群臣,外至守令,傳諭紳士,有忠義沈毅慷慨知兵之士,不拘資格,悉令薦舉,引見拔用,或交關內外軍差遣。各縣草澤中,皆有魁梧任氣忠義謀略之士,責令州縣各薦一人,拔十得一,才不可勝用,必有千城之選,足應國家之急者。是謂選將。 《管子》謂:「器械不精,以卒予敵。」外夷講求槍炮,製作日新。槍則德有得來斯槍、毛瑟槍,法有沙士缽槍,英有亨利馬梯尼槍,美有哈乞開司槍、林明敦槍、秘薄馬地尼槍,俄有俾爾達奴槍,而近者英之黎姆斯槍為尤精。炮自克虜伯炮、嘉立炮外,近有毒煙開花炮、空氣黃藥大炮,以及暗炮臺、水底自行船、機器飛車、禦敵戎衣、測量炮子表,巧製日新。日本步武泰西,亦能自製新器,曰苗也理槍。而我中國未能創製,只購舊式,經辦委員不解製造,於堅輕遠准速無所諳曉,或以舊槍改充毛瑟,貪其價廉,乃不可用,其中飽者益無論。聞近來所購者,多暹羅廢槍,香港以二兩八錢購得,而中國以十二兩購之。查同治十三年,德之攻法,每分時槍十餘響。光緒三年,俄之攻土,槍三十餘響。至日之犯我,槍乃六十餘響。我師潰敗,雖將士不力,亦器械不精,故膽氣不壯,有以致之。故吾非懸重賞,以厲新製,不足取勝。今不及辦,宜選精於製造操守廉潔之士,專購英黎姆斯槍十數萬,以備前敵,並廣購毒煙空氣之炮、禦敵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無恐,是謂購械。 又我南洋諸島民四百萬,雖久商異域,咸戴本朝。以喪師割地為外夷姍笑,其懷憤怒過於內地之民,其人富實,巨萬之資以數千計,通達外情,咸思內歸中國,團成一軍,以雪國恥。特去天萬里,無路自通。若派殷商,密令舉辦,派公忠智略通達商情之大臣領之,或防都畿,或攻前敵,並令聯通外國,助攻日本,或有奇功。所謂練兵以強天下之本者,此也。 然凡上所陳,皆權宜應敵之謀,非立國自強之策也。伏念國朝法度,因沿明制,數百年矣。物久則廢,器久則壞,法久則弊。官制則冗散萬數,甚且鬻及監司,教之無本,選之無擇,故營私交賂,欺飾成風,而少忠信之吏。學校則教及詞章詩字,寡能講求聖道,用非所學,學非所用,故空疏愚陋,謬種相傳,而少才智之人。兵則綠營老弱,而募勇皆烏合之徒。農則地利未開,而工商無製造之業。其他凡百積弊,難以遍舉。而外國奇技淫巧,流行內地,民日窮匱,乞丐遍地,群盜滿山,即無外釁,精華已竭,將有他變。方今當數十國之覬覦,值四千年之變局,盛暑已至,而不釋重裘,病症已變,而猶用舊方,未有不暍死而重危者也。 竊以為今之為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蓋開創則更新百度,守成則率由舊章。列國並立,則爭雄角智;一統垂裳,則拱手無為。言率由則外變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無為而諸國交爭,必至四分五裂。《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董仲舒曰:「為政不調,甚者更張,乃可謂理。」若謂祖宗之法不可變,則我世祖章皇帝何嘗不變太宗文皇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貝勒舊法為治,剛我聖清豈能久安長治乎?不變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馴至於亡,與變法而光宗廟之威靈,可以大強,孰輕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 不揣狂愚,竊為皇上籌自強之策,計萬世之安,非變通舊法,無以為治。變之之法,富國為先。戶部歲入銀七千萬,常歲亦已患貧,大農仰屋,羅掘無術,鬻官稅賭,亦忍恥為之,而所得無幾。然且旱潦河災,船炮巨帑,皆不能舉。聞日本索償二萬萬,是使我臣民上下三歲不食乃能給之。若借洋債,合以利息扣折,百年亦無償理,是自斃之道也。與其以二萬萬償日本,何如以二萬萬外修戰備,內變法度哉! 夫富國之法有六:曰鈔法,曰鐵路,曰機器輪舟,曰開礦,曰鑄銀,曰郵政。 今奇窮之餘,急籌巨款,而可以聚舉國之財,收舉國之利,莫如鈔法。今天下銀號報明貲本,皆存現銀於戶部及各省藩庫,戶部用精工製鈔,自一至百,量其多少,皆給現銀之數,而加其半,許供賦稅祿餉。其大者戶部皆助貲本,其虧者戶部皆代攤償,助其流通,昭彰大信。巨商樂借國力,富戶不患倒虧。以十八行省計之,可得萬萬。既有官銀行,上下相通,若有鐵路、船廠大工,可以代籌,軍務、賑務要需,可以立辦。國家借款,不須重息中飽,外國匯款,無須關票作押。公款寄存,可有入息,鈔票通行,可擴商務。今各省皆有銀票錢票,而作偽萬種,利不歸公,何如官中為之,驟可富國哉?此鈔票宜行一。 可縮萬里為咫尺,合旬月於晝夜,便於運兵,便於運械,便於賑荒,便於漕運,便於百司走集,便於庶士通學,便於商賈運貨,便於負擔謀生,便於通言語,一風俗。有此數便,不費國帑而可更得數千萬者,莫如鐵路。夫鐵路之利,天下皆知。山海關外,久已興築,今方連兵,其效已見,所未推行直省者,以費巨難籌耳。若一付於民,出費給牌,聽其分築,官選通於鐵路工程者,畫定行省郡縣官路,明定章程,為之彈壓保護,凡軍務、運兵、運械、賑荒,皆歸官用,酌道里遠近,人數繁寡,收其牌費。吾民集款力自能舉,無使外國收我利權。天下鐵路牌費,西人計之,以為可得七千萬,且可移民出於邊塞,而荒地闢為腴壤,商貨溢於境外,而窮閭化為富民。俄人琿春鐵路將成,邊患更迫,但為防邊已當亟築,況可得巨款哉?且可裁漕運,而省千萬之需,去驛鋪,而溢三百萬之項。此鐵路宜行二。 機器廠可興作業,小輪舟可便利通達。今各省皆為厲禁,致吾技藝不能日新,製作不能日富,機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窳敗,徒使洋貨流行,而禁吾民製造,是自蹙其國也。官中作廠,率多偷減,敷衍欺飾,難望致精,則吾軍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虜伯,英之黎姆斯,著於海內,為國大用,皆民廠也。宜縱民為之,並加保護。凡作機器廠者,出費領牌,聽其創造,輪舟之利,與鐵路同,官民商賈,交收其益,亦宜縱民行之,出費領牌,聽其拖駛,可得巨款。此機器輪舟宜行三。 《周官》「礦人」,漢代鐵官,開礦之法久矣。美人以開金銀之礦富甲四海,英人以開煤鐵之礦雄視五洲。其餘各國開礦,均富十倍。而藏富於地,中國為最,如雲南銅、錫,山西、貴州煤、鐵,湖、廣、江西銅、鐵、鉛、錫、煤,山東、湖北鉛,四川銅、鉛、煤、鐵,其最著者,互古封禁,留待今日。方今國計日蹙,雖極節儉,豈能濟此艱難哉?家有重寶,而仰屋嗟貧,無策甚矣。山西煤、鐵尤甚,星羅棋布,有百三十萬方里,苗皆平衍,品亦上上,德人以為甲於五洲,地球用之千年不盡。又外蒙古,阿爾泰山即金山也,長袤數千里,金產最著,苗亦平衍,有整塊數斤者,俄人並為察驗繪圖。至滇、粵之礦,尤為英、法所窺伺,我若不開,他人入室。今雲南已專設礦務大臣,熱河、開平亦設官局,並著成效。而未見大利者,皆由礦學之未開,採辦之非人也。礦學以比國為最,自山色、石紋、草木、苗脈、子色,皆有專書。宜開礦學,專延比人教之,且為踏勘。購機器以省人工,築鐵路以省轉運,二十取一而無定額稅,選才督辦而無濫私人,則吾金、銀、煤、鐵之富,可甲地球。此礦務宜開四。 錢幣三品以通有無,其制最古。自濠鏡通商,洋銀流入中國,漸遍內地,及於京師。觀其正朔,則耶穌之年號,而非吾之紀元也,是謂無正朔。考其漏巵,則每歲運入約數百萬,進口無稅,八成夾鉛,而換我足銀,市價漲落七錢二分之重,或有漲至八錢者,多方折耗,是謂大漏巵。名實俱亡,吾政之失,孰大於是!而吾元寶及綻,形體既難握攜,分兩又無一定,有加耗、減水、折色、貼費之殊,有庫平、規平、湘平、漕平之異,輕重難定,虧耗滋多。而彼重率有定,體圓易握,人情所便,其易流通,固也。查泰西皆用本國之銀,如俄用盧布,德用馬克,奧用福祿林,英用喜林,外國銀錢不許通用。我宜自鑄銀錢,以收利權。今廣東已開局鑄銀,但患經費不敷,未能擴充以鑄大圓耳。夫金銀質軟,只用九成。查美國鑄銀,每刻可成大圓一千二百,而每圓之利,三分移作製造之費,猶有餘饒,利亦厚矣。請飭下戶部,預籌巨款,並令行省皆開鑄銀局,其花紋年號,式樣成色,皆照廣東鑄造,增置大圓。由督撫選廉吏精明專司此局,厚其薪水,嚴其刑罰,督撫以時月抽提,戶部以化學核驗。他日礦產既盛,增鑄金錢,抵禁洋圓,改鑄錢兩,令嚴而民信,可以塞巵,而存正朔矣。此鑄銀宜行者五。 我朝公牘文移,諭旨奏摺,皆由塘驛汛鋪傳遞,而軍務加緊,又有驛馬遍佈天下。設官數百,養夫數萬,歲費帑三百萬兩,而民間書札不得過問。貲費厚重,猶復遠寄艱難,消息浮沉,不便甚矣!查英國有郵政局寄帶公私文書,境內之信費錢二十,馬車急遞,應時無失,民咸便之,而歲入一千六百餘萬。我中國人四萬萬,書信更多,若設郵政局以官領之,遞及私書,給以憑樣,與鐵路相輔而行,消息易通,見聞易廣,而進坐收千餘萬之款,退可省三百萬之驛,上之利國,下之便民。此郵政宜行六。 行之六者,國不患貧矣。然百姓匱乏,國無以為富也。 中國生齒,自道光時已四萬萬,今經數十年休養生息,不止此數。而工商不興,生計困蹙,或散之他國,為人奴隸,或嘯聚草澤,蠹害鄉邑,雖無外患,內憂已亟。夫國以民為本,不思養之,是自拔其本也。 養民之法:一曰務農,二曰勸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窮。 天下百物皆出於農,我皇上躬耕,皇后親蠶,董勸至矣。而田畯之官未立,土化之學不進。北方則苦水利不闢,物產無多;南方則患生齒日繁,地勢有限。遇水旱不時,流離溝壑,尤可哀痛,亟宜思良法以救之。外國講求樹畜,城邑聚落,皆有農學會,察土質,辨物宜。入會則自百谷、花木、果蔬、牛羊牧畜,皆比其優劣,而旌其異等,田樣各等,機車各式,農夫人人可以講求。鳥糞可以肥培壅,電氣可以速長成,沸湯可以暖地脈,玻罩可以禦寒氣,刈禾則一人可兼數百工,播種則一日可以三百畝。擇種一粒,可收一萬八百粒,千粒可食人一歲,二畝可養人一家。瘠壤可變為腴壤,小種變為大種,一熟可為數熟。吾地大物博,但講之未至,宜命使者擇其農書,遍於城鎮,設為農會,督以農官。農人力薄,國家助之。比較則棄楛而從良,鼓舞則用新而去舊,農業自盛。若絲、茶為中國獨擅,恃為大利。而近年意大利、法蘭西、日本皆講蠶桑,印度、錫蘭茶葉與吾敵,奪我之利,致吾衰減至千餘萬。而吾養蠶未善,種茶未廣,再不講求,中國之利源塞矣。宜設絲茶局,開絲茶學會,力求振興,推行各省。其餘東南種棉蔗,西北講牧畜。棉以紡織,蔗以為糖,牛毛之毳,可以織呢絨氈毯,以及沙漠可以開河種樹,海濱可以漁網取魚。種樹之利,俄在西伯利部歲入數百萬,漁人之計,美之沿海可得千餘萬。今林木之運,罐頭之魚,中國銷流甚盛,宜有以抵拒之。又美國養蜂,西人以為能盡其利,所入等於舊金山之金礦,宜有以鼓勵之。此務農宜行一也。 《周官》「考工」,《中庸》「勸工」。諸葛治蜀,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管仲治齊,三服女工,衣被天下。木牛之製,指南之車,富強之效也。嘗考歐洲所以驟強之由,自嘉慶十二年英人始製輪船,道光十二年即犯我廣州,遂辟諸洲屬地四萬里。自道光二十五年後鐵路創成,俄人以光緒二年築鐵路於黑海、裏海,開闢基窪,河爾霸等國六千里,其餘電線、顯微鏡、德律風、留聲筒、輕氣球、電氣燈、農務機器,雖小技奇器,而皆與民生國計相關。若鐵艦、炮械之精,更有國者所不能乏。前大學士曾國藩手定大難,考知西人自強之由,創議開機器之局。近者各直省漸為增設,而只守舊式,絕無精思,創為新製,蓋國家未嘗教之也。宜令各州縣咸設考工院,譯外國製造之書,選通測算學童,分門肄習,入製造廠閱歷數年。工院既多,圖器漸廣,見聞日辟,製造日精。凡有新製繪圖貼說,呈之有司,驗其有用,給以執照,旌以功牌,許其專利。工人自為身名,必殫精竭慮,以求新製。槍炮之利,器用之精,必有以應國家之用者。彼克虜伯炮、毛瑟槍,為萬國所必需,皆民造也。查美國歲給新器功牌一萬三千餘,英國三千餘,法國千餘,德國八百,奧國六百,意國四百,比利時、嗹國、瑞士皆二百餘,俄國僅百餘,故美之富,冠絕五洲,勸工之法,莫善於此。此勸工宜行二也。 凡一統之世,必以農立國,可靖民心;並爭之世,必以商立國,可侔敵利,易之則困敝矣。故管仲以輕重強齊國,馬希范以工商立湖南。且夫古之滅國以兵,人皆知之;今之滅國以商,人皆忽之。以兵滅人,國亡而民猶存,以商賈滅人,民亡而國隨之。中國之受斃,蓋在此也。今外國鴉片之耗我,歲凡三千三百萬,此則人盡痛恨之,豈知洋紗、洋布歲耗凡五千三百萬。洋布之外,用物如洋綢、洋緞、洋呢、漳絨、羽紗、氈毯、毛巾、花邊、鈕扣、針、線、傘、燈、顏料、箱篋、磁器、牙刷、牙粉、肥皂、火油,食物若咖啡、呂宋煙、夏灣拿煙、紙捲菸、鼻煙、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餅、洋糖、洋鹽、藥水、丸粉、洋乾果、洋水果,及煤、鐵、鉛、銅、馬口鐵、材料、木器、鐘表、日規、寒暑針、風雨針、電氣燈、自來水、玻璃鏡、照相片、玩好淫巧之具,家置戶有,人多好之,乃至新疆、西藏亦皆銷流,耗我以萬萬計。而我自絲、茶減色,不敵鴉片,其餘自草帽辮、駝毛、羊皮、大黃、麝香、藥料、綢緞、磁器、雜貨不值三千萬,值得其洋布之半數。而吾民內地則有釐捐,出口則有重稅,彼皆無之。吾物產雖盛,而歲出萬萬,合五十年計之,已耗萬兆,吾商安得不窮!今日本且欲通及蘇、杭、重慶、梧州,又加二萬萬之償款。吾民精華已竭,膏血俱盡,坐而垂斃,弱者轉於溝壑,強者流為盜賊,即無外患,必有不可言者。似宜特設通商院,派廉潔大臣辟長於理財者,經營其事。今各直省設立商會、商學、比較廠,而以商務大臣統之,上下通氣,通同商辦,庶幾振興。商學者何?地球各國貿易條理繁多,商人愚陋,不能周識,宜譯外國商學之書,選人學習,遍教直省,知識乃開,然後可收外國之利。商會者何?一人之識未周,不若合衆議;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會、大公司。國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務乃可遠及四洲。明時葡萄牙之通澳門,荷蘭之收南洋,英人乾隆時之取印度,道光時之犯廣州,非其政府之力,乃其公司之權。蓋民力既合,有國助之,不獨可以富強,且可以闢地,商會所關,亦不少矣。比較廠者何?泰西賽會,非騁遊樂,所以廣見聞,發心思,辨良楛。凡物有比較,優劣易見,則劣者滯消,而優者必行,彼之貨物流行中土,良由此法。今我並宜設立此廠,於是廣紡織以敵洋布,造用物以敵洋貨。上海造紙,關東捲菸,景德製窯,蘇、杭織造,北地開葡萄園以釀酒,山東製野蠶繭以成絲,江北改土棉而紡紗,南方廣蔗園而製糖,皆與洋貨比較,精妙華彩,務溢其上。又令吾領事探其所好,投其所欲,更出新製,且以奪其利,敵其貨而已。然後蠲釐金之害以慰民心,減出口之稅以擴商務。此外發金、銀、煤、鐵之利,足以奪五洲;製臺艦槍炮之精,可以橫四海。故惠商宜行三也。 我生齒既繁,鐵路未開,運貨為難。即以北口之皮,京師之煤,天津之貨,作貨者人四百,而運貨者人六百,生之者少,食之者多。其餘窮困無業,游散無賴,所在皆是。 京師四方觀望,而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殘疾,無人收恤,廢死道路,日日而有。公卿士夫,車聲隆隆,接軫不問,直省亦然。此皆皇上赤子也,皇上不忍匹夫之失所,但九重深居,清道乃出,不知之耳。若親見其呼號無訴,膿瘍臥道,豈忍目睹乎!以一人而養天下,勢所不給,宜設法收恤之。恤之之法:一曰移民墾荒。西北諸省,土曠人稀,東三省、蒙古、新疆疏曠益甚,人跡既少,地利益以不開,早謀移徙,可以辟利源,可以實邊防,非止養貧民而已。移有三:曰罪遣,今俄國徒希利尼黨於西伯利部,而西北利部以開;曰認耕,英之喀拿大、新疆般鳥各島,美之密士失必河東南各省,巴西全國是也;曰貿遷,荷蘭南洋諸島,皆商留者也。英自移民之後,闢地過本國七十倍,民益繁盛,豈有苦其生齒之繁而棄之。今我民窮困,游散最多,為美人傭奴,然猶不許,且以見逐,澳洲南洋各島效之,數百倍之民失業來歸,何以安置?不及早圖,或為盜賊,或為間諜,不可收拾。今鐵路未成,遷民未易,若鐵路成後,專派大臣以任此事,予以謀生之路,共有樂土之安,百姓樂生,邊境豐實,一舉數善,莫美於是。二曰教工。《周禮》有裏布以罰不毛,圜土以警遊惰。游民無賴,小之作奸,大之為盜。宜令州縣設立警惰院,選善堂紳董司之。凡無業游民,皆入其中,擇其所能,教以藝業。紳董以其工業鬻給其食,十一取之,以充經費,限禁出入,皆有程度。 其有大工大役,以軍法部署,俾充役作。其能改過,取保乃放,再犯不赦。其小過犯人,皆附入之,等其輕重,以為歲月。其乞丐之非老弱殘疾,咸收於外院,工作如之。窮民得食,而良民賴安,仁政之施,似難緩此。三曰養窮。鰥寡孤獨,疲癃殘疾,盲聾瘖啞,斷者侏儒,民之無告,先王最矜,皆常餼焉。宜令各州縣市鎮聚落,並設諸院,咸為收養,皆令有司會同善堂,勸籌巨款,妥為經理司其事。 經理有效,窮民樂之,聯名請獎,許照軍功勞績獎勵,則無一夫之失所,其於皇仁豈為小補?民心固結,國勢繫於苞桑矣。故恤窮宜行四也。 然富而不教,非為善經;愚而不學,無以廣才。是在教民。學校之設選舉之科,先王之法盛矣。然漢、魏以經學舉孝廉,唐、宋以詞賦重進士,明以八股取士,我朝因之,誦法朱子,講明義理,亦可謂法良意美矣。然功令禁用後世書,則空疏可以成俗;選舉皆限之名額,則高才多老名場。況得之則詞館而躐公卿,偕於旦夕;失之則耆碩不聞徵聘,終老茅菅。題難,故少困於搭截,知作法而忘義理;額隘,故老逐於科第,求富貴而廢學業。標之甚高,束之甚窄。甚至鑑於明末,因噎廢食,上以講學為禁,下以道學為笑,故任道之儒既少,才智之士無多,乃至嗜利無恥,蕩成風俗,而國家緩急,無以為用。法弊至此,亦不得不少變矣。若夫小民識字已寡,或有一省而無禮律之書,一縣而無童蒙之館,其為不教,甚矣。 夫天下民多而士少,小民不學,則農工商賈無才。產物成器,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遷善改過,亦難為治,非覆懤群生之意也。故教育及於士,有逮於民,有明其理,有廣其智。能教民,則士愈美;能廣志,「志」,疑應當作「智」。則理愈明。今地球既辟,輪路四通,外侮交侵,閉關未得,則萬國所學,皆宜講求。宋臣姚燮謂:「我之所為,彼皆知之;彼之所為,我獨不聞,安得不為所制乎?」嘗考泰西之所富強,不在炮械軍兵,而在窮理勸學。彼自七八歲人皆入學,有不學者責其父母,故鄉塾甚多。其各國讀書識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其學塾經費,美國乃至八千萬。其大學生徒,英國乃至一萬餘。其每歲著書,美國乃至萬餘種。其屬郡縣,各有書藏,英國乃至百餘萬冊。所以開民之智者亦廣矣。而我中國文物之邦,讀書識字僅百之二十,學塾經費少於兵餉數十倍,士人能通古今達中外者,郡縣乃或無人焉。 夫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土耳其天下陸師第一而見削,印度崇道無為而見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開其智。武科弓刀步石無用甚矣。《王制》謂:「贏股肱,決射御,出鄉不與士齒。」此武后之謬制,豈可仍用哉?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楨請廢武科,近年詞臣潘衍桐請開藝學。今宣改武科為藝學,令各省、州、縣遍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分立學堂,而測量、圖繪、語言、文字皆學之。 選學童十五歲以上入堂學習,仍專一經,以為根本;延師教習,各有專門。學政有司,會同院師,試之以經題一論及專門之業,通半中選,不限命額,得薦於省學,謂之秀才,比之諸生。五年不成者出學。省學書器益多,見聞益廣,學政督撫會同其院師,每歲試其專門之業,增以經,一論史,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選,不限名額,貢於京師,謂之舉人。五年不成者出學。京師廣延各學教習,圖器尤盛,每歲總裁,禮部會同大教習試之,其法與省學同,不限名次,及半中選,謂之進士。三年不成者出學。其進士得還為藝學州、縣總教習,其舉人得為分教習,並聽人聘用。其諸生得還教其鄉學塾及充作各廠。其文科童試,即以經古場為正場,自佔經解一,專門之學一。二場試「四書」文一,中外策一,詩一,亦及格即取,不限名額。每場考試,人數不得過三百。增設學政,每道一人,可從容盡力矣。其鄉會試,頭場「四書」義一,「五經」解一,詩一,縱其才力,不限格法,聽其引用,但在講明義理,宗尚孔子,二場掌故、策五道,三場問外國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額。殿試策問,不論楷法,但取直言極諫,條對剴切者入翰林。其文科、藝科願互應者聽。其有創著一書,發明新義,確實有用者,皆入翰林,進士授以檢討,舉人授以庶吉士,諸生授以待詔。如是則天下之士才智大開,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其餘州、縣、鄉、鎮,皆設書藏,以廣見聞。若能厚籌經費,廣加勸募,今鄉落咸設學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學,通訓詁名物,習繪圖算法,識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則人才皆可勝用矣。 《周官》「誦方」、「訓方」,皆考四方之慝,《詩》之《國風》、《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開報館,名曰新聞,政俗備存,文學兼存,小之可觀物價,瑣之可見土風。清議時存,等於鄉校,見聞日辟,可通時務。外國農業、商學、天文、地質、教會、政律、格致、武備,各有專門,以為新報,尤足以開拓心思,發越聰明,與鐵路開通,實相表裏,宜縱民開設,並加獎勵,庶裨政教。 然近日風俗人心之壞,更宜講求挽救之方。蓋風俗弊壞,由於無教。士人不勵廉恥,而欺詐巧滑之風成;大臣托於畏謹,而苟且廢弛之弊作。而「六經」為有用之書,孔子為經世之學,鮮有負荷宣揚,於是外夷邪教,得起而煽惑吾民。直省之間,拜堂棋布,而吾每縣僅有孔子一廟,豈不可痛哉!今宜亟立道學一科,其有講學大儒,發明孔子之道者,不論資格,並加征禮,量授國子之官,或備學政之選。其舉人願入道學科者,得為州、縣教官。其諸生願入道學科者,為講學生,皆分到鄉落,講明孔子之道,厚籌經費,且令各善堂助之。並令鄉落淫祠,悉改為孔子廟,其各善堂、會館俱令獨祀孔子,庶以化導愚民,扶聖教而塞異端。其道學科有高才碩學,欲傳孔子之道於外國者,明詔獎勵,賞給國子監、翰林院官銜,助以經費,令所在使臣領事保護,予以憑照,令資遊歷。若在外國建有學堂,聚徒千人,確有明效,給以世爵。余皆投牒學政,以通語言、文字、測繪、算法為及格,悉給前例。若南洋一帶,吾民數百萬,久隔聖化,徒為異教誘惑,將淪左衽,皆宜每島派設教官,立孔子廟,多領講學生分為教化。將來聖教施於蠻貊,用夏蠻夷,在此一舉。且借傳教為遊歷,可詷夷情,可揚國聲,莫不尊親,尤為大義矣。 夫教養之事,皆由國政。而今官制太冗,俸祿太薄,外之則使才未養,內之則民情不達,若不變通,則無以為養之本也。天下之治,必由鄉始。而今知縣選之既不擇人望,任之兼責以六曹,下則巡檢、典史一二人,皆出雜流,豈任民牧?上則藩臬、道府,徒增冗員,何關吏治?若京官則自樞垣、臺諫以外,皆為閒散。各部則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廩祿。堂官則每署數四,而兼差反多。文書則每日數尺,而例案繁瑣。至於鬻及監司,而吏治壞濫極矣!今請首停捐納,乃改官制,因漢世太守領令長之制,唐代節度兼觀察之條,每道設一巡撫,上通章奏,下領知縣,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望者充之。其知縣升為四品,以給御、編檢、郎員及道府之愛民者授之。其巡撫之下,增置參議、參軍、支判,凡道府同通改授此官。其知縣之下,分設公曹、決曹、賊曹、金曹,以州、縣進士分補其缺。其餘諸吏皆聽諸生考充,漸拔曹長,行取郎官。其上總督,皆由巡撫兼管,各因都會,以為重鎮。使吏胥之積弊,化為士人;三老之鄉官,各由民舉。整頓疏通,乃可為治。其京官則太常、光祿、鴻臚可統於禮部,大理可並於刑部,太僕可並於兵部,通政可並於察院,其餘額外冗官,皆可裁汰,各營一職,不得兼官。章京領天下之事,宜分以諸曹,翰林為近侍之臣,宜輪班顧問。部吏皆聽舉貢學習,以升郎曹;通政准百僚奏事,以開言路。駢枝既去,宦途甚清,以彼冗糜,增此廩祿。令其達官有以為輿馬僕從之費,而後可望以任事;其小吏有以為仰事俯畜之用,而後可責以守廉。若用魏、隋之制,予以世祿之田,既體群臣,庶多廉吏。 內弊既除,則外交宜講。春秋子羽能知四國之為,漢武下詔,求通絕域之使,蘇武不辱,富弼能爭。列國交爭,其任重矣。而今使才未養,不諳外務,重辱國體,為夷姍笑。今宜立使才館,選舉貢生監之明敏辦才者,入館學習,其翰林部曹願入者聽。各國語言、文字、政教、律法、風俗、約章,皆令學習。學成或為遊歷,或充隨員,出為領事,擢為公使,庶幾通曉外務,可以折衝。考俄、日之強也,由遣宗室大臣遊歷各國,又遣英俊子弟詣彼讀書。俄主彼得,乃至易作工人,躬習其業,歸而變政,故能驟強。 我親藩世爵大臣,與國休戚,啟沃聖聰者,而不出都城,寡能學問,非特不通外國之故,抑且未知直省之為。一旦執政,豈能有補?大臣固守舊法,習為因循。雖利國便民,力阻罷議,一誤再誤,國日以替。宜選令遊歷三年,講求諸學,歸能著書,始授政事。其餘分遣品官,激厲士庶,出洋學習,或資遊歷,並給憑照,能著新書,皆為優獎,歸授教習,庶開新學。則上之可以贊聖聰,下之可以開風氣矣。 夫中國大病,首在壅塞,氣鬱生疾,咽塞致死。欲進補劑,宜除噎疾,使血通脈暢,體氣自強。今天下事皆文具而無實,吏皆奸詐而營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號而莫達。同此興作,並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國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夫以一省千里之地,而惟督撫一二人僅通章奏,以百僚士庶之衆,而惟樞軸三五人日見天顏。然且堂廉迥隔,大臣畏謹而不敢盡言;州、縣專城,小民冤抑而末由呼籲。故君與臣隔絕,官與民隔絕,大臣小臣又相隔絕,如浮屠百級,級級難通,廣廈千間,重重並隔。夫天下萬物之繁,封圻千里之廣,使督撫樞軸皆是大賢,然是數人者,心思耳目所及,必有未周,才力精神之運,必有不逮,以之運驟四海,「驟」:疑當作「籌」。措置百務,已狹隘不廣矣。況知人之哲,自古為難,唐帝失之於共兜,諸葛失之於馬謖,任用偶誤,一切乖方,而欲倚之以扶危定傾,經營八表,豈不難乎?天下人民四萬萬,庶士億萬,情偽百端,才智甚廣,皇上僅寄耳目於數人,而數人者又畏懦保祿,不敢竭盡,甚且煬灶蔽賢,壅塞聖聰,皇上雖欲通中外之故,達小民之阨,其道無由。名雖尊矣,實則獨立於上,遂致有割地棄民之舉。皇上亦何樂此獨尊為哉? 夫先王之治天下,與民共之,《洪範》之大疑大事,謀及庶人為大同。《孟子》稱進賢、殺人,待於國人之皆可。 盤庚則命衆至庭,文王則與國人交。《尚書》之四目四聰,皆由辟門。《周禮》之詢謀詢遷,皆合大衆。嘗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廣益,通達民情,實以通優共患,結合民志。昔漢有征辟有道之制,宋有給事封駁之條。伏乞特詔頒行海內,令士民公舉博古今,通中外,明政體,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縣約十萬戶,而舉一人,不論已仕未仕,皆得充選,因用漢制,名曰議郎。皇上開武英殿,廣縣圖書,俾輪班入直,以備顧問。並准其隨時請對,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餉事宜,皆令會議於太和門,三佔從二,下施部行。所有人員,歲一更換,若民心推服,留者領班。著為定制,宣示天下。上廣皇上之聖聰,可坐一室而知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憂樂而忘公私。皇上舉此經義,行此曠典,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紓財,共贊富強,君民同體,情誼交孚,中國一家,休戚與共。以之籌餉,何餉不籌?以之練兵,何兵不練?合四萬萬人之心以為心,天下莫強焉!然後用府兵之法,而民皆知兵,講鐵艦之精,而海可以戰。於以恢復琉球,掃蕩日本,大雪國恥,耀我威稜。 昔德國相臣畢士麻克,嘗以中國之大冠絕四洲,他日恐為歐羅之患,思與諸國分之。後以中國因循不足畏,議遂中止。今若百度更新,以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人,二十六萬種之物產,力圖自強,此真日本之所大患,畢士麻克之所深忌,而歐羅巴洲諸國所竊憂也。以之西撻俄、英,南收海島而有餘,何至含垢忍恥,割地請款於小夷哉?及今為之,猶可補牢。苟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事機,則諸夷環伺,間不容髮,遲之期月,事變必來。後欲悔而改作,大勢既壞,不可收拾,雖有聖者,無以善其後矣。 且夫天下大器也,難成而易毀;兆民大衆也,難靜而易動。故先王懍朽索之馭馬,慮天命之無常,戰戰業業,若履淵冰。楚莊王之立國也,無日不訓討軍實,慮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怠;諸葛亮之佐蜀也,工械究極,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率皆君臣上下,振刮摩厲,乃能自立。稍有因循,即懷愍蒙塵,徽、欽見虜矣。近日土耳其為回教大國,不變舊法,遂為六大國割地、廢君而柄其政。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法,乃敢滅我琉球,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為鑑。 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為之君。自強為天行之健,志剛為大君之德。《洪範》以弱為六極,大《易》以順為陰德。 《詩》曰:「天之方鞈,無為誇毗。」說者謂誇毗,體柔之人也。伏惟皇上英明天鞺,下武膺運,歷鑑覆轍,獨奮乾綱,勿搖於左右之言,勿惑於流俗之說,破除舊習,更新大政,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夫無事之時,雖勳舊之言不能入;有事之時,雖匹夫之言或可採。舉人等草茅疏逖,何敢妄陳大計,自取罪戾,但同處一家,深虞胥溺。譬猶父有重病,庶孽知醫,雖不得湯藥親嘗,亦欲將驗方鈔進。《公羊》之義,臣子一例。 用敢竭盡其愚,惟皇上採擇焉,不勝冒昧隕越之至。伏惟代奏皇上聖鑑,謹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