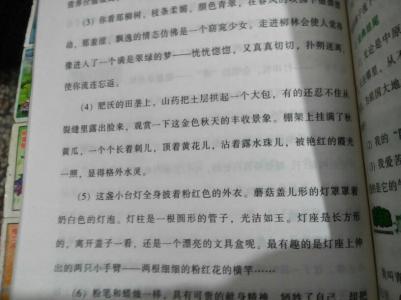巴金是我国著名的作家,他的写景散文,总是能够将景色的美惟妙惟肖的描写出来。下面是小编为你整理的关于巴金精美写景散文,希望对你有用!
关于巴金精美写景散文1:海上的日出
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时天还没有大亮,周围非常清静,船上只有机器的响声。
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地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陽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地望着那里。
果然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陽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这个太陽好像负着重荷似地一步一步、慢慢地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得非常可爱。一刹那间,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痛,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
有时太陽走进了云堆中,它的光线却从云里射下来,直射到水面上。这时候要分辨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倒也不容易,因为我就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
有时天边有黑云,而且云片很厚,太陽出来,人眼还看不见。然而太陽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透过黑云的重围,替黑云镶了一道发光的金边。后来太陽才慢慢地冲出重围,出现在天空,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这时候发亮的不仅是太陽、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明亮的了。
这不是很伟大的奇观么?
1927年1月
关于巴金精美写景散文2:繁星
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
三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也认得一些星星,好像它们就是我的朋友,它们常常在和我谈话一样。
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它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地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它们在对我霎眼,我仿佛听见它们在小声说话。这时我忘记了一切。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
有一夜,那个在哥伦波上船的英国人指给我看天上的巨人。他用手指着:那四颗明亮的星是头,下面的几颗是身子,这几颗是手,那几颗是腿和脚,还有三颗星算是腰带。经他这一番指点,我果然看清楚了那个天上的巨人。看,那个巨人还在跑呢!
1927年1月
关于巴金精美写景散文3:《春天里的秋天》
春天。枯黄的原野变绿了。新绿的叶子在枯枝上长出来。陽光温柔地对着每个人微笑,鸟儿在歌唱飞翔。花开放着,红的花,白的花,紫的花。星闪耀着,红的星,绿的星,白的星。蔚蓝的天,自由的风,梦一般美丽的爱情。
每个人都有春天。无论是你,或者是我,每个人在春天里都可以有欢笑,有爱情,有陶醉。
然而秋天在春天里哭泣了。
这一个春天,在迷人的南国的古城里,我送走了我的一段光阴。
秋天的雨落了,但是又给春天的风扫尽了。

在雨后的一个晴天里,我同两个朋友走过泥泞的道路。走过石板的桥,走过田畔的小径,去访问一个南国的女性,一个我不曾会过面的疯狂的女郎。
在—个并不很小的庄院的门前,我们站住了。一个说着我不懂的语言的小女孩给我们开了黑色的木栅门,这木栅门和我的小说里的完全不同。这里是本地有钱人的住家。
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我看见了我们的主人。宽大的架子床,宽大的凉席,薄薄的被。她坐起来,我看见了她的上半身。是一个正在开花的年纪的女郎。
我们三个坐在她对面一张长凳上。一个朋友说明了来意。她只是默默地笑,笑得和哭一样。我默默地看了她几眼。我就明白我那个朋友所告诉我的一切了。留在那里的半个多小时内,我们谈了不到十句以上的话,看见了她十多次秋天的笑。
别了她出来,我怀着一颗秋天的痛苦的心。我想起我的来意,我那想帮助她的来意,我差不多要哭了。
一个女郎,一个正在开花的年纪的女郎……我一生里第一次懂得疯狂的意义了。
我的许多年来的努力,我的用血和泪写成的书,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我给人唤起了渴望,对于光明的渴望;我在人的前面安放了一个事业,值得献身的事业。然而我的一切努力都给另一种势力摧残了。在唤醒了一个年轻的灵魂以后,只让他或她去受更难堪的蹂躏和折磨。
于是那个女郎疯狂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自由的婚姻、传统观念的束缚,家庭的专制,不知道摧残了多少正在开花的年青的灵魂,我的二十八年的岁月里,已经堆积了那么多、那么多的阴影了。在那秋天的笑,像哭—样的笑里,我看见了过去一个整代的青年的尸体。我仿佛听见—个痛苦的声音说:“这应该终结了。”
《春天里的秋天》不止是一个温和地哭泣的故事,它还是一个整代的青年的呼吁。我要拿起我的笔做武器,为他们冲锋,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Jeaccuser”(我控诉)。
一九三二年五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