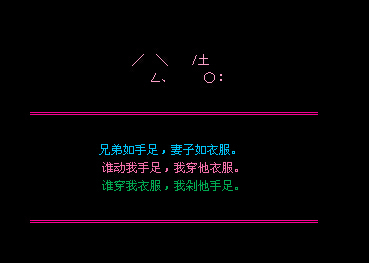“打虎亲兄弟”、“兄弟如手足”,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就流传下来的谚语和格言,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描写兄弟手足情的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描写兄弟手足情的文章:情深意重手足情
“打虎亲兄弟”、“兄弟如手足”,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就流传下来的谚语和格言。回顾几十年的生活经历,我总不会忘记哥哥对我的关怀、爱护、帮助。是他,在关键时刻指点并领我找到了一条生活之路,是他一次次匡正了我的行为,使我走好了我的人生之路。
哥哥大我三岁,八岁上学。爸爸同寅葛叔葛显庭给他起的名字叫康有泰,因为“康”和“泰”是平安吉祥的组合。哥哥因为闹脚病,休了一年学,所以只高我一年。我七岁上学,葛显庭叔替我起了康有山的名字,因为“泰山”的组合构成了坚强和力量。
小时候,哥哥很少带我玩,因为差三岁无论在兴趣上,还是爱好上,差距都挺大。哥哥只是在放八卦(风筝的一种)时带上我,好让我给他打下手、举八卦。记得我俩有一次放八卦,绳突然断了。八卦飘了飘,拐弯抹角掉到了一家人的房上。我俩吓坏了。因为听说断线的风筝掉在谁家的房上,那家一定要死人。哥哥马上拉着我,往家跑,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还特地拐了几个弯。跑到家,哥哥的脸吓得通红。过了几天,哥哥让我去打听一下,我找到那家邻居的小朋友一问,才知道那家的老头确实死了,不过是已经死一个多月了。有时,我也偏宁着要跟着他玩,他就想尽千方百计哄我回去。记得有一次哥哥跟他的小朋友刚走,我就追了上去,哥哥温和地劝我回去,并说:“我小弟可听话了”,我也不听,反说:“虚伪的夸奖”,把他们全说笑了。还是哥哥大,比我心眼多,就和我玩藏猫猫,让我先藏,等我藏好了,人家没找,走了。我在那藏了半天见没人找,出来一看人家走了,气得我哭着回了家。
上学之后,哥哥在上学放学时总是很关照我。有一次,邻居的一个小朋友比我大,勾引我说铁道北道口外的山丁子熟了,说红拉拉得可多了,领我去采。我跟他去了,结果哪有什么山丁子啊,他又说让人采光了,便领我去采蒲棒。边采边吃蒲棒绒。一来二去地一上午就要过去了。我突然想到上学的事,便回头要走。那个小朋友说,你回去不赶趟了,不然等放午学时混到人堆里再回去。我也就依了他。可是,偏偏不凑巧,还是让哥哥发现了,回了家哥哥把这事告诉了爸爸。爸爸把我叫到跟前一问,我如实的招了。这下子,受到了爸爸极其严厉的惩罚。爸爸问我口供,我认口服输,保证下次不再犯了。
虽然哥哥从小不领我玩,但看热闹却领过我。记得一九四七年有一次开斗争会,哥哥拽着我去看。那是一排土豪劣绅,十来个跪在那,农会的一个人抱来一抱镰刀把,放在地上。贫雇农们们排成一大长队,轮到了就过去对最痛恨的人打几下。等到轮到爸爸了,哥哥对我说,你看爸得打谁?还没等我回答,见爸爸过去了,却没拿镰刀把,而是解下了自己扎的皮腰带去抽了我姑老爷几下。我很不理解,哥哥告诉我说,听妈妈说,那会儿爸出劳工后,跑“毛子”,妈领咱俩躲到他家,他把咱妈撵了出来,所以咱爸恨他。
有一次,哥哥带我去看驴皮影,半道上哥哥突然想起来说,咱俩个小,看不着,你快回家去把板凳扛来,我扛来一个长条凳,我俩站在上边看。回来时,哥哥说:“来时你扛的,回去我扛着,这样就平杵了。”这事虽过去几十年了,我却仍然记忆犹新。
一九五○年我刚上学,就是那年冬天,张维区开公审大会,并且要枪毙大胡子头佘子良。学校组织学生去“参观”受“教育”。早晨刚到学校,老师就组织学生站队集合。不一会,哥哥急急忙忙找到我,告诉我不能去,怕吓着我,他又找到我的老师,告诉老师说,老师也认为我太小了,毛岁才七岁,就让我回家了。后来,听同学们讲,有的学生真吓坏了,半夜哭醒叫醒的有好几个。
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是我初小考高小那次。是数学么,题目是5月7日播下苞米种子,到9月3日收割,问玉米生长经过了多少天。我答的是(31-7)+30+31+31+3-1=118(天),可出来一对,他们都答119天,说我错了。我不服气,后来有个教常识课的老师也说我错了。我气得大哭,因为我一向自诩为优等生,怎么我会错了他们倒对了呢?于是下一科我就要不去考了。哥哥先是劝我,我还是耍熊不进考场。这时哥哥急眼了,拍拍搧了我两个大耳光。我立时就不敢再耍了。这时,哥哥又搂着我的脖子来哄我说:“凭我弟弟这样的优等生,指定能考上。”这样,我才进屋去往下考。后来,老师们也争论不休,可回家问我们邻居的大姐夏淑清,她也说我对。等晚上哥哥回家吃饭,他特别高兴地回来告诉我说:“学校研究的结果是你对了,他们错了。”我也特别惊喜,跟哥哥说:“得回你了,要不就完了”。这件事表面上看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它确实是关系了我的一生。如果不是哥哥,那就不知道我会岔到哪条路上去。
哥哥关心我的学习,也支持我的正当爱好。我忘不了哥哥给我借话本看的那些往事。我记得像《夏伯阳》、《卓亚和舒拉的故事》还有《绿锁链》这些画本,都是哥哥给我借回来的,有一次,哥哥的小朋友给他送来一大摞话本,都是哥哥不太爱看的。那个同学看他不喜欢,就要拿回去。哥哥就说:“我弟弟爱看,等他看完我给你送回去”。我看完之后,偏偏又被别人借去好几本。等哥哥要给人家送回去时,少好几本。哥哥把我好一顿训斥。告诉我说:“别人的东西不能随便往外借,要借必须经过主人的同意”。这使我受了一次教育,让我懂得了一条做人的道理。
小时候我爱干活,但都是哥哥带着我们干。无论是打柴、捡柴,还是侍弄园田,还是刨煤,开头都是哥哥带着我和老三。比如说刨煤,是哥哥教我们怎么打底,怎么能刨大块。记得有一次老三还小,上车时上了一半以后不敢上了。火车的车梯十多阶,五十吨的火车厢挺高。老三害怕吓得哇哇哭,大哥赶忙让我从另一端下去推他,他从上边拉他。打柴时我磨不好刀,哥哥教我怎么磨,“磨刀不误砍柴工”这句话就是从哥哥嘴里学来的。有一次打柴,我一不小心把手割破了。一流血我害怕了。哥哥给我按着伤口,去找了一个蜂窝上的马粪包,给我上在伤口上,很快止住了血。那时候,家里买粮米都是我跟哥哥的事。哥哥负责管钱,可往回背时,他总是背多的,让我背少的。有一年春节前,我俩去买大米和面,哥哥非常高兴,边走边唱:“若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骄傲的告诉他,这是我的家乡。”可我却一不小心把大米袋子摔坏了,撒了不少大米,我也没敢吱声,他看见了忙找把草把摔破的袋子塞上,回家也没有告诉爸爸妈妈,只是又找了条袋子和我把米串出来,使我如释重负。
就是那年过春节,做冰灯,我做的那个上下都没插木头棍,所以倒出来后上下没眼儿,哥哥告诉我,没有上下眼点不着蜡烛。后来他又帮我做了一个。午夜放鞭炮我不敢,他就找来根葵花杆,把香插在最前头,离很远去点捻,我感到这法儿挺好。在侍弄园田地时,也是哥哥教我怎么铲,怎么备垅。有一次在铲地时,我一不小心把黄瓜苗铲伤了。我就去地边抠了块湿土给它糊上了。哥哥告诉我黄瓜秧伤了,就是长上了,结出黄瓜也是苦的,不能吃。他就把那苗拔出来扔了,说哪天补上棵别的苗。就是打柴时打腰捆腰每项都是哥哥教我的。这些本领,在我一生生活中都发挥了作用。哥哥使我掌握了许多生活本领。
哥哥是一九五六年上初中,我是一九五七年上初中,差一年。他在四方台中学是第十八班,我则是二十三班。我上初中哥哥上初二。我刚一到四方台很发懵,找不到东南西北,哥哥就带我熟悉学校环境,星期天还带我到镇子的街里走一圈,告诉我哪是哪。第二个星期天,他和他们班的高求柏领我上了四方山,还上了和尚庙,告诉我铁道旁边的那座坟叫“公主坟”,是金兀术妹妹的坟。那时的学校伙食也不太好,吃饭的办法是交了伙食费的人十个人分一桌,大长条桌,吃饭时值日生负责领饭菜,菜是一大盆,饭是用大木头槽子装,每个人两个碗,一个装饭,一个装菜。开饭时由桌长或轮班分饭分菜。自从入学我俩交饭费是哥哥交,所以我俩总是分到一个桌。哥哥怕我吃不饱,他分的饭菜常常给我一部分。四方台离我家三十多里,星期六或星期天回家都是走,有时我跟不上哥哥,他就坐在铁道上等我一会,等我赶上来再走。记得我们俩买肥皂是买一块,一切两半,连洗脸带洗衣服。后来我那快丢了,哥哥就把他那半块又切一半给我。第二年,我们就分回张维中学。他们成了一班,我们成了二班,当上了创校生。
哥哥和我能考上高中,都是很不简单的。因为那时录取率很低。那时全县只有一中和二中两个高中。哥哥五九年考进二中,我六零年考进一中。我上一中前爸爸给我买了一张狗皮,怕我住宿睡床凉。其实那张狗皮原本是要给哥哥的,可哥哥说他不凉,就拿给了我。当时哥哥挺神秘地告诉我说,送我一件礼物。我不知是什么,当哥哥把那张大狗皮拿给我时,我摸着那又长又厚的毛绒绒的狗毛,心里温暖极了。可哥哥根本没告诉我爸爸是给他买的,只是高高兴兴地递给了我。上学那天,哥哥领我上了火车,事先他帮我把行李捆得紧紧地,怕下车背散了。下车后,他先把我送到学校帮我报完到,又帮我买了香皂、肥皂,还给我用纸壳缝了个皂盒,怕一湿就坏,他特意准备了一块铁片,嵌在里面。第二天是星期天么,学校的意思是让学生们休息或做一些别的准备,可他吃完早饭就来了,手里拿着两张电影票,说领我去铁路俱乐部看电影。他们二中离铁路俱乐部近多了,而一中在大南门外,铁路俱乐部在大东门外,远多了。那次的电影是《马路天使》,是为了纪念周璇去世十周年才演的。所以我的印象非常深。二中离我们虽远,但我星期天却非常愿到哥哥学校去,因为看见他心里有底,有个依靠。有时他领我去车站走一圈,有时领我去大舅家转转,有时到姨姥爷饭店走走。
哥哥一九六二年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因为他的无线电挺有水平的,被县广播站录用,分配到东富乡广播室。一九六三年我则考入了大学,发通知那天哥哥不在家,后来他知道了特意请假回来祝贺我。我清楚地记得还是他帮我打的行李,并把我送上车,把行李放在车架上。从此,我跟哥哥分开了,各自走上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一九六四年的寒假放得比较晚。仿佛已进了腊月底才放的。春节哥哥回来后,见到他我很高兴。闲唠中无意提到学校生活,说谁的篮球打得好,谁得小提琴拉得好,这一切被哥哥记在心里。过了春节我要开学了,一天哥哥兴致冲冲地回来了,他手里拎着一把崭新的小提琴,一进屋就递给了我。我接过一看,是个紫色琴盒,哥哥让我打开,我打开一看,白毛紫杆的琴弓在弓架上夹着,小提琴颜色和琴盒近似,松香放在琴盒小头的松香室内。哥哥让我试试,我就按拉二胡的办法拉了一支曲。我问哥从哪借的,哥哥笑笑说,问这干啥?就是你上大学送你的礼物吧。后来我才知道,哥哥买这把琴花了他一个月的工资。这把琴一跟我就好几十年,每当我看见琴、拿起琴、拉起琴,总是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哥哥嘱咐我好好学学,并且责备我说,那时拉二胡跟付正大好好学学是不是就好了。他说付正大老师也责备过他,说老二爱拉琴为啥不早告诉他呢?后来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起初,我常把我们学校的文件材料寄给他。六五年上半年讨论《海瑞罢官》、《清宫秘史》、《李慧娘》我都陆续寄给了哥哥,虽然哥哥也根本不清楚那场运动会怎么开始,到什么程度,怎么发展,怎么结局,但他没少嘱咐我一定要小心,说千万别像四方台中学的陈晓斗那样,年纪轻轻就成了右派。告诉我凡事必须小心谨慎,不可粗心大意。
我的恋爱也是一九六五年开始的。那年“五一”放假回家,我的中学同学张桂芳开始和我恋爱,她有许许多多的过人之处,长的少有的漂亮。但也有很大障碍,她出身是地富子弟,没有工作,在家务农。在那个讲成分的年代,这事非同小可。全家人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们全反对。可我态度却十分坚决。哥哥知道后,回来专门和我谈心,当他了解了我的思想后,表示了理解。最后我去张桂芳家去答复她时,哥哥送我到镇外的小路上,嘱咐我要冷静,不要冲动。后来他又做父母的工作,父母才最后批准了这门亲事。
我毕业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毕业分配是“四个面向”,那是一九六八年末,我出于离家近,要求分配到离张维屯二十多公里的绥棱县,那是一个很小的县城,在那里度过了十一个年头,先后从事教师进修校、五七大学、教革办、民政局、普通中学教育等工作。在绥棱那些年,哥哥常去看我,特别是绥棱失大火烧了我们家那次,哥哥带着三弟、四弟去看我,三弟见我就失声痛哭,老四也特沉重,大哥泪在眼边,还强忍着安慰我。他们呆了好一阵子,后来给我留下钱才走,我连饭都没给他们张罗。以后哥哥又一次去看我,我跟他说学生不太好教,我实在干够了,哥哥看我痛苦的样子,二话没说,回绥化就千方百计地找人,托关系往回调我。那时由于哥哥水平高、肯干,已经调到县广播站当上了技术负责人,所以在院里熟人也多。可那时调一个人太难了,找人事局、找接受单位,找了好多人,费挺大劲才把我从绥棱调回绥化。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七日,我正式到绥化市乡企局报到上班。由于乡企局没有宿舍,哥哥又和他们领导说,把我安排在他们站的员工宿舍,二十天后,即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哥哥托人帮我找了房,租下了房子后,我就把家搬到了绥化。
我不会忘记那次搬家的情景。那是十一月末了,天气已经特别冷了。哥哥领着四台汽车从绥化到绥棱,走公路有一百多里,装完车后,哥哥怕东西掉了硬是没进驾驶室,坐在了车外边的家具上。从绥棱到绥化,一路上冷风嗖嗖把哥哥冻得直哆嗦,脸煞白。汽车的副驾位上,坐着我的爱人、孩子和一个来帮搬家的亲戚。那亲戚实在不过意,我妻子也十分不安,几次停车让哥哥进去暖一暖,哥哥说什么也不肯。一直和三弟、四弟和我挺到绥化。下车后,哥哥和我们的脚全都不好使了。那是实实在在的冬天啊,一百多里地的路程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义啊?那是多么情深义重的手足之情啊?
哥哥不光对我好,对别的弟弟妹妹也好。老四当兵在吉林时,爸爸已经去世了。哥哥嫂子帮他找了对象,复员后,帮他结了婚。老六、老七当兵和退伍都是他一手操办。老六和老七的工作都是他想办法找人托人安排的。特别是老六,他第一个妻子车祸死亡后,哥哥带着我和老四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和她的单位交涉,按有关政策文件争取妥善合理地予以处理,取得了最好的效果。他的第二任妻子和他闹矛盾要离婚,哥哥带我和老四去女方家里做女方父母工作,受到了数落和难堪。老四夫妻闹矛盾,大哥大嫂深更半夜地做工作,反复劝解,哥哥可谓受尽了辛苦和操劳。
在孝敬父母上,哥哥是我们最可尊敬的榜样。在父亲生病住院时,哥哥家离医院那么远,可他一天跑好几次,送东西、找医生、还要照料父亲,一个来回十多里地,可他毫无怨言。父亲去世,是他一手操办,后来父亲的坟两次迁移也是他一手操办。父亲去世后,他主持了为母亲盖房子。母亲的房子从土改分到手,二十多年,是哥哥领我们和帮工、亲戚把房子翻新。以后又是他把母亲接到绥化,安排了房子,把母亲安顿好。母亲有病后,就是哥哥嫂子张罗给母亲看病治病。医疗费用、母亲生活费、保姆费用,哥哥总是踊跃承担。那么多兄妹,他总是拿大头。母亲去世后,他没在母亲的遗产中拿一分钱。他的行为和表现教育了我们,弟弟妹妹都敬佩他。
一晃,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哥哥将近七十岁了,我也向七十靠拢了。回忆起哥哥从童年开始对我的这份深情,至今犹让我时时激动。旧俗语中有“仇家转儿女,恩家转弟兄”一说,我对前一句坚决反对,那都是旧书中所喧嚷那套。特别是什么《呼延庆上坟》、什么《薛刚反唐》这些破书,什么薛刚是丑鬼杨凡一转,转世来报复樊梨花的这些胡言乱语,我绝不赞成这套。倒是恩家转兄弟这句话我特别欢迎。我这辈子都为有这样一个好哥哥感到欣慰和满足。
还是那句话:要有下辈子我还要这个哥哥。

描写兄弟手足情的文章:兄弟情
昨晚,收到一条短信,是高中同学发来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