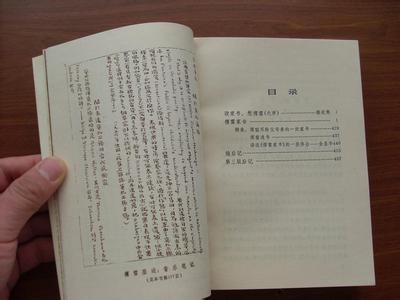《父与子》是屠格涅夫晚期的作品,主要塑造了巴扎罗夫这一复杂的形象。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父与子读书笔记,希望大家喜欢!
父与子读书笔记篇一
最近疯狂迷恋德国著名漫画家埃奥卜劳恩的漫画集《父与子》。这是一本超级幽默亲切的连环漫画书。书中的主要人物是一对可爱而有趣的父子。
一个又一个。幽默搞笑的故事看得我每次都捂着肚子笑得前俯后仰,但看过之后,也深深体会他们父子间暖暖的爱。
书中的父亲童心未泯,不但行为举止让人捧腹大笑,而且外貌形象也很滑稽可爱。你看光秃秃的脑袋贼亮贼亮,一双小而圆的眼睛,留着一大把黑胡子,挺着一个特别肥大的肚子。特搞笑吧!
《引人入胜的书》这个故事尤其经典。晚饭时间到了,爸爸妈妈都已在餐桌前坐下来了,可儿子上哪去了呢?“你去看看,你家宝贝儿子在做什么,怎么还不来吃饭?”于是,妈妈让爸爸——去房间找儿子!这时,儿子正趴在自己房间的地上看有趣的幽默漫画书呢!见爸爸来叫吃饭,儿子一骨碌爬起来去客厅吃饭。“咦?你爸爸呢?他不是去喊你吃饭了吗?”妈妈看看餐桌上还是少一个人,肚子已经“咕噜咕噜”直叫,很生气!“我去”。儿子起身又出去了。原来爸爸正趴在儿子房间的地上看儿子刚才看得幽默漫画书呢。这时候的爸爸就是一个不折不扣老顽童,早已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一个人沉浸在书里,双手托着腮帮子看上去就是一个长不大的老小孩。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好玩有趣的漫画故事,每个故事都是那么精彩和幽默。父亲和儿子之间像一对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他们热爱生活,充满温情,他们善良正直又真诚。看了这本书,好希望我的爸爸也能和书里的父亲一样可爱好玩,少一些威严和火气,多一些幽默和温情。
父与子读书笔记篇二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晚期的作品,主要塑造了巴扎罗夫这一复杂的形象。巴扎罗夫同周围的人——同学和信徒阿尔卡季、父辈、爱人以及平民的互动共同构成了小说的情节。故事主要发生在三处农庄:阿尔卡季及其父辈在马利因诺的农庄、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奥金佐娃在尼科利斯科耶的农庄、以及巴扎罗夫自己的位于一个小村的农庄。
巴扎罗夫出身平民,是莫斯科大学的毕业生,从事科学工作,崇尚“虚无主义”。贵族知识分子帕维尔之侄阿尔卡季是他的同学和信徒。故事从两人毕业回到马利因诺开始写起。巴扎罗夫同帕维尔在观念和信仰上的诸多差异使得二人起了口角冲突。阿尔卡季同巴扎罗夫替父辈赴约进城,通过商人之子西斯尼科夫认识了伪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库克什娜,他们又通过后者结识了孀居的贵族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奥金佐娃。两人到奥金佐娃家做客,先后爱上了她,而奥金佐娃有意于巴扎罗夫。然而“浪漫主义”的情感同“虚无主义”的相悖;巴、奥两人在人生观的距离令这场爱情在巴扎罗夫痛苦而激烈的表白后宣告无效——奥金佐娃又退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道。巴扎罗夫当即决定离开。他带阿尔卡季回到了故乡的小农庄和父母团聚,因为忍受不了故乡的空虚生活,他和阿尔卡季又回到了马利因诺。帕维尔更加厌恶巴扎罗夫,终于因为后者和酷似他年轻时的爱人P公爵夫人的费尼奇卡的亲昵举动引起了一场决斗。巴扎罗夫虽胜利了,却由此离开了马利因诺。路过尼科利斯科耶,巴扎罗夫得知阿尔卡季向奥金佐娃之妹卡佳求婚,他与阿尔卡季分道扬镳;同时他自绝了和奥金佐娃的爱情。巴扎罗夫回到故乡,日复一日地感到孤独和无聊,并在一次手术意外中感染伤口,很快地死去,这剩下年迈的父母无尽的悲痛。
在小说中,巴扎罗夫是军医之子,和阿尔卡季一同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他从事的是有关科学的工作,包括医学、生理学、物理学和化学。他知道许多关于化学的名著、他捉来青蛙和甲虫做解剖、他知道病理学,会给人看病。一方面,他是博学的,另一方面,巴扎罗夫自称自己是个虚无主义者。“虚无”是他的主要思想。所谓“虚无主义”,在巴扎罗夫身上主要表现为在对价值的虚无态度。他否定一切,包括权威、艺术、原则;当然包括他常挂在嘴边的,被他评价为“滑稽荒唐”的“浪漫主义”。
“虚无主义者是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受人尊敬的”[1]他的门徒阿尔卡季如是说。虚无主义的否定一切,有一种摧枯拉朽、排山倒海的气势,充满了力量,甚至有时显得凶猛。“我为什么要依靠时代?还不如让时代来依靠我。”[2]也正因为如此,巴扎罗夫显出“魔鬼一样的骄傲”(帕维尔语)。但虚无主义者只是“破坏”,并不“建设”,他们的否定甚至只是表现为谩骂。
而父辈的代表帕维尔·基尔撒诺夫对此十分不感冒。小说交代了他和尼古拉的过去,尤其是帕维尔的令人同情的经历。作为老派贵族和“浪漫主义”的代表,他对生活和艺术的品味极高,注重礼节,恪守既定的原则。这和以巴扎罗夫为代表的“虚无主义者”完全相反。帕维尔所恪守的,正是巴扎罗夫所反对和嘲笑的。二人在见面之初即充满了敌意。巴扎罗夫第一次到马利因诺,二人有两次正面的冲突;第二次见面,二人最后发展到要以决斗的武力方式来一决高下。帕维尔不满意巴扎罗夫在行为上粗鲁无礼,而巴扎罗夫嘲笑他的繁文缛节;帕维尔说巴扎罗夫“不相信原则,却相信青蛙”[3],而巴扎罗夫也曾下过“一个好的化学家比二十个普通的诗人还有用”[4]的断语。由于两代人价值观的不同,造成了他们诸多隔阂。这正是那个时代父与子的难题。“我们的下一代……现在轮到我们了……”[5]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无不感慨地说。崇尚自由主义的贵族的“多余人”的时代已经悄然远去,“以前是黑格尔主义者,现在是虚无主义者”[6]
正如小说的题目《父与子》所表达的那样,作者触及了一个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的父与子的难题。在本部小说的语境中,作者更是着力描写了两代人不同的价值观的不同所带来的对于政治时局和俄国社会走向的不同观点和态度。这其中当然包括了对农奴制的态度。虚无主义者大喊:“我们要破坏,因为我们是一种力量”[7]包括破坏他们父辈坚持的自由主义和进步。虽则父辈们所坚持的未必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虚无主义者的破坏甚至不承认“历史的逻辑”。
巴扎罗夫和帕维尔的矛盾最终因为费尼奇卡事件演化为一场带有象征性的决斗,时间在巴扎罗夫离开家第二次到达马利因诺。彼时,巴扎罗夫的恋爱受挫,回到家中呆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因为忍受不了无聊和空虚又回到马利因诺,狂热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帕维尔对巴扎罗夫的厌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两人的决斗以巴扎罗夫胜利、帕维尔的受伤告终。这似乎预示着一个旧的时代已经过去,帕维尔在经历过生死关头后也解开了心结,于是“他也确乎是个死人了。”
巴扎罗夫虽是“胜利者”,但他无法在马利因诺继续呆下去,他选择了离开。这似乎是一个隐喻,毕竟在小说中能让他发挥才智的唯一一个地方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父与子读书笔记篇三
屠格涅夫的小说喜欢将人物放在爱情的情境中来展现其性格,巴扎罗夫也“照例”陷入了爱情的困境。《父与子》毕竟是一部小说,而不是历史书。如果说在马利因诺,巴扎罗夫出场给人最初印象后,和帕维尔的论战更多地表现了他激进的思想和有力的一面,在尼科利斯科耶,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庄园,这个虚无主义者更多地展现了他的情感世界。

奥金佐娃是一个寡妇和女地主。她美丽动人,在年轻时即感受到了世事的沧桑变化,先是家道中落,后是嫁给一个她并不爱的人。在遇见巴扎罗夫时,她已继承了丈夫的遗产孀居。她是一位思想独立的女性,却过惯了“在轨道上爬行”的有规律的贵族生活,也受着情感空虚的苦闷。
而巴扎罗夫,这个自称的虚无主义者,在尼科利斯科耶做客时,和奥金佐娃每日的交往中,不自觉地爱上了他。这是“生活对某些偏执的概念的胜利”。 “爱情的巨大威力、青春的胜利同样也反映在巴扎罗夫身上。”
在和奥金佐娃的交往中,我们看到了巴扎罗夫追寻幸福的道路。虚无主义者一向轻视的“浪漫主义”以一种更加迅疾的方式降临到他的身上。这和他的教义是相违背的,于是,奥金佐娃在他心中唤起的感情,使他痛苦,使他愤怒,他照常奚落那些带有浪漫色彩的情感,可是“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生气地承认他自己也有了浪漫的情感了”[3]。除了巴扎罗夫自身思想上陷入的困局,社会地位上的差距、人生观的差异也横亘在两人之中。奥金佐娃认为巴扎罗夫应当一个更好的“前途”,而崇尚虚无主义的巴扎罗夫则拒绝考虑在“未来”发生的事件。
但即使是在重重的矛盾中,他自始自终对结果有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巴扎罗夫仍然做了勇敢的表白。“那么让我告诉你吧,我像一个傻瓜,像一个疯子那样爱着您……您到底逼我讲出来了。”对于这段复杂而又单纯的感情,告白意味着失恋,注定要以一方离开的方式来祭奠。巴扎罗夫久被压抑的情感以一种愤怒、强烈的方式发泄出来,使奥金佐娃既感到怜悯,又感到害怕,最终,她退回到原先的生活,拒绝了巴扎罗夫,安静地归好于一切。
巴扎罗夫觉察到了爱情,正当他正陷入其中时,那通往幸福道路的大门已经被关上,剩下的只有激情褪去之后的枯燥和遗憾。
巴扎罗夫同帕维尔决斗后,他第二次来到尼科利斯科耶,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已然退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扮演起她擅长的角色了。巴扎罗夫称自己恢复了理性,又摆回那副虚无主义者的样子与安娜对话,“爱情……只是一种故意装出来的感情罢了。”
同样是在尼科利斯科耶,阿尔卡季确定了和卡佳的关系。巴扎罗夫曾经的学生和他分道扬镳,于是,他选择离去,抑或如他自己所言:“飞鱼能够在空中支持一个时候,不过它们不久就得跳回水里去;……我回到我自己原来的环境中去吧。”
巴扎罗夫回到了他曾经感到无聊的家。那是一个落后的小村庄。他离开马利因诺时,给帕维尔留下了伤口;离开尼科利斯科耶时,将或许不可能的得到的幸福自绝了后路,让意欲回到过去的奥金佐娃“安了心”;告别了他曾经的伙伴阿尔卡季,给他下了“如是而已”的断语,却也留下了祝福。于是他回来了。故乡依然破败不堪,父母更加苍老,他还是在其中感到无聊和空虚。或许这故乡的破败正是他已然否认和决心要改变的。但这时,巴扎罗夫感到无路可走了。他那可以破坏一切的虚无主义无法付诸于行动;他以最悲剧的方式将自己的幸福宣布死亡。
起初,他还投入工作,却越来越感到孤独和烦躁。他之前的行动表明了他说奉行的虚无主义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没有人理解他,信徒离他而去,幸福也无疾而终,他摒弃了生活中所有可能的道路。和阿尔卡季决裂时,他提到他们这一类人将来的道路是严峻的,也可能是充满斗争的;然而,他还没有投入到那可能的生活中,他就因为意外急速地死去了。这样的结局,不知是否是作者有意为之。
“既然他没有必要生,那么让我们看看他如何死。小说的全部趣旨,就在于巴扎罗夫之死。”[1]作者对早早宣布了巴扎罗夫的死亡,却投入了全部的同情,显示出一个大作家的人道主义关怀。“虚无主义”本身蔑视的那些人之常情又显示了它的力量。巴扎罗夫和父亲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是本小说中另一种“父与子”的样式。两位老人的悲痛是“真正的悲剧”,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最后的告别令我们更加同情巴扎罗夫。
巴扎罗夫毕竟是有力量的。他的临终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他所坚持的和惦念的。“为什么我要死呢?因为我是一个巨人!现在这个巨人的使命就是:怎样才死得体面……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摇尾乞怜的。”[2]巴扎罗夫是一位真正的悲剧英雄,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地说道那句:“俄国需要我……明明是不需要我……可谁又是俄国需要的呢?”[3]真可令人潸然。
巴扎罗夫最终以死完成了他的存在价值,或许他在现实生活中无所作为,但他的真诚、他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他年轻而短暂的悲剧生命,令我们同情,也令我们对他肃然起敬。
历来人们对巴扎罗夫形象存在着争论。有观点认为在小说的前段,作者对巴扎罗夫的否定过于夸大;中段巴扎罗夫的爱情不符合逻辑;而在末尾将巴扎罗夫写成突然死去的结局太令人感到意外。
我认为这些不合理之处要从本部小说的创作背景来解释。
第一,本小说写作的时间跨越了俄国农奴制改革,那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作者自云:“我幻想一个阴郁、粗犷、巨大、从土壤中探出半截身躯、坚强、凶狭、忠诚的人物——他最后注定要灭亡,因为他终究站在未来的门口”[①]。这段话可以为巴扎罗夫的急速死亡做一个注解。或许,在那个变幻莫测的年代,作者本身也不知道他未来的走向,当巴扎罗夫否定了一切他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道路,又不知该往何处去时,死亡的结局反而保全了这个艺术形象的完整性。
第二,从作者的自身的创作特点看,屠格涅夫在写本部作品时,自身是一个“父辈”的代表,而他之前以塑造“多余人”的贵族知识分子为多。时局的激烈变化在他的作品中间反映出来,但在作品中留下了一些他作为“老辈人”的特质这些特质恰恰和“新人”巴扎罗夫的相去甚远,这可以解释为何小说前段对主人公的否定有时显得苛刻。
第三,爱情和女性是屠格涅夫擅长描写的。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也可以算是“屠格涅夫家的姑娘们”中的一员。爱情和女性往往体现了人性最本真的一面,令巴扎罗夫陷入其中,就如上文所说的只是体现了“生活对某些偏执的概念的胜利”。青春的力量也在巴扎罗夫身上得到了体现。我认为这恰恰是小说的精彩处之一。并且,当巴扎罗夫的幸福之路被阻断时,作者的同情便倒向了巴扎罗夫这一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观念在同巴扎罗夫“一同成长”。[②]正是这种“成长”令小说的趣旨改变了,小说后半段更多地充满了对人物的关爱和同情,我认为这才是《父与子》作为一部经典给人的启迪之处。正如小说结尾所说的那样,“它不仅对我们诉说着永久的安息……还跟我们讲说永久的和解同无穷的生命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