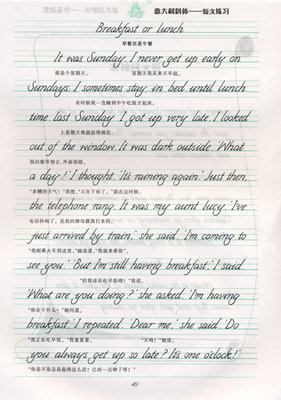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爱上乌鸦,那些浑身上下黑漆漆的鸟类。一次意外的旅行,让我彻底了解了乌鸦,并改变了对它们一贯的看法。我总以为乌鸦是不吉祥的鸟,但现在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乌鸦,是世界上最可爱的鸟”。
那次旅行,我走过云南好多地方,一路上遇见过好多只乌鸦,在天空自由地飞翔。而人们则对着它们微笑,撒下一粒粒谷子,供它们食用。墙壁上,屋檐下,到处都可以看到乌鸦们的画像。人们对它敬若神明。我有些迷惑,为什么这里乌鸦会享有这样高的礼遇?后来,在拉姆阿宗的述说里,我才得以释然。
拉姆阿宗,二十初头,是一名纳西族小伙子。他,浓眉大眼,皮肤黝黑,穿一身藏袍。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在一辆旅游大巴上。当时,他拿着话筒,说他是纳西族贵族后裔。我们深感荣幸,纷纷鼓掌。因为,他现在是我们的导游。为了调节气氛,拉姆阿宗用纳西族语言为我们唱了首歌,虽然我听不懂歌词,但我却被那荡气回肠的曲调所感染。那声音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一下子就穿透了我所有的防线,让我浸沉其中。直到一曲结束,我还没有回过神来。阿宗的嗓音充满磁性,有一种高原人独特的魅力。我想,如果让阿宗参加全国演出,他肯定会红遍大江南北。但是阿宗告诉我们,每一个纳西族人都能歌善舞,都有一种乌鸦的灵性与智慧。乌鸦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灵性与智慧呢?
阿宗说,乌鸦本是吉祥鸟,只是被人们曲解了。在古代巫书的记载中,乌鸦和黑猫一样,常常是死亡、恐惧和厄运的代名词,乌鸦的啼叫被成为是凶兆、不祥之兆,人们认为乌鸦的叫唤,会带走人的性命、抽走人的灵魂,因此乌鸦被人们所讨厌,认为是大不详之鸟。但实际上,乌鸦是一种很吉祥的鸟。乌鸦终生一夫一妻,而且乌鸦是特别孝顺的典型。当它们的父母年纪大了,老了,病了,厌倦世事了,无法觅食的时候,小乌鸦、年轻的乌鸦、儿孙辈的乌鸦,不但会给父母寻找食物,而且会把食物给弄得很可口,像人类吐哺以养育子女一样。这,就是乌鸦的“反哺慈亲”。听着阿宗娓娓的述说,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想起了上小学时的语文课文《乌鸦喝水》:瓶子里有半瓶水,乌鸦喝不到水。为了喝到水,乌鸦叼着一粒粒石子放入瓶中,水位上升,它最终喝到了水。可以说,乌鸦是最聪明的鸟了。莱菲伯弗尔的研究发现,世界上最聪明的鸟并非可以学舌的鹦鹉,而是普普通通的乌鸦。乌鸦很具创新性,它们甚至可以“制造工具”完成各类任务。在日本一所大学附近的十字路口,经常有乌鸦等待红灯的到来。红灯亮时,乌鸦飞到地面上,把胡桃放到停在路上的车轮胎下。等交通指示灯变成绿灯,车子把胡桃辗碎,乌鸦们赶紧再次飞到地面上美餐。多么可爱的乌鸦,它竟然想到了让车轮胎辗碎胡桃,然后再填充自己的胃。
在大巴车上,阿宗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七八年前的一天,一群上海游客开着白色奔驰轿车,到纳西古镇游玩。经过一条柏油路时,路上停歇着好多只乌鸦,他们什么也不顾,踩着油门飞驰而过。乌鸦的鲜血溅满了自己黑色的躯体,也溅满了整个宽敞的马路。马路上到处是乌鸦的尸体,它们的眼睛都睁的好大,好像不相信噩运会降临在它们身上一样。当时,阿宗也在场。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不由地流下了泪水。好多纳西族人都哭了,他们不答应外地游客这样对待他们的神灵。他们围攻了小轿车,条件是让游客为乌鸦举行葬礼。上海人大喊“荒唐!可笑!”,并企图以一沓厚厚的钞票解决问题。但村民们拒绝了,他们说“乌鸦是最具有灵性的鸟,任何人都不可以侵犯。”最终,他们坚持让上海人为乌鸦举行了葬礼。葬礼结束后,上海人才从纳西村民那儿知道了乌鸦的一些事情,且懊悔不已。从此后,每年的这个时候,那群上海人都会来到那些不知道姓名的乌鸦的坟前,说一些悄悄话。他们,也爱上了乌鸦。
阿宗还对我们说,他教育他的孩子要向乌鸦学习,学习它的聪明智慧,学习它的“反哺慈亲”。当他老了的一天,就让他的孩子向乌鸦一样喂养他这只老乌鸦。说这话的时候,阿宗的眼睛也是湿润的。
一路上,我沉默不语,除了看风景,就是想着乌鸦的一些事情。我想,人何尝不是一只只乌鸦,每天辛劳地觅食,有时还要遭受别人的误解和一些不必要的排解与打击。年轻时,拥有一幅强壮而又美丽的躯体,还可以自食其力。年老了,牙齿脱落了,羽毛掉光了,躯体变得丑陋不堪时,那些我们曾经养育过的小乌鸦会不会为我们四处觅食,反哺着喂养我们?
返程时,阿宗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就像一只乌鸦一样站在大巴车下,向我们挥手告别。

“再见!”,他磁性的声音有些哽咽。
车,渐行渐远。天空之上,到处是飞翔的乌鸦。
回忆,渐次模糊。阳光下,乌鸦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成为一个黑色的小点。
那次旅行过后,我就爱上了乌鸦,并教导自己的孩子 “向乌鸦学习!”。现在,我可爱的孩子也爱上了乌鸦。只要看见乌鸦,他再也不会忧郁着一张小脸,而只会开心地喊“乌鸦!我看到乌鸦了!”。
你,爱上乌鸦了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