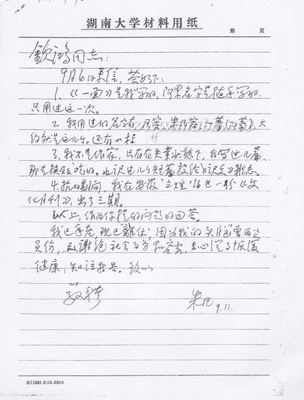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老街,下面是小编心中的老街。
《老街的记忆》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巷尾老爷爷卖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院,流浪猫睡熟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咪着眼。
周末回家拜望父母,饭后邀上老婆孩子,走了一趟家乡罗针田的老街。
三十年前的老街,是我儿时记忆中最繁华的处所、最向往的地带。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两旁,是清一色的旧木房。赶集的日子,供销社、铁匠铺、裁缝铺、小商店还有医院内,塞满了穿着深蓝、军绿、黑灰衣裳的庄稼汉与穿着花衣的村姑,板壁和地板不断发出卡啦卡啦地声响。各类小吃摊边、摆了小人书和连环画的地摊旁,常常被一大群赤脚的孩子围住,十数双眼睛直勾勾地盯在摊儿上,围着灰白围裙的老板一边手忙脚乱地劳作,一边拿孩子们的诨名取乐。街上偶尔有玩狮子的、打莲霄的、耍小猴小狗的,每当此时,大人们就停下手中的活儿,掏出旱烟袋边看边笑边点头赞叹,孩子们则又蹦又跳地试图去拽狮子的尾巴、摸小猴的脑袋……
老街呈东西向弧形,街道宽3米左右。1988年,鄂西电视台与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合作拍摄10集电视剧《天池山血泪》,曾在这里驻扎取景。如今,很多木房子都已损毁拆除或重建了,半数以上原住民都已迁走。我带家人从东头开始,去寻找与祖辈、与我有关的记忆。
最东头,是一段向上的青石阶梯,后来铺成了水泥路。无从考证,这段路是否为古巴盐大道的一部分。石阶两边,住着十余户人家,记忆最深的,是右边的一家谷米、面粉加工厂,小时候,常背一袋稻谷或玉米,随父母一起来加工;左边,是牲畜交易市场。如今,都只剩下断壁残垣了。
转过身来,是罗针田小学的发源地。上世纪40年代,我的伯父王开永在这里开创私塾,成为罗针田小学的创始人(恩施教育志有记载)。伯父是国民党员,解放时被抓去劳教,直到80年代初才回到故乡,并在小学旧址处租住四年后去世。对面,是一家刘姓照相馆,我的第一张单身照就是在这里拍下的,当时读小学四年级,我参加罗针田公社小学生听说读写四项能力竞赛获得冠军,学校安排在这里照了相,可惜不知这张宝贵的照片到哪儿去了!

继续西行,来到我记忆中最温馨的地方——龚老裁缝铺。儿时,祖父带我上街,必到这里来坐上好一会儿。龚裁缝孤独一人生活在一间小木屋里,屋前是高高的柜台,台上有四块可拆卸的板门,台侧的屋门上挂着长长的铁扣,屋内摆放着一张床、一块裁布的台板、一架老式缝纫机、一只火盆、一张又黑又笨的抽屉、一个矮小的木柜和两条板凳,地板上满是碳灰和油渍。每次来到这里,祖父坐在板凳上与主人攀谈,我便好奇地去摆弄缝纫机或台板上那只装着木碳的铁熨斗,两位老人总是叮嘱我别弄坏了东西。坐一会儿后,龚裁缝就到门口买上一毛钱的米粑粑或油香塞到我手里。要是冬天,还会把粑粑放在火盆边烤得发黄后再递给我。如今裁缝铺的位置被别人修建了一栋三屋小楼,站在这里,已想不起当年周围的景象,但两位白发老人亲切交谈的身影,似乎还是那么清晰明亮地呈现在眼前!
再前行,到李大爷夫妇家门口。大娘正站在门边沉思,大爷身体不便躺在堂屋内的躺椅上,二老膝下无儿无女,所以房屋依然是老样子。我上前招呼了一声李大娘,大娘以友善而疑惑的目光盯着我们,我说:“我是健娃儿啊!”她的目光突然亮起来,屋内的李大爷也欠身望向门外。“你是东瓜山的健娃儿?”大娘有些吃惊又非常兴奋地问道,“哎呀!我记得你的时候你还只有这么高!”边说边用手在腰间比划了几下,然后手舞足蹈地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我不听话,祖父便逗我说把我送给李家,甚至有一次把我关进了他家的寝房内,我又哭又闹、又踢又打,直到大爷塞给我一个烧苞谷棒才停下来。李大爷年轻时是生产队长,老是用大嗓门指挥这个、呼喊那个,我儿时最怕的事就是被送给他家……他们问我儿子吃的什么东西?咋长这么胖?我们呵呵做答,他们呵呵大笑!大爷对儿子说:“我年轻时和你爷爷是生产队的能手,打谷子、掰苞谷、犁田打坝,没人搞得赢我们!”估计生活在城市的儿子,也想像不出生产能手是个什么样儿!
听到热闹的交谈,邻居几位大爷大妈也走出门来观看、问候!
辞别众乡亲,我们来到宋铁匠铺。这里关门插锁,人已不知去向,街坊说他家后人早搬走了,这里一直空着。小时,这里是我感觉最有力量的地方——四五个淌着黑汗的赤膊大汉,抡大铁锤、操小榔头、抽大风箱、拿大火钳的,合力把一大块通红的铁砸成锄头、镰刀,叮铃咣啷的声音震动着半条老街!
铁匠铺的西边,本来是一栋吊脚楼,上世纪50年代,我的祖父、祖母、父亲曾在这里租住过好几年,现在也修成了洋楼。
再往前,是老街的西入口,估计也应该巴盐古道的一段。
走完老街,心情颇为复杂,有温馨、有思念、有迷惘、也有期待。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居住在乡村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有几位老人去世多日后才被发现;住进高楼的农家人,似乎也不像过去那么纯朴、热情好客了!不管怎样,期待家乡一切安好吧!
透过手指间看着天,我又回到那老街,靠在你们身边渐行渐远。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