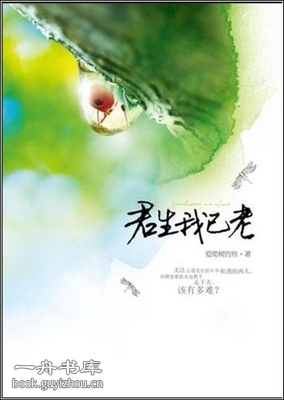若不是那一缕缕沁人心脾的熟悉的花香的诱惑,我是断然不会来到这里的。
这里就是位于城东的河滨公园。说是公园,里边几乎没有五颜六色的花儿,倒是沿河栽种的树木生长得非常繁茂,附近居住的人们早早晚晚地出来散散步,打上一会儿太极,抑或是双手扶着河边的栏杆静静地伫立一会儿,倒也是一处不错的所在。

如今正值盛春季节,远远地就能见到一片郁郁葱葱的绿,心情自然清爽了许多。这一片的绿色和小河的走向匹配着自南向北顺势而下,如一个细长细长的绿色屏障,横亘在小河和喧嚣的马路中间,仿佛一下子将城市的嘈杂与浮华隔将开来。
公园里栽种的树木既有女贞树、银杏树、火炬树及一些灌木类等常见绿化用树,它们因为自身的特点,有的炫耀着细挑匀称的身姿,有的盘根错节地兄弟四五个拥挤在一起,有的则将粗短的枝条扭成龙爪状,算是形成一个错落有致的梯队。像毛白杨、笨柳树、槐树、榆树等已经生长很多年的老树,虽然数量上比不过其他的树木生长起来气势汹汹,但只是树干就有十几米高,已经高出其他的树木一大截儿,龟裂着皮肤,或枯或荣,或弯曲盘旋,或直插云天的枝杈,将天空和地面远远隔离开来的硕大的巨伞状的树冠,也足可说明它们的不同寻常了。
对于这些老树,或许因为从小接触的多也最为熟悉,感情上自然觉得格外亲切。记得老家屋后就曾有一棵高大的杜梨树,每逢树上结出密密麻麻的褐色的小果子,小伙伴们便三五成群地爬到树上摘杜梨果,最终却是享受不了那种涩涩的味道而作罢。村子南头的沟边有一大片槐树林,每年四月底五月初就缀满整树整树的白色清香的细碎的花朵,蜂儿成群结队地赶来了,蝴蝶身着美丽的花裙衫飞来了,再加之几只淘气的鸟儿在花间探头探脑地叫上几声,就像参加农村里的结婚宴席一样的热闹。几个趁着假期外出打猪草的孩子自然不会闲着,他们有的去路边折上几根细长的杨柳枝,翘着脚抽打低处的槐枝儿,有的举着双手,伸着细长的脖颈接散落下来的花穗儿,放进嘴里擎在手里,兴高采烈的样子就像收获着一枝枝的宝贝儿。在村子前街的正中央还有一棵更老的老槐树,爷爷的爷爷时就已经存在,如此算来一百年是有的了。老槐树的树干已经部分出现中空,顶端已经没有硕大的树冠,树干的某一处在春末了时还仍然钻出嫩嫩的枝条,证明它老而弥坚的生命力。一人高的地方有一个圆圆的洞,村里的所谓得道之人说是老槐树已经成了仙,这圆圆的洞口就是树神的眼睛,每逢农历中几个重要的节日到来时,便率领着一群善男信女们在树下焚香烧纸膜拜,无比虔诚的表情令天真的孩子们都相信了神的存在了,哪还不敢对这些老树存有半点的不敬之心呢。
后来在泰山脚下的岱庙里瞻仰了体形硕大的古汉柏,在济南的千佛山上见过的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树龄的唐槐,据传是唐朝开国将领秦琼上山为母亲祈福时拴马用过的,故又称“拴马槐”,蒙山顶上也有一棵老银杏树,这些老树虽是经过岁月几次三番地历练和洗礼,如今仍然身姿挺拔且枝繁叶茂,令人敬佩,给人以鼓舞。
其实,喜欢这些老树,也许就是喜欢它们的那种精气神。这就如跋涉在人生长河里的一代代过来者,经历过一路的风风雨雨,仍然保持铿锵有力的前进步伐,仍然保持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始终给人一种老而弥坚,处事不惊,在艰险困难面前从不服输,不轻言放弃的生活态度,对于后来者不也是很好的启迪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