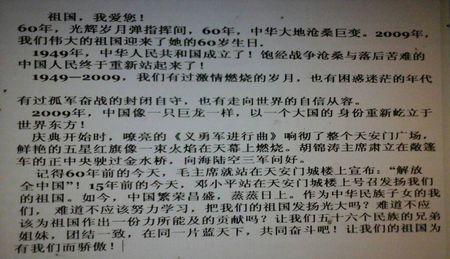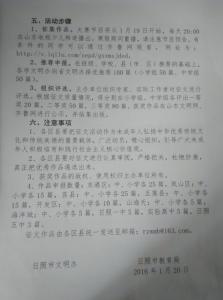国学名言是高考语文必考的重要内容,国学名言的记忆对于高考语文复习是很重要的,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国学经典名言,请考生认真复习。
国学经典名言:
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
2.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三国志》
3.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论语》
4.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论语》
5.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论语》
6.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
7.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
8.当仁,不让于师。 ——《论语》
9.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论语》
10.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
11.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周易》
12.满招损,谦受益。 ——《尚书》
13.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

14.言必信,行必果。 ——《论语》
15.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论语》
16.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
17.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论语》
18.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论语》
19.不怨天,不尤人。 ——《论语》
20.不迁怒,不贰过。 ——《论语》
21.小不忍,则乱大谋。 ——《论语》
22.小人之过也必文。 ——《论语》
23.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论语》
24.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论语》
25.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论语》
26.三思而后行。 ——《论语》
27.多行不义必自毙。 ——《左传》
28.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左传》
29.不以一眚掩大德。 ——《左传》
30.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中庸》
31.知耻近乎勇。 ——《中庸》
32.以五十步笑百步。 ——《孟子》
33.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孟子》
34.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
35.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韩非子》
36.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诗序》
37.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 ——《孔子家语》
38.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明代谚语
39.千经万典,孝悌为先。 ——《增广贤文》
40.善恶随人作,祸福自己招, ——《增广贤文》
41.学而不思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
42.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
43.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
44.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 ——朱熹
45.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论语》
46.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荀子》
47.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王之涣
48.强中自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警世通言》
4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礼记•学记》
50.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劝学》
拓展阅读:
■王开岭每个故乡都在消逝每个故乡都在消逝
我要还家,我要转回故乡。
我要在故乡的天空下,沉默寡言或大声谈吐。
——海子
1
先讲个笑话。
一人号啕大哭,问究竟,答:把钱借给一个朋友,谁知他拿去整容了。
在《城市的世界》中,作者安东尼·奥罗姆说了一件事:帕特丽夏和儿时的邻居惊闻老房子即将拆除,立即动身,千里迢迢去看一眼曾生活的地方。他感叹道,“对我们这些局外人而言,那房子不过一种有形的物体罢了,但对于他们,却是人生的一部分。”
这样的心急,这样的驰往和刻不容缓,我深有体会。
现代拆迁的效率太可怕了,灰飞烟灭即一夜之间。来不及探亲,来不及告别,来不及救出一件遗物。对一位孝子来说,不能送终的遗憾,会让他失声痛哭。
2006年,在做唐山大地震30年纪念节目时,我看到一位母亲动情地向儿子描述:“地震前,唐山非常美,老矿务局辖区有花园,有洋房,最漂亮的是铁菩萨山下的交际处……工人文化宫里可真美啊,有座露天舞台,还有古典欧式的花墙,爬满了青藤……开滦矿务局有带跳台的游泳池,有个带落地窗的漂亮大舞厅……”
大地震的可怕在于,它将生活连根拔起,摧毁着物象和视觉记忆的全部基础。做那组电视节目时,竟连一幅旧城容颜的图片都难觅。
1976年后,新一代唐山人对故乡几乎完全失忆。几年前,一位美国摄影家把1972年偶经此地时拍摄的照片送来展出,全唐山沸腾了,睹物思情,许多老人泣不成声。因为丧失了家的原址,30年来,百万唐山人虽同有一个祭日,却无私人意义的祭奠地点。对亡灵的召唤,一直是十字路口一堆堆凌乱的纸灰。
一代人的祭日,一代人的乡愁。
比地震更可怕的,是一场叫“现代化改造”的人工手术。一次城市研讨会上,有建设部官员忿忿地说:中国,正变成由一千个雷同城市组成的国家。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能指认和珍藏一个故乡,且故乡信息又是各自独立、不可混淆的,那么,面对千篇一律、形同神似的一千个城市,我们还有使用“故乡”一词的勇气和依据吗?我们还有抒情的可能和心灵基础吗?
是的,一千座镜像被打碎了,碾成粉,又从同一副模具里脱胎出来,此即“日新月异”“翻天覆地”下的中国城市新族。它们不再是一个个、一座座,而是身穿统一制服的克隆军团,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分泌物。
每个故乡都在沦陷,每个故乡都因整容而毁容。
读过昆明诗人于坚一篇访谈,印象颇深。于坚是个热爱故乡的人,曾用很多美文描绘身边的风物。但10年后,他叹息:“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一种谎言。”
是的,“90后”一代肯定认为于坚在撒谎、在梦呓。因为他说的内容,现实视野中根本没有对应物。该文还引了他朋友的议论:“周雷说,‘如果一个人突然在解放后失忆,再在今年醒来,他不可能找到家,无论他出生在昆明哪个角落。’杜览争辩道,‘不可能,15年前失忆,现在肯定都找不到。’”
这不仅是诗人的尴尬,而是时代所有人的遭遇。相对而言,昆明的被篡改程度还算轻的。
2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梦牵魂绕的旧影?此即替自己收藏童年、见证青春的地方?
当眼前事物与记忆完全不符,当往事的青苔被抹干净,当没有一样东西提醒你曾与之耳鬓厮磨、朝夕相处……它还能让你激动吗?还有人生地点的意义吗?
那不过是个供地图使用、供言谈消费的地址而已。就像北京的车站名,你若以为它们都代表“地点”并试图消费其实体,即大错特错了:“公主坟”其实无坟,“九棵树”其实无树,“苹果园”其实无园,“隆福寺”其实无寺……
“地址”或许和“地点”重合,比如“前门大街”,但它本身不等于地点,只象征方位、坐标和地理路线。而地点是个生活空间,是个有根、有物象、有丰富内涵的信息体,它繁殖记忆与情感,承载着人生活动和岁月内容。比如你说“什刹海”“南锣鼓巷”“鲁讯故居”,即活生生的地点,去了便会收获你想要的东西。再比如传说中的“香格里拉”,即是个被精神命名的地点,而非地址——即使你永远无法抵达、只能诗意消费,也不影响其存在和意义。
地址是死的,地点是活的。地址仅仅被用以指示与寻找,地点则用来生活和体验。
安东尼·奥罗姆是美国社会学家,他有个重大发现:现代城市太偏爱“空间”却漠视“地点”。在他看来,地点是个正在消失的概念,但它担负着“定义我们生存状态”的使命。“地点是人类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发生地。没有地点,人类就不存在。”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简言之,“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之出处。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记空词、一朵谎花。
当一位长辈说自个儿是北京人时,脑海里浮动的一定是由老胡同、四合院、五月槐花、前门吆喝、六必居酱菜、月盛斋羊肉、小肠陈卤煮、王致和臭豆腐……组合成的整套记忆。或者说,是京城喂养出的那套热气腾腾的生活体系和价值观。而今天,当一个青年自称北京人时,他指的一定是户籍和身份证,联想的也不外乎“房屋”“产权”“住址”等信息。
前者在深情地表白故乡和生壤,把身世和生涯溶化在了“北京”这一地点里。后者声称的乃制度身份、法定资格和证书持有权,不含感情元素和精神成分。
3
让奥罗姆生气的是他的祖国,其实,“注重空间、漠视地点”的生存路线,在当下中国演绎得更赤裸露骨、如火如荼。
“空间”的本能是膨胀和扩张,它有喜新厌旧的倾向;“地点”的秉性是沉静和忠诚,无形中它支持保守与稳定。二者的遭遇折现在城市变迁中,即城区以大为能、建筑以新为尚,而熟悉的地点和传统街区,正承受垃圾的命运。其实,任何更新太快和丧失边界的事物,都是可怕的,都有失去本位的危险,都是对“地点”的伤害。像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一个人再把它唤作“故乡”,恐怕已有启齿之羞——
一方面,大城欲望制造的无边无际,使得任何人都只能消费其极小一部,没人能再从整体上把握和介入它,没人再能如数家珍地描叙和盘点它,没人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老人”。
另一方面,由于它极不稳定,容颜时时变幻,布局任意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暂时、偶然,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情怀。总之,它不再承载光阴的纪念性,不再对你的成长记忆负责,不再有记录你身世的功能。
面对无限放大和变奏、一刻也不消停的城市,谁还敢自称其主?
所有人皆为过客,皆为陌生人,你的印象跟不上它的整容。而它的“旧主”们,更成了易迷路的“新人”,在北京,许多生于斯、长于斯的长者,如今很少远离自己的那条街,为什么?怕回不了家!如此无常的城市里,人和地点间已失去了最基本的约定,同一位置,每年、每月、每周看到的事物都闪烁不定,偶尔,你甚至不如一个刚进入它的人了解某一部位的现状,有一回,我说广内大街有家馆子不错,那个在京开会的朋友摇摇头,甭去了,拆了。我说怎么会呢?上月我还去过啊。朋友笑道,昨天刚好从那儿过,整条街都拆了。我叹息,那可是条古意十足的老街啊。
吹灯拔蜡的扫荡芟除,无边无际的大城宏图,千篇一律的整容模板……
无数“地点”在失守,被更弦易帜。
无数“故乡”在沦陷,被连根拔起。
何止城市,中国的乡村也在沦陷,且以更惊人的速度坠落。因为它更弱,更没有重心和屏障,更乏自持力和防护性。我甚至怀疑:中国还有真正的乡村和乡村精神吗?
央视所谓“魅力小镇”的评选,不过是一台走秀,是在给“遗墟”颁奖。那些古村名镇,只是没来得及脱旗袍马卦,里头早已是现代内衣或空空荡荡。在它们身上,我似乎没觉出“小镇”该有的灵魂、脚步和炊烟——那种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美学和心灵秩序。
天下小镇,都在演出,都在伪装。
真正的乡村精神——那种骨子里的安详和宁静,是装不出来的。
4
“我回到故乡即胜利。”自然之子叶赛宁如是说。
沈从文也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
他们算是幸运,那个时代,故乡是不死的。至少尚无征兆和迹象,让游子担心故乡会死。
是的,丧钟响了。是告别的时候了。
每个人都应赶紧回故乡看看,赶在它整容、毁容或下葬之前。
当然还有个选择:永远不回故乡,不去目睹它的死。
我后悔了。我去晚了。我不该去。
由于没在祖籍生活过,多年来,我一直把70年代随父母流落的小村子视为故乡。那天梳理旧物,竟翻出一本自己的初中作文,开篇叫《回忆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那是一个群山环抱、山清水秀的村庄,有哗哗的小溪,神秘的山洞,漫山遍野的金银花……傍晚时分,往芦苇荡里扔一块石头,扑棱棱,会惊起几百只大雁和野鸭……盛夏降临,那是我最快乐的季节。踩着火辣辣的沙地,顶着荷叶跑向水的乐园。村北有一道宽宽的水坡,像一张床,长满了碧绿的青苔,坡下是一汪深潭,水中趴着圆圆巨石,滑滑的,像一只只大乌龟露出的背,是天然的游泳池……”
坦率说,这些描写一点没掺假。多年后,我遇到一位美术系教授,他告诉我,30年前,他多次带学生去胶东半岛和沂蒙山区写生,还路过这个村子。真的美啊,他一口咬定。其实不仅它,按美学标准,那个年代的村子皆可入画,皆配得上陶渊明的那首“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几年前,金银花开的仲夏,我带夫人去看它,亦是我30年来首次踏上它。
一路上,我不停地描绘她将要看到的一切,讲得她目眩神迷,我也沉浸在“儿童相间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想象与感动中。可随着刹车声,我大惊失色,全不见了,全不见了,找不到那条河、那片苇塘,找不到虾戏鱼溅的水坡,找不到那一群群龟背……代之的是采石场,是冒烟的砖窑,还有路边歪斜的广告:欢迎来到大理石之乡。
和于坚一样,我成了说谎者,吹嘘者,幻觉症病人。
5
没有故乡,没有身世,人何以确认自己是谁、属于谁?
没有地点,没有路标,人如何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个时代,不变的东西太少了,慢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头也不回地疾行,而身后的脚印、村庄、影子,早已无踪。
我们唱了一路的歌,却发现无词无曲。
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却忘了为何出发。
■王开岭权利的傲慢耶路撒冷有一间名叫“芬克斯”的酒吧,面积仅30平方米,却连续多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入世界最佳酒吧的前15名。究其奥妙,竟和这样一则故事有关――
酒吧老板是个犹太人,罗斯恰尔斯,在其悉心经营下,酒吧小有名气。一天,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到耶路撒冷,公务结束后,博士突然想光顾一下酒吧,朋友推荐了“芬克斯”。
博士决定亲自打电话预约,自报家门后,他以商量的口吻说:“我有10个陪同,届时将一同前往,能否谢绝其他顾客呢?”按说,出于安全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这样的政要造访,对一家商户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幸事。
谁知老板不识抬举,他接受了预约,但对国务卿的附加要求却不接受:“您能垂幸本店,我深感荣耀,但因您的缘故而将他人拒之门外,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博士几乎怀疑耳朵听错了,气冲冲挂了电话。
第二天傍晚,“芬克斯”的电话又响了,博士语气柔和了许多,对昨天的失礼致歉后说,这次只带三个同伴,只订一桌,且不必谢绝其他客人。
“非常感谢您的诚意,但还是无法满足您。”
“为什么?”博士惊愕得要跳起来。
“对不起先生,明天是礼拜六,本店例休。”
“但,我后天就要离开了,您能否破一次例呢?”
“作为犹太人后裔,您该知道,礼拜六是个神圣的日子,礼拜六营业,是对神的亵渎。”
博士闻后,默默将电话挂上。
读完这则故事,我默然良久,为那栋叫“芬克斯”的小屋怦然心动。
我想,基辛格博士是不会轻易忘掉这件事的。
这样的事既令人沮丧,也令人鼓舞。人人生而平等,人最重要的权利即拒绝权力的权利……博士从这位傲慢店主身上领教到的“公民”涵义,从一份商家纪律中感受到的“尊严”与“权利”,比那些镌刻在纪念碑、印在白皮书上的,显然更深刻,更有分量。
权利,面对权力,应该是傲慢的。
后来,我竟莫名地打量起它的真实性来,会有这等傲慢发生吗?
很快我明白了,疑心完全是“以己推人”的结果。是对自己和周围不信任的结果。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中深陷太久的结果。无论地理还是灵魂,耶路撒冷,都太遥远了,像一抹神话。
一件小事,仔细品味却那样陌生,那般难以企及。从开始到完成,它需要一个人“公民”意识的长期储备,需要一种对尊严和规则牢固的持有决心,需要一个允许这种人、这种性格、这种人生――安全、自由、稳定生长的环境……
坦率地说,我对这等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不抱信心。即使这个故事让我倍受激励,假如我有一间“芬克斯”,便能重复那样的傲慢吗?(哪怕是作秀,哪怕是一个市长)作为一记闪念,或许我陡然想对权力说不,但该念头是否顽固到“不顾世情”“不计弹性”的地步,是否有足够的决绝以抵御惯性的纠缠――而绝无事后的忐忑和反悔?我真是一点信心没有。
我是我环境的产物。我的一切表现都是环境和经验支付的,我实在拿不出有别于他人的“异样”。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遗传的力量总是大于变异。
我向往,但我不是。
■熊培云守住良心的“一厘米主权”许多人热衷于讨论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其实,不唯国家有主权,每一位国民也有主权。而且,个体主权之是否沦陷,更是人人最要面对的精神事件。
所谓个体主权无外乎两种:一是“对物”;二是“对己”。
“对物的主权”,18世纪的欧美贤良已有精彩论述。如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有关物权的至理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美国政治活动家詹姆斯·奥蒂斯反对政府的任意搜查令时的慷慨激昂——“一个人的住宅就是他的城堡,只要他安分守己,他在城堡里就应当受到像王子一样的保护”。
至于“对己的主权”,则包括个体的身体自治(行动自由)与精神自治(思想自由)。
一定条件下,无论“对物”,还是“对己”,两种主权都具有某种可让渡性。比如,通过谈判你可以变卖房产,替人工作、听人差遣,甚至接受思想与行为的培训等等。但是没人希望自己因此变成奴隶,既失去了“对物的主权”,也失去了“对己的主权”,成了“大公无私”时代里一无所有的“新人”。
最常见的情形是,人们敏锐于拥有“对物的主权”,而无视自己成为彻头彻尾的沦陷区。比如汉娜·施密特,电影《朗读者》里的纳粹女看守。法庭上的汉娜,犹如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优雅、温顺,而且理直气壮。在那里,刽子手被还原成普通的德国市民,忠于职守,对上级及既有法令无条件服从。当法官质问她为了不出乱子宁愿让三百人活活烧死时,汉娜反问法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法官一时无言以对。相信这也是人们最怕面对的问题。
汉娜为什么最终被判终身监禁,影片未展开,答案在德国的另一场真实的审判中。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
和汉娜一样,亨里奇的律师辩称这些卫兵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并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释。
体制内的作恶者莫不把体制与命令作为其替罪的借口,为自己主权沦陷、良心失守卸责。然而,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仍是可以选择的。君不见,在修砌柏林墙的第一天便有东德卫兵直接逃到西柏林,而柏林墙正是从那天开始了持续几十年的坍塌。
你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卫兵。亨里奇案作为“最高良知准则”的案例早已广为传扬。“抬高一厘米”,是人类面对恶政时不忘抵抗与自救,是“人类良知的一刹那”。这一厘米是让人类海阔天空的一厘米,是个体超于体制之上的一厘米,是见证人类良知的一厘米。
人类之所以高贵,正在于人类的良知。如梭罗所说,“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他的身体是他的圣殿,在里面,他用完全是自己的方式崇敬他的神??”中国人不也常说“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么?前者是他律之神,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后者是自律之神,人因有良知而自律,而超越罪恶的樊篱。一旦丢掉了良知,人类神性的庙宇也就坍塌了,人类所能看到的,便只有猥琐的世相与一望无际的残酷。
为了克服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抵御随时可能发生的权力之祸,尤其在经历极权主义盛行的20世纪之后,各国越来越注重对其国民抵抗权的保护。这既是一种法律上的救济、政治道德上的分权,也是一种良心上的共治。具体到今日中国,现行《公务员法》第54条不也规定公务员有抵抗上级的权利么?只可惜有人于法不顾,以为可以尽享良心沦陷的红利,且永远不受责罚。而这也是网民穷追暴力拆迁、跨省追捕等恶性事件之原因所在。
当一个人因不分善恶、惟命是从而导致自己主权沦陷,这样“亡国奴”式的人生是否才更可怕,更无希望?在此意义上,所谓良心发现,岂非“救亡图存”?
年少时爱看《加里森敢死队》,如今只记住一个镜头:盟军战士逃跑时,一位德军士兵开枪射击,可是怎么扣不动扳机,嘴里还嘟囔着,“什么老爷枪!”二十年后想起这个细节,仍忍俊不禁。我真希望那是德军士兵“蓄意不谋杀”,正管理他的“一厘米主权”呢!
 爱华网
爱华网